通过解谜重新发现历史
倪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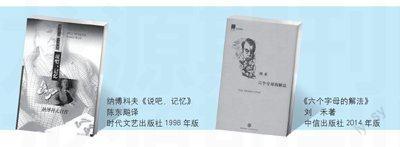
纳博科夫喜爱编棋题,这是他在欧洲流亡期间养成的嗜好。为了构思一道特别的棋题,他甚至会一连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煞费苦心地设计各种精巧的骗着和虽然简单却最出人意料的正解。纳博科夫后来曾感叹,在他精力最充沛也最多产的岁月里,这一美丽、复杂而又刻板的艺术吞噬了他太多本该用于写作的时间。编棋题让他体验到一种精神愉悦的刺痛,得以暂时忘却流亡的艰辛和苦痛。他也从中悟到了写作的奥秘,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就类似于棋题编制者和解题者之间的竞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纳博科夫的小说—甚至包括自传在内,都是一道道精心编制的棋题,复杂而精妙,充斥着各种难解的谜团。作为读者,我们总能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看见他那略带嘲弄意味的狡黠目光。
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就是一部解谜之作,她想解开的谜藏在纳博科夫的自传《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曾与一位英国同学过从甚密,两人有着相近的文学趣味,但政治见解却大不相同。这位绰号叫奈斯比特的英国同学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坚决地捍卫列宁和俄国革命,还冷酷地为革命中所发生的野蛮的恐怖行为辩护,这让身为俄国贵胄却因革命爆发而被迫流亡从而失去了家园和初恋的纳博科夫颇为恼火,两人常常因此激辩,不欢而散。奈斯比特是否实有其人?他究竟是谁?这正是刘禾要解开的谜。
纳博科夫笔下的奈斯比特身材瘦长,烟斗不离手,他喜爱诗歌,而且还参加过一战。在《六个字母的解法》里,叙述者正是抓住这些线索来一步步解谜的,其间虽也遇到类似于棋题中的骗着的各种交叉小径,但每一次误入歧途又都会带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这些散佚的历史断章不仅令人兴味盎然,而且也发人深思。我们因而得知在一战后的剑桥竟还有一个人数不少的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不仅有思想激进的作家文人,还有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这样的杰出科学家;我们还吃惊地发现奥威尔这位头上一向罩着反专制、反极权的光环的文化英雄,竟然也干过向英国情报部门告密这等令人齿冷之事,而他的两本名著《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也是在英国情报调查局(IRD)和美国中情局的资助下才得以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开来。这些事实都足以颠覆一些既有的历史叙述,促使我们去思考是否存在着被遮蔽的另一种历史,而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一些知识和观念却可能是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建构?在冷战的阴影并没有彻底消失的“后冷战”时代,这种提醒恐怕仍然是必要的,它也许能把我们从历史终结论的迷梦中唤醒。
在几经周折、排除了多位可能的人选之后,谜底似乎已昭然若揭,种种迹象表明奈斯比特极可能就是英国著名作家和戏剧家J.B.普里斯特利。普里斯特利一九一九年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堂学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并在伦敦西区崭露头角,二战中又因主持BBC的一档广播节目Postscripts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一个热诚而活跃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一政治立场,一九四一年英国情报局勒令取消了他在BBC的节目,他的名字后来也登上了奥威尔的“黑名单”。普里斯特利是二战前后英国最著名的剧作家,其声誉之隆不免让人联想到易卜生。纳博科夫在自传里说,“奈斯比特”(Nesbit)这个绰号倒过来可以读出“易卜生”(Ibsen)。大学时代的奈斯比特长得像青年高尔基,十多年后又像极了剃掉浓密胡须的易卜生。这一说法恐怕不能当真,多半是纳博科夫皮里阳秋的笔法。他曾贬损高尔基是一个平庸的地区性作家,在他心目中,易卜生大概也是一个被过度高估的作家吧。易卜生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强烈关注显然不合纳博科夫的胃口,所以他很少提到易卜生,只是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谈到契诃夫的剧作《海鸥》时才轻描淡写地说,契诃夫总是急切地想把事情尽快解释清楚,这和易卜生如出一辙。把奈斯比特比作易卜生,听上去不像是褒扬,而更像是揶揄挖苦。实际上,普里斯特利的戏剧虽然也关心社会问题,其主题和风格却并不像易卜生,而更接近于布莱希特,有人因此称他为英国的布莱希特。普里斯特利貌似也有着某些与奈斯比特较为接近的个人特征。纳博科夫曾形容奈斯比特是一个瘦长的巨人,普里斯特利身材魁伟,虽然不尽相符,却也算得上是个巨人。他也爱抽烟斗,在他的家乡布拉德福德市的国家媒体博物馆门前,有一座他的铜像,刻画的正是他手持烟斗、沉思远眺的神态。当然,也有一些不相符合的地方。据纳博科夫说,一九三七年他在伦敦与奈斯比特重逢时,发现他已经戒了烟,容貌也变得柔和了,但普里斯特利却一辈子都没有放下过烟斗,这可以从他晚年的许多照片得到印证。
还有更多的疑点。奈斯比特举止优雅,显然出身于有着良好教养的家庭,极可能像大多数牛津、剑桥的学生一样,来自英格兰南方的中上社会阶层。普里斯特利却不是那种典型的牛桥学生,他出生于英格兰北方曾被称为羊毛之都的布拉德福德,父亲是个教员,家境寒微。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学校,在一家羊毛商行里当店员。如果不是一战爆发,他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跨入剑桥的大门。一九一九年,在法国前线的战壕里摸爬滚打了四年半之后,普里斯特利终于有幸以退伍军官的资格进剑桥读书,当时他已经二十五岁,比同一届的学生年龄大了四五岁。也许是想摆脱战争留下的惨痛记忆,在剑桥期间他远离政治,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唯有书和二三知己相伴。他自己说是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英国人,躲在高高的围墙里和紧闭的门户后。后来,是戏剧而不是政治把他从如此封闭的个人世界里拉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他的几部剧作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普里斯特利声名鹊起,终于摆脱了拮据的家庭生活。他热情好客,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往来的都是作家和戏剧界人士。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都是乐呵呵的,精力旺盛,性格强硬,有很强的支配欲。他热爱世俗生活,交游广泛,绯闻不断,甚至连座驾也是簇簇新、亮闪闪,看上去很俗艳的那种。虽说贵为文化名流,但他却不是那种典型的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而是举止粗鲁,言语傲慢。据说著名演员拉尔夫·理查德森(Ralph Richardson)曾因为嘲笑普里斯特利的车样子有点土而一度被驱逐出他的朋友圈;三四十年代伦敦西区的大佬级戏剧制作人宾凯·鲍蒙特(Binkie Beaumont)曾邀请普里斯特利为他旗下的明星写戏,他竟答复说“我可没时间来伺候该死的明星或是明星制度”,结果弄得两人反目成仇。诸如此类的例子还真不少。有人嘲笑普里斯特利粗俗,说他是土豪,爱炫富,既财迷又好色,一看就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他本人似乎也不想掩饰自己的阶级出身,要知道这可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根基所在。爱憎分明,绝不妥协,从来都不遮遮掩掩,可见他实在是一个性情豪迈率真的人。纳博科夫笔下的奈斯比特却像是另一种人。一九三七年,纳博科夫重访伦敦,跟奈斯比特在一个小地方吃午餐。奈斯比特显得心绪不宁,直接的原因是帮他料理家务的一个表妹或是未婚的妹妹刚被转到了比奈的诊所。流亡法国却无法获得工作许可的纳博科夫本指望这位老友帮个忙,看看能不能在英国的大学里找到一份教职。可奈斯比特根本没兴趣听他说,而是不顾一切地谈开了政治。他怀着恐惧说出一些遭到斯大林清洗的人的名字,而对自己青年时代激进的思想态度却没有半点反思。这个琐碎、冷漠且因为自己过去的理想破灭而陷入到厌倦和迷惘之中的奈斯比特,和活得劲头十足的普里斯特利,看上去的确不像是同一个人。
不是普里斯特利,那还能有谁会是那个神秘的奈斯比特呢?若是依据剑桥出身、左翼立场和爱抽烟斗这三条线索来查寻,我们至少还能举出一人,那就是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马丁也是在一九一九年进的剑桥大学,虽然他入读的是麦格达伦学院,而不是纳博科夫所在的三一学院。马丁的父亲是个牧师,也是个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受父亲影响,在一战中马丁拒绝入伍参战,但同意作为医护人员前往战场,他在法国西线战壕里一直待到了战争结束。在剑桥期间,马丁在政治上很活跃,他是民主控制联盟(UDC)和费边社成员,和J.D.伯尔纳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毕业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找到一份教职,在同为费边社成员的政治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手下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马丁接任著名左翼刊物《新政治家》的主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了一九六○年退休为止。在英国左翼知识圈里,他始终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丁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同时又是个死硬的亲苏派。一九三七年他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发表《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一文,把托洛茨基狠狠挖苦了一番,他还不准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刊文评论托洛茨基的新著《被背叛的革命》。凯恩斯是马丁在剑桥读书时的老师和朋友,他说马丁对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可谓一片赤诚,即使偶有怀疑,也会想方设法去打消。但没想到的是,两年后斯大林却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让马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幻灭,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他还曾批评自己多年的好友伯尔纳,说他像H.G.威尔斯一样坚信可以通过科学获得进步,却对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数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事实无动于衷,对荒谬而残酷的大清洗也不置一词,因为在伯尔纳看来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过程的一部分。尽管摇身一变成了反斯大林主义者,马丁却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奥威尔的“黑名单”上,他也赫然在列,在他名字后面奥威尔的批注是:“蜕化的自由派,很不诚实。”马丁身材高大,手里总是拿着烟斗,这些细节连同他的生平和思想经历,似乎都与奈斯比特若合符节。但我们却无从知晓他在诗歌方面的趣味,而且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他与纳博科夫有过交往,所以他是不是奈斯比特,仍是个未知数。
究竟谁是奈斯比特?这个问题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明确的答案。在《说吧,记忆》里,纳博科夫曾谈到这本自传的写作方式:“我承认我不相信时间。我喜欢在使用过后把我的魔毯折叠起来,使图案的一部分重叠在另一部分之上。就让造访者旅行去吧。”尽管这主要是就整本书的结构原则而言,但未尝不可以说也是他刻画人物的方法。奈斯比特这个人物很可能是杂取了两三个人的形象重叠而成,那么他就不只是这一个或那一个了,而可以代表包括普里斯特利、金斯利·马丁等作家文人以及李约瑟、伯尔纳等红色科学家在内的整整一代英伦知识分子。纳博科夫希望他的读者把阅读当作一次旅行,尽情享受沿途的风景和奇遇,而不必追问究竟去向何方。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就把解开奈斯比特是谁这个谜也看作是一次旅行吧。
作为著名文学研究专家,刘禾对纳博科夫的写作策略自然不陌生,她知道重要的不是谜底本身,而是解谜的过程。只要能引领人们一路饱赏平时看不见的奇景,启发他们去反思那些早已被当作常识而接受下来的固化观念,那么,谜底到底是什么实在已无关紧要,或者可以说解谜的过程本身就是答案。出于这种考虑,刘禾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跨文类的写作方式,将学术探究与佚闻掌故以及亲身经历编织在一起,以便尽可能地包容各种貌似松散的材料,使一波三折的解谜过程渐渐充满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本书读起来的确很愉悦,它没有学术著作艰涩高深的内容,却不乏优秀学术著作通常拥有的严谨以及巨大的思想容量;它也不能算是一本小说,因为里面很少有虚构性的内容,也没有充满叙事张力的完整故事,但它又的确是一部叙事作品,有着出色的小说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和趣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禾谈到自己这种开放式的写作,认为这是在尝试着“重新发明文学”,让文学重新获得厚重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含量。在此书后记中她还提到,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既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有关,也和我对二十世纪蹉跎岁月的整体思考有关,其中包含许多内心的困惑和纠结”。虽然她没有明说这些内心的困惑和纠结是什么,但细心的读者大概也不难从书中有所领会吧。
刘禾反复强调这本书是写给中国的普通读者看的,她显然是希望与更多的同胞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她讲述的虽然主要是“剑桥帮”的故事,但其中也不乏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片段委实都大有深意。
在与剑桥有缘的中国人里,徐志摩大概是最为人熟知的,他的《再别康桥》等诗文已经将他与剑桥紧密地连在一起。事实上,说起剑桥,国人头脑中首先浮现的可能就是徐志摩用华美的笔调所描绘的那个画面:清澄柔碧的剑河,岸边古老庄严的建筑和织锦似的草坪,黄昏时分金柳披垂,仿佛在殷勤护卫那一脉风流;水底青荇招摇,河面上轻盈的篙船像翠条鱼一般滑行,船上是戴着宽边薄纱帽的女郎,歌声和着远处教堂传来的钟声……剑河的柔波抚慰了徐志摩因失恋而悲苦的心,也摇荡起他的一腔诗情。可令人稍感纳闷的是,除了剑桥的旖旎风光外,徐志摩对当时剑桥的学术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任何记载。虽说这可能是因为他只是一名特别生,所以没能完全融入剑桥的学术思想圈,但要知道他在剑桥的那几年正是一战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学生中思想左倾的大有人在,按理说待在这种环境里怎么也该受到点熏陶吧,更何况之前他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待过半年,好歹也曾师从于拉斯基。但我们的诗人却表现得很超然,他似乎更享受剑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里火热的思想氛围。在剑桥,他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下午茶和牛油烤饼,看闲书……也许是剑桥培养了他对资产阶级的悠闲生活方式所象征的那种自由的向往?也可能剑桥的左翼氛围早已引起了他的警惕所以宁愿躲得远远的?在回国后,他就不那么超然了,而是急着要来讨论苏俄和共产党问题。他甚至担心多吃一碗饭多抽一支烟的耽误都有可能使像他那样的“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追悔不及。一九二七年,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一书出版,徐志摩随后在其主编的《新月》上发表了此书的部分译文,并在编者按语中称赞拉斯基是“在学理上掊击共产主义最有力的一人”,他的这本书也“早经评定为剖析共产学说最精深亦最可诵的一部书”。拉斯基的确反对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认为它必然会导致专制,但若是因此认为他根本上是反共产主义的,那就谬以千里了。可见徐志摩其实并不理解拉斯基,正像他未必真正懂得剑桥一样。
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于剑桥大学的中国人当然不只徐志摩一人。温源宁、叶公超、邵洵美等人也都是剑桥出身。温源宁与纳博科夫同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剑桥国王学院,也算是与纳博科夫同一时期的校友了。也许是因为学得刻苦,温源宁简直就是一个高仿版的英国绅士。据说他归国后装出的模样比英国人还英国人,穿英国绅士的西装,手拄拐杖,吃英国式的下午茶,连说英语也学结结巴巴的剑桥腔,好像是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词才能说话。和纳博科夫一样,他也推崇剑桥诗人A.E.豪斯曼的诗,这自然也是从剑桥学来的。据徐志摩说,为了学会像剑桥学生那样抽烟,温源宁可是“出了大英镑正式去请教”的。看来剑桥的一切都是他所热爱而且热衷于去学习的,唯独左翼的思想学说除外。叶公超在剑桥只待了一年,拿了张文凭,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究竟受了些什么熏陶。邵洵美在剑桥的两年里,倒是学会了欣赏“花一般的罪恶”,回国后还兴兴头头地想把唯美颓废文学的种子四处播撒开来,结果却招来一片骂声。
为何同在剑桥,徐志摩们与他们的英国同学们思想差距就这么大呢?莫非这也与阶级出身有关?社会底层的苦难和不公大概很难进入贵介公子们的浪漫唯美之眼,或者即使看到了,也还是不会有切肤之痛吧。作为“少数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们对政治倒未必真的漠不关心,至少徐志摩就曾对国内掀起的共产风潮很是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革命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唯一理想的政治方案当然是点滴的改良,慢慢来,人人各安其分,各尽其力,如此便天下安稳、风月常在了。只可惜他们的这等理想连同为此付出的些许努力都打了水漂。天下偏有那么多不安分而且粗暴的人们,这也难怪,毕竟不是谁都能过上他们那种既优渥又风雅的好日子的。及至后来风暴骤起、天地变色,名士风流连带着“独立见解”就全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尘封了许多年。然而属于他们的时代终究会来临,在大潮退落后,他们依旧是世人眼中被遗落在沙滩上的珠贝,会有许多双手将它们捡起,抚摸,把玩,啧啧称赞。耐人寻味的是,徐志摩们的英国同学,红色的“剑桥帮”,他们的命运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轨迹。在“太平成象盈秋门”的盛世,还有谁会记得他们的名字?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卓然不群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大概都是悖谬、迂阔、不可理喻的,他们对理想社会的热烈想象、对社会正义的执著追求,恐怕也只能用知识分子的幼稚和天真来解释吧。
短暂的二十世纪结束了,但历史却并不会终结。纳博科夫说,螺旋就是一个精神化的圆,它以螺旋的形式解散开来,不再是恶性的循环,它的每一次盘旋又都可以看作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螺旋还在上升,被暂时遗忘的记忆会苏醒,正如泛起的沉渣最终还是会落下。时间仍然值得相信,只是我们需要不时地提醒自己,别被那些在历史中瞬息变幻、不断交叠的繁复花样耀花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