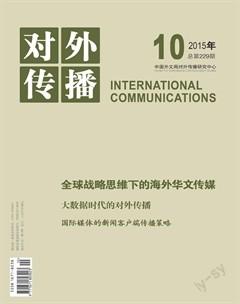中西方媒体关于9·3阅兵报道的对比分析
王爽
2015年9月3日,我国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举行的盛大阅兵,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次阅兵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作为我军形象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阅兵在中西媒体报道中呈现出不同的镜像,中西方媒体对其意义也有不同解读。
一、报道内容的差异化呈现
中西方媒体在9·3阅兵报道呈现中,差异明显。中方媒体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保持较强的新闻敏感性,阅兵前后的报道总体呈现积极、自豪的基调。而西方媒体则在报道倾向中呈现出差异化,同时对此事件的关注有不同的侧重点,报道内容多样。
在此次阅兵报道中,中国的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在报道倾向中呈现出一致性,对阅兵的前期准备、阅兵流程中的各个细节、阅兵的意义和价值等方面做了很多微观解读。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9·3阅兵”成为微博热搜词,表现出网民对这一事件的关注。
从西方媒体报道中的高频词来看,它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先进武器装备、裁军计划、军事实力、出席首脑、中日关系、北京的天气等方面,但大多是主观先行,从预设的立场出发进行报道。
在此次之前,中国自建国以来已经举行过13次阅兵。对于阅兵事件,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相对稳定,同时随着国家实力、国际关系等的发展,报道框架也与以往有所不同。比较新鲜的报道框架有“为什么西方不愿意出席抗战阅兵”、“看完阅兵来华外国政要去了哪儿”、“日批评潘基文出席阅兵”等。
外国媒体对此次阅兵的报道框架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有的媒体以“中国以二战军事狂欢秀肌肉”“中国是在炫耀武力试图吓唬日本”等为报道框架,有的则以“展示中国军队的先进水平”、“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斗和牺牲的战士”等为报道框架。
二、阅兵事件的符号化解读
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是符号学的重要理论,他将话语生产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编码阶段,这一阶段是指创作者对原材料和客观事实的筛选、加工和制作;第二个阶段是成品阶段,编码完成后,制作者赋予话语一定的意义,并进入流通;第三个阶段是解码阶段,受众对话语意义进行解读。这种话语生产的过程同样适用于新闻传播领域。
1.意义生成:影响西方阅兵报道新闻选择的因素
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新闻报道的第一阶段是指创作者对原材料和客观事实的筛选、加工和制作,这一过程要受到“知识框架”、“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的影响。
所谓“知识框架”是指创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如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媒体在报道我国阅兵时选择新闻的角度不同。中国媒体受“知识框架”影响,在选择报道素材时呈现出对出席阅兵的中外领导人的关注,同时中国媒体侧重于选取主旋律、正能量的素材。有的西方媒体则在其“知识框架”影响下搜集素材,渲染中国威胁论。
“生产关系”的影响在于为了经济效益或其他目的,编码者一定会考虑受众的喜好和选择。外国媒体之所以对于阅兵这一举世关注的重大事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从事报道,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其中,女兵、北京天气等新闻素材的选择迎合了受众的兴趣。
“技术基础”因素,就是所谓的选择什么传播工具。俄罗斯各大主流媒体在网站上对阅兵进行了视频和文字直播,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全俄广播电视公司一台、俄罗斯第一频道等多家电视台进行了全程直播,足见俄方媒体对此次阅兵活动的重视。其他各国也都通过网络媒体分享阅兵消息和新闻。
2.意义建构:西方价值观影响下的阅兵报道
罗兰·巴特的“神话”系统披露了隐含在表征系统背后更意识形态化的深层意义。而大众传媒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为了潜移默化地宣扬自身的意识形态,也会极力去编织一个“神话”系统,从而形成该媒体的报道框架。
西方媒体在获取素材的基础上,按照其报道框架,加入自身的价值评判,对新闻进行加工。
在此次阅兵报道中,西方媒体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方面,许多媒体设置积极的报道框架,肯定这次阅兵的积极意义,对中国的做法作出了积极评价。例如,英国《卫报》指出这次阅兵是“为了展示中国军队的先进水平,纪念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斗和牺牲的战士”。在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看来,中国盛大的阅兵仪式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其战时贡献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不必赋予其过多的政治色彩。
另一方面,有的外媒设置消极的报道框架,持唱衰论调。《华盛顿邮报》以“中国阅兵将显示对日本的胜利,并让邻国为难”为标题发表评论。比如《纽约时报》还作出“阅兵对老百姓一点儿好处没有”的价值评价。
西方媒体在对武器装备的相关报道中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彭博社设置的报道框架中,阅兵中的武器装备“代表了中国军队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和新形象”。英国《卫报》则认为,中国政府进行如此大规模阅兵是凭借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舞台上“秀肌肉”。
3.意义解读:中西方受众对阅兵事件的差异性认识
霍尔认为,由于受众不同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社会地位等原因,受众对媒体的解读形成不同的假象立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1)支配式解码。这一解码方式即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一致,受众完全接受了大众媒体传递的信息及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培养”理论认为社会成员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客观事物有大体或接近的认识。对于中国受众而言,在众多媒体报道阅兵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此次阅兵抱有极大的热忱。人民网将民众对此次阅兵的感想总结为四个关键词:感动、英姿、震撼、忆史,这就是受众在自身爱国情怀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支配式解码。
(2)协商式解码。对于编码者传递的主导意义,解码者既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但也试图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立场进行适当地修正。例如,在印度视频网站播放阅兵视频后,印度民众Redragon在评论中说:“ztz99和德国豹二看起来非常的像,不是吗?”同时有其他网友对这一观点进行回复。这就是网友基于自身对武器装备的关注和兴趣,对于阅兵报道的协商性解码。再例如,中国网民在看完阅兵视频直播后“吐槽”央视的直播效果,还有的商家运用女兵图片进行化妆品营销,这些都属于协商性解码的做法。
(3)对抗式解码。观众完全明白话语中给出的字面意义和内涵隐义,但他或她偏用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译码。例如,在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的情况下,有的西方民众仍然对中国阅兵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赞扬中国的做法:“高效务实的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的心愿、奉献精神与决心共同造就了中国的崛起,她将继续发展并达到更高的高度。”
通过对阅兵报道编码/解码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媒体对于阅兵的编码差异性报道,使得受众在解码过程中也呈现出支配、协商、对抗的不同态度。对于具有倾向性的报道,受众较多地呈现出支配式解码方式;而对于事实报道,受众在解码过程中自由度更高,可以在支配、协商、对抗的态度中自由选择。也不排除受众对于倾向性报道产生排斥心理,从而进行对抗式解码的情况。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中西方价值观等方面差异导致各自新闻报道的巨大差异。在媒介全球化、多样化的时代,媒体在对外传播中承担着消除差异、增进了解的职能。在我军形象的对外传播中,中国媒体应当打破传统惯性报道模式,注重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形象建构与输出,力争破解西方媒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断,将自身从误解困境中解救出来。
「参考文献」
1.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