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静动入出之间
曹德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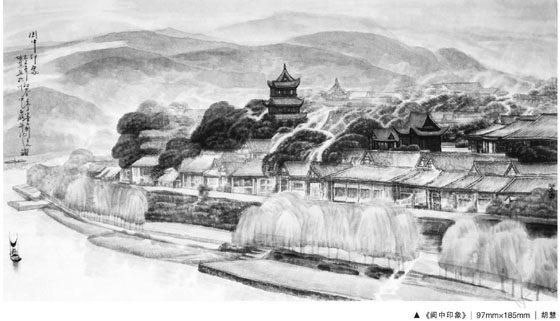
黄书泉先生的《独自散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出版后送我一本。他的专业是文学批评,我的专业是语言研究,俩人虽为同事却非同行。照理说我没有资格就其新作评头论足,不过该著主要谈文化、谈社会、谈人生、谈旅游见闻,谈读书感受,因为在这些方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作为读者我还是可以说几句的,加之该著表现出的人生态度及思想倾向我不只由衷认同且极为欣赏,结果品茗书香之后,禁不住产生就此说几句的念头。由外而内综观,该著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其一,面宽底厚,运笔老到。《独自散步》由作者近年撰写的各类随笔汇编而成,可见它属于散文集。该著内分五章,依次冠名为“文化反思”、“社会透视”“人生情怀”“走读天下”“另类阅读”。2011年黄先生推出小说新作《大学囚徒》,介绍创作背景时他说:这些年来“我已经通过各类文章向这个世界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一些话”,其中有“关于历史”的,“关于时代”的,“关于社会”的,“关于革命”的,“关于改革”的,“关于大学”的,“关于教育”的,“关于体制”的,等等(见《我有话要对这个世界说——写在长篇小说〈大学囚徒〉出版之际》)。当时他一口气列举了21个“关于”,围绕这些“关于”撰写的各类文章大多收入《独自散步》。即此可知,该著五章标题不过是给所收作品作一个大致分类,而微观地看其所涉内容相当广泛。近些年来社会风气浮躁,信口开河之作汗牛充栋,以致葛兆光公开声言,时下的出版物“百分之九十都是‘学术垃圾”。(《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2012)对于以上说法这里不作评论。不过可以肯定,葛先生如有机会翻阅《独自散步》,绝不会亦对其嗤之以鼻。因为黄先生的新著不仅具有篇幅上的厚度,总计346 页;同时具有思想上的厚度,从“另类阅读”反映的阅读面可以看出,该著乃厚积薄发之作。毋庸讳言,与出版过同名散文集的朱苏进相比,黄先生的笔下工夫稍逊风骚。但在同行中其援纸握管能力仍属上乘。安徽诗人王多治曾评论道:“黄书泉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文字好,这是大家公认的。”(见《黄书泉长篇小说〈大学囚徒〉研讨会综述》)我懂点修辞,以修辞标准衡量,黄先生的运笔堪称“老到”。其“老到”不只表现在措词的言简意赅和行文的自然流畅,更表现在善于用典。这里所谓“用典”主要指引用名人名言。前述特点在《独自散步》中表现十分突出。如《质疑“知识分子”》文末对瞿秋白有关论述的引用,《愿天下同乐——春节感言》中间对聂夷中有关诗句以及拉布吕耶尔有关感言的引用,《从大学反观中学》结尾对爱因斯坦有关见解的引用;《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读〈梁漱溟口述实录〉》收官处对钱理群有关说法的引用,等等,均起到画龙点睛,甚至点石成金的作用。东坡云“腹有诗书气自华”,雪芹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黄先生博闻强识且善于借鉴,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的用典不仅使笔下魅力丛生,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同时增强了论析的说服力,提升了文章的品味和境界。
其二,情系民生,关注现实。数年前有人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反映皖北农村教育落后面貌的PPT。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的我国,有的农村地区教育条件依然那样恶劣。鉴于唯有政府和社会共同重视才能促使前述状况及早扭转,当时我除了将PPT传给了教育厅领导,还传给了院里同事。令我诧异的是对此有人竟持嘲笑态度,而黄先生不然。有天路上相遇,他主动提起那PPT。交谈中我意识到,他属于始终把民生问题搁在心头的公共知识分子。该类学人有个特点,就是不止像杜少陵那样有着情牵“天下寒士”的仁爱之心,而且总是以各种方式努力促进全社会共同呵护弱势群体。黄先生正是这样的身体力行者。近年来他为此不断撰文发稿。其中有的篇目,如《愿天下同乐》《“爱”的匮乏》、《废墟上的独白——汶川大地震随想录》,已收入《独自散步》;有的篇目,如《解读何家庆》(2004),《不问鬼神问苍生》(2007),虽未收入文集,但仍在其博客上继续发挥着鼓与呼的作用。前些日子安徽大学新闻网报道:“4月的皖北仍然是春寒料峭,但文学院教授黄书泉带领他的研究生前往固镇陈王小学开展的赠书活动,却给孩子们带来一缕温暖。”黄先生不仅是真真切切情系民生的公知,同时也是真真切切关注现实的社会性学人。前面提到的21个“关于”,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现实论稿。收入集子的《独立、求是、参与的学术人格》一文,为阅读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之后写下的随感。李先生在书中表示:“我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我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独立、求是、参与的学术人格》对此给予极高评价。黄先生之所以对李先生前述著作以及前述表态高度认可,除了因为彼此所见一致,更因为黄先生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既超脱世俗、淡泊名利,同时又积极关注社会民瘼,所谓‘大隐隐于市。尤其是像新时期十年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思想文化最为解放、活跃的时期,他们更是不会躲进学术的象牙之塔去追求所谓的‘不朽,而是以自己面向现实的学术研究积极参与、投入其中”。
其三,目光敏锐,见解深刻。“美”乃各类文本的共同要求,而文学作品对此尤为重视。抒情诗、叙事诗等对“美”的追求多从“形而下”入手,诉诸情感和形象的抒发和描写;文化随笔、思想随笔等对“美”的追求多从“形而上”切入,依靠理性和智性的艺术化论析。《独自散步》收文96篇,其中文化随笔、思想随笔之类占了相当比重。故而能否完成“形而上”的“美”的塑造,即理趣和智趣的生成,很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有观察的敏锐性和思想的穿透力。赏读《独自散步》,我以为上述两大前提均有出色体现。《从大学反观中学》谈教育问题,作者从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令人堪忧状况,如人生观模糊、价值观紊乱,人格、个性、心理缺陷严重,认知水平低下,厌学情绪强烈,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和与人相处能力,人际关系失调等等,探本溯源,反思中学应试教育结下的苦果,说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疗治得从根入手,对症下药。《一个非球迷的足球感悟》谈足球赛给予自己的启迪,其中分析足球赛缘何而生,作者认为:“也许,在所有的体育竞技项目比赛中,只有足球,将体育的竞技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人性深处具有进攻性、征服欲,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成为胜利者、征服者,这是人类无数次战争的心理根源。然而,人类社会生活需要和平与秩序,于是,发明了体育竞技,将人的进攻性、征服欲通过正当、合理的渠道,加以转移、释放、升华。”《解读“家庭暴力”》乃是针对“李阳殴妻”事件发表意见,其中谈到为什么近年来家暴屡屡发生于名流家庭,作者指出:“当今某些社会上的所谓‘成功人士,激烈的社会竞争,复杂的人事关系,外部的种种诱惑,自身欲望的无法满足,对名利的无休止的追逐,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心理发生畸变,致使他们回到家庭稍不如意,便会反弹、宣泄,家暴由此发生。这也是近年来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家暴行为增多的重要原因。”《“莫言热”后,文学依旧》是就莫言获奖及其对我国文学的影响表达看法,文章说,“莫言只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莫言之后,中国也许还会有作家获诺奖,但仍然产生不了伟大作家,因为已不存在产生伟大作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土壤。”《独自散步》中类似析论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将“目光敏锐,见解深刻”视为该著重要特点。
其四,针砭时弊,痛快淋漓。我是南京人,2004年才来安大,但即便如此,与黄先生已有十多年交往。印象中黄先生属于从不掩饰真实情感的爽快人。我是搞语言的,根据对有关标准的了解,敢于断言,黄先生的普通话连三级乙等都达不到,但每年春节院里联欢,他都自告奋勇,用带有浓重肥西方音的普通话来段诗歌朗诵。由此可见,他乃性情中人。或许因为性情使然,或许因为服役期间受过正统教育,或许因为天生眼里容不得沙子,黄先生自从有了“拿起笔做刀枪”的能力,那些人性上以及制度上的非健康非正常现象,也就几无例外地成为其披露、批评、讽刺、质疑、抨击的对象。例如《质疑“实话实说”》披露说,在中国说实话难度很大,过去如此,现在依旧,从《实话实说》栏目的逐渐变味到最终退场,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又如《“爱”的匮乏》批评说,如今“爱”字满天飞,但大多不过是些官样文章、职业语言、作秀姿态、广告包装、精神佐料、文人话题、商界噱头而已。一旦动真格许多人则借故回避,可悲的是,表里不一、言是行非的丑态每每表现在道貌岸然的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身上。《文化八问》第二问讽刺说,媒体在反对虚假广告上调子最高,而大量虚假广告恰恰是通过媒体堂而皇之传开,原因在于广告乃其最重要经济来源,为利益所驱动,许多媒体滥用权力,来者不拒,给虚假广告大开方便之门。《文化八问》第四问质疑道“学术何以能够腐败”,指出“不是学术本身腐败,而是已与‘官本位接轨的现行学术体制腐败,是掌握高校和研究机构学术权力和资源的某些人腐败”。《说“原”》抨击道:近年来非官方和民间举办的大型会议以及重要庆典中,总会出现许多“原”官员,主持人介绍时总是特别突出其原先官位和级别。原因在于这些人当过官,有的职务还较高,瘦死的骆驼大似马,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他们曾经拥有的级别和职务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仍能镇住人,能提高会议或活动的“规格”“档次”。由此可见“中国的官本位体制积重难返,中国人的权力依附意识根深蒂固”。诸如此类嫉俗如恶,嫉恶如仇,似匕首、似投枪的犀利文章,黄先生写了很多,大概为了减少麻烦,避免是非,有些文章,如《我们如何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如《给安徽小说创作把脉》(见天涯社区网站),没有收入文集。
二十年前在《文艺评论》上,黄先生发表过一篇名为《随笔:透视作家的一扇窗口》的文章。其中说:“随笔,既是作家实现展示表白自我、与他人直接交流欲望的一道门,又是读者占有、欣赏、了解、认识作家人生的一扇窗。”我以为这话说得很好。所谓“文如其人”并不准确,因为事实上并非任何作品都可以作为窥探作家内心世界的渠道,在各类作品中最有资格担此重任的乃是随笔。黄先生通过随笔探秘别人;我通过他的随笔,收入和没有收入《独自散步》的,探秘黄先生。其间我注意到,在《独自散步》中,“静”“动” “入”“出”这四个关键词深刻影响到黄先生的为人和为文。根据其有关说明,“静”是指安坐书斋,与书为伴、以笔为业;“动”是指参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活动,品味多姿多彩的人生(见《动静之间——我的人生态度》);“入”是指达则尽心尽力,广济天下;“出”是指穷则自我排遣,独善其身(见《苏轼文化人格的现代意义》)。黄先生认为学者需要处理好“静”与“动”之间以及“入”与“出”之间的关系,无论怎么说都不可固守一隅,失于偏颇;明智的态度乃是执两用中。他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是在“独自散步”,但“从心所欲不逾矩”,始终徜徉于静动之间和入出之间。正是得益于前述“度”的理智把握,黄先生创作了那一百多篇有张有弛的各类随笔,也正是得益于此,他推出了又一部可圈可点的学术新著。
责任编辑 何冰凌
安徽文学2015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