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德国浪漫派
丁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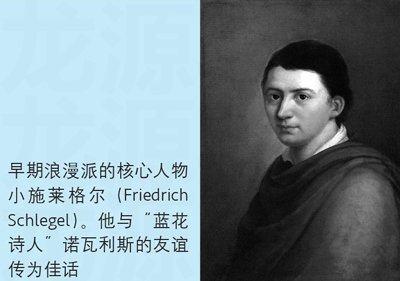

某日突然读到纳粹又把另一个我崇拜很久的艺术家拉下了水。
这类事情简直没完没了。早些年刚上大学,刚会读一些书,读到尼采的东西,瞬间崇拜到五体投地,后来惊闻他跟纳粹的肇始脱不了干系。后来崇拜瓦格纳(当然部分是跟着青年尼采的风),又发现他也被指责为纳粹主义的始作俑者。再后来还有埃兹拉·庞德,甚至有里尔克,有阿诺德·勃克林,数不胜数。
再后来读到桑塔格那篇著名的《迷人的法西斯》,隐约觉得德国浪漫派所代表的那一条精神传统线索,可以整个与法西斯挂起钩来。让人不禁反问,那些德国浪漫派的艺术家怎么都是法西斯的帮凶或者预言家呢?
或者只是偶然而已?只是这些“邪恶”的浪漫派艺术家,恰好他们反犹而已?
可是这样的话,那些本身就是犹太人的艺术家怎么办?比如马勒,比如门德尔松?比如身为犹太人而居然提出反犹的作家卡尔·克劳斯?比如敢回到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犹太人巴伦博伊姆?
不久前读萨弗兰斯基的《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发现他居然要开始探讨德国浪漫主义和法西斯的关系了,而且居然要实地考察(对人不对事地)希特勒那些具体主张、纳粹政权具体的“Leitmotive”(元动机),以及它们与德国浪漫派传统中最核心的那些元素到底存在哪些重合,到底存在怎样的历史因果。
萨弗兰斯基是时下德国最著名的自由学者和非虚构类书籍作家之一,他的精神史传统的人物传记(主要是德国历史文化名人),长期以来名列畅销书排行榜前列。这本不久前刚出版的中译本的书名和德文原书标题大不一样,德文书名是“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re”。德文Aff?re一词,几乎等同于英文的affair,这里大概接近中文“外遇”的意思,旨在表现出,浪漫派这个复杂事件同时具有的热烈与新奇、“荣耀与丑闻”,于是直译过来应该是“浪漫派:一次德国外遇”。而原文标题中也丝毫没有要“反思”德国浪漫主义的意思,这本书的写法和作者一贯以来坚持的狄尔泰式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写作方式保持一致,是一种从头到尾的梳理。虽然中译本标题完全不能表现出原文标题的多义性,但由于Aff?re一词在中文中缺乏对应词,所以也只能改换标题。
据萨弗兰斯基考证:那些把艺术家们拉下水的其实不是纳粹政权的任何一号人物,其实首当其冲的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一大批“嘴最长”的文化史家。
比如著名的神学家、教会史学家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他就四处高喊,“法西斯主义是政治的浪漫主义”。
再比如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里面他肯定是在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在他的短文《理性的落败》中说:德国精神史和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转折点是非理性主义战胜了理性传统的人文主义,也即浪漫主义诞生这一历史事件。
似乎我们也可以仿照卢卡奇将纳粹归咎于浪漫主义这一精神史事件的做法,将世人通常以为德国人就是传统的理性、严谨和刻板这一史上最重大的误解归咎于卢卡奇这类故意误导的说法。
比如,对绝大多数人来讲(不管是普通大众,还是很多以读书写作为职业的人们),康德和他的“三大批判”是典型的“德意志”的精神模式的代表。那种庞杂而完整的抽象体系,让人望而却步,却始终敬佩不已。而康德的“三大批判”体系建立的一大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史上浪漫派运动的诞生。这样看来,大多数人看到康德“三大批判”形式上的晦涩艰深就完全不顾他在哲学史、精神史和艺术史上到底造成的是哪种影响了。其他不论,就在文学艺术方面,他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其实是浪漫派最亲近的“精神父执”之一,绝不是被普遍误解的“理性传统的”。(当然哲学史上,这个理性传统又是容易误导的了,比如这里不是指笛卡儿那个理性主义的传统,而是简单指相对于十九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浪漫派而言的那个浪漫主义的对立面。)
不过如果连卢卡奇的话都听起来不够疯狂、不够令人信服的话,那么再听听以赛亚·伯林的话:“浪漫派让个性的、创造性的主体的力量超过了客观的、有组织的物质世界,然后这种超越很快扩展到了政治和道德领域。”(参看他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一章)
于是这种逻辑可以简化成,法西斯=疯狂=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所以:法西斯=浪漫主义。
这个“推理过程”和维克多·克伦普勒(Victor Klemperer,他的关于纳粹时期德国文化史的书不久前出了中译本)几乎不谋而合。
我们来做一些拆解试试:德国浪漫派,到底怎么跟纳粹扯上干系的?最著名的那些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文化史言论,最主要有哪些论点,这些论点有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德国浪漫派作为一些艺术家或者自诩的哲学家、神学家,他们所提出的美学观是如何(被)推广到道德、政治领域的?面对一个世纪以后的那场政治劫难,他们究竟是无辜还是罪孽深远?
首先得说说德国浪漫派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德国浪漫派,在世界文学史中,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试图尽读天下书,探索一切学科的逻辑门径;对一切知识,历史的、当下的,以经过“古典时期”梳理后的冷峻的眼光,咀嚼、吞咽或者吐掉;对自然抱以最均匀最无轮廓的热情;对古希腊罗马的理解与思考,具备多出前辈许多的范畴;对中世纪取消“黑暗时代”的标签;对与他们持相反艺术观、人生观的十八世纪的前辈持尊敬乃至崇拜的态度;对地方神话、民间传说、童话、寓言有着生理性的狂热;时而虔敬,时而又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时而将自我意识推演至极继而狂妄而自恋,时而又自嘲喟叹个体的渺小无力。如果有一个大一统的教会将他们联合起来,这个教会就叫“人的精神”。
他们被后世一批又一批雄辩的嫉妒者斥为唯心主义、异教徒。他们不单是诗人、艺术家,也是神学家、哲学家乃至政治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这些属性往往能在他们中的一个人身上同时拥有)。他们游历世界,不满现状,但和他们同时代(或同精神父执)的英国浪漫派、法国浪漫派等相比,仿佛缺少一些行动力和开展行动的决心。似乎在他们那里,精神不单是居于肉体之上的,且是唯一有效的“人的活动”。他们是人类精神的狂热教徒,穷毕生之力为“人”寻找定义。
他们活跃于从一七八九年—那个永远与“革命”、“自由”等一些字眼联系起来的年份—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的约半个世纪间,他们塑造出许多英雄和偶像。他们崇拜古希腊神明,崇拜基督,崇拜远东的圣哲和歌者,崇拜伟大的古罗马。他们企图通过文字—那经过歌德与席勒这两位英雄变得光荣、细腻而典雅的德语—将他们的英雄与偶像昭示天下。于是世人也崇拜起他们的英雄,慢慢地,世人开始崇拜他们。
他们认为荣耀是必然的,伟大是绝对的,崇高是完整的。而美是最荣耀、最伟大且最崇高的。同辈中济慈、布莱克,晚辈中波德莱尔、戈蒂耶,都被后世妒忌者唤作“唯美主义者”。而唯有他们,可以用断片集斥责道德家的虚伪,用未完成的诗体小说或韵律优美的长诗赞颂美的绝对性,而同时又免于受责难、受诽谤。
他们因是人之精神的教徒,故而轻视肉体。他们往往短命,“天妒英才”,或者“光荣而美丽地回归自然”。他们并不常沉溺肉体之欢,但绝不节制。他们互相结交,文稿、通信往来,共办文学杂志,参加沙龙、画展、音乐会,甚至布道、讲经,辩论教义。他们关注形而上,也会对彼此间的友谊无比珍惜。
就是这样一群互相结交的年轻艺术家们,在十九世纪最初的几年,大工业时代的浓浓黑烟即将笼罩西方世界之时,用断片集、零散出版(很多甚至是互相资助自费出版)的诗集和一部自命清高的杂志《雅典娜神殿》,就几乎颠覆了整个西方文化史前进的方向。在启蒙运动的大浪中沾沾自喜的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停了下来,听听这些年轻的德国人有什么要说的。结果斯达尔夫人首先听到了,她用她的《论德意志》向法国人首先介绍了这些炙热的灵魂,随后才有了雨果、戈蒂耶、夏多布里昂们。
他们,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荷尔德林、克莱斯特、E.T.A.霍夫曼,德国浪漫派的这些独立而又紧密相关联的心灵,发起这场运动的最初,提出了哪些核心主题(Leitmotive)?
首先是“das Volk”(民族)。
比如说海德堡浪漫派,阿尔尼姆(Archim von Arnim)和布伦塔诺(Clemens Bretano)这一对,花大力气收集民谣(Volkslied)。注意,不是后来舒伯特写的那种“艺术歌曲”(Kunstlied)。
受赫尔德最初的启发,浪漫派(包括后来的格林兄弟)都对民间文学、民俗传说充满热情。他们企图通过收集和推广这些民俗文化来缔造一个“民族性”的概念。然而,浪漫派所推崇的这个“民族”,首先它不是专指“德意志民族”。虽然从政治史上讲,他们这个时候提出倡导“德意志民族的觉醒”是非常合理的(普遍看法是,因为英法等统一的民族国家走在了前面,德国人这时候才产生了“统一的觉悟”)。但这的确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的初衷始终是美学意义上的,是一种艺术、文化观念上的“民族性”,与血统、民族志的那种“民族”并无多大关系。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统一起来的,是一个泛德意志文化圈,或者按照诺瓦利斯和小施莱格尔的想法,是一种“普世的诗学”(Universalpoesie)。他们是想通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联结来推广他们的美学理想—让全世界充满诗。这里诗就是美的同义词,而不是德意志血缘的人用某一种所谓“典雅德语”写出来的诗。
不管怎样想,可是至少那些德国浪漫派们,比如阿尔尼姆那样真正的诺瓦利斯式的诗人,怎么可能不是精英主义的呢?怎么可能反对个体,崇拜集体呢?他们只是在个体中寻找集体,而不是要将个体置于集体之中,任其湮灭。
这跟作为政权的纳粹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再者,关于“国家”、“祖国”(Nation, Staat,Heimatland,Vaterland)以及国家和社会中的“有机体”(das Organische)概念。
浪漫派提出的“有机体”是相对于工业时代萌芽期的、机械主义的、功利主义的社会的。他们(虽然一切都源始自法国大革命)在这里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
而纳粹,是作为反对魏玛共和国这一旧政体而建立起来的新政体。与浪漫派在“政见”上的相似之处,也就仅有这一点了:都是反对旧规则建立新规则。除此之外,比如诺瓦利斯(Novalis)的《基督教或欧罗巴》,其实是想建立一种人文主义的基督教的世界图景,而纳粹政权是要将其政治和社会结构带着文化强权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Reich)。
其他一些核心观念如“Weltfremdheit”(陌生感,或“去魅”),比如非理性(Irration)。
以赛亚·伯林在提及浪漫派的“去魅”观念时,将其标注为“最初无害,但并不是一直保持无害下去”。他在《现实感》(The Sense of Reality)一书中论证了这一点。浪漫派意图使世间万物重新“陌生化”,产生康德意义上的“审美距离”,从而使得一切人们在理性时代理所当然接受的一切道德律令、政治法则都变得不再理所当然,不再不容置喙。人造的道德条令也好,自然的物理法则也罢,都应当是人的、主体的“再创造”,脱离了这个审美的、静观的而又沉思的主体,这一切规则都应该失去意义。意义应当由这个主体创造。
这样一来,作为虔诚基督徒(大部分还是天主教徒)的浪漫派们,一个个都成了实际上的无神论者,他们命自己的主体为上帝,为一切重估价值。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现实观念(即一种脱离主体不可能存在的客体观,其深刻来源,可以说是康德的“第三批判”,也可以说是费希特著名的“主客二分法”),导致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政治观念史上的动乱,从而间接造成了一个世纪以后的政治灾难。
看起来像是没有什么漏洞的论证。但其实深究起来,是有一点循环论证的意味的。即:首先假定了法西斯们熟悉并了解德国浪漫派的“真谛”,然后再开始论证这种了解是如何对他们产生影响的。
萨弗兰斯基写道:“Gewi?, die Ideen Hitlers waren ganz und gar nicht romantisch. Sie kommen aus den vulgarisierten, moralisch verwahrlosten und zur Ideologie gewordenen Naturwissenschaften: Biologismus, Rassismus und Antisemitismus.”(希特勒的观念显然不是浪漫主义的,这些观念来自一些庸俗的、非道德的、几乎沦为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生物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
书中接着说,希特勒自杀前曾感叹,他曾标榜为最杰出的日耳曼民族还是太“虚弱了”(zu schwach),认为整个民族应当同他一起死去,不可以继续存活下去。随后作者并没有深究下去。然而,托马斯·曼在Bruder Hitler一文中说,希特勒作为一个失败的艺术家,是想以全世界的人民作为材料,完成一部心目中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什么“雅利安人至上论”,只是编了这么个谎言,欺愚大众,好让大众乖乖沦为他的材料。也许事情不像托马斯·曼所说的,希特勒确是相信“雅利安人至上论”、“日耳曼民族至上论”或是“某一民族至上论”。反正他走火入魔地投入血腥的试验,终以失败而告终。
红极一时的德国电影《浪潮》(die Welle),讲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如何形成。而针对的是宽泛的极端的集体主义。法西斯主义不止是极端的集体主义,也不止是极端反犹主义。
不得不引用希特勒本人的话,在《我的奋斗》里,他说:“Im ewigen Kampf ist die Menschheit gro? geworden. Im ewigen Frieden gehen sie unter.”(在永恒的斗争中人性得到了升华,在永远的平和中人类则会沉沦。)简言之,意思是说,犹太传统—他的确借用了很多尼采在《敌基督》里的推理和结论—是摩西引领人民走出埃及,走向西奈山顶,走向应许之地,由混乱和不确定走向永恒的真理和确定性的过程。
按他的意思,这是人性腐化的开始。只有永远的不确定,永远地“斗争”(用的是Kampf这个词,即标题“我的奋斗”中的奋斗)下去,才是人类的正途。
用萨弗兰斯基的话讲,这叫把个人妄想视作人类使命。
这和浪漫主义又有什么关联呢?
如果要说这和希特勒所理解的浪漫主义有关联,尚且都不大行得通。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真的明白德国浪漫派艺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他真的很喜欢阿诺德·勃克林(Arnold B?cklin)的画,很喜欢瓦格纳的音乐。
在柏林著名的犹太博物馆里的一个展厅里,通过一些旧画报和旧收音机(按动机关可以让收音机播放当时的音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政权里,人们的视听世界是怎么进入这样一种“伪勃克林”、“伪瓦格纳”化的情形,被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原本(依据康德,那个德国浪漫派伟大的父亲)有着完全“自足性”(Autonomie)的艺术作品,在这里只是符号而已。它们麻木,而且为了麻木。
关于法西斯的起源,半个多世纪以来,德语学界已经有太多的专门研究。从一本宽泛介绍法西斯理论(Faschismustheorien)的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出,包括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在内的二十世纪许多著名学派,都对法西斯主义提出了理论建构。精神分析法、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统治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思想界的“主义”们,也都纷纷向其伸出了解构的触手。
到了今天,和所有其他历史上著名的文化、政治事件一样,法西斯如果是“迷人的”,首先也仅仅因为它是“复杂”的,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本身,而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它教唆人们做什么,等等。
从这点上来说,法西斯和浪漫派又何尝不是一样呢?
最后,文章开头说的那个“被拉下水”的艺术家叫卡斯帕·大卫·弗雷德里希(Casper David Friedrich),他虽然不是前文所述的那一批互相结交的德国浪漫派中的一员,但他绝对是浪漫派的忠实信徒。他的“心灵风景画”(geistliche Landschaft)独创一格,影响了后世无数的艺术家。甚至有人视他为视觉艺术领域唯一真正的浪漫派的实践者。
的确,和他比起来,透纳(J.M.W.Turner)都未免太自然主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