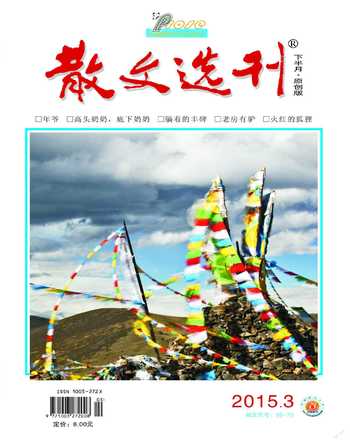火红的狐狸
王小忠
小镇经过一季的休养生息,渐渐从瑟缩中舒展起来,山梁上缠绕着初春时分的尘烟,低洼处也有了湿度,田地像发酵的面团蓬松而肿胀,树林似待嫁的姑娘带着娇羞的容颜。
我走在二月的田地里,大叫几声,真有点儿无法说清的感觉。坐一阵,走一阵,阳光在坐坐走走里却已转过了身子。回到家,把一天的欢愉之情安放在椅子上,心突然就空了。说不清楚,也搞不明白,这种奇怪的感觉长期盘踞在心底。房屋后面的山坡不大,山坡四周同样是不大的树林。打开窗户,我就能听见万物的私语。
狐狸在小镇上是稀奇之物,偶尔见到年老者头戴狐狸皮帽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许多不安分的想象。小镇在很早以前四处全是森林,豹子、狼、鹿,自然不会缺少,可现在却很难见到它们的影子。有位年老的长者曾经告诉过我,说这里最多的是狐狸。由于狐狸的贪吃和狡诈,小镇上许多人家鸡窝里的鸡无法安生,于是大家便大肆捕捉。当大家把它追赶进窝,然后挖掘的时候,狐狸就会耻笑人类的愚笨,因为狐狸的巢穴有许多出口。猎人做陷阱的话,狐狸会悄悄跟在猎人屁股后面,看到对方设好陷阱离开后,就到陷阱旁边留下可以被同伴知晓的恶臭作为警示。狐狸看到河里有鸭子,会故意抛些草入水,鸭子习以为常后,它就偷偷衔着大把枯草做掩护,潜下水伺机捕食。因而,在人们心里狐狸就成了凶险和奸猾的代名词。没几年,狐狸在小镇上就不见身影了。
长者讲述有关狐狸的故事已是许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位慈祥的长者也将家安在山洼深处,成了狐狸的邻居。也或许是狐狸身上每一部分都极具价值,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故而难逃杀身之祸,于是它们就不断改造自己,让自己适应环境。可惜我们看不到这点,也没有人从狐狸生存的本身去思考,而一味诋毁它的奸猾,大肆宣扬自身的善良。狐狸的善良只有智者尚能发现,蒲松龄在其小说中还原过它的本性,相比而言,人类心灵的丑恶和虚伪就很难遮掩了。
还有位老猎人说,最好的狐皮需要捉到活狐狸,然后绑在树干上,把烧红的铁棍从它屁股里捅进去,狐狸在疼痛与挣扎下全身会无限扩张,毛发竖起来,看上去像钢针,摸起来却柔软无比,那样的狐皮才可以卖到天价。老猎人讲完之后,我早汗颜不已。很多次,我在深更半夜总要打开窗户,想象着会不会有狐狸从我眼前跑过。可我看见的却只有黑乎乎的山林,只有安静入睡的小镇。于是,众多美好的狐狸的故事就会浮现在脑海里。于是,我就在纸上写下这样的句子:
等待我的人在不远的地方
怀有善良,也怀有恶意
我看见聊斋里的女子依然呢喃
痴情的书生在烛光下
想象还有多少时日
她就是那只火红的狐狸……
有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睡梦里听见“咕咕”的声音。是狐狸?我爬起身趴在窗口,却什么也没看到。可那声音一直叫着,悠长、哀怨,夹杂着无尽的凄凉。是狐狸的声音,那声音和当年的长者告诉我的狐狸的叫声一样。一定是火红的狐狸,一定是当年遗留下来的狐狸的子嗣,一定是前来拜祭曾经的祖先,一定是来偷窥小镇上人们自私的生活状态。
没有狐狸的小镇和有狐狸时的小镇无本质区别——风吹日落,花开雪飘。
二月是狐狸发情的季节,我想,它会不会对小镇有了新的看法而决意留下后代?或是在彻底告别前作最后的回首?我不得而知。
——长者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