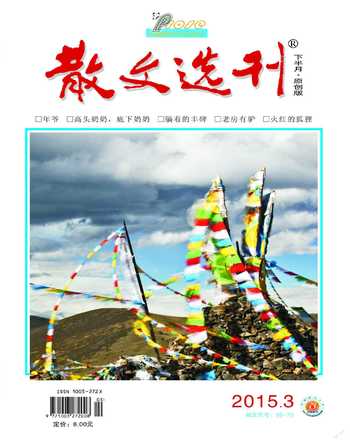嫂子是用来疼的
李永胜
又到了周末,几个朋友又聚到了一块,吃吃饭,喝喝酒,叙叙股市,论论反腐。尽兴之后,才发现忘记了时间,回到家里时,已经将近十点钟。好在有月光,淡淡的,院子里的情形还辨认得出。我轻轻地拧开楼梯门,小心地迈上台阶。 “嗒,嗒——嗒,嗒!”
右手的食指关节轻轻地磕了磕卧室的门,屋里没有任何响动。我知道,妻子肯定在里边,绝对没有睡着觉。我贴着门板屏息听了听,里边安安静静。算是打过招呼了吧,我没再言语,轻轻地移开脚,慢慢地转过身,扶着冰冷的扶手,一步一探又摸开了楼梯门。突然,院子里一下子弥漫了白光,模模糊糊,轻轻柔柔。光线是从父亲的窗口散发出来的,可能是关楼梯门时手重了些,响声有点大。我不敢打搅他老人家,就蹑手蹑脚,打开院门,静静地走了出去。沿着院墙东边的水泥路,一直向北,慢慢地溜着。虽然刚刚十点多钟,但,已是初冬时节,又处在乡村,路灯已经熄了,不见行人,凉意袭人。路边的水道里,或紧或慢响着细碎的哗哗声,不大,却清晰,这是哪位乡亲在给麦苗灌过冬水。
今天晚上,酒倒是下去不少,但我确实没喝多少,奔五十的人了,已经过了海喝豪饮的年龄。空旷的麦田里,微风阵阵,汩汩的流水上泛着蒙蒙的月光.难得有这样的景致,我小心地探到水道沿儿边,双脚落稳,屈膝,弯腰,借着月色,掬了两把水,朝脸上撩了撩、抹了两把,又漱漱口。刚从井里抽出的水还带着地温。
我没有理由埋怨妻子。有几次,喝高了,我吐在床单上、被沿儿上、地板上,碎面条、下酒菜和酒精搅混出来的味道,让人家戴着口罩躺在床上,彻夜不能成眠。第二天,还要再戴上手套擦洗被褥、拖洗地板;接下来,还要呼吸着我俩都不愿闻的空气清新剂睡几天觉,想起来我就心疼。又一阵风吹过,刚刚湿过水的脸和手冰凉冰凉的,我不由得转过头,向家的方向望了望,楼下西边有一小块亮色,白白的,灰灰的,隐隐约约,不留意的话,根本注意不到。但是,我不能不留意,那是从老父亲的后窗口透出的灯光。母亲走得早,父亲孤孤单单不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没有原来利索了,两年前,就是因为骑白行车而跌断了左腿,卧床三个多月。妻子端水送饭、擦屎刮尿,硬是让老父亲重新骑着那辆老式的“永久”牌白行车四处赶集。那之后,他老人家也好像更加关注子女们了。
我必须马上回去。这一次,拉楼梯门的时候,我有意加了点劲,院子里霎时暗了下来。走到卧室前,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小兄弟打来的。
“还没睡吧,哥?”
“没有。”
“被关在门外了吧?嫂子咋那么没规矩呢?哥要是下不去手,兄弟我去!”透过手机,仿佛一股酒味冲了过来。
我赶紧捂了捂嘴,轻声回了一句:“多谢了,你嫂子是用来疼的。”随即,挂了电话,一把摸着把手,轻轻地推了推门。
一线橘黄色的、熟悉的、和着睡味的温暖的光从细细的门缝里挤了出来。原来,门是虚掩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