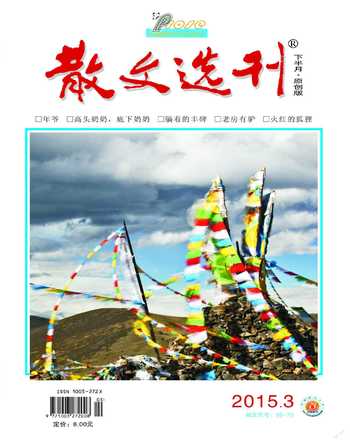响在心头的“骨碌”声
王茹华
我的心里头一直响着那“骨碌、骨碌”美妙、动听的车轮声。 那是一个晚饭后。 我来到天岳广场散步,广场到处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广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有成百上千跳广场舞的人们,有打太极拳的,有游泳的,也有打篮球的,还有跳绳、拔河的……广场最西边,巨型电视正在播放着当地的新闻。
突然,我看到了前方一辆手推车由远向近缓缓地推来,看得出,这是一台残疾人坐的车,像农村人早些年婴孩坐的那种座篮一样。四周用木板固定,中间留一个大的空隙,供人坐在里边。下面安装了四个轮子,由坐在里边的人推着向前跑。
由于隔得较远,我只能模糊地看了看车里的人。从露出的半个头的发型来看,车里的人是个男人,三四十岁左右的样子。他实在太矮小了,以致只露出半个头在外面。让你觉得这辆车不是由人推着跑的,而是自己在滚动着跑。
在这个热闹、宽阔的广场里,这辆车“骨碌、骨碌”地向前滚动着,很不符合这个广场的步伐和节奏,显得很另类,因而格外打眼。这辆手推车拼命地往人多的地方挤去,那里有百来个正在学跳舞的人们,也有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们。可周围的人没有谁特别关注有一辆残疾人坐的手推车停在他们的周围。
一直以为他只是像个小孩好奇地前来看热闹,原来,他是想借晚上天岳广场人多来做做小本生意,以赚点钱养活自己……这是个多么有头脑的人!
望着这辆手推车,我的心头不由得为之一振,应该可以说是“震撼”吧。
我的脑海中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中午,我下班回家,经过西道月池塘商场的时候。我发现地上躺着一个里面用层层蓝布包裹着、外面再用塑料布包裹着左脚的壮年男子,正用肩膀拖行着一个巨大的坐垫,坐垫上坐着一个不足八个月的男婴。乍一看起来,这个男人的左脚似乎是被折断成了两节。
他每见一个过路人经过就伸出手乞讨着:“可怜可怜我这个残疾人,做点好事给点吧!”很显然,这个断了左脚,又拖儿带女的残疾人明显博得了很多善良人的同情。于是,一下子施舍的人不断。
我一直关注着这个男人。接近中午,当人们都纷纷散去时,我发现这个壮年男人突然站了起来。原来,他是一个四肢健全、身体完全健康的男人,我目测了一下,个头还不矮呢,大概有一米八的样子。这在我们当地,这样高个的男人还不是很多。
望着这个高个而猥琐的男人,我为自己刚才不分真假的善举感到羞愧,为善良人们的同情心被玷污感到气愤,更为壮年男人失掉尊严的乞讨而愤慨。
正当我沉浸在回想中时,突然旁边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在叫我。我只好立刻转过身来与朋友招呼。当我告别朋友再一次寻找那辆车时,那辆车已经不见了。
九点多,夜慢慢地变得安静。
我从广场抽身往回走。此时路上行人很少,散步的差不多散完了,只剩下几个和我一样夜猫子一样的人在外面行走。
路上很静、很静。月亮透过树隙把皎洁的光芒撒在地上,地上树影婆娑,斑驳片片。月光很亮,但路上却显得很清冷。
突然,我远远地听见了前方有车辆滚动的声音。在这静静的秋夜,“骨碌、骨碌”,像是被谁吹响的一支韵味十足的短笛,十分清脆、响亮地在这寂静的路面弥漫开来。
是广场上的那辆残疾人的车!车推得很慢很慢,也很沉重。我也走得很慢很慢。我装作很白然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后面。虽然我知道他也不可能回头关注我,那个车子空间那样小,几乎不容他有回头的机会。
车子推到防洪堤坝300米时,他突然停止推车了。他,不!确切地说是那辆车,停在了防洪堤的路边。我也跟着停住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突然停下来?
为了防止被他发现有一个人在默默关注他,我装作站在旁边不经意地看风景。路上除了稀疏的几个人在行走,几只蟋蟀拖着长声在叫,此外就是寂静。这辆车就静静地、寂寞地停在那里,车上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少。苍宇下,他和他的那辆车显得是那样地渺小与落寞,犹如马路上的一只小蚂蚁,悄悄地爬过路面而不被知道、更不被关注。
我很想走过去,走到他的身边,把他车上的东西全买下来;或者帮他推一下车,哪怕是问候他一下也好。我搜遍身上的口袋,居然一分钱也没有带……
终于,慢慢地,慢慢地,他推着车往回走了。也许是回天岳广场,那里人多,总比前面没有人的地方有希望;也许是回家吧,家总比路边要温暖,路边毕竟太冷清了。
我目送着他和他的车渐渐地离去,慢慢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