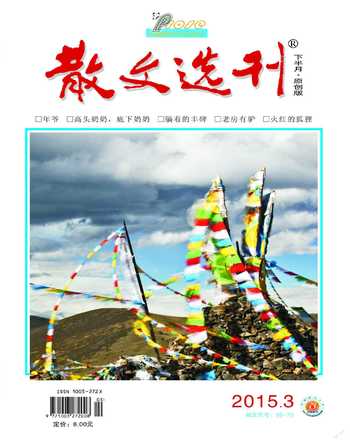冰雪情话
王若楠
生活在北方,尤其是有寒冷冬天的哈尔滨,到了下雪的天气,总想对着冰和雪,说些个情话。
在下雪的天气里,出去走走,呼吸之间,你会感受到一节一岁的变化,你会感觉到这上天恩赐的礼物,是那样地让你舒服与自在。雪就那样静静地下着,自由而散漫,伸向城市远处的街树和参差而栉比的房舍都在雪雾当中显得那样地梦幻与童话,来往的行人更像是从安徒生笔下的世界里走出来的一样,个个都显得那样地温暖有人情味。在这如画如诗般的雪雾之中,你的心里,倏忽间生面别开,派生出许多新的欲望和鼓荡如风的冲动,让你的灵魂如飘雪般地舞蹈起来,而欲罢不能。
曾几何时,站在雪覆的十里长堤上,凭栏眺望,那条已成乳白色大玉的松花江,空空荡荡,一任夹雪的天风肆意横吹。“可怜江上雪,回风起复灭。”雪舞冰啸,昏鸦瑟瑟,那不尽的荒凉呵!仰天长叹之中,让你这个踏雪的来客把栏杆拍遍了。
伸出手来,精巧的雪花一片儿、一片儿,落在你展开的手心上——是啊,这纤美如翼的雪花里,也一直蕴藏着你的那个梦想呵……
记得,刚刚读小学的时候,初次与南方的同学通信,那边的小同学回信说,让我给她寄一片哈尔滨的雪花。然而,落在我手心上的雪花,却一片儿、一片儿地融化了……
未曾谋过面的伙伴,今天的你是不是正在哪座下雪的城市里赏雪呢?
很多的外地朋友都称哈尔滨是“冰灯的城市”。冰灯便成了这座寒冷之城的一个神奇而美妙的象征。而哈尔滨也的确是一座在冰雪中建造起来的城市,并在大雪的沐浴下开创的冰雪艺术的历史,成为这一城独特的冷艺术。
我甚至有一点喜欢“冰灯之城”这个称谓,很特别。
其实,在很久以前,哈尔滨的老百姓就开始了冰灯的制作。最原始的冰灯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照明工具。早年,在朔风凛冽的黑龙江,纸糊的灯笼是经不住刀子一样寒风的摧残的。所以,冰灯就成了冬季里主要的照明工具。他们把冰灯放在饭馆、客栈、药铺、马号和澡堂子门前,就像雪海中的航标灯一样,给远来的旅客指示着方向。
后来,在节日里,人们将这种简单的冰灯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放在柴门口,或者放在离自家不远的大道上,以表示节日的欢乐心情,也是给自家的亡亲照亮回家道路,更是给财神指示方向。既然冰灯制作是民间的一种风习,久而久之,千姿百态的冰灯也就应运而生了。
小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可以亲自动手做各种各样的冰灯,用小桶、小盆作为冰灯的模型,在未冻实的冰面上敲一下,未冻的水一下子全都流出来,然后在里面点一支蜡烛,倏忽之间一个让我们整个冬天都沐浴温暖烛光的冰灯就做出来了。我想,那时候的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冰雪艺术家。那一盏盏看似拙朴的“冰灯”,都蕴藏着一个冬天的童话,闪烁着一个天真的梦想。而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楼房,每一棵树,每一座标志性建筑,甚至每一个行人、游人,都成为这些冰灯的天然而绝妙的大衬景,成为它们的天幕,冰灯在这些衬景之下是流动的、亲切的、有生命力的,像翡翠、珍珠、白玉和玛瑙一样,卓尔不群地点缀在哈尔滨城这个雪美人的各个地方。
与现代冰灯的炫目多彩相比,我喜欢我小时候看的冰灯。那时候的冰灯当然不如今天冰灯制作得那样隆重、巨大而精致。但是,简单与稚拙的艺术,有时比精致与巨制更具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稚拙的艺术不仅是情感的、游戏的,更是精神圣殿里的天籁之音。
天籁之音是艺术的灵魂。
在人们的感知世界中,那山是我的山,那河是我的河,那冰灯是我的冰灯,只有这样,艺术才能进入情感,进入记忆,进入历史,走进美的永恒。
那么,现在的那些制作巨大的冰灯景区,是我的冰灯吗?我有点茫然。有的艺术活在灵魂里,像影子一样伴随你的终生,有的艺术仅仅停留在视觉中,视线离开了,它便消失了。
哈尔滨除冰之外,另一个点缀在这座浪漫城市之上的,就是雪了。早年城市里无处不在的雪人,同样是我孩提时代的欢乐。雪,在哈尔滨人被称为“天降的曼娜”,意思就是神赐给人间的食粮。也有人说,“雪是一封封天降的书信”。这诗一般的语言里渗透着人们对雪的亲情。早年,哈尔滨的雪是极大的。在下雪的日子里,小孩子们堆的雪人到处都是,几乎每家的栅栏院里都有一个雪人。
我不知道“雪人”和雪人的故事是不是舶来品。但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在这座城市寄居的洋人的确非常之多,甚至超过了当地人的一半以上(单是犹太人就有5.5万人),洋人多到了当地中国人并不以为他们是洋人。
洋人的到来,与雪人的出现,不能说毫无关系。他们在白家的栅栏院里堆雪人,引起了当地中国孩子的极大兴趣。在洋孩子、中国孩子,还有混血孩子,共同制作雪人的游戏中,使得后来长大成人的他们,对人类的看法从没有那种狭隘的种族主义偏见,这种不带偏见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孩子,直到今天,哈尔滨骨子里仍然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北方之城。
今天,我仍然怀念早年的大雪和雪中的城市。在我的记忆中,早年的大雪才是真正的大雪,厚厚的,下起来没完没了,漫天皆是,漫天飞舞,一枚枚雪花,片片都硕大无朋。走在大雪飘飘、雪人遍城、冰灯处处的城市里,你本身就是一幅画。
无处不在的大雪把这座洋气十足的城市装扮成了银色的世界,银色的房子,银色的街道,银色的树,银色的栅栏,银色的雪人,这就非常神奇。
彼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小姑娘。街道上的人很少,银色的街道上仅有几条黑色的人影而已。学生们上学、放学大都是非常欢闹的,女同学会打着“出溜滑”上学,在各条通往学校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断断续续的窄条“冰道”,通过些冰道可以一直“打”到学校。而一些男同学,则会用那种脚滑子(谁发明已经无从知道,但它的确简单而实用),在一块脚形大小的木板上镶上粗铁丝,再用绳绑在脚上,然后在雪地上一蹬一蹬地,就飞速地前进了。上学、放学的路上,到处都是我们这些欢闹的孩子们,与其说是去上学,不如说是享受上学路上的欢笑与热闹。
少年时候的冰雪之戏,都是由孩子们自己创建的,无论是路边一堆堆迷宫一样的雪洞,无论是松花江大堤上的陡峭的冰川,乃至简单的冰灯、雪雕,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成人们除了感慨,是极少参与的。应当说,独立的个性不仅是早年冰雪儿童的优美秉性,也使得他们成为这座城市冰雪旅游之历史的先驱,是开拓者,也是创造者。当代的冰雕雪塑自然不失为一种精致,一种高贵之美,然而出自少儿手中的冰之拙品却更接近冰雪文化的灵魂。
大雪仍旧在下着,自由自在地下着,慢慢地将自己的洁白铺满整座城市……城市为历史在不断地更新着,这一页和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年的少儿如今已经人到中年。这座城市孩子们一定会重塑这一独有的、优美绝伦的雪中盛景,重新找回父辈们儿时的勇敢、爱与激情。
冰雪中长大的孩子,他们也会尽情诉说冰雪的情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