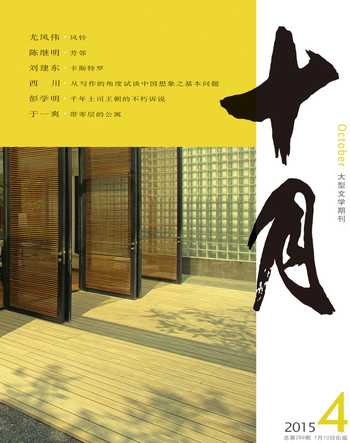电子厂·毛织厂
郑小琼
电子厂
黑暗中,宿舍像一片海湾,床像一艘艘船,我们在上面漂浮,带着乡愁、梦境、理想、悲伤、恋爱……它不停地摇晃,劣质蚊帐沾满时间的尘埃,铁架床露出斑驳的铁锈,一大片暗红的铁锈将淡蓝色的油漆噬咬,掉在地上、床单上、被子上、木板上……迅速被碾碎。坐在床头,无聊,我会剥落那些铁锈,放在手掌,我的手掌染成了一片暗红的光氲,不由心中涌起无限伤感,那些脱落的油漆块,很薄,淡淡的,一片一片,脆弱,掉在地上便无法再拾起来,像我暗淡的青春,哀伤,易碎,掉落地上。被流水线蚀空、生锈,掉落地上。工厂一天一天咬掉我的时光,我有些不甘心,试图反抗,却无能为力,我感觉自己渐渐在消失,青春、梦想、童年、未来……剩下电子元件,晶片,合格纸,产量,拉速,订单,速度再快一点,我变得呆滞而木讷。人生,只剩下一个不停重复的动作,它像铁锈噬咬着我,吞没着我,我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更小的一块,它细碎、孱弱、易逝,从我的生命脱落。刚进电子厂车间,换好白色工衣,拉长便跟我说,这条拉线是工厂最好的拉线,每天产量四万多,其他拉线三万多,工厂计件,员工工资是工厂最高的。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拉线员工集合在车间过道,开早会,白色桶式工衣,六十四个员工,排成三队,穿蓝色工衣的拉长站在前面点名,不停地说要提高产量,说拉速要更快点。他在计算每天能提高多少产量,我计算着装配一个零件要多少时间。我和工友们计算着拉线各工位的时间,用它来称呼这个员工。插旗仔工序只有一个人,工友们叫谢芳谢一秒,我的工序是装边制,复杂些,要三个人完成,我、李芳、戴庆杰被工友唤作郑三秒、李三秒、戴三秒,左右制工序两个人完成,分别叫刘二秒、史二秒。在流水线上,我们彼此用谢一秒、郑三秒,刘二秒称呼着对方。在唤作郑三秒前,我称作装边制的。在流水线上装配的速度稍慢,便变成郑四秒或者郑五秒,如不能将郑四秒提高到郑三秒,会挨拉组长骂,如你的手再慢点,连续几次由郑三秒变成郑四秒、郑五秒,身边会堆积来不及装配的半成品,拉长跑过来,大声骂起来,全拉线的员工都听得见,有时会留下罚款单。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适应苍白而冷漠的罚款单,一张薄小的纸片,写着工号:247,工位:装边制,罚款金额:10元或者20元。一张小小的纸片,好像一张无形的血盆大嘴,一口咬掉我们一天或者半天的时光,接到罚款的工友抱怨着白做了一天。车间白炽灯下,陪伴我们的是机器、喧哗、产量、废品、速度……生活变成一条绿色拉线,漂浮着黑色半成品,车间像巨大的旋涡裹胁着我们,机械地运转着,分不清白天与黑夜,我们丧失了所有关于时间的概念。在这里,时间被机器的节奏无情地分割,以一秒、两秒、三秒为单位循环,生活对于你的所有意义与节奏只有一秒、两秒、或者三秒,短暂的一秒、两秒、三秒的循环动作,构成了你的全部,所有的生活,每一次都是简单重复,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想象,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想象。工厂制定了标准动作,每个细微的姿势都必须合乎标准,手指如何弯曲,身体如何坐,先左手还是右手,具体到每一个指头,只有按标准,才不会从郑三秒变成郑四秒、郑五秒,一个小时,重复它,郑三秒,一天重复它,郑三秒,一月重复它,郑三秒,一年重复它,郑三秒。郑三秒,郑三秒,你只能做郑三秒,你必须做郑三秒,你的人生是郑三秒,所有时光与青春都浓缩为郑三秒,自己的工资、未来都安置在不断重复的三秒上。郑三秒,郑三秒,我不喜欢这样的称呼,却没有力量拒绝,我想逃避郑三秒的生活,换工厂成为我唯一的选择。在车间,除了变成郑三秒或者郑四秒、郑二秒,不再有别的位置,在玩具厂,我是郑五秒,为玩具装上左手臂,在家具厂,我是郑十秒,打磨工……生活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快速地转动,一点一点将我吞噬,然后被旋涡甩开,离去,被它彻底抛弃。
我来这里时,谢一秒已经在流水线重复了四年,她身材矮小,一米四八,贵州人,瘦、孱弱,明亮的眼睛有种莫名的忧伤。从她的眼里,我看到谢一秒四年的全部生活,谢一秒,一次,一秒钟过去了,谢一秒,六十次,一分钟过去了,谢一秒,三千六百次,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整整四年,谢一秒都在重复这个动作。四年的重复中,谢一秒学会了闭上眼睛装配旗仔,夜班,我看见前面的谢一秒在半醒半睡中重复着动作。我不想做郑三秒,我不断责问自己,我又能做什么,换工厂,做郑十秒,或者郑五秒,郑一秒。深夜的车间,拉线匀速地转动,绿色的拉带磨掉了一块油漆,拉线两边是流动的面盒与底盒,它们从拉首被第一个工序分开,拉线两边谢一秒、刘二秒、史二秒、李三秒、戴三秒等装配好零件,到拉线的末端合在一起,在自动螺丝机上打好螺丝。我刚进工厂,不习惯夜班,睡意像雨水,浸濡着我的躯体,午夜两点,它开始淅淅沥沥落着,缓缓地渗入我的意识,我的躯体慢慢变得柔软,手指有些不听使唤,我责备着自己,但身体像泥土,在雨水的浸泡下,松软,一点,一点,直至崩塌……意识提醒我,不能崩塌下去,工友李芳递过一小瓶清凉油,我涂在太阳穴,驱逐睡意。谢一秒处于半醒半睡状态,她低着头,桶式工衣的帽子遮住了她的脸,两个手指以每秒一个或快于一个的速度装配着细小的旗仔,我分不清她是睡还是醒。刘二秒在轻轻唱歌,她边唱边装配零件,刘二秒做了一年半。睡意不断折磨着我,折磨着我的眼睛,我的大脑,我身体的每一部分。车间灯火通明,犹若白昼,机器轰鸣着,液压机喘息,高分贝的声音也无法驱逐我的睡意。开始,睡意只是炊烟般,袅袅升起,随着钟点的转动,睡意如黏稠状的泥塘,将我吞没,越挣扎陷得越深,我想站起来走走,我想到午夜的床,我想到此刻的窗外,有星辰照耀,纯粹而干净的天空如此寂静,它们都进入了蓝色的睡眠吧!我渴望不再重复谢一秒或者刘二秒的生活,我感觉到内心对睡眠的渴望和眷恋,我想离开郑三秒的生活,想离开流水线,我不知道能到哪里去。四处都是流水线,都是工厂,都是夜班,都是郑一秒,郑五秒,郑十秒……生活对我来说,它所有的意义只是变成不同的郑三秒,我抬头看了看谢一秒,她的动作那样利索,你无法猜想,四年的一秒生活,她似乎在这一秒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半醒半睡间,她不断重复人生的每一秒,刘二秒、李三秒、戴三秒……她们是流水线上熟练的工人,工作半年以上。是的,我不断告诉自己,现在我是郑三秒了,我必须做一个合格的郑三秒,我不能连郑三秒都做不好。刘二秒还在唱着歌谣,是的,为什么不歌唱,我跟着刘二秒慢慢地哼起来,李三秒加入了我们的歌声,戴三秒,史二秒,半醒半睡的谢一秒听到我们的歌声,她苏醒过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歌声中我们驱逐睡意。歌声越来越亮,拉线管理员走了过来,我们停止了歌唱,短暂的歌声安抚了我的睡意,歌声给我们的身体注入了新的活力,睡意像潮水般退去。我们沉默,低头,手指飞快地装配着零件,拉线管理员站了一会儿,走了,我们笑起来。这些年,面对夜班,面对漆黑的夜,面对不知终点的流水线,疲倦时,我都用歌声驱赶内心的孤独、寂寞、瞌睡、厌倦,我喜欢蔡琴的歌,忧郁、纯净、空灵,它扎根在我的内心深处,让我在工业区的油腻、铁锈、塑料的碎片、城中村的暗处……在慌乱而不知所措的生活中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上班时的歌声,下班后的诗歌,成为我打工生活的安慰剂,让我在黑暗的现实中不再惧怕,让我有勇气面对郑三秒或者郑一秒的生活。我不断哼着那些歌,只是在内心,比如《橄榄树》,我不敢在车间唱出来,我害怕那些机器的轰鸣,那些汗液,那些胶味,那些细小的弹弓,那些晶片,会污染刺伤它里面的纯净,歌声带给我对远方的眺望,诗歌带给我内心的绿荫。
爱情在荒凉的流水线上蓬勃地生长,它带给流水线上的年轻男女们希望。许多年后,我想起异乡工业区的爱情,依然有一种温暖。两个年轻人,来到这个工厂,在冷漠、孤独的机器丛林中,相爱,没有想过房子、车子,没有问过对方来自哪里,家庭如何,只是纯粹的爱情,是的,这些浪漫或者理想的爱情,有的因为生活的漂泊不定,最终消失了,有的在这里顽固地生长。想爱,就跟一个人走吧,无数次,我看到这样的男女,他们来自湖北、河南、广西……一同出厂,一起离开,又一同进工厂,在流水线上生存,开花结果。而我不再有二十岁的浪漫,生活的潮水不断洗刷着我,在躯体上留下盐味的咸与潮水冲刷过的沧桑,流水线上单纯而美好的爱情成为我回忆流水线最美丽的风景,最温暖的记忆。恋爱的工友,她们的笑容、悲伤、幸福、失望……让我深深地羡慕。在网络上,看到岳母娘推涨了房价,看到各地娶媳妇的成本,想起那些散落在流水线的爱情,干净而纯粹,透明而真实。十九岁的谢一秒不敢谈这个词,她盼望着这个词,这位来自大山的女孩,十五岁跟随老乡出来,她是那样的小,小眼睛,小脸,小手指头,小小的身躯……很多这样矮小的来自贫困内陆乡村的女孩,她们没有读过多少书,骨子里的自卑让她们显得木讷、缓慢,瘦小的谢一秒看上去比自己年纪更小,她压抑着自己的情感,言谈中对爱情、男朋友、恋爱时的拖糖充满了热情,拉线某个女工交了男朋友,她会向女工要拖糖,她是最好的倾听者,倾听着每个细节,分享着恋爱中的女工友们的喜悦与忧伤,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她是沉默的,孤独的,自卑的,她觉得爱情离她那样遥远。她老实,吃苦,不像一些漂亮女工,喜欢换工厂,跳槽,她在一个工厂再苦再累也会待很长时间,她耐劳,好管理,手指头灵活,在流水线拉组长眼中,是个十足的好员工。拉线上的热闹与喧哗不属于她,她只是活跃员工的跟随者,是很多如她这样的好员工中的一个,她们来自西南的山区,贵州、云南,她们不像河南、湖北人那样扎堆,也不像安徽人那样喜欢搞小圈子。在同一个工厂,有十几个老乡,她们没有像别的地方老乡那样捆在一起,贫穷的她们有些自卑,黝黑的脸,头发灰黄,普通话不太标准,发音很低,没有河南口音那种强硬,她们十几个人零散地成为别的扎堆人群的跟班者。在女多男少的流水线,她们缺少爱情,男工们似乎忽视了她们。有几次,镇上的劳动局来工厂检查流水线上有没有雇佣童工,管理员觉得谢芳看上去太小,让她躲到厕所,或者休息半天,避开劳动局的检查。64个或者65个人的流水线上,15个男工,男女比例极度不平衡,没有多少男工关注她,她被忽略着。
坐在谢芳对面的刘忠梅。四川人,漂亮,眼睛大、圆,身材丰腴,她爱笑,笑时眼睛弯成一条线,很美。有个机修技工的男孩在追求她,她还没有答应,男机修常到拉线帮刘忠梅装配零件。机修工湖北人,技校毕业,在工厂做学徒,个子很高,老实,穿着蓝色工衣,他低头走过,小心翼翼。他还没有表白,不敢,怕拒绝,有次加班时,他跟刘忠梅说,出去走走,说完,转过头,看着窗外。刘忠梅没有做声,矮小的谢芳跟随在刘忠梅后面,说,他叫你出去走走,说完笑了起来,我们都笑了起来,说,走走,没发糖哪个跟你走。刘忠梅还是没有出声,她拉着谢芳下楼,男孩跟了下去。
李芳说得最多的一句:流水线上,今天不知明天会流向何处。李芳有自己的爱情,李芳是四川人,男朋友是湖北人,戴一副眼镜,瘦,是车间另一条线的线长。李芳跟我同一个宿舍,她身材好,皮肤白晳,我们上下班经常在一块,她说,家里反对她谈恋爱,说找个外地人靠不住,她也不想嫁那么远,嫁到异乡,受了欺负,没有人倾诉,她问我的意见,我说,你爱他,或者他爱你就行了。她没有做声,还是有点担心。那个男线长我们经常见面,很老实的人,他每天跟在李芳的后面,他们很甜蜜,李芳说谈谈看吧。李芳有自己的担心,我们那时上白班,工厂两班对开,一个班十一个小时,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夜班的另一个车间,有个女孩跟一个男孩恋爱,女孩怀孕了,男孩离开了工厂。女孩第一次出来,胆小,怀孕了也不敢做声。听说女孩把小孩生在厕所。那几天,拉线上都在谈论那个女工与生到厕所的小孩,有人说孩子被扫地阿姨捡了,送给了附近的人,有人说卖给了一个河源人,也有人说是潮州人,有人说小孩长得好,哭声大。那个女工听说被派出所带去问话了,没有再回工厂,有人说被派出所抓了,也有人说没脸待下去,离开了工厂。我刚进厂,常听到打工久的工友说起这类事,真实发生在身边时,我心里依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想起瘦弱的女工,想起可怜的孩子,想起宿舍厕所的环境,在那里分娩,我闷着头,对爱情有了惧怕。大家像流水,在流水线上流来流去,永无终点,在命运中流动着。李芳跟我说起那个女孩,她问我,为什么不去人流呢,她后来又说,谁敢独自去,又爱面子,不跟工友说,她叹了一口气。后来,我遇见很多这样悲伤的爱情,有的女工怀孕去黑诊所人流,刮宫未尽,剩下部分,只能再次去。半年后,我们拉线一个女工怀孕了,男朋友不是工厂的,在社会上混。后来,女孩自己去东坑医院做了手术,之后,离开了工厂,听说去了酒店。李芳1997年出来,她有丰富的打工经验,跟我是老乡,同一条拉线,同一个宿舍,她告诉我她遇到很多这类事,一定要保护自己。她说去酒店的女孩碰上了专门从流水线拐带漂亮女孩去从事色情行业的男人,很坏,要小心。她不会找外面的,要找在工厂做上一年左右的,这样的可靠。我刚出来,只是点头。
别人悲伤的爱情影响着流水线的工友们。但更多的幸福爱情,刘忠梅跟机修工在一起了,李芳告诉我,她跟男友商量好,过年前一个月,计划辞工,先去湖北,再从湖北坐车去四川,见见双方父母,她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机修工去商场买了糖,我们拉线上的工友每人得到四颗糖,谢芳接过糖,剥开糖纸,放在嘴里,一边插零件,一边大声说,喜糖比其他糖甜,大家笑了起来,我看见谢芳露出失落的神色,这个小姑娘盼望着爱情,在女多男少的流水线上,像她这样的姑娘,爱情又在哪里。
毛织厂
小镇有它的内在秩序,它连接混浊的记忆与时间,从它的街道、房屋、车站、小巷、工厂、轰鸣的机器、酒店、广告招牌等去辨认它今天的气质、繁华、喧嚣、凌乱,小镇在外表上更换着自己,它渐渐失去了往昔的宁静。我与小镇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味道,一个有着贫寒童年与少年的乡下女人,劳作让我的骨骼偏大,皮肤黝黑而粗糙。我从乡村走向城市,学会使用城市的化妆品和服饰等来遮住乡村的部分,粗大的指节泄露了我的秘密,突出的关节像利器剥去我的伪装。我骑自行车穿过小镇,来不及拆迁的村落、祠堂、带着庄稼印迹的老人等告诉我小镇往昔的光阴,有着温情味的农业小镇在我面前浮现。池塘、荔枝林、溪流、庄稼地……残存着旧日痕迹,我的房东,一位老妇人,不愿意跟儿女去商品楼盘居住,她生活在低矮的院落中,她告诉我,她不喜欢楼房,那里不接地气,她在荔枝林深处开了一块地,种丝瓜等。在小镇工业区生活的人,一群来自有着传统气息的乡村人,带着浓郁乡音的普通话,工业城市还没完全磨去他们属于乡村的细节,他们租下老人空荡荡的铁皮房。
小镇弥漫在针织的声音中。从竹园路到巷头路。从巷尾至毛织大道。织针的声音从四处散了过来。从狭小的楼梯口,从豁嘴张开的门面房,从宽阔的厂房。织,织,小镇像一个巨大的织机在织着,织着。嗡嗡的声音,从租住的宿舍,狭小的收银柜台,老式民房,油腻的机台,粗大的手指,疲倦的眼神……涌出。它们细小如白色线头,抽丝,再抽丝,细,更细,嗡嗡,当当,哼哼……在织机梭间穿行,十三针,八针,十六针……它们交织,混合,白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灰色的,绿色的,交错,重叠……它们织成布匹、衣物,覆盖着整个小镇。白色的线转动着。机器转动着。车轮转动着。工人转动着。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车轮。机器的齿轮。铝梭子轮。木梭子轮。整个小镇转动着。像一头头喘息的兽,吱—哧,哧—吱,不停地喘息。幽暗的褐黑色木楼,低矮的门扉似睁开的慵倦的眼睛,悬挂的白炽灯管无力地散发着疲倦的光,照亮一张张如落叶的面孔,荡漾的枯涩让转动的机器织进了毛线中,它们瞬间消逝,隐匿在线圈间。在道路上行走,我发现自己是一根毛线,越拉越细,被小镇拉着,被梭子拉着,被时间拉着,被梦想拉着,装在机台上,转动,来回转动,织进布匹,我与一群人,她们来自湖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她们和我。我和她们。挤着。织着。不安。烦躁。焦急。现实的梭子将我穿进生存狭小的针孔,在生活这台机器上转动,织成人生的布匹。这不是我设想的人生。印象中,我人生的布匹不该这么灰暗啊,但它将要织进小镇的布匹,我觉得自己身体有了纱线的味道,浓烈的化学染剂味,从开包的纱线浸入我的衣服、毛发、皮肤、肉体、骨头……不断积聚。我离开车间,独自沉思,它们沿着身体释放出来,我像一根纱线在机台与宿舍间抽动,曾有过的体温、梦想都被织进这个喧哗的小镇中。
我的机台靠近窗口,明亮与幽暗,现实与梦想,陈旧与新潮,沿沾着纱尘的窗口投影在机台,身体。低矮的小镇布满了织机,转动的声响犹若蜂群在耳畔,嗡嗡,嗡嗡,低低的,如小镇的节奏。转动的轮间,细线不停地穿梭。明亮细小的毛织线,陈旧而锈斑的机台,五彩的毛织布匹,树木旁的破旧屋舍,从黑色木质窗户朝外看的年轻女工,她们明亮的眼神将一扇扇老窗棂照亮。中年的毛织师傅,年轻的查补工,蓝色的工衣将她们裹在隐秘的世界。她们久坐,超负荷劳作,臀部肥大变形,长时间站立,小腿粗壮,散发出劳动者健康野蛮的气息。迷茫、幽暗、动荡、阴郁、躁动、不安、灰尘、呆滞……车间浮动的情绪扑向我。散乱的布匹,在毛绒、棉丝、麻线、呢绒……交错的空气中,弥漫着布匹洗涤液的味道,凝重而忧郁地塞满整个屋子,结成了一种看不见的黏稠物,在车间缓慢地晃荡,遍布各个角落,冲进嘴里、肺腔里、血液里,在体内流动。这幢四层旧楼房,一楼是门面与食堂,二、三楼是车间,四楼是宿舍。外墙裸露出红砖,锈蚀的窗栏、滴水的厕所,一股腥味弥漫在空气中,融入毛线布匹,水泥地,墙壁的涂料间。二楼六台织机,散乱的布匹,红色、蓝色、黑色、灰色的半成品与成品,在地上,在编织袋里。车间混杂着人的味道、浊气的味道、毛织散发出的洗涤液味道,一幅混浊的生存镜像图,构成了小镇内部的真相,农业的重浊的遍布汗水味的身体,工业的油腻的浓郁的化学涤剂味的半成品布匹,商业的精致典雅味的成品衣物,混合成小镇的气息。凌乱的车间里,我想起自己凌乱的人生,我拖着行李来到这里。我想象着东莞,整齐的城市,看得见的华丽与热烈,更多时候,城市给我的印象性感而冷艳,没有温度的霓虹灯,马赛克高楼,蓝色的玻璃镜面,来去匆匆,面无表情的行人。乡村是保守温情的,宽阔的田野,随意招展的树木,清澈而柔情的河流,充盈多汁的花朵。舅娘带我进入车间,一种荒凉的感觉靠近着我,冷漠而窒息,残酷而尖锐。我试图设想以后的生活,跟舅娘学缝盘技术,如她一样地坚守布匹中的人生,我有些沮丧。看着前面的女工,坐在机台旁,蜷缩着身子,像蒙眼的驴子围着阴暗的石磨转动,麻木而机械,走进来一个人,头都没有抬,浑然不知周围的一切。她额前的头发有些凌乱,灰黄,沾满了毛线绒,一小块一小块灰色的布匹停靠在头上,衣服上布满细绒灰,织机陈旧,布满发亮的污垢。
领班将我带到一个中年女工面前,告诉我,跟她学习缝盘。师傅四十多岁,湖北人,姓伍,1993年来这里,八年了。八年里她的生活被分解为一小块小块灰暗的毛线,凌乱的线团里,织机飞快地转动间,每月一千两百多块钱的工资让她成为称职的母亲、妻子,孝顺的女儿,她把生活坚实绵密地织进布匹中,运往遥远的地方,换成一张张或新或旧的纸币,从东莞寄到遥远的湖北乡下。师傅声音很小,走路很轻,生茧的手指沾满毛线绒。她脸色苍白,身体像塞满棉绒、毛绒,迟缓而闭塞,瘦弱而破败,像一块陈旧的老棉絮,沾满了时间溃败的痕迹。她朝我点了点头,坐在机台前教我分线、排针。来东莞前,她是湖北咸宁的一个普通农民,在家里种过多年地,重体力加上长期的劳动使她的手指有些变形,粗大的关节蕴藏的是力量,是健康,在握、抓、提中,在弯曲与伸展间,它们像土地充满丰盈的力量,我的跟她们的一样。工业的手指是纤细的,灵活的,精巧的,精确的,像工业制品一样充满灵性。后来多次,我去面试,要求伸出双手,他们来回检视着我的手指,让我做各种动作,观察我是否适合他们工厂的工位。进入车间,拉线管理员第一件事让我伸手,一遍遍盯着,再安排给我工位,装配细小的弹弓需纤细的手指,装配钢通可稍微大些,手掌大点、手指零活可以装配较大的零件……看到自己粗大的指节,好一阵难过。乡村的气息是迟缓的、坚韧的,一点一点在我的手上与骨骼上蚀上印痕,烙到我的内心,在异乡它再次展现出来。面对城市,我充满了自卑。
伍师傅带我来到机台边,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空气中浮动着毛绒,细小、蓬松,缓慢进入身体,它们是温柔的,置身其中,我感觉自己一点点在车间的毛绒灰尘里湮灭,一点点,如丝,如尘,从我的脚到膝到腹部到嘴鼻孔,缓慢进入到我的喉咙,肺,血管……它们在我的器官里驻扎,脸上通红,发烫,它们在我体内积聚,结合,拧成一根根丝线,捆住我的肺,让我透不过气来。它们越来越紧,我咳嗽,高烧,被看不见的毛绒线捆住。身体塞满了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小尘埃。它们聚集起来,形成蓬松的小团,拧成细的线。我拿碗舀起工厂食堂做的猪血汤,灰暗的汤里有腥的味道,我不喜欢吃猪内脏,不喜欢喝猪血,我对血有着本能敏感,每次吃饭,舅娘与伍师傅总对我说,要多喝点猪血汤,能润肺,能带走肺管的毛绒。说完咕咚喝下一大碗猪血汤,那些膨胀的、暗红的、布满小孔的猪血,犹若一张张嘴,将要吸走我身体积聚的毛绒,它们穿过我的血管、肺部,带走积聚在我身体的毛绒,还我一个干净的身体,没有被工业污染的身体。我又喝下一碗猪血汤,毛绒会随它一起,经肠道排出吗?
进去的第五天,我还是不停地咳,高烧,舅娘与伍师傅说,可能你不适应车间的气味。我病恹恹地坐在窗口,晨光下,那些毛绒尘,飞扬,盘旋,跑动,舞蹈,光影中,它们那样活跃,它们长满了腿,朝我扑过来。我被它们包围着,像夏日傍晚在乡村路边走时遇到的细小蚊蚋群,不咬人,却伺机钻进头发,嘴里,我咳嗽,烦闷,伸出手左右扇动,它们越来越多。这些比蚊蚋更小的毛绒尘,柔软而坚韧,它们的侵略让我无处可藏,我举手投降,它们依然不会停止侵袭,它们将我的呼吸湮没,将我的血液变得黏滞,不再流动,再将我一点点吞食掉,将我变成它们的一部分,我一点点溃败,再溃败,溃不成军。
伍师傅在我前面,四周都是织机转动的声音,嗡嗡—嗡—嗡——嗡嗡嗡——是针撞着针孔的声音,嚓吱——嚓——吱——嚓吱,是梭子来回转动的声音,伴随线圈不停抖动的声音。伍师傅见我不停咳嗽,安慰说,慢慢就会习惯,你身体弱,要多几天才会适应,她站在旁边教我一些简单的检查,锁眼不正时漏眼漏针、错漏模行、锁眼错行、走边不正、跳线、松线、混色、锄眼针路不对,等等。我记不住,照搬在学校的方式,用笔记下。伍师傅没读过书,这些专业术语的词不会写,她只不停跟我说这种是如何造成的不良品,那种又是啥原因的,她不善于表达,我听得稀里糊涂。她依靠经验处理问题,八年的打工经验,形成了她固有的职业习惯。面对各种不良品,我常常看不出问题,要么忘了检查这,或者检查那。我心里不停抱怨,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像学校一样把不良品的样板摆在那,对照学习。伍师傅会将我检查过的织品再检查一次,我心里满是愧疚。伍师傅不断安慰我,我带过十几个了,刚来都这样,需要经验与时间。伍师傅又自言自语,你们年轻人在这样的小作坊做不了多久,就会换厂。每次见到伍师傅,我都有一种复杂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来自于我的舅娘,多年相同的工位在她们身上留下太多印迹,她们柔软却坚韧,习惯了小镇的节奏,上班——加班,上班——加班,属于工业的另一种机器,跟机台的梭子一样来回运转着,像机器一样磨损、老化、报废……新的机器替代。长期加班,缺少睡眠,她显得有些衰老,身体折旧得厉害,脸色干枯,眼神疲惫,暗淡无光。平常老板安排加班两个小时,她选择加班更久,她不像年轻人关心有没有假期,她更关心老板有没有货,每次老板发货,她尽可能领多点,为完成任务,她不停加班,常工作到深夜,节假日,也选择待在工厂加班。这些年,我遇到无数这样的中年女工,出没在我身边,三十五六岁,现在看来年纪不大,但在2001年,已经很老了,招工启事上要求的年龄女性十八—二十八岁,她们已被工业这台榨汁机榨干了汁液,剩下残渣,将被抛弃。她们的字典里,没有累,像永不疲倦的机器,不停运转。习惯了,慢慢你就会习惯,做多了就习惯了,她们如此说。
我终就无法习惯毛织厂的味道,我对气味天然敏感,咳,再咳,高烧,发烫,我请假,走进车间又发作,那些声音那些毛绒似乎在跟我作对,轻易便将我击垮。我无力地坐在机器边,蜷缩起身体,承受疾病带来的挫败。半个月,我生病,请了三天假,老板觉得太多,让我收拾行李,走人!
责任编辑 谷 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