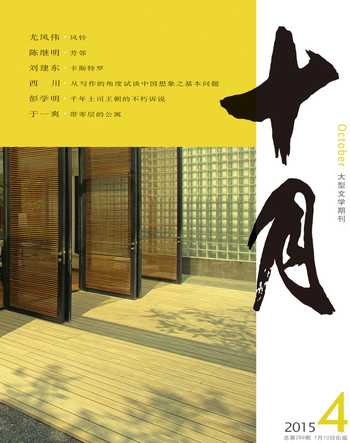三人食
于一爽
杨天给我打电话,电话里说自己要离婚了。我说就这些?杨天说就这些。我说然后呢?杨天说喝点儿。我没说是因为自己也想喝点儿。我是一个没有心事的人,没有心事的人为什么要喝点儿呢?我又没离婚。我应该结婚。
杨天总喜欢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当已经不能从这种关系里面得到快感的时候就应该马上结婚。(难道她以为结婚之后就会重新得到快感?)看看别人的生活,我就总是没有愿望生活了。事实上也没有那种机会。另外,这种关系当然是指男女关系。
杨天住在一个小院子里,院子里有棵枣树,看上去快死了。她说真的快死了。我说怎么办,她说等它死。其实在她这种年龄,离婚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事。难道让男人爱她们一生一世?她们凭什么让男人爱一生一世呢?这不是赤裸裸的绑架嘛!她都这么老了,快绝经了吧我想。我们认识三四年了,我三十岁,她四十岁。我是说三四年前,所以她现在真的快绝经了。我们并不十分熟,至少比起那种无话不谈的女朋友来说,她为什么叫我来呢?她大概只是想找人喝点儿。坐在那棵快死等死的枣树下面,我问她——你有几个离婚证了?
她说——俩。她又说——半年前。
接着我说——那你这半年有性生活吗?
枣树上零星点缀的几个枣掉了一两个在地上。7月份正是枣树结果的时候,可是她的枣树奄奄一息。
喝什么?杨天问我。我说有什么?她说喝什么有什么。我说有男人喝吗?她说要去冰箱看看。两分钟之后,我们两个人手里分别握着一瓶啤酒。她说像不像?我说像。
就像握住一个男人。
杨天喝得很快,一口就下去大半瓶,于是她把瓶子在手上晃来晃去,给我造成了一种十分眩晕的效果。
她的第一个男人很快就被喝完了。现在酒瓶可以用来砸人了。她说。
我说——去砸你前夫吧。
杨天一下子没有了力量。
后来的时间,我们聊这个聊那个,她说——你瘦了。
(我是多么讨厌或者说恶心,女人之间的这种话题啊)我摸了摸刚被啤酒胀满的肚皮说——有吗?然后我又把肚皮缩了回去。
但是杨天真的比半年前胖了。
我说——你倒是没怎么变呀。
她说——不会吧。
我说——真的。
她说——离婚的女人都会变胖。
我说——看来你真的没性生活。
于是我们又喝了第二瓶。我慢慢开心起来。
一阵微风吹过,又一个枣掉了下来,正好掉在枣树旁边的小池塘里,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池塘,甚至都不能称作池塘,里面有些脏水,这会儿我们的头顶就是蓝天白云,但是池塘完全没有办法呈现出全部的倒影。我说——你该换水了。
杨天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住这了。
我说——哦,忘了,你要搬家了。
她说出这句之后,就好像她已经不住这了,我开始环顾四周,枣树旁边还有一棵圣诞树,塑料的,看上去傻乎乎的,才7月份,离圣诞节还很遥远,离上一个圣诞节也已很遥远。圣诞树上面还有风铃,钥匙挂件,发光小星星,圣诞老人铃铛,一阵微风吹过,铃铛就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用手使劲摇摆了一下铃铛说——那你以后住哪儿?铃铛的声音还有细微的醉意不可避免地向四处流淌。杨天用手把铃铛突然按住,凑过来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因为她说这句的时候离我实在太近了,于是她的满嘴酒气扑面而来,不光酒气,还有她脸上的细纹,虽然她今天精心化了妆,可还是被我一眼识破。因为她离我太近,以至于我很容易想到一个事实——再过几年,她的皱纹就会像被狂风吹皱的水面一样了。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们面前的池塘,池塘里的脏水,竟然动了起来,起风了。
我想起去年圣诞节,就是在这个小院子,还有她的前夫,还有我,我的朋友,杨天的朋友,前夫的朋友,圣诞树就是那会儿留下来的。好像时间就这么结束了。
杨天说——进屋坐吧,天气预报说下午有雨。她说这句的时候,整个人又离远了。我说——下起来再进去。我就是这种人,总是愿意等待事情真正地发生。
一丝凉爽出现在这个7月的闷热的午后,我也开始觉得坐在这里并不是十分浪费时间了。
算了,杨天说,这种事能赖谁呢。
我说,你这怎么还留着圣诞树?
但是她完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了就不想回答。如果她不回答我就不会再问,这么多年,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追问杨天。我们继续喝酒。杨天缩成一团,下巴贴在膝盖上,看上去成了垂头丧气的模糊的一团。夏天已经到了,光和热交织在一起,虚幻不实。
就是这样,她坐在我对面,嘴一动一动,跟我说了一些她的生活,还有工作,我听出来了,单位里有个男人喜欢她。(如果她不离婚也会一直喜欢她的意思)刚离婚就这么婊了,我想。可我还被她的话吸进去,她也被自己的话吸进去。完全罔顾这些话是否会伤害我的事实。我比她年轻大概十岁,可是追求她的男人是那么的多。不管她的脸上有没有细纹,重点是,她有胸。我和杨天中间隔了一个酒杯的距离。这已经不是最开始的位置了。我发现:她的胸还是很大。并没有因为缺乏性生活的半年而缩小,以至于有一块儿已经跑到了腋下。可是一般女人连跑到腋下的资格都没有。胸会改变一个女人的实质,我不由得得出这种结论。
后来她就突然哭了,啤酒又被喝完了一瓶。我也想哭,可是我没伤心的事怎么也哭不出来,我既不被别人爱也没有爱别人,这是一种持久的伤心,说实话我都习惯了,已经变成了身体里的一颗痦子之类的小玩意儿。
于是这样一来,她的哭就更让我烦躁,雨水和眼泪一起往下掉。雨水噼噼啪啪落在池塘里,眼泪哭花了妆。枣树也被弄湿了。
该进屋了。我说着就站了起来,像一个失望的将军在发号施令,自然,没有人听,杨天整个人被雨淋湿了之后,才开始缓慢往屋里走。
我怀孕了。进屋之后杨天低声对我说,非常低的声,以至于,雨声再大一些的话我就听不到了。我多么希望雨声再大一些啊,我为什么不能有听不见的权利呢?重点是她四十岁了,真是医学的奇迹。她根本不是半年没有性生活,我不由得得出这种结论。我怎么会相信呢,刚才,我真是一个天真的人。
别同情我,她接着说。
我差点儿以为自己听错了,我说我不同情你。但是你能别喝了吗?我把她手里的瓶子拿过来,然后她就开始吐,好像在故意用一种早孕的反应让我更为难堪。我又说了一遍我不同情你。这么说是因为我真的没有骗她。因为我真的不同情她。我同情自己还来不及呢,我比她年轻至少十岁,我比她距离更年期的时间更长,我没有细纹,我有少女一样的平胸,我甚至可以陪别人一醉方休,然后什么要求也不提,我都快被自己的善良打动了。可我为什么没有她这么多的爱情呢,哪怕因为爱情造成的哭泣,就像现在一样,也都是我羡慕的。我也想有两个离婚证,我觉得杨天太自私了,因为自私所以得到了全部。虽然事实上是因为胸于是得到了全部。以至于我现在特别想逃跑,到一个听不见她哭的地方。还有她怀孕这个事实,她竟然敢怀孕。她是故意气我吧。我有这么重要吗让她故意气我。
声音越来越大,哭声混合着雨声。很久之后她才平静下来。杨天把头重新抬起来的时候,我真担心她把自己的眼泪包括鼻涕一起吃进去。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和她之间还是隔了一个酒杯的距离,雨水落在房顶上,我把酒杯拿起来,透过玻璃看刚刚哭过的杨天,我想到一个词——梨花带雨。她这个人总是夹杂着很多的爱恨情仇,难怪她在市场上占尽优势。我就算再活十年,也没有办法超过她,我和她是阿基里斯与龟,差距是确定的。
谁的孩子,我认识吗?我们两个人重新“咕咚咕咚”喝起来,她一定是流了太多眼泪的缘故。我都能听到她“咕咚咕咚”的声音仿佛正在给一块贫瘠的土地补充水分。给人一种性欲依然旺盛的感觉。
我老公的。她说。
我保证,并不是所有人都听到过这几个字。
我问——谁?
她说——我老公的,是的,离婚了虽然。
我控制着自己的惊讶,因为我的惊讶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烈,我干脆说,嘿,从前夫变炮友了。
杨天说——半年了,上个月见面,他给我送钱来,他以后住这,我走。
剩下的话她还没说完,我就急急忙忙警告她——别走,走了就亏了。(我就差点儿说——你总得有个家吧)
这房子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男的买房。女的拿钱。
杨天说——我就是要让他对不起我。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给人一种咬紧牙关的感觉。
他拿了房子还把你操了,我说——孩子你要吗?
不要。她说得很坚定,房间空调的冷气吹出来,外面下着雨,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凉爽起来了。
杨天叹了口气,又叹了口气,叹了很多口气之后就不再说话了,好像刚刚做过流产手术,十分虚弱。我不知道说什么,趴在桌子上竟然就这么睡着了。我也累了。
醒来的时候,杨天正在屋子离我最远的地方打电话,我们构成了屋子中间的对角线。冷气把杨天的裙子吹起来了。她看上去还是十分苗条,虽然比之前胖了,可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孕妇,我伸了伸腰,桌上还有剩的酒,泡沫已经消失了。她都没有发现我醒来。
杨天又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之后,把头转过来,冲我做了一个意义不明的表情。
你还爱他吗?我整个人突然精神百倍地说。声音顺着对角线传过去。
我们离婚是因为他不爱我了。
别这么。我说,所以你们就又上床了?
是他要求的。
对啊,这种事情,对男的来说,免费的都好,前任的好处彰显无遗了,彼此熟悉身体,还没有负担,只要你不拒绝,更何况你还爱着,他伸伸小拇指你就会像狗一样爬过来。我接着说,你们就这么在这个院子里谈判的时候,突然操上了?就是这个屋子,就是这个位置?或者院子里,把枣树都给摇光了?
说完这些之后我很吃惊,这种吃惊主要是对自己的。我从来没有这么对杨天说过话,她是这么优秀的女人,被男人爱,虽然不年轻了,但是不年轻才更有过人之处。我凭什么这么说,于是整个人又躲进了喝酒的姿势里。
杨天从对角线里走过来说,我就是怕她不爱我,我就是要让他欠我的,房子算什么,如果不离,他是不会爱我了,我们生活一年,一百年都一个样儿,他都不会再爱我了。
那你知道他爱上谁了?我问,
有女人被他迷住一点儿也不奇怪啊。杨天说这句的时候,口气很让人失望,尤其是那个语气助词(啊),好像她的老公只是被人迷住,而依然被她牢牢掌握在手里一样。
我们两个人的酒意等待挥发。我已经不想再坐下去了,快黄昏,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我大概睡了很久,太阳抹过西面墙头。
你是不是希望我把孩子做掉?我刚才给医生打了电话。
我靠在椅子上,杨天走过来,在我头顶的位置,声音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我又被吸了进去。
我哼了一声。她这句话把我吓坏了。
你别吓我,这种事儿我可没经验。呵呵。另外……他知道吗?说完这句之后,我把头抬起来和杨天的目光对视。她的目光很模糊,也许是衰老的前兆,我突然觉得自己问得残酷而且感觉非常害怕,我不等杨天回答,就接着说——还有吗,在哪儿,我去拿。
我当然是指酒。
我们就是这么喝了一杯又一杯,然后干上的。杨天说。
是在厨房吗?我一边往厨房走一边问,她的声音在后面一直说个没完没了,我真想把自己的耳朵用刀子切下来。
他本来是过来商量房子的事,我们都离婚这么久了,几个月了,他可能,一定早就被别的女人吸引了,不对,应该是别的女人早就被他吸引了,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我已经自己走到了厨房,但是冰箱里什么也没有了,杨天看来真的要搬走了。我一个人靠在灶台上,还有她上一顿吃剩的方便面,面桶里结了一层红油,她甚至都懒得拿一个碗。我拿起来闻了闻,很厌恶地放下了。十分酸辣。厨房很乱,刀整整齐齐地插在刀架上,一共三把,从大到小,小的用来切水果,大的用来切肉,中的可以切菜。理论上是的,但谁会这么做呢?
我看着方便面和刀构成的奇怪画面,感到十分振奋,我甚至在很短一瞬间想到——不会是因为我吧。
虽然我和杨天老公是上过一两次床,不止一两次,可能有三四次呢,但总不会是因为感情吧。事情就发生在圣诞节之后,而且发生得很快,杨天得到了那么多,怎么会在乎一个老公呢,可他们怎么就离婚了呢,不会是因为我吧。我这样想着,想到自己如果当时的表现更出色一点,搞不好他们真的会因为我离婚,可我也只是这么想想。
别找了,没有了,杨天的声音从远到近,她跟着过来了。我吓了一跳,我跟自己说——不是我干的(要是我干的,我会对自己更满意,事实上。可是我哪儿有这种能力呢,或者说,魄力)。
就是这个位置,她用手使劲拍了拍我正靠住的灶台,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在这儿干的。
但我并没有因为联想而躲开,我用后背在灶台上轻轻蹭了几下,说——我都猜错了,既不是在屋子里,也不是在院子里,你也太不讲究了。枣树下面多好,还有一池塘脏水。
杨天用右手在其实很难看出来的肚子上揉了几圈,就像另外一只手在揉,突然,这只运动的手停住,放在了我的肚子上,这带给我的并不是吃惊,而是我害怕痒,竟然笑了起来,但是一点儿也不痒,可我停不下来地笑,我一边笑一边说——杨天,把你的手拿开。你吓着我了。
可是她并没有拿开,还突然,把手移动到我胸口的位置,或者是胸的位置,但是我的胸太小了,所以她根本感觉不到。
是这儿吗?
杨天用一只手捂住说,他就是这样捂住你的胸,你的平胸?
接着,她爽朗地笑了起来,混合着苦楚,就把手挪开了,我用双手撑住灶台,调整呼吸,然后突然抓住杨天的两只手,放在我的胸上,告诉她——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捂住我的平胸,你说得没错,不过是两只手。
杨天迟疑了很短时间之后,突然把手抽回来,猛烈拍打自己的肚子,我让她别骗自己了,可是她拍打得更猛烈,把手攥成一个拳头,使劲地捶起来。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报复他?我告诉杨天这个事实,但并没有阻止她。(还有后半句我没有说出口,我想告诉她——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羞辱我?)
她停止了拍打,突然用手捂住肚子,从拧起来的眉毛上能看出正在经历一阵绞痛。之后突然开始尖叫,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什么事情,她把刀架上的刀也给打翻了,分别落在了地上,三把刀竟然隔着相等的距离。
没有人想把它们捡起来。它们就这样落在地上,很好,竟然隔着相等的距离。我和杨天同时注意到了。
他不爱你了。我说,当然,他也不爱我,你知道,你老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叫我过来,就是告诉我这个?
说这些的时候,我始终没有离开灶台,一个月前,他们就在同样的位置做爱了。我把双臂展开,我想象杨天就是这样,用来支撑身体的力量。
就像吸引她一样,她的前夫也总是可以靠同样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女人,更别说我这种一般货色了,他爱我或者不爱我都不是事情的关键,关键是,有一个男人愿意和我通奸?我想到的是通奸这个词,竟然就已经感恩戴德了。但,我必须让自己做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因为我的原因,绝对不是。而是因为杨天太蠢了,真的,太蠢了,这能赖我吗,如今她还怀孕了,胸大的女人都蠢,我想。我又看了一眼自己扁平的胸,王凡随时可以因为这件事抛弃我,我对他们离婚这种事很遗憾,但,这和我毫无关系,我十分确定,就像这会儿如果天上掉下一架飞机,也和我毫无关系一样。
我倒是想他因为我离婚呢,我说,不过我也就是这么想想。
我只是用来满足王凡偶尔喜欢一个平胸女人的特殊嗜好而已,我突然开始觉得委屈了。
我们到底算不算朋友,杨天突然问我,她问得十分搞笑,就像香港电影里义薄云天的两个人。
我很想告诉他,我没有朋友,
我想起王凡发泄的时候总喜欢摁住女人的头,如果在这个灶台摁下去,杨天的脑袋可能早就烧着了。他们竟然还敢有孩子。我用手紧紧捏住那盒杨天吃剩的方便面,里面的汁水涌出来,涌得四周都是,我用沾满油污的手一把推开杨天,她像一张纸一样,很轻松地就被我推倒了,她整个人整整齐齐地坐在三把刀子上,我回头看了一眼,看上去,她毫发无损,我迅速往院子跑去,拿上外套,我只是想离开。几个小时前坐过的院子被雨水打得很湿,还有几个空酒瓶。
只是刚刚走出院子,我就听见一声刺耳的尖叫。最终我还是给王凡发了短信,告诉他——杨天怀孕了。
我等他回我短信,站在院子外面,四周人来人往,匆匆赶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圣诞节之后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我还觉得这是杨天应该给我的呢,她已经得到了这么多,可是我比她更年轻。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
就这样,我想等他回我短信再离开,但是他迟迟没有回我短信。我就坐在院子门外的台阶上,院子里面很安静,无法想象还有一个崩溃的女人,或者说,她正在酝酿崩溃的迷人气质。大概十几分钟之后,他的短信才过来,很简单——三个字——知道了。
接下来轮到我了,我应该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呢,是因为我刚刚告诉了他,于是他知道了?还是他早就知道了?而这样一来,我这句话就显得多此一举,我有资格关心别人的家庭吗,当然没资格,而我以为拿走了杨天的东西,我只是想试试这种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良好。我应该继续坐在这个台阶上等他吗?等他来?等他们破镜重圆,然后我也应该十分知趣儿地得到他们的宽恕,继续努力寻找自己的爱情,而不要再成为别人婚姻的绊脚石?或者,就干脆一走了之,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我这样想着,刚才方便面里的汁水还在手上,已经风干了,味道十分强烈,我竟然舔了两口。
很快,王凡的第二条短信过来了——他说——你别走。
他总是喜欢三个字。三个字代表简单粗暴,他就是靠简单粗暴得手的。简单粗暴的好处是,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恨自己。
于是我只能重新坐在台阶上,太无聊了,我竟然开始回味起这三个字——你别走。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前后语境里,这三个字是多么的美好啊。他竟然跟我说——你别走。
之前,他说得最多的是——你来,你别来。或者我去,我不去。
他大概从来没有请求过谁,更别说请求过我了。
你别走。我学着王凡的语气说了几遍,越说越像,我天生具备这种卓越的模仿能力,我被自己的能力惊呆了,我为什么要具有这种能力呢,它又不能让我得到爱情,也就更不能得到和爱情一样重要的理解了。
王凡过来的时候已经快晚上了,可我竟然从来没有这么早见过他,我十分吃惊,他甚至称得上风尘仆仆,这我就更吃惊了,我开始后悔给他发的短信了。
人呢?
他就像没有看见我,或者说,看见了,但我起码不是他现在,此时此刻,最希望看见的。我只是一个路人甲,告诉她——真正伤亡的人在哪儿。但难道是我让他看见的吗?明明是他让我别走。我要是能立马消失多好啊,我突然成了两个藕断丝连的人的障碍。我从台阶上站起来,坐了太久,站起的时候重心不平衡,王凡看见了,并且扶住了我,如果他不扶住我,事情就简单了,我总是容易产生这种错觉,他凭什么扶住我呢?大概我也不是一点都不重要吧。
扶住我之后,他又重新变得严肃起来了,用手使劲捏住我的肩胛骨说——你怎么在这儿?
啊?他竟然问我你怎么在这儿?
难道我应该告诉他——因为我预感到了整个下午,甚至预感到了从圣诞节到今天的全部狗血剧情,所以我就在这儿了?
我把他的手拿下来说——她在厨房,你快过去吧。
希望她这会儿还在厨房。
王凡走路的步子很大,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上。这正是我们希望的。
杨天真的还在厨房。看上去要躺一个世纪。
和刚才没有任何区别,整个人躺在三把刀子上,脸侧过来贴着地面,不难看出她对这个姿势十分满意,几缕头发盖住了眼睛,胸堆在地面上,她并没有喝多,也没有睡着,更没有死去,她现在还缺乏死去的动力,想到她肚子里的孩子,我竟然想到了“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种语录。她就这么躺着,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安详的。
王凡过去抱起她,她轻轻一抱就起来了。杨天有一种本领,或者说是天赋——她竟然能把自己变成一张纸片。她整个人垂在王凡的怀里,看上去十分无辜,我站在厨房的门口,就像另外一棵枣树,一动不动。树上的枣已经掉得差不多了。
这之后,我走进厨房,将三把刀捡起来,整整齐齐地插回刀架里。最大的那把十分钝,我用手摸了摸,甚至有了一种冲动,但是旋即就消散了。也许杨天从来不用它切肉。除了方便面,也许她什么都不想做,不会做。她只是一个胸大的女人,大到无法承受男人和她离婚的事实。而她竟然以为这个事实的全部原因是我,我实在受宠若惊。王凡和我干的时候就已经不爱她了,如果爱她怎么会挑她的朋友,就算我们不是那么好的朋友,所以这种事怎么能赖我。虽然我嫉妒过她,嫉妒她跟一个不错的男人生活了很多年,但是这算什么呢。这又不是爱。
我恍恍惚惚走到冰箱前面,啤酒已经全被喝光了,还有几个鸡蛋,白的而不是黄的,看来她连鸡蛋都不会买。(我不由得同情起这个女人)我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碗,把鸡蛋全部敲碎在里面,找不到筷子,就用方便面里的叉子,刚刚掉在了地上,被我重新捡起来冲洗干净,然后拼命地搅拌,蛋黄和蛋白全部融合在一起,我的手快速旋转,这种事情我十分在行,王凡总是夜里过来(在他有限过来的那几次,杨天一定以为他在彻夜加班为家里奔波),如果他肚子饿,我就会给他摊上几个鸡蛋,我感觉自己的双手变成了某种不受大脑控制的旋转的机器,我整个人都欢快起来了,我心安理得地遵循这种机械的动作。必要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哼唱出一首轻松的歌曲。蛋液在离碗几寸高的地方翻飞。我把煤气点开,点了很多次才开,往平底锅里倒油,少许,热了之后就把蛋液全部倒进去了,不断膨胀,他们竟然能在这个地方做爱,我把煎好的一面翻过去,很快,另一面也煎好了,这种事情有什么难的。可惜他们家没有葱花(是的。我当时脑海中想的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是一个和我无关的地方,而我只是过来摊鸡蛋的。看着金黄均匀的鸡蛋饼,我甚至愿意把他们家的厨房打扫一新。
你还真有心情。王凡突然靠在门边问我,他只是那么靠着,而不是走过来,像抱住一张纸一样地抱住我。
我把鸡蛋饼摆在盘子里,端在他的眼前,鼻子的前面,和嘴的前面,最后,我拿着鸡蛋饼,从他双臂和门之间的空隙里,走开了。
我一直往前走,我发现我对这里其实是十分熟悉的,穿过院子,进到屋子里,杨天完全醒了,坐在我刚刚坐过的椅子上。胸放在桌子上,用一只手把两只眼睛捂住。我不知道她是哭还是笑。但是她的胸再一次吸引了我,这也不能怪王凡,就算离婚了,他也不用抗拒诱惑,他也不能抗拒诱惑。一个女人的胸是独立于一个女人存在的。也许他只是在厨房摸了她的胸,于是她就怀孕了。而我的胸就像这盘摊鸡蛋。我把盘子放在杨天面前,如果她还没有丧失味觉的话,必然赞叹我的手艺。
这个世界上并不缺乏会摊鸡蛋的女人,王凡也不是为了夜里吃上这个去敲我房间的门。但我竟然为她做了一盘摊鸡蛋,现在,此时此刻,这一时刻比得起世界上,古往今来的,全部的,酸甜苦辣的摊鸡蛋。摊鸡蛋在桌子上袅袅地冒着热气,这多像一家人的晚餐中的一部分啊。
好香呢。
王凡走过来,拿了一瓶酒,真不知道他从哪儿变出了一瓶酒,这毕竟是他的家,我用一只手按住另外一只手,这样我才不会把整个盘子扔在他的脸上。有吃的有喝的,他还真是一样不落下。
房间里十分安静,只有一个男人喝啤酒的声音,喝得十分迅速,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追上我们一个下午的成绩。杨天已经被声音吵醒了,把手从脸上挪开,妆更花了,连着她的大胸,看上去十分风尘,我都快被感动了,有了拯救她的愿望,比起一个风尘女子的失魂落魄,我的喜怒哀乐实在不值一提啊。
这之后,杨天从椅子上站起来,也往厨房的方向走去。我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没多会儿,她竟然拿了三副碗筷出来,叮叮当当的声音一定是洗刷的声音,碗筷十分干净,纯白色的,就像在闪闪发光。她还拿了那把大号的刀,刀架在碗筷上面,就被她这样郑重其事地拿出来了。她竟然是用自己的双手洗涮的。并且也是从王凡双臂和门之间的空隙里钻出来。
重新坐回刚才的位置之后,杨天用刀在鸡蛋饼上比画了几下,横几下又竖几下,可惜鸡蛋饼无法切成均匀的三块。她想了想就从中间切开,把其中的一块放在盘子里,推到我面前。切得十分准确而且凶残。
既然推到我面前,我就非吃不可了。杨天递过来一双筷子,我在桌子上把它敲打整齐。从半圆形鸡蛋饼的边上戳下一块,当着他们夫妻的面,我就这么吃了下去。至少他们做过夫妻。
只是这会儿,王凡突然走过来,把我盘子里剩下的鸡蛋饼全部塞进嘴里,他正塞着,一口又一口,杨天也完全无视自己盘子里的,竟然开始抢我手上的,抢王凡手上的,抢掉在地上的。
香喷喷的一张鸡蛋饼就这样没有了。
吃够了没有,王凡突然在屋子中间开始骂人,吃够了没有,够了没有。
他的声音十分简单粗暴,这就是他唯一吸引我的地方,如果说他有什么地方吸引我的话。但我还是被吓坏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我够了没有。
但是我可以告诉他我吃够了没有,当然没有,肯定没有,但,如果说,他们这个家还有什么可吃的话,那只能是院子里的那几个烂枣了。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