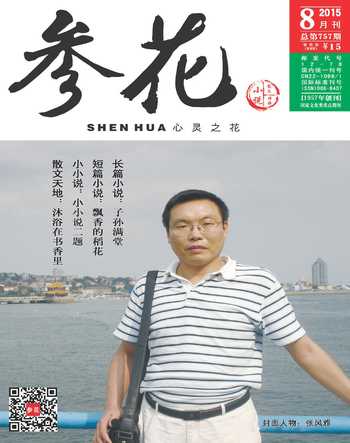飘香的稻花
◎吕维彬
飘香的稻花
◎吕维彬
1
稻花村居住六十多户人家,村后有一条小河儿,这条小河儿是当地人的母亲河。
顺子打小儿就和小玩伴在村后的小河边儿嬉戏。
卷着漩涡流淌的小河儿水,水纹泛着波光,清澈透底。也许这条小河儿在千千万万条名江秀川中,连个名分都没有,如果不是当地人把它捧在心里,外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许多地方像这样的小河儿,绝大多数都已干涸,成为名副其实的干沟子。而稻花村后这条小河儿虽然不是很深,但河里的水流湍急,撞击在河底里裸露的石头和一簇簇水草上,一个劲儿地发出哗哗的声响。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一刻也不停歇,不间断地流着,淌着,听上去缠绵柔婉,清脆纯心。
这天,是星期日,阳光暴烈。
顺子和小玩伴来到小河边儿,手拿着吃空的罐头瓶子,脱掉鞋子,高高地挽起裤脚儿,飞身跳进小河儿里,弓着腰,不错眼珠儿地瞄着水里乱钻的小鱼儿。顺着小鱼儿漂游的影子,看准了,不管能不能捉住,上去就是一把,伴着脚下涓涓的河水,噗通一声,一个大大的水花溅湿了全身。小玩伴忙活了半天,无获而收,谁也没有抓住滑溜溜的小鱼儿,骂骂咧咧地嘲讽对方,争强好胜地相互埋怨。
瘦大个扯着脖子喊:“看你笨得像个猪,你乱扑腾啥啊?我都快抓到了,让你把鱼给吓跑了。”
“你别拉不出屎,怨地球没吸引力,是你刚才撅着腚,放个又臭又响的屁,熏得鱼都不敢过来了,你还怨我?”小胖墩回击说。
小玩伴抓不到鱼,迁怒于同伴儿,双手挖着小河儿里的水,互相扬着,发泄着快乐之余的郁闷。然后灰突突地甩着胳膊,趟着水,懊丧地上了岸。一边嘟嘟囔囔继续骂着,一边转移了游戏战场。在小河岸边儿,有的捉着蜻蜓,有的撵着蝴蝶。他们时而蹲下,双手捧着下巴颏儿,歪着脑袋,好奇地仔细观赏蜻蜓和蝴蝶飞的姿态。
顺子没有参加他们的斗嘴,蔫蔫地站在小河儿里,任凭河水对自己下肢的冲刷,不动声色地看着小河儿里流着的水,盯着若隐若现的小鱼儿,听着小玩伴的争斗,他没有怨天尤人,可心里堵着气,也不是个滋味儿。河里的小鱼儿比手指大不了多少,两只眼睛那么点儿,连一条腿儿都没长,竟然那么贼,溜得倒是挺快。这么小的东西,人比小鱼儿的体积大这么多,却连个鱼毛儿都没沾着,真是好奇怪,太邪性了。
蜿蜒的小河儿绕着顺子住的大半个村子。
河床上的草,吐着草香,紧紧地贴着地皮,安静地趴着,吮吸着水分,呼吸着空气。这些草的叶子,叠拧在一起,仿佛人工精心编织的墨绿色地毯,严严实实覆盖在地上。草垫子上,高低错落地开着笑嘻嘻的小花儿,黄的,紫的,白的,各色的花儿,借力于甜甜的风丝儿,微微地抖着花瓣儿。
小河儿两岸,一边是稻花村农民歇居的房子,一边是天工造就的一马平川的田野,金黄的稻田一望无际。稻子的秸秆晃晃悠悠的,举着厚厚实实的稻穗儿,在微风的吹拂下鼓着稻浪,掀起层层波澜,飘过去,又甩回来,稻穗在一起摩擦着,碰撞着,摇得沙沙作响。
顺子家,三间砖瓦大房,紧靠小河边儿。打开家里的后窗,河面上,铺着亮晶晶的太阳光,含着小河儿湿漉漉的气息,裹着稻花散发的芳香,沁人心扉,闻香自醉。
稻花村的农民,靠这条小河儿的滋润,依仗源源不断的水资源,引用小河儿里的水,灌田育稻,滋补农田,浇灌着生活,养育全村的人。
农民离不开耕地。不管耕地是肥沃,还是贫瘠,是水田,还是旱田,都是他们的赚钱之源,也是他们的生存之本。
从春天开始,稻花村的农民走出家门,在地里堆着“口字型”的格子,忙忙碌碌地整地,灌田,育苗,然后就是插秧,施肥,再然后就是收割,卖粮。一年一季庄稼,一个周期下来就是一年。说是一年的农活,实际上一年十二个月,农民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在地里操持着农耕,这样循环往复的生活,也算自在清幽。
2
顺子的父亲叫永福,四十刚出头儿,体壮如牛的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永福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三个姐姐相继出嫁,他不到二十岁,就开始顶门过日子。在村子里,永福眼瞅着别人家,男人带着女人,女人领着孩子,热热闹闹地忙着家里的杂事儿,自己总觉得家里缺点什么,空落落的,没个生气劲儿。
直到有一天,也就是永福母亲离开人世不久的那年,杏花来到了稻花村。杏花是她的乳名,这样叫久了,大伙儿都称她杏花。自从杏花踏进了永福家的门槛儿,家里才有了活分气儿。家中的话题多了,笑声多了,与邻里乡亲走动的机会也多了,给这个沉寂而淡漠的家,增添了快乐的气息。村里所有的人都放出了艳羡的目光,啧啧夸赞永福命好,娶了个明事理的贤惠媳妇。
杏花脑瓜儿好使,眼界开阔,点子也多。从她第一天到稻花村起,就深深被这个稻米之乡所吸引,感觉这是一个宜居而且是充满希望的好地方,眼见着稻花村地多水足,出了家门儿,没几步远,就是大片的稻田地。
杏花琢磨:生活在这样的风水宝地,怎么还能守着金山富不起来呢?应该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把地里的黄金捡回来,否则岂不是辜负了上苍的恩赐。
于是杏花就和永福商量说:“咱农民要想过上好日子,奔向富日子,就得把脚踩在地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种水稻,家能富爆。”
永福说:“你说的倒是不错,多种水稻是个好事儿,上嘴唇儿,搭着下嘴唇儿,说起来容易,钱呢?地底子钱从哪出啊?这年头儿,没钱是玩儿不转转的啊!”
“人家城里人,买车买房子都先贷款,咱们要想富,就是不贷款,也得敢拉饥荒,舍不出孩子套不住狼,你要是同意,我去张罗钱,管我同学先借点儿,卖了水稻再还他们。”杏花信心满满地说。
永福说:“这个家,你说了算,你说咋办就咋办。”
杏花没让永福失望。
家里种上了一百八十亩稻田,有永福自家的承包地,也有包种乡邻的水田,每年收入不少,家境混得过去,说不上大富大贵,年吃年用后,还有了一大部分存钱。
顺子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但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也不一样。家里人视他为至宝,从小娇生惯养,生活在蜜罐里,没跟着家人吃过大苦。
顺子八岁那年,一个火热的天儿,顺子的母亲杏花离家出走了,抛下了顺子和顺子的父亲永福。
那天早上,顺子刚睁开眼睛,就听见母亲和父亲在争吵。顺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过父亲和母亲吵得这么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父亲骂母亲是勾人的狐狸精,是个野娘们儿,说母亲是狗改不了吃屎。母亲委屈地哭着,回击父亲没良心,日子过好了烧的,像个土鳖,说父亲二虎吧唧的,就是个血口喷人的大混蛋。接着,父亲“爹长妈短”地大骂,全是一大堆不堪入耳的脏话。吵骂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是歇斯底里,然后就是噼里啪啦地摔着东西。顺子光着脚,穿着短裤,战战兢兢地趴在母亲和父亲住屋的门口,看着屋地上打破的暖瓶,到处都是破碎茶杯的玻璃碴子,还有他那唯一心爱的电动玩具小汽车,也被摔得七零八落。眼前乱七八糟的,一片狼藉。当时,顺子还不谙世事,不明白大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和母亲的吵骂,对顺子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事儿,他不知道这场恶战是个什么性质。过了一会儿,母亲不说话了,只是“咿咿呀呀”地哭,哭得像个泪人儿,一件一件从衣柜里往外倒腾着衣服,胡乱装在一个三角布兜里。
顺子眼睁睁瞅着母亲踉踉跄跄踏出了屋子,头也不回,抹着眼泪,一溜烟地小跑儿,跨过了村后那条小河儿上的木板桥。
永福坐在炕沿上,阴沉着脸,喘着粗气。
顺子在惊恐之余,突然反过神来,沿着母亲跑的方向,蹒跚地追赶着,大哭着,高喊着:“妈,你别走,你嘎哈去啊?你别走啊!等等我啊!”
杏花对顺子撕心裂肺的呼喊,回头看了一眼,大声说了一句:“儿子听话,你等妈妈回来”。说完径直朝前跑着,不一会儿,母亲在稻田的那边儿,变成一个红色的小点儿,渐渐消失了。
站在小河边儿跺着脚又哭又叫的顺子,被赶来的父亲生拉硬拽地从小河边儿薅了回来。父亲边扯着顺子,边说:“你这个小杂种,嚎什么嚎?她都不管你了,你撵她干什么?你让她跑,有本事她就别回来。”
顺子从生下来就依偎在母亲的怀抱。白天,母亲晃着脑袋,不厌其烦地一字一句教他背诵唐诗,给他解释诗的含义。晚上,母亲先是给顺子讲故事,接着就哼着摇篮曲,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胸脯,哄他进入梦乡。顺子长这么大没离开过母亲,没有母亲的日子,顺子没了主心骨,整天哭鼻子,吵着闹着向父亲要母亲。
3
杏花嫁给永福是个偶遇中的意外。
那年,也是在稻花飘香的季节,顺子的祖母患了妇科疾病,县医院初步诊断为宫颈癌。永福听后如雷轰顶,就和已经出嫁的三个姐姐商量,不能让老太太等死,老太太就这样离开人世,当儿子的心里不安,怎么也得到大医院看看。只要走到了地方,花到了钱,就是治不好病,以后老太太驾鹤西去了,心里也就没了疙瘩,不能后悔一辈子。永福领着老太太住进了省医院,天天在医院陪护照料着老太太。
杏花就住在老太太的邻床,飘着一头长发的她,走起路来宛若飘着的仙女,见人不笑不说话,一笑起来,尾音儿打着成串的嘟噜儿,脸蛋儿上镶嵌着两个深深的酒窝。杏花嘴甜如蜜,眼睛传神,病房里的患难病友都夸她是个会来事儿的姑娘。不管永福在不在老太太身边,杏花每到饭时,都热情地帮着老太太买饭打菜,天天如此。老太太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但却明白自己的病不是什么好病,一个姿势躺着,心慌,忙叨,在床上来回翻转,唉声叹气地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杏花看在眼里,满脸堆着笑,凑过来和老太太拉家常,没话儿找话题,逗老太太开心,家长里短地哄得老太太眉开眼笑。老太太觉着自己土埋大半截了,没成想在余气残生中,倒在医院里还能遇到投脾气的杏花,这保准是前世修来的缘,八成是祖坟上冒了青气,菩萨心明眼亮,把和自己这么对撇子的小丫头,送到自己的身边,打心眼儿里喜欢眼前这个闺女儿。
那天晚上,老太太看杏花不在病房,煞有介事地偷偷和永福说:“老儿子啊,你瞅瞅杏花,是多好的闺女儿啊,我这辈子要是能娶上这么个儿媳妇,我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
永福说:“妈啊!你可别瞎想了,好好养病吧,你没听人家说吗?人家是大学毕业生,是有学问的人,怎么能嫁给咱们这样满地捡稻穗儿的庄稼人呢?”
老太太说:“老儿子,你也别那么说,我看呐!什么有学问没学问的,要是缘分到了,一准儿能成。”
“妈,咱们得搬块豆饼照照,咱是什么样,咱自己还不知道啊?咱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永福说。
杏花的老家在山区,居住在两山之间的山坳里,前望是岭,回首是山。生活在这个草深树茂的古野环境,树枝上,草丛里,小河边儿,房檐下,到处都是虫鸣鸟叫的声音,在一个调门儿上“混声合唱”,昼夜吱吱唱个不停,叽叽喳喳地回响在耳畔。杏花从小学到高中就没离开过山区,听老辈儿人说,生活在这里的人,起初是砍树,然后是栽树,后来是护树。长辈们经历了山区“放下斧头锯,拿起锄头去铲地”的整个变革过程。杏花在电视上看到外面五色缤纷的世界,充满着新奇、冲动和向往,立志使出浑身解数也要走出大山,到山的外面,去趟趟二十年之后人生这条沸腾的河,感受城里人那种上班坐车下班遛街的生活。
高中毕业后,杏花考上了省城一所名牌大学,在种子生物学专业读书,飞出了山区,实现了她的进城梦想。
杏花在大四快要毕业的时候,一次与大学同学聚会,偶然认识了一个大学同学的中学同学,大伙儿都管他叫来顺。
来顺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凭着自己天生的商人灵悟,进了省城,做起了化妆品生意。能说会道的来顺,这几年赚了不少钱,腰缠钱袋子,出手阔绰大方,有东北汉子那种豪爽劲儿,说话办事“呼哈”地直来直去,身上藏着散不尽的男子大丈夫气魄,从头到脚弥漫着顶呱呱的男人味道。
穷追猛攻是来顺套住女人的一贯伎俩。
杏花和来顺交往了,同时也在品评着来顺,心里评价来顺不像斧凿雕刻的型男,与自己还算合眼缘儿,一来二去地被来顺的执著所打动,逐渐折服在这个讨欢的男人膝下,投入了来顺的怀抱。
杏花有了身孕。
闯荡南北的来顺,在天姿与润肤的夹层缝隙中,玩转着色与钱的双重砝码,用手里的化妆品,为女人的心窝化妆,也给自己的形象涂上一层仁厚华丽的包装,以商贾王子的化身,潜心营造着自己掌中的女人王国。来顺徜徉在女人的世界里,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女人。身边的女人多了,对女人渐渐由一见钟情,变为钟情一现。在来顺面前,他青睐过的这些女人,似云烟,如昙花,一闪即逝,一个一个地成为他床上的匆匆过客。
杏花,还有一帮叫这个“花”,那个“花”的,如果来顺看上了,都成了来顺股掌中的玩偶与流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花”,只要来顺碰过了,随之他就视为残花败柳。杏花想象不到,自己会在含苞待放的花样年华里,懵懵懂懂地喜欢上一个男人,并且深深地迷恋着他,爱着他,依靠着他。而就是这个她深信不疑的男人,在她的身上,刻下了这个挥之不掉的烙痕。
这个柔情似水的女人,从结识来顺那天起,就在情网中,梭织自己与来顺未来甜美的故事。哪承想,心中天使般的来顺,如同真空,杳无音信,仿佛一缕青烟,顷刻间化为乌有,留给自己的只有腹中的胎儿和呼吸的空气。
杏花还没有离开大学殿堂,一个人孤零零地饱尝禁果儿的心酸。天性活泼的杏花,犹如自己坠入了与人隔绝的天体,把自己裹在了黑漆漆的空洞之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时光一天一夜地过着,这本来是杏花从愿望到盼望的运程,到头来,却是绝望。杏花没了眼泪,只是摇了摇头,彻底醒悟了,方知是一场血淋淋的噩梦。杏花的希望破灭了,这个在杏花心中画得色彩浓重的情爱花瓶,被曾经的来顺打得粉碎。
既然是泡影,而且还是玷污情感之后过路的泡影,就不能留下悔恨的孽种,在这个充满爱的人世间,绝不可以延续一个风流浪子的生命。
杏花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医院,决心割舍身上的“赘肉”,拔掉令自己蒙辱的含羞草芽儿,来个斩草除根,彻底在记忆中挖断这段不该有的破碎情缘,还有这个阴暗情缘下罪孽的种子。这是一个女人愤怒到极点后,慢慢滋生出来的平静与淡定的抉择。
打掉来顺种在杏花腹中的苗儿,不是十分复杂的手术。偏偏在医生检查中,发现杏花得了盆腔炎,每天输些抗生素类药物,炎症消除后才能手术。
杏花耐心等待着刮掉腹中孽种那一刻。医院床位紧张,杏花暂时住在了肿瘤科病房。
顺子的祖母病情加重,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永福手足无措,心情焦虑却又无力挽救老太太的生命。杏花在旁边一直安慰永福,向永福讲着生老病死的道理,给着体贴,送着温情。
老太太骑着阴阳两个世界的门槛,张望着,一阵糊涂,一阵明白。
这会儿,老太太神志又清醒了,眼睛四处乱转,满病房踅摸着杏花。抓住杏花的影子,立马伸出发抖的手,紧紧拉着杏花,眼泪流成了两条线,不住地往下淌着,老泪纵横。老太太嘴角抽搐着,张了张嘴,好像有许多话要对杏花说,几次欲言又止,似乎不好启齿。
杏花也跟着老太太哭着,坐在床边儿,用纸巾轻轻擦拭老太太脸上的泪水,对老太太说:“大娘,你别着急,病会好的,有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地和我说吧!”
“杏花啊!大娘求你,你把肚子里的孩子留下吧,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你和我老儿子一块儿把这个孩子养大,我家永福特稀罕你,我们是斗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人,他怕你看不起他,他不敢开口说啊!你要成了我的儿媳妇,我死了也心安了,也就没什么牵挂了。”老太太瞪着凹陷的眼睛,眼巴巴地看着杏花,一字一句地重重咬着每个字,对杏花说。
老太太喘着粗气,呼吸急促,声音微弱,每句从牙缝挤出的话,都透着一个长辈的嘱托和厚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恳求着杏花。那种渴盼而又求助的眼神儿,电击着杏花的心灵,酸溜溜的,是痛?是爱?是怜悯?是恻隐?是同情?还是真动了心?到底是什么呢?杏花说不清楚,翻江倒海地搅拌着心中的血液。也许是老太太的一番贴心话,在杏花的体内注入了化学因素的成分,勾起了融合的反应,浮起了一股暖流,一股家的暖流。
老太太睡着了,眼睛闭得死死的,安然地走了,走的没有留下遗憾。
4
杏花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只身来了稻花村,走到了永福的身边。
顺子呱呱坠地了,生下来就哭个不止,闭着眼睛不停地哭,哭累了,蹬了两下腿接着再哭。
杏花说:“永福你看,这就是个捣蛋鬼,哭八精转世了,哭起来就没个完。”
“小孩子都这样,听老辈儿人说,刚下生的孩子不哭还不好呢!哪有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就嘎嘎笑的啊?那不得把你吓懵了啊?”永福微笑着说。
杏花听了咯咯直笑,眼睛盯着这个小东西,对永福说:“你还挺幽默的,你别说,也是啊,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又被别人哭着送离这个世界,铸就了人的一生很不容易啊!就让他哭吧,权当运动了,对了,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永福说:“嗯?你是识文断字的人,你叫我给孩子起名字,这不是磕碜我吗?还是你起名吧。”
“你看,你叫永福,那他就叫继福吧,让他永远继承你的幸福,也继承咱俩的幸福,就是听着土气了点儿。”杏花说完,又打着嘟噜地咯咯笑着。
永福上初中认识那点字儿,这些年早都就着饭吃得净光了。
杏花说这个孩子叫继福,永福开始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有自己名字的影子,挺暖心的。转念又想,心里咯噔一下,他叫继福,我是他的继父,叫起来有谐音,犯忌讳,不太好。
永福想了想,对杏花说:“我叫永福,他叫继福,听着好像哥俩儿,还是叫继顺吧,他的亲生父亲叫来顺,血脉不能丢啊!小名就叫顺子,你看行不行?”
杏花刚才还笑嘻嘻的,听了永福这几句话,满心不快。孩子是生下来了,谁知道他是个顺子,还是个逆子呢?这个受过伤的女人,不情愿再把刚刚愈合的伤口撕开,永远不想再提及那个让她伤透了心的人,更不喜欢降临人间这个小东西在名字上与那个人有任何瓜葛,但觉得永福说得也有道理。人的名字,就是那么回事儿,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叫什么无所谓。
没有女人的家,日子不好过。
永福不会操持家务,杏花离家这些天,顺子在三个姑姑家轮流吃着“百家饭”,俨然是一个端着饭碗的流浪儿。
杏花和永福在一起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爱情的结晶。不是杏花不给永福生孩子,是永福的那个东西不好使。杏花领着永福看了多家医院,没有一家医院有能让永福做父亲的绝招儿。
在农村,没有后人承继香火会遭人白眼,没有孩子就是断后,别人背地里都管这样的人家叫“绝户”。尤其是那些好扯老婆舌的老娘们儿,扯显摆的时候就拿这个说事儿,动不动就说三道四,在这些人看来是个不光彩的事儿。
永福就是个顶着门户的独苗儿。到了自己这辈儿,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子众门红,家兴庭旺。可自己没这个能耐,偏偏没有这样的命,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儿。好在有了顺子,外人也不知道顺子的身世,永福心里也就踏实了一些,舒服多了,把顺子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
顺子从周一到周五,背着双肩书包,东跑西颠地吃饭,上学。永福的心簌簌发抖,疼得发颤。后悔当初与杏花吵架,说了一大堆绝情话,伤了杏花,气走了杏花,更苦了顺子。
晚上,死一般的沉寂,安静得叫人窒息,就连以前村子里连绵不断的“汪汪”狗叫声,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永福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炕上,抓耳挠腮地怎么也无法入睡。心里长满了“痒痒草”,放不下杏花,像回放电影一样,眼前一幕一幕闪现着杏花的身影儿。永福两眼望着房棚,想着杏花对他的千情万好。人家一个大学毕业的姑娘,完全可以在城里找一个像样的男人,过着舒心的生活,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跑到了自己的身边,跟着自己成了一个纯粹的农家妇女。再看看杏花这几年,苦巴苦业地和自己在稻田里滚,稚嫩白皙的一双秀手,变得红里透着黑的粗糙,且长着疙瘩琉球的老茧。杏花所有的累,一切的苦,都明晃晃地写在了这双手上。永福想着杏花对他和对这个家的付出,也想着他和杏花吵架那个天崩地裂的日子。
吵架的前一天晚上,永福喝得醉醺醺地进了院子的大门,前仰后合地打着趔趄,歪歪斜斜走着S步,嘴里嘟嘟囔囔骂着:“来顺,德行,王八犊子,狗杂种,杏花,你,你,你也这么犯贱。”然后一头扎在炕上,身上没“打捆”,倒头呼呼便睡。
世间有太多的事儿,是在巧合中发生的,就和电视剧里描绘的情节极为相像。八成是老祖宗有先见之明,早就整好了程式化的模板,留给了后人,如同一个模子扒下来的一样,套在了杏花及杏花周围的人们身上。
永福喝醉这天,他在镇上无意间碰到了初中时的班主任,旁边还站着一个人穿戴时髦的男人。同在一个乡,师生各忙各的事儿,见面次数屈指可数。
永福说:“张老师,好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咱们去整几杯吧!”
“就是啊,好像有八九年没见了,咱们喝点儿,正好,今天我也出来吃饭。”张老师说。
饭桌上,张老师向永福介绍说:“永福啊,这是我小舅子,叫来顺,在省城做化妆品生意,可能赚钱了,人家现在可是大富翁了啊!现在的流行语叫什么土豪?”
来顺微笑着说:“什么土豪啊?只是做生意而已。”
永福听到“来顺”这个名字,满脸疑惑,惊愕不已。这个名字对永福而言并不陌生,可这个人坐在自己面前,却是那么的突兀,永福大脑一片空白。是真的?是听错了?还是重名?能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来顺端起酒杯对永福说:“认识你很高兴,敬你一杯。”
永福,来顺,张老师,三个人推杯换盏,互相敬酒。尽管永福听着来顺这个名字窝心,有一股别扭劲儿,可谁知道他是不是那个来顺呢?索性还是喝酒吧!
张老师说:“永福啊,听说你媳妇杏花是有知识的人,对种水稻还很在行,你是真有福啊!找了个能帮你过上好日子的媳妇。”
来顺听后愣着神儿,自然自语地说:“杏花?是叫杏花吗?这么巧?”
“对呀!永福媳妇叫杏花,人家是城里大学毕业的呢!怎么?你认识啊?”张老师说。
来顺说:“不认识,不过我原来处过一个对象,也叫杏花,小巧玲珑的,很招人稀罕,说实话,我现在还有点想她。”
永福喝了不少酒,听着他们的对话,酒劲儿上来了,脸红得发紫,开始往上涌,接着来顺的话茬儿,大舌头啷唧地说:“喝酒就是喝酒,什么桃花杏花的?你看你们,嘴上老是杏花,杏花的,她是我老婆,你们老念叨个啥?和你们有关系吗?”
这顿酒,是师生偶然相聚的酒,没承想,来顺的出现,闹得不欢而散,也给永福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埋下了永福和杏花家庭没有硝烟的战争隐患。
5
小两口打架不记仇,这话真不假。再怎么说,杏花和永福两个人,也是顶着风浪走过来的婚姻,打闹过后很容易复合。
杏花走了大半年,终于回到了稻花村。
永福盯着杏花,看了好大一会儿,眼睛湿润了。
杏花说:“一个大老爷们,那么脆弱啊?你不是说我是破鞋吗?这回我穿着新鞋回来了!”
“那都是话赶话说出来的,两口子打仗还有好话吗?什么解气说什么呗!你别记恨我就行。”永福笑着说。
杏花说:“记恨你?还亏得你和我打一仗,要不我怎么能尝到新鲜事物呢?”
永福满脸茫然,呆呆地瞅着杏花。
这次杏花出走因祸得福。
杏花走出稻花村那一刻,明知道娘家是不能去了,回娘家也不能得到好脸看,就坐车到了省城。
在省城,杏花与留在省城工作的几个同学追忆着大学时的悠悠岁月,从大学生活,到步入社会的不同领域,再到今后的前行路径。当大家说起杏花当时的贸然举动,都夸赞她勇气可嘉,鼓励她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在农村要闯出一片天地来,别像城里人节奏这么快,压力这么大,活得这么累。
几个同学商量,要带杏花去见一个人,也就是省种子研究所梁研究员。梁研究员是杏花在读大学时的老师。师生见面有说不完的话,聊到了农村,聊到了农业,也聊到了生物学和种子。梁研究员把新研发的高产水稻品种,推荐给杏花,让杏花做水稻新品种试验,杏花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实验室,毅然决然地与种子研究所签订了新品种试验合同。
回到了稻花村的杏花,铁了心要介入农业科技成果试验和推广。杏花找到村主任,联合了二十多户农民,组建了高产水稻新品种试验合作组织,实行土地连片种植试验,形成了规模化的良种试验基地。
水稻新品种栽培试验成功了,亩产平均高于其他水稻品种一百八十斤。杏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成了农业科技试验和推广带头人,被县政府评为扎根农村的农业科技推广领军人物。
杏花笑了,笑得那么香甜,那么自信。她知道,她的路子还很漫长,她要让高产水稻品种撒满沃野良田,稻花飘香千里。
(责任编辑 王曦)
吕维彬,男,高级政工师,196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市,现居北京市。先后在中等教育、政府办公、经济管理、政策研究和金融部门工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霸王殿》《伤归隐》《小秘书》《祖父的神韵》《归路》《纸灰的影子》《管闲事儿》,分别在《参花》和《青年时代》杂志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