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吴、恽画跋略览
薛金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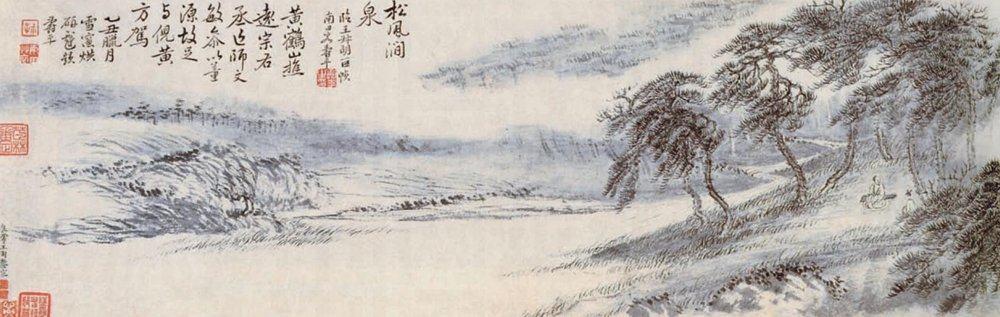

我认识恽南田,是从他的画跋开始的。依照常规,认识一位画家,当然应该主要是从他的绘画作品去感觉和评判。但南田的绘画,本不是那么易得其趣,我们生存的时代,又已别是一番天地,南田那些清柔笔墨中的荒天绝叫,其振动频率在我们能够接收的范围之外传不到我们迟钝的耳中了。加上那时也实在看不到他一张原作,而他的淡墨细线的画又特别难以印女子所以最初接触他的画,几乎未留F印象。
可是最初从宗白华《美学散步》的引文里读到南田“洗尽尘滓,独存孤迥”这样的句子,尽管片言只语,却怦然心动。文字比之笔墨语言,毕竟更多地游移于意识层面,自具理性的清晰。画的表达则可能因微妙而飘忽,因清柔而虚无,让缺少视觉训练的人恍兮惚兮,触目成幻。
后来读《南田画跋>,竟一读不能释手。南田的个性风神,一一鲜明地显现出来。此时回看他的书画作品,烟消雾散,真境呈露,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之后又读其诗,搜索其传闻轶事,渐渐地,一个完整的恽南田,一个有才、有识、有守,多情、多思、多趣,既清和又狂逸,既朴素又妩媚的恽南田,就如在近旁了。人称诗、书、画为“南田三绝”,“三绝”云云,我理解未必指他这几个单项在各自领域内就怎样空前绝后,而是说这位具多项才能的画家,由于在这三个领域的高水平表达并且已经相互印证贯通一气,合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家形象。这样的艺术家,在整个中国绘画史上,寥寥可数,更遑论同称“清初六大家”中的“四王、吴历了o 其实,仅熟悉南田,还不足以最终理解南田。只有熟识了他所属的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活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状况,才能了解他与侪辈的同和异,以及他在这个时代的特殊意义。
“四王”及吴、恽六家,在清初画坛上当然都非等闲之辈。后人评说,互有抑扬,单看绘画,也各擅胜场,一时难分轩轾。这时我就想比较—下六家的画跋,看看他们在勾皴点染之余,各自是怎样认识、怎样选择、怎样思考的。如果说画作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客观成果,那么画跋正显现出他们的主观追求。成熟的艺术家,其文其画,皆一如其人,都是合成全人不同侧面的材料。所以画作虽是认识画家的主要依据,文字却也是重要参照。尤其是,这些画家是以“文人画家”的身份载人中国绘画史册的。
一
在“清初六家”中,王鉴大约最为质直无文。恽南田有篇《记<秋山图>始末》的文章,记名迹流传,神物变化,迷离恍惚,十分精彩,其中一段生动勾勒出王鉴等人的风貌。《秋山图》是王时敏早年见过一次、终生念念不忘的黄公望极品巨迹,后传为一王姓贵戚所得。贵戚遣使招娄东二王公来会。时石谷先至,便诣贵戚,揖未毕,大笑乐日:“《秋山图》已在橐中。”立呼侍史于座取图观之。展未半,贵戚与诸食客皆觇视石谷辞色,谓当狂叫惊绝。比图穷,惝恍若有所未快。贵戚心动,指图谓石谷日:“得毋有疑?”石谷唯唯日:“信神物,何疑?”须臾,传王奉常(时敏)来。奉常舟中先呼石谷与语,惊问王氏已得《秋山》乎?石谷诧日:“未也。”奉常日:“赝邪?”日:“是亦一峰也”日:“得矣何诧为?”日:“昔者先生所说,历历不忘,今否否,焉睹所谓《秋山》哉?虽然,愿先生勿遽语王氏以所疑也。”奉常既见贵戚,展图,奉常辞色一如王郎气索,强为叹羡,贵戚愈益疑。又顷,王元照郡伯(王鉴)亦至,大呼“《秋山图》来。”披指灵妙,俪俪不绝口,戏谓王氏,非厚福不能得奇宝。于是王氏释然安之。
这其实是一次三王串演的鉴定会。石谷先去,一看即知不是《秋山图》,心里“有所未快”,却不说破,还要求老师王时敏采取同一态度,“强为叹羡”,糊弄得画的贵戚。在这样一个重要活动中,王时敏理所当然是中心人物:石谷作为“二王公”共同的得意弟子'被王时敏倚为心腹助手,既了解事实真相,也显得颇有心计。而作为“娄东二王公”之一的王鉴,却被隔在秘密之外,不明真相,还来“披指灵妙,俪俪不绝口”地瞎起劲一番,显得有点滑稽了o此时的王时敏,庆幸有此一个调剂气氛的角色,却也有点在心里暗笑的吧。
王鉴的画,我原来也并不理解,以为是板刻之尤。后来在常熟博物馆见到他两帧册页原迹,惊为绝品,那种纯粹、坚洁、古劲之美,也是达到一种极致了。从此对此老另眼相看,渐以为颇能得其佳趣。
但他的题画文字却实在乏善可陈。他的习用语是“愧不能仿佛万一…‘不禁小巫气索”之类,在前人面前,永远像小巫见大巫一样低声下气,毫无自信。这当然也可正面理解为自知之明或者在大师面前应有的谦虚,可是它谦得没有内容,没有任何丰富人启发人的信息在内,与画面也形不成互动。所以他为数不多的画跋在六家中最无可读性。这里聊举一跋为例,是他约60岁时题在《青绿山水图卷>上的,此卷被印入许多画册中,应是他较重要的作品:
余向在董思翁斋头见赵文敏《鹊华秋色卷》,及余家所藏子久《浮岚远岫图》,皆设青绿色,无画苑习气。今二画不知流落何处,时形之梦寐。闲窗息纷,追师两家笔法而成此卷,虽不敢望古人万一,庶免近时蹊迳耳。戊戍长夏王鉴
面对赵孟頫、黄公望的名作,似并无什么感想,“皆设青绿色”,这种浅表的描述,近于废话,“无画苑习气”又过于空泛。它只是暗示了自己的这幅青绿山水画可并非画院匠工俗品,而是有着高远师承的呢。
当然,他的一个基本信念牢存心中,不会暂忘,这就是续“正脉”,拒“外道”:
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钟王,舍此则为外道,唯元季大家,正脉相传。……
前面他自幸与之保持了距离的“近时蹊迳”,正是指的那些违背了南宗正脉的“外道”。这样,王鉴给自己的定位是:在“正脉”之内,面对古人,自己很低很低;但面对“外道”,则自己立场正确,态度鲜明,有无可置疑的优越地位。这也正是“四王,前后两辈人共同的口吻和心态。
二
王时敏是“四王,之中最早给我好感的人。最早的印象,来自曾鲸画的青年王时敏肖像,翩翩白衣书生,丰神秀颐,英气四溢,端凝的目光流露出平和的自信,让我叹赏良久。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人物画中最动人的青年形象。周文矩、顾闳中的画里虽也出现过一些贵族子弟,却非纨绔气十足即奶油味太重,缺少人格魅力。唯有王时敏,让人目悦神爽,顿生向往之心。
王时敏的画,也让人一见便有亲切感。早时接触明清山水画,多从石涛、八大山人这些“野逸派”开始,初见“四王,一路的‘‘正统派”山水,真一无感觉。偏是看到王时敏的册页,才觉得‘‘正统派”亦自有其正统的魅力。前人评日“运腕虚灵,丘壑浑成”,还仅是就画论画。他的画洋溢着的那种蔼然的温厚与淡然的平和,才让人领略了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中的某种迷人气息,感到人间也确不可少此一格。
王时敏结集有《王奉常书画题跋》(又称《烟客题跋》)一百八十余则,他对“外道”的批判比王鉴表达得更明确更激烈,很表现出一派宗主的气度:
近世攻画者如林,莫不人推白眉,自夸巨手。然多追逐时好,鲜知
古学。即有知而慕之者,有志仿效,无奈习气深锢,笔不从心者多矣。
迩来画道衰替,古法渐湮,人多自生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
可救挽。
而他对前贤尤其是黄公望的认识,也确实深入而有独得之见:
子久画原本董、巨,而能神明变化,别出奇思,不拘守其师法。每见
布景用笔,于浑厚中仍饶波峭,莽苍处转见娟妍,纤密而气益闳,填塞
而境逾廓,意味深远,故学者罕得其津涉。
但他画跋的大部分文字却是由自谦和誉人两部分组成的。他的自谦,几乎成为自污,读来生厌;他的誉人,则近乎谀人,颇令人生疑。
且看他的自贬之词:“资质劣弱,老懒无成”,“笔砚久荒,自愧伧父俗笔”,“笔与意违,徒有浩叹而已”,“软甜稚弱,何异小儿涂墙”,“境违神滞,心手相乖,如古井无澜,老蚕抽茧,了无佳思,以发奇趣,下笔不胜汗颜”,“全未得痴翁脚汗气”,“仅如蜗涎延绣壁,仿佛成形,视近时名家,犹不堪作奴,何况子久?”说自己的画不过相当于小孩子在墙上乱涂,甚至只是蜗牛爬行留下的涎迹,不要说还没得到黄公望的一点脚汗气,就是在近时名家面前,也不具备做一个奴才的资格。从文字角度说,也算得上创喻独特,联想丰富吧,却只只是为了自贬到自我作践的地步,亦一奇也。不过,看看今日天下画者皆“自夸巨手”的局面,王时敏也就显得有点可爱了。
而他称誉王鉴、吴历、石谷甚至石谷的弟子辈,却不惜集画坛颂词之大成,誉人誉到毫无分寸的地步。王鉴是“旷代绝艺”,“近代一人,断断无疑”,吴历也“信是当今独步”,石谷则“罗古人于尺幅,萃众美于笔下,五百年来,从未之见,惟我石谷一人而已”。连石谷弟子杨子鹤,以及何处的什么圣符,也获得几乎与石谷同样的评价。大约当时已引起微词,所以有人为之辩护日:“虽或有溢美,亦非全无斟酌,一味漫与也。”其实,“全无斟酌,一味漫与”,正是这些题跋给人的印象。我们可以将这些文字阐释为一位画坛领袖人物道高心下,一意揄扬后进的表现。好作溢美之词,也是中国传统文人中的普遍现象,连臧否人物一向严苛的钱钟书先生,不也有许多当不得真的“钱誉”吗?何况烟客!但他的文字与他英气勃勃的肖像和他怡然沛然的画作留给我们的印象,毕竟差距太远了。
南田画《春烟图>,题日:“春烟图似得造化之妙o初师大年,既落笔,觉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驾而上之,为天地留此云影。…‘初师”是学古惯性,“既落笔”而自性呈现,遂觉与古人不合处,更自觉超越古人处,遂能自得造化之妙,自得心源之妙不期然而竟然地进入了创造的状态。“为天地留此云影”,说得何等豪迈又何等自然。烟客题跋中,从无此种语言。
三
吴历与石谷同岁同学,在这个艺术圈里,受到王时敏、王翚、王原祁的一致推重。他的画,以湖天春色,青草杨柳一路最具特色,那种柔美清丽的江南景物,给人十分真切的感受。
吴历有<墨井题跋》六十余则。其中几则记录了画坛前贤的作画轶事,可资后学参考:
黄鹤山樵扫室焚香,邀痴翁至,出绘学
请质。子久熟视之,却添数笔,遂觉岱华气
象,相传为黄、王合作也。
梅道人深得董、巨带湿点苔之法,每积
盈箧,不轻点之,语人日:今日意思昏钝,俟
精明澄澈时为之也。
另有几则记其南行澳门的印象,倒也是当时留下的少见而特别的文字资料。此外则平平无奇,未见高明。如:
半幅董源传闻久矣,愿见之怀不啻饥
渴。一日过太原之拙修堂,幸得饱观,其笔
力扛鼎,奇绝雄贵,超轶前代,非后学者能
窥其微蕴也。
可谓泛泛而论,不得要领。又如:
山以树石为眉目,树石以苔藓为眉目,盖
用笔作画不应草草,昔僧繇画龙不轻点睛,
以为神明在阿堵中耳。
引了张僧繇画龙不轻点睛的典故,说明画树石、苔藓皆“不应草草”,不能轻率从事。其实山水画中树石是主体,点苔则可能是最后的调整收拾,扯在一起,颇无逻辑。这种文字,显得意平语钝,有点不知所云。又如:
往余与二三友南山北山,金碧苍翠,
参差溢目,坐卧其间,饮酒啸歌,酣后曳仗
(杖?)放脚,得领其奇胜。既而思之,毕
竟是放浪游习,不若键户弄笔游戏:真有
所独乐。
“四王”圈子里的这些画家,整日临仿古人,“与宋元人血战”(王时敏题吴历画跋中语),偶尔游山,真是太重要的补充,吴历却偏要反思“放浪游习”之误时,思路拘隘如此,今人大约是很难理解了。试看南田画跋中的态度,正截然相反:
清夜独倚曲木床,着短袖衫子,看月色
在梧桐篁筱间,薄云掩过之,微风到竹,衣
上影动。此时令人情思清宕,纷虑暂忘。
秋夜与王先生立池上,清话久之,暗睹
梧影,辄大叫日:好墨叶!好墨叶!
三五月正满,冯生招我西湖。轻舟刀出
断桥,载荷花香气,随风往来不散。倚棹中
流,手弄澄明,时月影天光,与游船灯火,
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弦鼓吹,与梵吹
风籁之声,翕然并作。目劳于见色,耳疲于
接声,听揽既异,烦襟澡雪,真若御风清泠
之渊,闻乐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尚在人间
与否。冯生日:子善吟,愿子为我歌今夕。余
日:是非诗所能尽也,请为图。图成景物宛
然,无异同游时。南田生日:斯图也,即以为
西湖夜泛诗可也。
三则题跋,尽隋表达了南田在“键户弄笔”之外,游息于自然中的愉悦和收获。第一则是自然无所不在的对于艺术家心性的滋润:第二则是寻常景物对画家寻找艺术语言的偶然启示:第三则更全面展现游览对于一个山水画家进入好的创作状态的促发作用。不知主要是由于文字上的局限还是认识上的局限,吴历画跋中显然缺少此一境界。
四
王翠是南田的朋友,是南田与“四王'艺术圈发生关系的主要纽带。从青年时期订交起,两人就在艺术上共同切磋、互相影响,对各自的艺术路向都产生过相当的作用。人们多传说南田主攻没骨花卉是因为石谷山水独步一时,自己耻为天下第二的缘故,却从未将石谷之画早年不失虚灵,晚年渐渐刻露伤韵的现象,与南田的影响联系起来。其实我们可以隐隐看出,经南田题跋的石谷作品,大多带有一些南田的审美趣味,显得比较清逸简率,那也正是石谷与南田交往时所作。大约自南田去世,石谷繁琐近俗之作日多。当然,事情真相并不像文字叙述这么清晰明确,影响之强弱也难作量化评定,但明眼人当不以我此言为生造。
陈履生著《王石谷》-书,收集了一些石谷题跋,其中有小部分文字,从用词到趣味,都近南田,如:
米敷文(米友仁)有《潇湘图》,云气
飘渺,发人浩荡奇逸之怀,余正未能得其
神趣。
天游、云西用意飘洒,天真烂然,故能
脱去町畦,超于象外。
令人奇怪语气何神似南田,简直好像南田代为草拟的一样。后来见到画上原题,才知它们本出于南田之手,是陈著所误收。 在石谷的有些作品上,王、恽二人都留下了题跋,两相对照,颇见高下。如《亘古无双图册》-页,石谷自题:
荒江垂钓仿惠崇小景,丙寅初夏石谷
王翚。
南田题:
千株乱柳一片荒江,此中横小艇为吾两
人垂钓之处,王君其有遗世之思耶。南田草
衣题于玉峰精舍。
石谷自题,笃实无趣,南田虽亦寥寥数语,而一派豪情绮思,呼之欲出,为小小画面生色不少。
又如《仿吴镇临董源五株烟树图》,石谷题:
董源五株烟树图,名著海内,未得寓
目。今年春,在娄东王奉常斋中见仲圭临
本。枝如屈铁,势若张弩,苍莽道劲,如书
家篆籀法,令人洞心骇目,正非时人所能窥
测。余此幅不能得仲圭形似,安敢望北苑神
韵耶。石谷
而南田在画外题跋则日:
视仲圭临北苑,犹未免为北苑神气所
压,石谷得法外之意而神明之,视仲圭真后
来居上矣,玩此惊叹因题。恽寿平
不排除石谷出于自谦,而南田作为友人鼓励叫好的因素,但在古人面前,各自态度确有区别。石谷在习惯性的谦词以外,只能对前人笔墨赞赏备至。南田则涉及了更重要的话题:学习古人要避免为古人“神气所压,要“得法外之意而神明之”。这种立志“后来居上”、敢于超越前人的豪气,正是“四王们共同欠缺的精神状态。
石谷<仿王蒙秋山草堂图轴>自题:
王叔明秋山草堂图师法右丞,其设色只
用浅绛皴染点缀,与流俗所见不同,为董宗
伯所鉴赏者。吴中杜东原,文五峰诸公,专以
此幅为师,始知古人各有源本,不敢杜撰一
笔遗讥后世也。癸丑十月既望虞山王晕
赞赏别人谨守“源本”,也即显示自己的观点态度。这个“源本”,在这里不仅不是传统的整体,甚至不是某位大师的全部,而只是某一个古人的某一幅画。当然石谷自己还是转益多师广泛吸取的,但‘不敢杜撰一笔遗讥后世”的自我警告,还是制约了他在集大成式的建构中,尽管广度上铺展不小,深度的拓进却不足,画风毕竟少了些南田那样奇宕的真气和超迈的逸情。
石谷在六家中是最典型的职业画家,对技法的重视和锤炼自然是放在第一位的,在画跋中处处可见对法的讲究:
古人惜墨如金,不妄用墨耳……盖墨之轻重浓淡处,气韵全自
此出……
这是讲究墨法。
麓台云:山水用笔须毛,毛字从来论画者未之及,盖毛则气古而
味厚。
这是论笔法。
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染,余于青绿法,静
悟三十年,始尽其妙。
这是说设色法。
枯树最不可少时于茂林中见,乃苍秀。
这其实是研究小章法中的对比手法。总之,石谷确是当时技法纯熟的一流高手,画跋中虽也不免老生常谈,但确有一些来自实践经验的真切见解,值得注意。其中尤为经典的,是可以视作他集大成总纲领的这句话:
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 这样一种设计好像强强联手一样,在想象中简直是太完美了。奇怪的是,包括石谷自己在内,实际上谁也没有画出过这样的完美作品来。元人的笔墨是为元人的丘壑准备的,唐人的气韵也只能在唐人的笔墨丘壑中才浮现出来,仅在技法的层面作拼凑嫁接,不太有效果。
石谷把前人有丰厚内涵的范畴技法化了,也简单化了。更显著的例子是对“逸”的理解。石谷《题仿倪山水》日:
凡作画遇兴到时,即运笔泼墨,顷刻间烟云变化,峰峦万重,苍茫
淋漓,诸法毕具,真若有神助者,此为天真。得天真而成逸品,逸品在神
品之上。所谓神品者,人力所能至也:所谓逸品者,在兴会时偶合也。
“兴会时偶合”,需要的是笔墨挥洒的娴熟技巧,充沛饱满的作画情绪,所谓“妙手偶得”即是。如果这样就算“逸品”的话,它实在不足以取得超越神品的至尊地位。试看南田如何论“逸”:
不落畦径,谓之士气。不入时趋,谓之逸格。
清如水碧,洁如霜露,轻贱世俗,独立高步。画品当作此想。
高逸一派,如虫书鸟迹,无意为佳,所谓脱尘境而与天游,不可以
笔墨畦径观也。
画家尘俗蹊迳,尽为埽除,独有荒寒一境,真元入神髓,所谓士气
逸品,不入俗目。
逸品逸格是南田为人、作画的最高理想,它是精神独立、“不入时趋”,疏离于主流,自放于边缘的一种自觉追求,只有表达了这种追求的作品,才称得上“逸品”。所以,这种“逸品”,既是主观上“无意为佳”的产物,又是客观上‘不入俗目”的东西,‘不可以笔墨畦径观也”,它是超越于笔墨层面的。南田时时提及“荒寒一境”,那正是“逸”的象征。而石谷的画,恰恰是离开荒寒最远的啊!
五
禹之鼎有《王原祁艺菊图卷》,为我们留下王原祁的肖像。图中王原祁欲过中年,广颊丰髯,大腹便便,执杯箕坐,一派地方豪强或江湖老大的气度,与初看他山水画但见碎石满纸的感觉不太吻合。
王原祁是王时敏之孙,在“清六家”中生年最晚,却是“四王,艺术最具水准的发言人,是“四王,中最有理论素养,画跋中最多真知灼见的一位。虽然他的《麓台题画稿》和《雨窗漫笔》总共只有六十余则,却显得分量颇重,可以远远超越前面“三王,加上吴历的总和。
《麓台题画稿》云:
画有五品,神逸为上,然神之与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贯
虱之巧,则难至也。元季梅道人传巨然衣钵,余初学之,茫然未解。既
而知循序渐进之法,体裁以正其规,渲染以合其气,不懈不促不脱不
粘,然后笔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泼墨为能,工力为上,以为有成法,
此不知庵主者,以为无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
在另一处又云:“元章峰峦,无一非法,无一执法。”王原祁尚法而不死于法,这些话都说得十分精彩。但他既说神之与逸不能相兼,他自己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应该只是追求神品的路子,而且也确实达到大多数画家难望其项背的高度。相比之下'恽南田凭其虚灵本性,天马行空,在缥缈意境中自由往来,饱看人间天界春色,以王原祁的标准看,也不免有未做到做实之处。所以后来颇受王原祁画论影响的黄宾虹评论南田,也说过“求脱太早”的话。但南田实是去世太早,以他这样的天性,艺术道路恐怕也只可能这么走。时代更近的,如潘天寿、傅抱石等人,都曾受到过类似的嘲讽,也并不妨碍他们终成大家。正因为神逸不相兼,所以追求神品,即使做到出神入化,也与“逸”的追求有异。这也正是王原祁与恽南田之异。
《麓台题画稿》: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痴之笔,用山
樵之格,便是荆关遗意也。随机而趣生,法
无一定,丘壑烟云惟见浑厚磅礴之气。……
不谓六法中道统相传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
见窥测,便去千万里,为门外伧父,不独径
庭而已。
“法无一定”,本是论画之“活法”,却又转论到“道统不可移”,警告后生不可沦为“门外伧父”去了。
世人论画以笔墨,而用笔用墨必须辨其
次第,审其纯驳,从气势而定位置,从位置
而加皴染,略一任意,使疥癞满纸矣。每于
梅道人有墨猪之诮,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
解,何以得古人用心处?
也是强调正统法规的重要性,而告诫后学切不可“任意”。“任意”一词,多少有重视“意”所以就放纵“意”的意思,此处则主要指轻法。轻法的后果,是“疥癞满纸”。南田其实也一样重视正统法规,但他更有对另一个层面的关注,那就是重意。所以他希望在“得古人用心处”也即得法之后,更能“到古人不用心处”。那是一个“法外遗意”之处。
董宗伯画不类大痴,而其骨格风味,则
纯乎子久也。石谷子尝与余言:写时不问粗
细,但看出进大意,烦简亦不拘成见,任笔
所之,由意得情,随境生巧,气韵一来便止。
此最合先生后熟之意。
赞董其昌不似黄公望而神似黄公望,这本是一个如何从学古人中创造新格的命题,却引用王石谷的话,转成了如何在临摹学习中灵活应变的话题了。“随境生巧”云云,也算得极精彩的经验之谈,但毕竟是在一个“意临”层面上的话题。大话题就这样常常转成了小话题。
画中设色之法,与用墨无异,全论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气。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纸背,大约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悦目,不问节腠,不入窾要,宜其浮而不实也。
笔不用烦,要取烦中之简:墨须用淡,要取淡中之浓。要于位置间架处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虽渲染周致,终属隔膜。梅道人泼墨,学者甚多,皆粗服乱头挥洒,以自鸣其得意,于节节肯綮处全未梦见,无怪乎有墨猪之诮也。
古人技法之精要,都不仅在表面文章,而皆须深入裒要,得其真意,方可免为仅得皮毛的肤浅之徒。王原祁诸如此类的许多画论,正是对学习者切实要紧的指导。他眼光透彻,多在“节节肯綮处”计议掂量,这本是其高出众人处,却也是形成他一定的局限之处吧。
笔墨一道,用意为尚。而意之所至,一点精神在微茫些子间隐跃欲出,大痴一生得力处全在于此。画家不解其故,必日:某处是其用意,某处是其着力。而于濡毫吮墨随机应变,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火候到而呼吸灵,全幅片段自然活现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则茫然未之讲也。
“意之所至,一点精神在微茫些子间隐跃欲出”,这真可看作是见道之语,却终落实到“濡毫吮墨随机应变”的层面上。一个终身以大痴为专师的人,“所学者大痴也,所传者大痴也,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的人,五十余年苦心用力,所谓“可解不可解处有难以言传者”,都聚心目于纸上笔墨之中,却不免“纸上得来终觉浅”,与黄公望终日忽忽于山巅水涯,领略山川气息,得于心而形于笔的那种陶醉于自然的状态,似乎愈近愈远,终隔一层了。
惠崇江南春写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画法悉本此意,而纤妍淡冶中更开跌宕超逸之致。学者须味其笔墨,勿但于柳暗花明中求之。
“柳暗花明…‘田家山家”者,画之题材而已:“纤妍淡冶…‘跌宕超逸”者,则是画中精神之所出。王原祁诸如此类论前贤名迹,俱有深见。“学者须味其笔墨”,这里的“笔墨”可以理解为画家精神的物化,正与他‘不泥其迹,务得其要”的一贯态度相合。但“迹”也好,“要”也好都是古人画中物,王原祁始终面对的是学习古人的问题,始终在研究仿古如何仿得高明。
学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蓝者无几。宋元以来宗旨授受,不过数人而已。…余少侍先大父,得闻绪论,又酷嗜笔墨,东涂西抹,将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蓝之道,终不可得也。
所谓“出蓝”的努力,大多数人仍只是在“蓝”的标准下挣扎,或可加厉,而未敢变本。王原祁说“董巨画法三昧一变而为子久,,子久自是真正的出蓝高手。王原祁认识到‘不敢似古人,,也已是学古的高手了,却是未敢变本的高手。“求出蓝之道终不可得”,这在王原祁算是一句谦词,还是心有更高远的追求?
房山画法传董、米衣钵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学者窃取气机刻意摹仿,已落后一著矣。尝读雪窦颂古云:江南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学房山,即可以学董、米也。
所引雪窦诗大佳。鱼已化龙而去,人犹戽水抓鱼,何可得鱼?化龙的鱼,就是不断变化的传统。学传统不可刻舟求剑,戽塘求鱼,死守传统,以至于死于传统。王原祁这些议论,大都可与南田相呼应。但总体看来,二者之间还是明显区别的。王原祁再怎样强调“须以神遇,不以迹求”,他的画再怎样受到今人更高的评价,至以“东方塞尚”的称号相许,我总以为他在笔墨形式上的贡献,初非出于本意,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不知其然而然”的不自觉的创造。这当然另是一种了得。但他心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还是“古人,二字。而南田则处处有“我”字,画跋云:“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乃为逸品。当其驰毫,点墨曲折,生趣百变,千古不能加。即万壑千崖,穷工极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谓写胸中逸气也。”作画是出于本真,表达生趣,好传统是激发出自己的真趣,否则,“千古不能加”,古人也不能给我们增添什么,又何必为先匠所拘呢?
六
在略览前五家文字时,作为参照我引了几则南田画跋,也许从中已可一见南田狂放豪逸的风神。南田友人顾祖禹在南田诗序中说:“世有独至之人,而后有独至之诗。—南田之诗就是“独至之诗,而非随声附响,自弃性情,强为嚬笑者”。读南田诗,“忽焉使人凄其流涕,忽焉使人怒发上指,正如易水一歌,商徽乍更,喜怒顿异者,听者之性情,不觉移于歌者之性情也”。其诗中“多豪宕感激之什”,“尤多精辟之语”。南田有诗集《瓯香馆集>传世,是当时号称“昆陵六逸”的诗人群体之首。而他的画跋,正是诗情洋溢,逸气纵横,为明清以来各家画跋文字所无。用他画跋中的话说,是“笔笔有天际真人想,有一丝尘垢之点,便无下笔处”。这是他与“四王吴历的文字最鲜明最直接的不同。
《南田画跋》:
秋夜烟光,山腰如带。幽篁古槎相间,
溪流激波,又澹荡之。所谓伊人,于此盘
游,渺若云汉。虽欲不思,乌得而不思?
触景思人,对自然敏锐的感受与对“伊
人的深厚情意相融无痕,正是中国诗歌传统
一脉相承的风人之旨。而画,就是在如此动情
的情绪中“思”的流露并转化为视觉的形象。
秋夜读《九辨》诸篇,横坐天际,目所
见,耳所闻,都非我有。身如枯枝,迎风萧聊,
随意点墨,岂所谓“此中有真意”者非耶?
枝高撑天,叶大于掌。含霜聚雨,凉籁
吹荡。空堂无风,时作奇响。几回停笔不得
下,令人心在白云上。
南田易感而多思,读《九辨》即身与俱化,幻在天际。此时作画,当是意丰神超,欲辨已忘言。至于“空堂无风,时作奇响”,恐怕更多还是出于他心中的奇想。在常人看来,不过一隅空屋老树而已,却触动了南田满腔情思,悠远缥缈而又波澜万状。于是笔下竟是何等神奇高旷呵!正如凡-高,心中在燃烧,所以他笔下的田野、星空、花树,也无不在燃烧:南田怀抱奇情逸致,无可消遣,无可排解,所以笔下的一切,也就无不奇逸非凡了。
雪中月季,冰鳞玉柯,危干凝碧,真岁
寒之丽宾,绝尘之畸客。吾将从之,与元化
游,盖亦挺其高标,无惭皎洁矣。
画《岁寒三友》题:予独爱此三种,喜
其积雪凝寒之候,能表贞素之华,矫然有以
自异,可方遁世之君子。
雪霏后,写得天寒木落,石齿出轮,以
赠赏音,聊志我辈浩荡坚洁。
自古以笔墨称者,类有所寄寓,而以毫
素骋发其激宕郁积不平之气。
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
着笔。所谓天际真人,非鹿鹿尘埃泥滓中人
所可与言也。
…一不为高岩大壑,而风梧烟筱,如揽
翠微,如闻清籁,横琴坐忘,殊有傲睨万物
之容。
“四王,”们画画就是画画,山水就是山水,论画就是论如何画得可以上比古人。而南田在画画时想些什么呢?是“与元化游”,“挺其高标,无惭皎洁”,是“矫然有以自异”,“聊志我辈浩荡坚洁”,更是“以毫素骋发其激宕郁积不平之气”,“非鹿鹿尘埃泥滓中人所可与言也”,“殊有傲睨万物之容”……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对于精神上“挺其高标”的强烈追求的气息。画画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是画者人格的表现,是精神世界的展示,而且在表现的过程中得以进一步提升。所以,值得倾全身心而为之。即使到今天,我们又能找到多少关于绘画精神性的更真切动人的表达呢?我们最常态的作画,是为展览而画,为卖钱而画,即为名利而画。上不了展,卖不了钱,名利不可得,则为消遣而画,为自娱而画而已,极少能视之为精神的修炼、情怀的骋发。我们在必要时也会准备一些好听的说词,诸如“献身艺术”之类以应付场景,但大多不成系统,不能自圆其说,与平日其他言行也难以互证,所以可信度甚低。南田其实是卖画为生,不免四处奔走,寻找市场。他画那许多柔美的花卉,也确实主要是一种市场化努力。但四百余则画跋读下来,数百首诗读下来,若干传闻轶事读下来,我们眼前已能够浮现出一个较为一致可信的飘逸而质朴的形象。他在谋生之余,念兹在兹,耿耿于怀的,是追求过一种“无惭皎洁”的生活。尽管他没能留下详尽的传纪资料和成体系的文字资料,但在现有文字中呈现的这个影影绰绰的影像,已经与“四王'、吴历的精神面貌大异其趣了。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
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
人悲,又能令人思。写秋者,必得可悲可思
之意,而后能为之。不然,不若听寒蝉与蟋
蟀鸣也。
群必求同,同群必相叫,相叫必荒天古
木,此画中所谓意也。
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
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古人论诗
曰“诗罢有馀地”,谓言简而意无穷也。
可别等闲看过一幅荒天古木,其中有同群相叫之意。画中若无此“可悲可思之意”,则‘不若听寒蝉与蟋蟀鸣也”。“意”之对于南田,是画的灵魂,是画之可作不可作的分判,也是画中技法、笔墨、形式的最后根据。那么这个相叫的“同群”是些什么人呢?这个无穷的“意”是些什么感情呢?南田喜用“解衣盘礴”一语,此语源出《庄子》: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
立,舔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
值僵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
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
真画者也。”
这个不拘礼节,无所顾忌,放浪形骸,超越利害的“真画者”,应当是南田的精神导师。斯人之后,在中国画史上更形成一个逸士的谱系。用朱景玄的话说,他们是“性多疏野,不知王公之尊重”:用黄休复的话说是“襟抱超然”:用张伯雨的话说是“意匠摩诘,神交海岳,达生敝睨,玩世谐谑”;用董其昌的话说则是“质任自然”。逸士们在超越世俗的姿态中都多少包含了疏离、批判和抗争的意识。南田正是自觉地与他们为伍,与他们同群相叫,而画中笔意无穷。后人赞倪云林画,说是“冰痕雪影,一片空灵,剩水残山,全无烟火,我观其画,如见其人。用来移赞南田那些最优秀的山水作品,也是无愧色的。
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
独存孤迥,烟鬟翠黛敛容而退矣。高逸一种,
不必以笔墨繁简论。如于越之六千君子,田
横之五百人,东汉之顾厨俊及,岂厌其多?
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独行西山,维
摩诘卧毗耶,惟设一榻,岂厌其少?然其命
意,大谛如应曜隐淮上,与四皓同征而不出:
挚峻在汫山,司马迁以书招之不从:魏邵入
牛牢,立志不与光武交。正所谓没踪迹处潜
身,于此想其高逸,庶几得之。
南田有多段如此酣畅淋漓、博喻纷呈炫耀才学的文字,读来令人眼花缭乱。此段命意,是论繁简的两个层次。一个是‘不必以笔墨繁简论”,繁与简可以各有根据,各有精彩:一个是“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必以简为贵。繁简问题也是一个从来难以论定的命题,南田于此,可谓片言解纷,此外似乎未见更有深论。
尝谓天下为人,不可使人疑。惟画理当
使人疑,又当使人疑而得之。
这是多么“现代”的态度!从来理论都具排他性,是以我之是,攻彼之非。南田写下那么多的画理,却要“使人疑”,使人在质疑和证伪中自得之。此“得”不是盲从,而是经过各自探究之后的吸收、改造、摒弃和再创造了。
更为超前的,则是这段题在王翚画上的赞美文字。这样的赞美,王石谷当然当不起。也许世上的画家,还无人能当得起,南田自己也远未达到此种境界。但是他提出了这种理想,这是一种怎样的理想呵:
观其运思,缠绵无间,飘渺无痕,寂焉
寥焉,浩焉渺焉,尘滓尽矣,灵变极矣。
也许这样的画只能存在于优美的文字中吧?但重要的是,南田发现了这样的艺术,也开始了这样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指向古人已经创造了的世界,而是指向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浩渺无边的却又清洁宁静的世界。这应当是颇具抽象意味的一种全新的画面!叔本华等西方思想家谈论音乐的时候,有过相近似的文字。在他们看来,音乐展示了灵魂的缥缈的运动,揭示了世界的隐秘的本质,是那种无法表述的内在冲动的表达。其他艺术方式或多或少试图驯服这冲动,试图命令它、厘清它、组织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它、歪曲了它,以致于杀死了它。而音乐最大限度地远离一切对客观事物的描述,直接而纯粹地表达了我们的灵魂。也许在南田看来,那许多模山范水的刻画之作,也限制了、弱化了,以至于杀死了山水所蕴含的自由精神。他的画笔虽还没有能彻底超脱,但心里一定在向往着飞越,酝酿着突变。“灵变极矣!”这是对着未来的呼喊吧。
“四王、吴、恽,一直被看作清初正统派的代表画家。他们尊崇的传统,看起来略无不同,经常提及的古人,也都大致相仿。但在“四王”眼里,先师们是一些孤立于世事的伟大偶像。而在南田这里,却是一些帮助他解决自己的课题,帮助他立身于世的一种力量。其实真正的艺术传统必与社会和时代的课题相关,从“四王'的文字中却很难看出这种联系。而读南田的文字,与读明末性灵派文人,读董其昌,甚至读李贽,其间气息相通,略无隔膜。南田既是中国隐逸文化传统自觉的继承人,也多少是明末思想新潮和艺术新潮的受惠者。但这些内容,已非这篇“画跋略览”所能包括,也许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四王吴恽与四僧书画特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