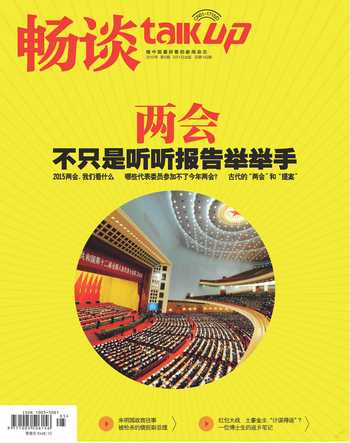木心: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王绍叶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有人说木心先生的这首诗中,“大雪纷飞”是他内心的狂舞,而“黑暗”,不仅指他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个人际遇的千难万险,更有那种“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孤独。
不过现在也有不少人拿这首诗作为情话,讲给爱人听。
人是经得起浪漫的
木心的人生,是经过了漫漫的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虚无散淡,大道无极,却终给人带来一种可媲美宗教的解脱。他的人生太漫长,他曾说,年轻是一种天谴。看了他的诗,人们才发现,他是成了六旬老翁之后,才开始写诗的,却是生命于晚来天际间盛放的焰火。
木心走了四年了,他留下太多的谜。他一生没结过婚,也没有太多关于他的风流韵事。但是,浪漫却贯穿着他人生的始终。正如他自己所说,人是浪漫得起的,浪漫不起的还算人?他让我们懂得,在丧失任何浪漫可能的时代,而依旧浪漫的人,才是真正的浪漫。他无疑是二十世纪最痴情的情人之一。他是一个敏感多情、挑剔刁钻,而捉摸不定的情人。
他曾自称,看这世界时,我用的一只是情郎的眼,一只是辩士的眼。知道他的人,读过他的诗的人都会认为,木心是一个情圣,更是写情诗的圣手。以他的生命体验,最直接最强烈的痛苦与快乐,莫过于爱欲。在《我纷纷的情欲》里,情欲是天地的滥觞。“尤其静夜,我的情欲大,纷纷飘下;缀满树枝窗棂,唇涡,胸埠,股壑,平原远山;路和路,都覆盖着我的情欲。”
往过去看,一代比一代多情
在他的回忆里,爱曾是燎原的火。当年的爱,大风萧萧的草莽之爱,每度的合都是苍茫的野合。也许在《泡沫》里的爱情观,是最能代表他的。“我一生的遇合离散,抱过吻过的,都是泡沫啊;爱情洗净了我的体肤,凉凉的清水,冲去全身的泡沫。”因此,他的爱是唯美主义的,他只爱爱情本身,具体的爱只不过是泡沫。
在他看来,往过去看,一代比一代多情;而往未来看,则一代比一代无情。多情可以多到没际涯,无情则有限,无情而已。他又说,不知爱,多迷茫于色情;而不知文学,便写些浮薄伤感的诗。确实如此,所以我还是喜欢,他关于旧时爱情的描写。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得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他所追求的爱情,总是轻轻的,淡淡的,就像从前那慢悠悠的日子。那些浅到快要不是爱的那种程度,故能持之以恒;而浓烈的爱必然化为恨,否则就是死。至此,我们也明白了,为何他的爱情,总是风过无声,雪落无痕?是因为他的爱情几乎没有具象的缠绵,或者痴迷,却能达到一种大爱无相的境界。他说,爱情,只是人性无数可能中的,一种小小的可能。
任何回忆都显得是纵欲
木心曾断言,在爱情上,单单浪漫是不够的,以为凭一颗心就可以无往而不利,那完全错了。形象的吸引力,惨酷得使人呼天抢地,而只得默默无言。
甚至于圣洁的心,任何回忆都显得是纵欲。因为爱情本来就没有多大涵义,全靠智慧和道德,生化出唯美的景观。如果因爱情而丧失智慧和道德,即可判断,这不是爱情,是性欲,性欲的恣睢;而凡是因爱情,而丧失智慧和道德的人,总说,为了爱情,我不惜抛弃了智慧和道德。对于他来说,爱情亦三种境界耳。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于审美,而中年以后,则归向求知。
爱或者不爱,都是无法做出的选择
于是,爱情在他心里,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共同体,爱或者不爱,都是一种无法做出的选择。他认为,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就会有写不完的诗;但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就没有这样的世界了。所以,他觉得,说了等于不说的话,才是情话。
在他热烈的爱情颂歌里,也充满着挥之不去的怀疑主义。他写道,“你燃烧我,我燃烧你,我无限信任你,却又时刻怀疑你,我便是这样爱你。”到最后,爱也好,恨也好,都将化为人间云烟。爱是熟知,恨也是熟知。
诗人米沃什的诗歌《礼物》,可谓是晚年木心心境的一种参照。诗中写道,“如此幸福的一天,霧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劳作,蜂鸟停在忍冬花上。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那些曾遭受的不幸,也都已经淡淡忘记。想到过去现在的我同为一人,并不让我难堪;当直起腰来时,我唯望见大海和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