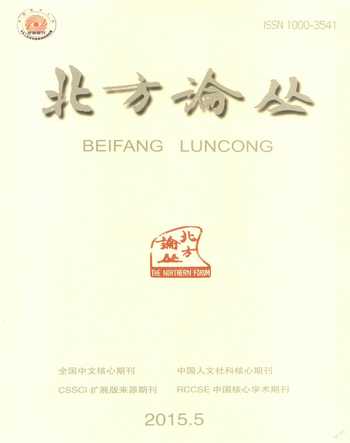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淮河上游的地缘政治与蛮族势力
杨文春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上游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趁势而起的蛮族势力以之为凭借,依违、游离于南北政权之间,但不足以在南北对峙之间成为第三方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一般是作为南北朝的附庸,通过不可忽视的战略角色凸显出来。在这个大动乱的历史进程中,淮河上游原有的地域社会文化逐渐瓦解。通过战争洗礼和蛮族融入而重新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淮西风俗),对淮河上游地域社会产生了长远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淮河上游;蛮族;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5-0078-04
[收稿日期]2015-07-06
① 本文讨论的淮河上游仅以其流经的地理核心为限,范围约相当于今河南省东南部的驻马店、信阳两地,不含淮源所在的桐柏县,亦不含包括河南省中东部在内的整个淮河上游流域。
② 淮河上游所在蔡、申、光三州之政区在唐代才全部形成并基本稳定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区多变,为行文方便,文中有时用此三州代指淮河上游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淮河上游地区一直深陷其中。因其在南北对峙中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淮河上游诸州郡①一直都是南北双方积极争夺的对象。与此同时,应时崛起的蛮族势力以之为跳板或凭借,依违、游离于南北政权之间。不过,以田益宗为代表的蛮族势力,自始至终都是为南北政权所利用的角色,最终没能真正成为南北之间的第三方力量。而蛮族的文化习性则融入四战之地的淮水上游地区,对整个地域社会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一、淮河上游的政治、军事格局
淮河上游地区(今河南省东南部)处于我国地势第二第三级阶梯过渡带(由秦岭余脉至淮河平原),地理区位的独特性和重要性非常明显:地貌多样且层次分明,呈现由山区过渡到平原的特点,山脉、丘陵、河谷、平原错落有致;既是中原、荆楚、江淮三大区域的交通要道,也是军事重镇,在南北朝沿淮对峙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因其特殊的地缘优势,淮河上游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交通路线,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得到开发,是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重要通道之一。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六《河南淮南区》,对该区交通地理有详细的梳理与考证,兹不赘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区交通路线的发达与该地区战事频繁、战略地位直接相关,因而交通路线又多以军事要道的面目呈现。
先简单言及淮河上游蔡、申、光三州②的军事战略地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〇《河南五·汝宁府》对此有非常集中和全面的总结。据其分析来看,蔡州“屏蔽淮、泗,控带颍、洛”;申州“北可以争许、洛,西可以出宛、邓,东可以障淮西”;光州“襟带长淮,控扼颍、蔡”[1](卷五〇,pp.2357-2382)。此三州实乃连为一体,相互牵制,又彼此呼应。淮河上游重要的地理区位,使之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极力争夺的前沿战略阵地,其中以对汝南(悬瓠)、义阳的争夺最为激烈。悬瓠为南北朝兵家必争之地,地当中原、海岱地区入淮上、江汉诸道之枢纽,故自古为重镇也。顾氏专论悬瓠一城在南北朝对峙时期的特殊军事地位:
及晋室多故,南北瓜分,悬瓠之地,恃以屏蔽淮、泗,控带颍、洛。宋大明中悬瓠丧败,而淮北之地遂成荒外,中原声闻日以隔远。历齐、梁、陈之际,南国之势往往折而入于北者,悬瓠不复之故也[1](卷五〇,p.2357)。
汝南郡是东汉中后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士人群体极为活跃。汉末乱世,群雄争霸,曹操与袁绍、刘备等势力对汝南屡次展开争夺。汝南士人随之依附各方诸侯,政治中心地位不再。官渡之战后,曹操击败刘备、龚都,汝南成为曹氏势力范围,并以满宠为太守,削除未归附的地方势力。曹魏代汉后,淮河上游属于战争前线地带,军事地位完全取代政治地位。而这也是南北朝时期淮河上游的常态。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军事普遍实行都督制。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都督制度形成。严耕望发前人之覆,指出都督区在行政区域上的固定性和重要性都超过州域[2](p.24)。淮河上游所属的荆豫都督,明显是以之备吴、蜀两国。甘露四年(259年)后,荆豫都督一分为三,以陈骞都督豫州。豫州治汝南郡安城县,另辖有颍川、弋阳、安丰、谯、陈等郡。在平孙吴之前,豫州都督戍守一方的军事职能十分明显。嘉平以后,镇南将军多都督豫州诸军事。曹魏末期,豫州都督治所已由汝南转移至许昌,应与孙吴式微,汝南地位随之下降有关。司马氏代魏后,都督制与宗室封王结合起来。咸宁三年(277年),司马亮徙封汝南王,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西晋一统后,豫州都督继续镇许昌。
永嘉之乱后,中原官民大量南逃,汝南地区的民众分别避难荆襄和江淮等地区。经此动乱,汉魏以来形成的汝南世家大族与士人群体多已不存。在东晋初期取而代之的是,以流民势力为基础的祖氏兄弟,此外,还有武装自保的其他流民组织。晋室播迁,南北对峙局面初步形成,淮河上游的政治、军事地位亦开始凸显。永嘉五年(311年),石勒大军南下,“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3](卷一〇四,p.2715),汝南王司马祐仓皇逃窜建邺。司马炎在建康复国后,任命怀匡复中原之志的祖逖为豫州刺史,积极备战。祖逖以部曲为核心,大量招募流民,组成北伐军事力量,于建武二年(318年)挫败困于汝南的石勒军队,收复黄河以南大部分失地。此后,祖逖以汝南为根据地,抗衡石勒。同时,在东晋内部政治斗争中,豫州一般扮演平衡荆、扬之争的角色。故祖逖“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乱,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3] (卷六二,p.1697)。作为外来力量的祖氏,并不能将豫州永嘉乱后重新构建起来的地方势力完全统一起来。祖逖死后,其弟祖约更是难以服众。而祖约亦是以豫州为资本,叫板朝廷,参与苏峻之乱。祖约失势叛逃石勒后,祖氏在豫州的影响力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南渡至此并逐渐扎根下来的新“土人”豪族。
此后,东晋内乱不断,虽有桓温等人的北伐,淮河上游地区仍几次南北易手,不可避免地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前沿阵地。悬瓠城与义阳三关等一般是南下或北伐的重要军事通道与据点。东晋末年,刘裕势力崛起,义熙十二年(416年),趁后秦政局不稳之机,率兵北伐,收复黄河南岸广大地区。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后,宋魏两国在淮河中上游连续开战,汝南太守陈宪率领千余将士,在悬瓠城抵抗魏军围攻40余天,得到臧质增援后,魏军败走。这一战也充分体现出汝南悬瓠城在南北对峙中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刘宋后期,爆发了争夺最高权力的义嘉之乱,汝南地方势力亦参与其中。《宋书·殷琰传》详载其事。殷琰为明帝所任豫州刺史,但他不能控制豫州局势,在当地具有支配力量的是当地豪族即“土人”,这些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新“土人”势力,既是豫州叛军的主力,亦是刘宋政权赖以平叛的主要对象[4](p.81)。他们内部斗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豫州的政治走向,不仅使其成为刘宋某一政治集团的一员,而且还最终决定汝南等地的南北政权归属。最后,太守常珍奇的政治抉择使依违于北魏、刘宋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汝南选择了前者。与此同时,淮河上游南部弋阳地区的蛮族势力(田益之等)兴起,开始活跃于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之中。
常珍奇降魏后,包括蔡州地域在内的淮西七郡全部为北魏所得。河南华夏正统之地皆为北魏所有后,淮河一线的战略地位开始发生改变:义阳的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吕思勉注意到了这一点:
南北之兵争,至宋末而形势一变。宋初,中国尚全有河南,魏大武之南伐,中国虽创巨痛深,然虏亦仅事剽掠,得地而不能守也。及明帝篡立,四境叛乱,淮北沦陷,魏人始有占据河南之心,至孝文南迁,而虏立国之性质亦一变,于是所争者西在宛、邓,中在义阳,东在淮上矣[5](p.463)。
以南朝的角度而言,悬瓠乃淮河上游之本,悬瓠失守,义阳则代之。又蔡州多数时间里不在南朝控制之下,淮河上游以申州(义阳郡、信阳军)军事地位最高。如吕思勉所言:“至孝文南迁,而虏立国之性质亦一变,于是所争者西在宛、邓,中在义阳,东在淮上矣。”[5(p.463)义阳又有建安戍,乃“淮南重镇,彼此要冲。得之,则义阳可图,不得,则寿阳难保”[6](卷一三四,pp.4461-4462)。在北朝方面,随着政治中心在中原的确立和边境线的南移,北魏开始对河南、淮北地区进行一些非军事化的管控与经营,试图将其纳入“内地”范畴,此前(延兴四年十一月)就曾“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观察风俗,抚慰初附”[7](卷七上,p.141)。南朝在失去淮北后,更加重视对义阳(司州)、弋阳等军事要地的保护与利用。体现在淮河上游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是汝南的相对隐退和义阳(司州)、弋阳的“崛起”。蛮族势力则成为左右这一格局变动的关键性地域因素。
二、地缘政治中的蛮族势力
蛮族由来已久,南北朝时在淮汉地区极为活跃。一般认为豫州蛮主要分布于淮汉交错地带的山区及其周边,即以今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的桐柏山脉,至大别山脉间为中心。《魏书》卷一〇一《蛮传》大致能说明当时的分布情况:
(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周一良言:“蛮人虽出没无恒,盛衰时异,其分布地域则亘南朝二百余年间无大变动……当时蛮人实跨在南北疆界上。”[8](p.124)淮河上游地区正是长期处于南北疆界上。关于豫州蛮的活动区域的分布,《宋书》卷九七《豫州蛮传》的记载更为精确:“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 其中汝南郡(豫州)是蛮族活动的重要区域,例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使(臧)质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蛮,大破之,获万余口”[9](卷七四,p.1911);《陈书·周文育传》载:“(沈)庆之使(周)荟将五百人往新蔡悬瓠,慰劳白水蛮,蛮谋执荟以入魏,事觉,荟与文育拒之。时贼徒甚盛……。”[10] (卷八,p.137)因蛮族势力依违于此,淮河上游地区颇受其害。《魏书》卷一〇一《蛮传》亦有此类记载:
二荆、西郢,蛮大扰动,断三鵶路,杀都督,寇盗至于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萧衍遣将围广陵(今息县),樊城诸蛮并为前驱,自汝水以南,处处钞劫,恣其暴掠。连年攻讨,散而复合,其暴滋甚。
“自春秋之时,伊、洛以南,巴、巫、汉、沔以北,大山长谷,皆蛮居之。”[6](卷一〇四,p.3273)淮河上游正处于以上区域之间。汉末三国以后,淮河上游地区蛮民的来源与成分越来越复杂,除了先秦时期就生活在这里的土著蛮民,还有源自夷陵等郡的廪君等蛮族后裔,西汉末年以后,大量涌向山林湖泽的中原流民[11](p.116),以及魏晋以来,“逃亡入蛮”的汉民。约言之,除了蛮族土著,流民、盗贼、越族遗民等社会边缘群体往往皆而有之。关于蛮汉融合的认识,后世多着眼于蛮族的“汉化”,而对汉民的“蛮化”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蔡州为例,除了战争因素的影响之外,蛮族的影响是该地区民风风俗表现出犷戾尚武特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蛮族在“汉民”的记忆或文字记载中,多以习性好寇掠的“盗贼”姿态出现 [12](p.52),这与淮河上游蔡州等地原有的“民不识义,惟战是习”[13](卷一四,p.250)“盗贼公行”[9](卷五一,p.1645)“暴悍好寇贼”[13](卷五八,p.1009)等现象基本一致。实际上,南北朝时,已常见将“盗贼”视作“蛮”或“夷”。蛮族势力成为区域性的主导力量后,诸如蔡州等地的民风蛮化现象肯定愈加显著。
据上可知,淮河上游三州皆是蛮民的重要分布区,又以“北接淮、汝,南极江、汉”[9](卷九七,p.2398)的豫州蛮(西阳五水蛮)为主。因弋阳、义阳有桐柏山、大别山的地理形势,蛮族势力尤为活跃。泰始二年(466年),“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攻郭确于弋阳……田益之率蛮众万余人攻庞定光于义阳。”[9](卷八七,p.2209)刘宋以来,蛮族开始成为中间地带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势力。他们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依违于南北政权之间,其中以田益宗家族势力最为强盛。
魏晋以前,弋阳等地已有西阳蛮活动的记载。东晋及刘宋前期,淮河上游多处于南朝控制之下,但少见政府对这里的蛮族采取措施,与其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地方力量有直接关系,亦与弋阳等地在这段时期尚未成为南北对峙的直接前线有关。元嘉后期,北魏南下,西阳蛮随之开始骚动。很快,刘宋政府就采取敌对政策,进行武力讨伐。大明四年(460年),沈庆之出兵伐蛮,西阳五水蛮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一部分退守大别山腹地,积蓄力量准备再次崛起。466年,义嘉之乱爆发,西阳蛮首领田益之与田义之、成邪财、田光兴等选择支持宋明帝,攻克郢州(义阳)。这是蛮族与官方合作的开始,明帝政权马上给予回报:
以(田)益之为辅国将军,都统四山军事,又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田)义之为宋安太守,(田)光兴为龙骧将军、光城太守。封益之边城县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户,成邪财阳城县王,食邑三千户,益之征为虎贲中郎将,将军如故[9](卷九七, p.2398)。
此次合作无疑取得了双赢的结果。在北魏虎视眈眈之下、内部政治形势尚不稳定的明帝政权暂时免除了蛮患之忧,能够进一步控制淮河上游流域,是其蛮族政策多样化的表现之一;西阳蛮势力由此获得了官方认可,稳固了活动空间,有利于发展成为有特定政治利益诉求的地方军事势力。田益之所封的边城县在弋阳郡,势力范围西至义阳。即申、光二州皆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田益之的继承人田益宗是西阳蛮(光城蛮)史上的重要酋帅。由宋入齐后的初期,田氏家族应是继续与南朝保持合作。《南齐书·蛮传》载:“西阳蛮田益宗,沈攸之时,以功劳得将领。”田益宗附魏可能与萧齐改变了刘宋以来的蛮族政策有关。朝廷意欲分化、瓦解以田益宗为首的蛮族势力,手段之一是召其入朝为官,远离弋阳大本营。王延武对此早有推论[14](pp.187-203)。蛮族势力仍是南北对峙中,能对时局产生重要影响的中间力量,而这也是田益宗等蛮酋能够充分利用地缘政治获取生存空间的资本,断然不可能将其葬送。在上述边城、宋安、光城、阳城四地中,光城最北,在北朝南进形势下,光城蛮最易同北朝建立联系。太和十七年(493年),田益宗举众四千余户附魏。北魏孝文帝对此十分重视,派杜纂前去“安慰初附,赈给田廪”[7](卷八八, p.1905),两年后正式对其封官晋爵:
拜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光城、弋阳、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诸军事、冠军将军、南司州刺史,光城县开国伯,食蛮邑一千户,所统守宰,任其铨置。后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为司州,乃于新蔡立东豫州,以益宗为刺史。寻改封安昌县伯,食实邑五百户。二十二年,进号征虏将军[7](卷六一,p.1370)。
东豫州领汝南、东新蔡、新蔡、弋阳、阳安、长陵等郡,治新息广陵城。田益宗的势力范围北接淮、汝,南至长江,西至义阳、宋安,东至举水、白露河的上游。这一范围大体是两晋西阳郡的主体部分。北魏对田氏家族的联合与利用,有效地控制了淮河上游地区,使其在南北对峙中处于优势地位。田益宗则借助北魏的力量,排除南朝的侵扰,巩固自己在淮河上游的势力范围。直至延昌三年(514年),田益宗一直为北魏镇守南疆,为北魏巩固南线、进攻南朝出力颇多。
永平元年(508年),淮河上游悬瓠等地叛魏附梁,北魏、萧梁都在争取田益宗。萧梁诱降的条件与南齐当年的政策颇相似,即以空名头衔相赠而不予实利。田氏在权衡之后,继续效命北朝。史籍记载:“当时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节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7](卷六一,p.1372)作为依违南北之间的地方势力,无论是与南朝,还是与北朝结合,彼此之间都是合作与利用的关系。南朝(北朝)希望利用田氏等蛮酋的力量在稳定当地局势的情况下能够遏制甚至攻击北朝(南朝);田氏则希望充分利用南北对峙的条件,积极巩固、拓展蛮族势力的生存空间。所以,田氏与北魏虽然有紧密合作,彼此之间芥蒂犹存,摩擦亦开始增多。北魏利用田益宗蛮族的首要目的是夺取淮河上游的重镇义阳,巩固对寿阳的占领,控制淮河水道,以确保洛阳安全。这也可视为北魏迁都洛阳后南线对峙的影响之一。北魏在达到目的后,田益宗与蛮人受到的待遇与双方合作前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田益宗子田鲁生在“淮南贪暴,扰乱细民,又横杀梅伏生”[7](卷六一,p.1372)为由,开始对田益宗势力进行一系列的肢解。“年稍衰老”的田益宗已无法纵横依违于南北之间,其子鲁生、鲁贤、超秀辗转魏梁之间,未能复振。蛮族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在南北双方的军事压力之下,逐渐衰落并同化于汉族。田益宗死后,西阳蛮再也没有足以影响南北政局的首领出现。而随着北朝的强势南进与南朝的衰落,南北战事移至长江一线后,淮河上游地区慢慢丧失南北对峙下的地缘优势,不再有产生新的地方独立政治、军事势力的环境。蛮族群体多数转入编户齐民,少数回到山区的蛮民已无力凝结成新的势力集团。同时随着南方开发的加快,蛮民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成为华夏包围之中的“孤岛”。
三、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上游地理区位的政治作用与军事地位相辅相生。蛮族势力没有形成真正具有独立性的地域性政治力量,一般是作为外部强势政治、军事力量的附庸,通过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后世对蛮族的认识,除因史书书写的正统立场带来的偏见外,也与自然环境给蛮族带来的生存压力密切相关。在这个大动乱的历史进程中,淮河上游原有的地域社会文化逐渐瓦解。通过战争洗礼和蛮族融入而重新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淮西风俗)在蔡州等地注入犷戾尚武的血液,为唐后期藩镇割据、叛逆奠定了重要社会基础。南北朝时期蛮族势力未能实现的目标,因而在唐后期历史舞台上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体现。
[参 考 文 献]
[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Z].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2]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房玄龄,等. 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韩树峰. 南北朝淮汉迆北的边境豪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C]//周一良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1]雷翔.魏晋南北朝“蛮民”的来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1).
[12]吴凤家.南北朝时期豫州地方势力与南北政权的关系[D].台北: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4]王延武.豫州蛮和田益宗——《魏书·田益宗传》读后[C]//[日]谷川道雄.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东京:玄文社,1989.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博士后)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