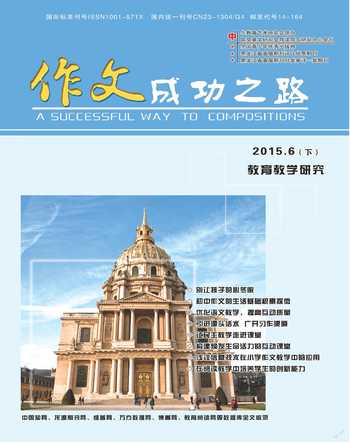飘香的粯子粥
朱文茜
记得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在一起,奶奶喜欢喝粯子粥,平常是隔三差五喝,到了夏天就是一天不拉都会煮一大锅,于是我也早早有了喝粯子粥的习惯。
没事的时候,我就陪奶奶做粯子粥。
奶奶将淘好晾干的米放入锅中,便坐在灶前烧起了粯子粥。奶奶用麦秸秆烧锅,每一把秸秆送进灶膛,立刻就腾起一串红红的火苗。随着火苗在灶膛内翩翩起舞,很快锅子里的水就开始嘟嘟作响了。等到沸水开出一朵朵晶莹的小花之时,奶奶便开始在灶上忙活起来。
奶奶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半瓢粯子,一手持瓢悬于锅的上方,一手拿着勺子。随着她持瓢的手略略抖动,粯子便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飘落进沸水中,另一只手不停地在锅内搅动着。一片片雪花轻轻地落到汹涌的浪花上,又倏地钻入浪花中……很快,锅里的水不再清澈,呈现出一种略显浅黄的颜色。“拔草像马跑,烧灶如烧窑,铜勺像摇橹,锅里像落潮…… ”奶奶一边搅拌,还一边用纯正的靖江话哼哼着,像是在吟唱一首最美的歌。
半瓢粯子洒完了,奶奶又在黏糊糊的锅里快速用明矾在锅里扫一下,然后继续搅拌。这时锅里的粥像被施加了魔术,立刻变成褐红色。浓郁的麦香开始弥漫开来。这香味,氤氲在空气中,经久不散,沁人心脾。我顿时就有了先飽口福的冲动,可是奶奶却制止了我。她说,这时还不是喝粯子粥的最佳时机,粯子粥凉一点喝起来会更香更爽更有味。
终于,在我焦急的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奶奶将一碗粯子粥端在了我面前。我看之,赏心悦目;闻之,垂涎欲滴;而尝之,那浓浓的滑滑的暖暖而又爽爽的感觉,立刻涌遍我全身。我觉得粥里的每一颗米,都柔软而富有韧性。
在靖江,粯子粥是一种再最普通不过的食物,就跟山东的烙饼陕西的馍,蒙古的奶酪云南的米线一样,深深地植入这个地区所有人的血脉之中,它不仅成为这里生活、美食的一部分,更成为这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这里与外地沟通和交往的一部分。
喝一碗仔细熬好的粥,米的醇香在口舌之间缭绕,弥久不散。我想:即使将来,我也成为远离家乡故土的游子,但你醉人的芳香,也一定会伴随我,在每一个清晨,在我居所的厨房内,飘荡,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