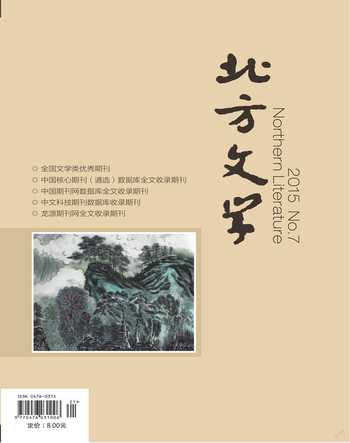那年,我们十八岁
徐宝龙
仰望的天空,是湛蓝湛蓝的。行走的路,却是坎坎坷坷的,留着我们摇摇晃晃的身影。
无法选择梦想,也无法选择现实。火红的年代给了我们一张无法拒绝的,走向生存,走向发光的通行证:矿工。然后,从繁华大都市,被装上火车,载上汽车,到达一千多里路外一个陌生偏僻,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地方:矿山。肉体和灵魂开始被放养。
那年,我们十八岁。
领到崭新的工作服、长统胶靴、雨衣雨裤、安全帽等一套矿工装备,数着预支的四十六元钱,掂着厚厚一叠五十六斤饭票,我们在内心为得到的独立而自豪不已,为第一次富有而乐不可支。
但是,接着而来的上班的艰险,很快使这种快乐云消雾散。站在井口边,看着那个黑咕隆咚,深不可测的大洞,从洞不断冒出的股股寒气,听着钢绳与滑轮支支咯咯的磨擦声,腿已酥软得迈不开步了。费劲地爬进高一米二十,直径一米的被称作罐笼的大铁桶。人与人之间紧挨,像一个个木楔子插着,几乎没有空隙。站在罐的边沿,个子矮小的,仅能露出个头。如果插在中间,那就得鼻子贴着别人的后脑勺,什么也露不出来了。我们静静地站着,大气也不敢出。两声清脆的铃声响过,罐被拉到空中,悠悠晃晃,心被提到了嗓子眼。随着“啪啦”的响声,井盖门打开了,一个黑洞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脚下。
这是一口正在施工中的竖井,大概将近八百米深,还没有巷道和其它的辅助设施。我们这个班的工作,是下去把已经被爆破炸碎的石头清理上来,行话为“出渣”。
铃声又一次响起,信号显示灯闪了三下,罐笼唰地掉入了黑暗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不一会,一股硝烟味扑鼻而来,呛得使人睁开眼。闭上眼睛,心却越抽越紧,一个“死”字在脑海越旋越大。这毕竟是八百米深的井啊,万一钢绳断了掉下去,万一罐笼倾斜把人甩出去……昨天,安全科那个老头还在说,井下安全得很,他干了四十多年矿工,还没死过一回呢。纯粹是胡扯,人还能死两回、三回吗?手无意识紧拽着罐的边沿,汗也在不知不觉中渗上了额头。时间好象被凝固,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看到了灯光,罐笼下降的速度开始慢了起来,在一个悬空着的工作平台稍作停顿后,继续向下落去。
随着“哐”的一声,泥浆四溅,罐笼歪斜着着了底。一个个爬出来,脚跨在近半靴子深的水中,却怎么也站不稳,踉踉跄跄的,像是要跌倒,原来脚下全是刚刚爆破炸开的不规则的石块。还没定过神来,像暴雨一样的水珠就劈头盖脸打下来,在安全帽上啪啪啪直响。几乎已不能自由地睁开眼睛,只有在眯缝的状态下,才可发挥有限的视觉功能。倚着井壁,揪紧的心渐渐舒缓开来,借着从上面工作平台上漏下的暗淡灯光,才看清了身处的环境。这是一个圆形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的平面空间,浑浊的水几乎淌满了每一个角落,只有几块较大的石头和两台抓岩机在水面上露着黑影。还没有经过混泥土浇注处理的井壁,叠满了呲牙裂嘴的石块,委实可惧。但所有的人都只能贴着它站着,也分辨不出谁是谁,被雨衣雨裤裹罩得一摸一样,粗粗看去,活像一尊尊黑色的人体雕塑。
不一会儿,弧光灯亮起。两台抓岩机开启了。巨大的风动的噪音,完全隔绝了耳膜与其它声音的联系。人与人的交流,全靠并不清晰的手势进行。在强劲的风力的驱动下,抓岩机张开四只形似铁锹般的爪子,开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移动,不停往罐笼里装岩石。两个罐笼也开始交替升降,下来一个,上去一个……不算太大的空间里,呈现着十分忙碌的景象。而我们,既要用耙子把岩石从死角扒到抓岩机的有效工作范围内,又要在罐笼提起或着地的时候,拉住它稳定它,不让它碰到井壁或倾翻,还要像躲避飞机炸弹似的,尽可能敏捷地不断移动脚步,以免被罐笼压成肉饼,被抓岩机撞得七窍流血。在这样的场合,容不得你有任何的懈怠和迟钝,所有的动作,几乎都是本能的反应。
不知不觉中,到了下班的时间。回到地面,在更衣室里脱下的衣服,都像从水中捞起来的一样,而靴子里倒出来的水都能用大碗来盛。到了宿舍,只觉得腿也酸,手也酸,浑身上下不自在。晚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以后的日子,心中充满焦虑。
井下死人了,是被塌落的石头砸的。死者是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矿工。
井下工作的危险性自不待言。小的时候看过电影《星火燎原》,那井下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我们的矿是铁矿,远没有煤矿的自然条件险恶,至少是没有瓦斯,而且矿里的生产设备和安全保障设施也比过去要先进得多。但是,危险的现状并没有消失。因此,如果能不下井,恐怕也没有人主动要求下去的。不过,自我们上班几个月来,倒是还没发生过危及生命的事故,因此,尽管始终有担惊受怕的心理状态,但也不至于恐惧到如临末日的地步。当然,正如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样,在井下干活,今天手上擦破了皮,明天腿上磕碰出了血,那是常有的事。即使砸断腿,砸断手,也不算奇怪。
得到噩耗,我们一个个都惊呆了。一个蕴藏在心间的问号,突然化作现实的感叹号。这对于身临其境的人来说,就像一直走在一座长长的危桥上,总是有不祥的疑问,又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否定的回答,而桥真的断了,并且有人掉下去了时,内心受到的震撼不亚于晴空中的霹雷。转而,一串复杂的心理活动开始在静默中不断被牵引出,有惋惜,有悲伤,有恐惧,还有侥幸……
那天,正好轮到我们上夜班。走在路上,本来远远就能看到的井塔楼上的灯光却异常地消失了,漆黑的塔楼无声无息地耸立着,在旷野里显得格外阴森。走到塔内的井台边,只见孤零零的几盏灯亮着,勉强维持着一方空间的亮色。本来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上班的上班,下班的下班,一片忙碌的景象。现在,却是静悄悄的,见不到人影,也听不到任何机器的声响。显然,自从井下出事后,生产已经停了下来。走进休息室,里面却是灯火通明,队长、书记已坐在靠墙的简易条凳上,穿着雨衣雨裤,不停地吸着自卷的喇叭烟,一脸沉重。工人们一个挨着一个进去,自动找地方坐下。往常,这个时候应该是气氛最为热烈的时候。大家可以充分运用这一天中难得坐在一起的机会,拉拉呱,开开玩笑。可是眼下,却一个个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就连几个平时话最多、最活跃的也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人一到齐,队长就站起来,简要通报了井下发生事故的情况,重点强调了安全方面必须注意的问题。接着书记也讲了一番话,希望大家消除恐惧心理,注意安全,继续努力搞好生产。听着的人,几乎没有反应的表情,还是默然地坐着。直到队长书记走出休息室率先下井去了,人们才陆陆续续慢慢站起来,开始换衣服,开始准备工具,也才有轻声的话音……这个班上得特别地沉闷,时间也好象过得特别慢。
两天以后,追悼会召开,我们都去参加了。死者静静地躺着,如果不注意他的呼吸和肢体,与睡着了没有什么两样。几天以前,我们还看到他在沙堆里与人摔交,在食堂里与人扳手腕,在球场上打篮球……这么个活生生的人,却被死神划上了人生的句号,再也不能起来。如果不是那块该诅咒的石头,如果那时他往前或者后退一步,或许,悲剧就不会出现,但这谁能预先知道呢?他的年迈的父母来了,他的一双幼小的子女来了,他那纤瘦的妻子来了……一队不幸的人,步履蹒跚,满面泪痕,前来为不幸的人送行。那悲戚的氛围,那号啕的哭声,仿佛把人间所有的悲伤都汇集到了眼前的空间。我们的心被挤压着,被抽打着,憋闷得喘不过气来,感受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在哀乐的旋律里,我们解读着矿工的人生字典,为常在生死一步之遥的险境中生存的命运的叹息。
失去了一个有形的课堂,却得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纷繁的无形课堂。囿于课本的幻想,被阳光曝晒得无形无踪。犹如被放养的的动物,在一足一爪的前行中,磨砺着肌肤,磨砺着灵魂,烙下通向成熟的印记。
那年,我们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