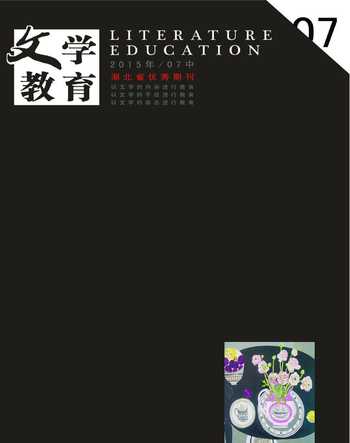我的第一课
童庆炳
1958年冬天,在新一教室(编者注:独立一间的平房阶梯大教室,在学16楼西北角位置)里,我走上讲台,咳嗽两声,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就这样,在台下四百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注视下,我开始了留校教学的生活。
为了准备第一堂课,我不知下了多少工夫,真是体味到了当一个大学老师的不易。因为过去没有写过讲稿,于是要模仿人家的东西,还要逐字逐句改。这时候还谈不到什么创造,无非就是把现成的知识,做个梳理概括。
文学的类型是个较为浅显的题目,国外是三分法,中国是四分法。三分法,就是抒情类、叙事类和戏剧类。咱们中国呢,就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那么就要讲这些文体与题材的特点。关于特点,有很多教材都可参考,但是怎么取舍这些论点,费了很大工夫,我简直是用出了所有的聪明才智,还经常开夜车。我很重视自己的第一课,终于能把第一课的讲稿拿出来了,就请黄药眠先生看稿子。黄药眠先生翻了几页,却说:“你这个字啊,写得太差了,不好认。”然后让一位年轻讲师帮我誊写了一遍,再请黄药眠先生看。黄药眠先生说:“写得太全太多了,有很多东西不是某个文体的特点,而是所有文学体裁的共有特点,这些你总体上讲几句就够了,要删掉。”所以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做修改,真是不知折腾了多少遍。终于到了新一教室,面对400个学生,我讲出了“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讲台。
我的第一课啊,讲的是非常失败的。为什么说非常失败?因为我离不开讲稿,我不能脱稿来给大家很生动活泼地说明一个问题,或者是把一个例子解剖得很细,我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这个课,大家听起来有条理,但实际上就是一般的知识,还是靠念讲稿念出来的,不是从心里面说出来的。现在,习近平主席主张甩开讲稿来讲话,这个非常重要,能说出来的东西这才是真东西。你真懂的东西,才能脱开讲稿说出来,而不懂的东西只能念,念过去了可能你不懂,学生也不懂。
我想,我让那400个学生感到失望了。当然,后来我还上了几次课,慢慢有些提高,但总的来说,讲得都不是很好。对我而言,不可能一上台就能够那么从容,能够尽情地发挥,就像小孩刚刚开始走路,还在蹒跚学步的阶段。下课后,我非常难过,嗓子也讲哑了,出了一身大汗,可是课却失败了,这就是我的第一课。当时,也有别的老师坐着听我的课,看我讲得怎么样。他们也感到不满意,给我提了意见,于是我陷入了教学的困境。
由于讲课的失败,我在文学理论组待的时间不长,便发生了工作的变化调整。在当时教研室主任同时兼系副主任的提议下,硬是把我排斥出了文学理论教研室。系里没有办法,只好把我调到学校的教务处。
教务处分为三个单位,一个是教务处,一个是社会科学处,一个是自然科学处。我就在社会科学处的一个科当科员,每天要上8小时的班,上班的时候只许看报纸、喝茶,但是不许看书。其实,那时社会科学处也没有多少工作,所以白天这8小时过得非常漫长、枯燥、没意思,但是又不能不去。可以说,这就是我在留校以后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但也是在这过程中,我开始了思考:怎么能够提高我的业务水平、学术水平,返回中文系。于是我就开始研读《红楼梦》,一方面因为我对《红楼梦》的确有兴趣,另一方面正好遇到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当时毛泽东的口号是“劳逸结合”,希望大家缩短工作时间,休养生息。但对我来说,那是关键时刻,是决定我还能不能够继续走文学研究道路的关口。所以,我把《红楼梦》真的不知读了多少遍。毛泽东说要读五遍,还有人说要读十遍,我读《红楼梦》啊,肯定不止十遍。我印象里,《红楼梦》这一百二十回的章目,我是全部都能背诵的,又有几章我也能够背诵。据我所知,全中国能背诵《红楼梦》全本的,只有一个人———茅盾,他能把《红楼梦》从头背到尾。你要说背诗词、背古文,这都比较容易,但是要背一部长篇小说,这很难的,但是我当时就冲着这个目标努力的。我先把一百二十回的章目都背下来,然后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章节,特别是介绍性,比如说“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像这些带有概括性的章节,我都背下来了。林黛玉第一次出现在贾府那一回,我也背下来了。我把《红楼梦》弄得滚瓜烂熟,到最后我的论文写完以后,我的脑子都还沉浸在《红楼梦》中。
1962年年底,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这篇文章经过中文系五个教授的鉴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他们写的鉴定就是“思想文字皆好,可以在学报发表”。
那时候,我们发表文章的阵地是很少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也是刚创刊,青年教师甚至教授要发论文都不容易。我的论文受到好评并在学报发表以后,总支决定把我调回教学岗位。这样,我就又回到中文系,还回到文学理论教研室。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1963年夏天,中宣部来北师大,要搞一个“整党试点”,专门批判知识分子中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些人说:“人民内部矛盾当中,有一部分人想成名成家,不想为党工作,要批判这些人。”结果就是,中宣部来北师大搞“整党试点”的中心任务就是各个系都要抓出两个人来,一老一少。在我们中文系,老的就是郭预衡先生,他研究散文与鲁迅,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光明日报》不知发了多少文章,连《红旗》杂志都请他写鲁迅,这被当作“白专道路”的典型给揪了出来。然后,我也被揪出来了,说我在困难时期,不好好响应毛主席“劳逸结合”的号召,竟然去写《红楼梦》的论文,想成名成家,这不是“白专道路”是什么,头脑中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这样,就开始了对我们的批判,整整批了一个月,还贴大字报。最后,我得了肺炎,住进了校医院。但是党组织对我还算好,当我病快好时,他们也决定不再开批判会了。然后,总支的副书记——一位上了点年纪的女同志,到我的病房来征求我的意见:“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派你到越南去工作,到那去当专家。但是越南现在是炮火连天,河内也遭受了轰炸。你去的学校是河内师范大学,有一定的危险。你自己选择一下,去还是不去。”连想都没想,我就赶紧说:“我去,我不怕死。”我想啊,到那里我就能够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备课、静静地给学生讲课了,也就可以不参加国内的这些政治运动了。事实也证明,我1963年去了越南,1964年就是“四清”,所有的人都被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