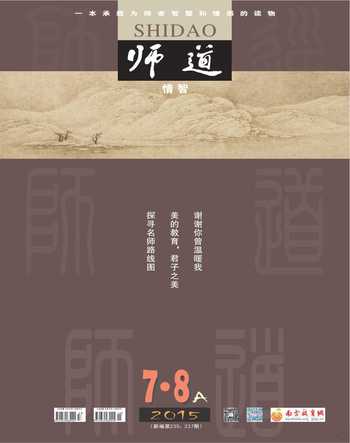职校四年
茅卫东
写下这个题目,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此刻,我已经向学校提交了辞职报告,离开学校干回了编辑这一行。
一
“你在职校当老师,屈才了!”
“学校少了一个好老师,媒体多了一个好编辑!”
熟悉不熟悉的朋友都对我的这一选择表示了理解和支持,认为编辑这个工作更适合我。这与四年前,朋友们得知我离开中国教师报回到绍兴老家,在一所职业学校当了老师后的反应很是一致。当时,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教师报?”然后就是或同情或鼓励:
“你不当编辑记者跑到职业学校当老师,是不是很有失落感?”
“报社少了一个好编辑,学校多了一个好老师!”
我承认,职校四年,我干得很不开心。不过,失落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更没有认为自己必须在哪个位置上,不该出现在哪里。尽管现在许多人——这其中也包括职校系统的各级领导与职校普通教师——对职校和职校生有看法,我的观点是,不偷不抢,学点技术以后能够自力更生,这样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我尊重职校生,同样也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屈才、失落,只是朋友们出于对我的关心而产生的想当然的看法。
因此,当我自己的孩子由于成绩太差上普高无望而选择我任教的这所职校时——我们当地有四所职校可供选择——我完全尊重孩子的意愿,从没想过这是给我丢脸而让他选择其他学校。而且,他选择的是幼师专业。一个一米八四、体重超过两百的男生以后要去当“男阿姨”,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也只能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的选择。我问他:“你知道幼儿园老师要做哪些事情吗?”儿子说,知道。“你觉得你喜欢做那些事情吗?”儿子说,喜欢。“现在幼儿园老师的收入很低的。”儿子说,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最重要,收入以后再说。那就OK。
讲这个事,只是想说明,我对职校和职校生并没有成见,我对自己到职校当老师的选择也没有后悔。
我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如果去当兵,我一定会踏踏实实做一个优秀士兵,但不会想到以后一定要当将军。做了教师,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学生在成长——我指的是在我的影响下的成长,而不在乎职称,不在乎是不是名师。所以,在职校,我没有失落感。当有学生怀疑我也和许多人一样看不起职校生时,我告诉他们,我儿子和你们一样就在这个学校就读。
人的成长,不论身心,都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以为,教师应该是一个安静中助人成长同时自己也得到发展的职业,但现在,这一职业太闹腾了。许多校长抱怨,现在什么部门都可以干预学校工作,教师自然也无法安静地工作,因为各种材料的准备,各种活动的配合,最终是需要教师来完成的。
再说职称评聘。欧美国家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的中小学都没有职称评聘这个事,而我们这块工作倒是越做越精致。以前中小学职称只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档,据说有些聪明而勤奋的教师三十多岁就高级职称到手,从此马放南山,得过且过。领导们看不下去了,将这三档职称又细分为四等,一共三档十二等,每一等级的晋升都有年限规定。这样,拿到高级最高等,差不多也可以退休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倒是让人活到老,争到老啊。但是这种制度的设计者们有没有想过,当一个教师一生的努力就是追求外在的评价和认可,这究竟值得赞许还是认人悲叹?
其实,又何止教师如此,校长们也同样在为争这个级抢那颗星而东奔西跑上窜下跳。
当教育中人已经无法静心思考孩子们的成长,无法静心思考自己的职业伦理,当教育的一切都为外在规定所捆绑,甚至沦为名利场时,这样的教育还能剩下多少教育的意味?此时的教育者还能享受到多少教育工作本身带给自己的乐趣?
这样的闹腾中,学生只能成为教师和学校手中的工具,成绩差、没有特长的学生自然不受教师待见;而教师也只能成为校长和学校的工具,应试水平不够、抓学生不狠的老师当然评不了优秀拿不到职称。同样,重点学校看不起普通学校,普通高中看不起职业中学,而教师群体羡慕编辑这一行,也都不难理解了。
我想,之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当年离开报社回到学校会有失落感,认为我在职校当老师是屈才,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教育被扭曲得太严重了,现在的教师——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太没有职业尊严了。
如果你只关心“这条小鱼在乎”,你愿意看见皇帝没穿衣服,也就无所谓失落,无所谓屈才。
二
扯到这儿,或许会有人质疑:那你为什么在职校干了四年又离开了?
這四年里,我带出了一批学生(11外贸5班,11级学生中入学成绩最低的几十个学生组成的一个班),我给学生上过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和法律、哲学与人生、政治经济生活、现代礼仪等课程;同时,为两个专业部的同事讲过教育写作,也在区职校政治教师教研活动上做过讲座,给退役军人培训班讲过课,还连续三年为本专业部就业班学生作实习前的指导,针对本校文化课课程改革向学校提交一份数千字的书面建议。个人通过培训考试获得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国家职业指导师二级两本证书,出了《重建教师尊严》《心平气和当老师》《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和《怎样的爱才合适——做一个不过分的家长》四本教育类小书,共发表了大概七十篇左右的文章,写有百万字的工作日志,也算没有虚度这四年时间,对得起学生和自己。
关于职校经历,之前我写过三篇相关文章《白天不懂夜的黑——我在职校这三年》《三年班主任,一地鸡毛》以及《还在教育的边上》,拙著《心平气和当老师》里也有专门一章《职校工作日志选》,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络搜索找到相关文字。
我就说说为什么坚持不下去而选择离开。
2014年12月12日下午,在三联韬奋图书馆的一次研讨会上,钱理群在总结发言时说,“告别的时刻到了”,因为“我已经不理解当代的青年了,……网络时代的青年的选择,无论你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都是可笑的,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
虽然钱理群老师比我年长许多,我也没有钱老那样丰富而坎坷的经历,但是读到这段话,还是心有戚戚。
是的,和钱理群先生一样,我也看不懂现在的职校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理解他们的,但他们并不需要我。“无论你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都是可笑的,年轻人根本不听你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这些话,也正是我的感觉,是我想说的。
刚到职校时,我还偶尔可以准备好PPT给学生讲讲时政新闻,还可以让学生提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进行课堂讨论。慢慢地,新的一批学生对校园外的世界不感兴趣了,网游、八卦、韩剧、鬼片这些除外。我开始剪辑《职来职往》《非诚勿扰》这样的热门节目,和学生讨论求职、交友等我以为很实际的问题。开始也不错,越来越多的学生慢慢习惯了先看片断再发言讨论这样的教学模式。但新一批学生来了,他们愿意看视频,却不想讨论。
职校四年,真的非常能够体会到“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这是一个教育者不应该说出来的话,所以我知道我不应该再待在学校了。在给学校的辞职申请中我这样写道:“曾经我以为职校学生有许多是处于迷茫之中,我可以对他们有所帮助。可是四年下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职校生其实并不迷茫,他们只是不想努力。学生懒,这是我作为教师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四年时间我曾尝试过对话式教学、游戏式教学、案例讨论、视频观摩讨论,但几乎毫无效果。”
我知道习得性无助,也看过《热血教师》《死亡诗社》《放牛班的春天》《超脱》等教育电影,或许就像有朋友说的,我不应该有太强的引导意识,而是应该从和他们一起嗑瓜子一起吃饭一起踢球开始。的确,从心理咨询角度来讲,有一种方法是帮助一个人回到原点,快速重新成长一遍。在这个过程中看清楚一些问题的本质,同时满足自己当年未曾满足的愿望。如此,或许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自我。
但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没有能力帮助这么多人重新成长一遍。内心深处,我甚至对这种方法很有抵触。或许,这是我的一大局限。
我们绍兴有个“偷白鲞,咬奶头”的故事。一位母亲从小对孩子百般娇惯,儿子小时偷人家白鲞,母亲不以为怒,反而称赞。结果儿子长大后成了江洋大盗,被判极刑,临刑前借口再吃母亲一口奶咬掉了母亲的奶头,表达对母亲“养而不教”的恼火。
故事中这个儿子的做法,完全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和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当然是有极大的关系,但人不是只生活在家庭里,更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自己的行为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这其实是每一个人自我成长的好机会。每个人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慢慢学会争取、妥协、联手......
不得不承认,在职校生面前,我越来越没有存在感。四年里,愿意参与教学讨论的学生越来越少,愿意和我课后交流的学生越来越少。到最后,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介绍电影,他们很感兴趣,巴不得上课就看这片子了。放学回家,却没有人愿意自己去网上找来看。
在我离开学校前后两个月里,学校发生了三起家长进校殴打教师的事件,幸好都没造成大碍,但对教师的心理影响应该不小。都是局内人,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自有感受。
其實,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教书。站在讲台上,看学生轮番上阵言语激辩;回到办公室,翻开学生随笔看他们或谈观感或发议论或写心事;再找机会,一起外出踏春赏雪搞调查做公益,多好的事……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