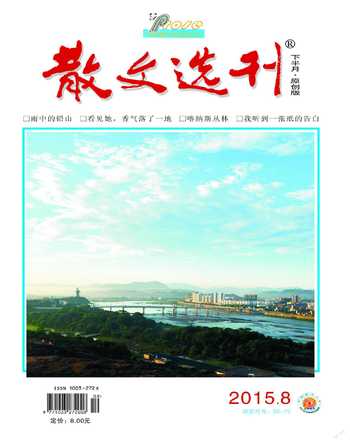书院旁,古道边
喻莉娟
走上铅山鹅湖书院边的古驿道,从不写诗的我,脑海巾竟然跳出两句我也不知道为何物的句子:
千年古茶有余香,鹅湖寺内书声琅。
满眼沧桑,仿佛听到挑夫们歇脚的吼声——嗨~呀!也仿佛听见那“欺乃一声山水绿”的船桨号子;仿佛看到来来去去的文人墨客,凉棚下,端一碗河口红茶……
自唐代开始,武夷山红茶,便畅行世界。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中国茗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河红茶曾经四百多年间,被西方人奉为至尊名茶,誉为“茶中皇后”,西人“能品一盏,竟不问价”。蓦然回首,历史悠悠,这里,不仅留下了朱熹、辛弃疾、陆游、徐霞客的身影,更有那挥汗缓缓而行的崇安担。
武夷山起起伏伏的山路,挑着一担担河红茶的挑夫——多少年了,这条闽赣古道上的货物,就是这样,靠着人力挑运。这些挑夫,来自于武夷山崇安镇,人称崇安担,他们挑着武夷山的红茶,辗转多少个山头,在铅山河口,被称为“茶巾皇后”的红茶,就从这里上九江,再到山西晋中,到河北张家口,至蒙古,达俄罗斯。万里茶道,就是他们挑出了千年古镇河口的繁荣,河红茶就此而扬名。
这些挑夫们,古驿道下的书院,便是他们歇脚的场所。
鹅湖书院,山石作屏。山巅的巨石,千姿万态。两侧山势合抱,重峦叠嶂,古树苍苍,新枝绿叶,苍翠欲滴,山石间,飞瀑倾泻而下。山谷的小平川,古木参天,曲径流泉,幽静无比。书院轻烟笼罩,古老的庭院,就这样静静地坐落在鹅湖山北麓古道旁。
山下,人家,翻过的土地,一道道肥沃的沟垄。眺望这富庶的铅山,唐代诗人王驾的《社日》悠然而浮现在脑海中: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鹅湖书院,因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理学与心学的大讨论,堪称“千古一辩”,遂有了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
朱熹,江西婺源人,因父亲在外做官而出生于福建。他四岁读书,十九岁便巾了进士。他广读儒家经典,现存著作共25种,六百余卷,总字数在两千万字左右。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孟子》一书因朱熹的注解,至此获得了中国古代典籍巾“经”的地位。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暮春,理学大儒朱熹及门生八人,在“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陪同下,从福建寒泉精舍越过分水关,抵达鹅湖。而心学大儒陆九渊、陆九龄也带着抚州家乡的众多弟子,由金溪出发,泛舟东行来到鹅湖书院。在吕祖谦的邀请下,朱熹、二陆四贤大儒相聚鹅湖。
在“上饶记忆”网站中,“鹅湖山翁博客”的博文中描述:“与此同时,散布于南宋朝各处的学者,如江浙诸友、福建学者刘清之、赵景明、赵景昭、朱桴、朱秦卿、邹斌、詹仪之等百余人众闻讯纷至沓来。他们都是胸怀济世雄才和情操的时代骄子,期待着为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建功立业,虽然他们之巾多有命运乖舛者,却始终未能泯灭心巾的希望之火,坎坷与灾难反而成就了他们执着的情怀和瑰丽的人格,摩擦出能够照耀整个时代的思想火花,他们对待国家、对待故园、对待学业、对待艺术、对待人生的态度,足以让历史为他们书写下厚重的一笔。”鹅湖辩论会上,双方各持己见,酣畅淋漓的精彩辩论,令后世的学者万分景仰、崇尚。
鹅湖之会,朱熹难以忘怀。三年后,他写《和鹅湖子寿韵》诗以为纪念。诗言: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淳熙八年(1181年)春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亲率同僚诸生迎接,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席。于是陆九渊乃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提出“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诸生有听而流涕感动者,朱熹当场离席言曰:“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
十三年后,爱国志士、伟大词人辛弃疾与陈亮相会于鹅湖书院,畅谈国事,面对山河破碎的民族灾难,为统一祖国而呐喊抗争,拳拳爱国之心,光辉永照。
这是内容不同,而历史意义俱伟的第二次“鹅湖之会”。而两次双璧“鹅湖会”,使这里飘飞着文化思想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