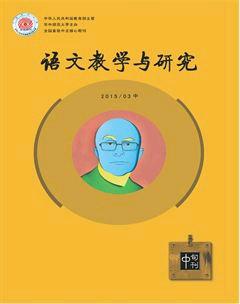高高地俯视故乡
对于故乡,我最初的印象完全是模糊的。刚出生的那几年,我的使命基本上是无端地哭泣和贪婪地吃奶。除此而外,世界好像与我无关。就是到了所谓的醒事阶段,我好像也没怎么特别地打量并审视过她。我只是朦胧地感到,这是一个小山村,小得目光一下就能走完所有的山山岭岭,直达白云深处。但那时我好像也没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似乎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对于一个简单的生命来说,有山,有水,有田,有人,有花在山上开着,有鱼在水里游着,有玉米在田里长着,有鸟在天空横过,这就够了。至于美与不美,以我们的日子做证,那时的我实在没能力拥有这方面概念。
但我还是旗帜鲜明地觉出故乡的丑陋。准确地说,是我到县城读书之后。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游子身份远行。当耳闻目染了两年外面世界后,我一下子觉得故乡是那样的小,那样闭塞,那样贫穷。既没有公路,也没有电灯,甚至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村子整日彻头彻尾地寂静着、荒凉着,好像被上苍丢弃在天地之外似的,整个生活就和原始社会没有两样。再以后,我又有机会接二连三地到了更遥远更精彩的外面世界,这种印象就更加尖锐。
从此,我羞于在外人面前提到故乡,并下定决心做了一个永远的游子。虽然我也常常回到故乡,那也只是为了看望不得不生活其间的父亲母亲及相关亲人。但后来,母亲草草地死去;再后来,父亲也草草地死去,相关的亲人也一个个赴喜宴似的争先恐后地草草死去,故乡越发显得空旷荒凉。至此,我于故乡最后一缕情结随之而断。
坦白地说,作为一个我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故乡,若硬要叫我说爱它,我确乎不能做到,但硬要叫我不想它,分明又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在不经意之间突然回到她身边的时候。
那日,因为工作关系,我和同事到离故乡二十多里的一个地方办事。车子在海拔近二千米的地方的公路上颠簸的时候,我透过玻璃突然看到了山崖下面我的故乡。不知怎的,一种无以言说的亲切一下牢牢地攫住了我的心。我实在有点不由自主,连忙要求司机停车。这之后,我设法找到一个很堂皇的理由让其他人继续坐车赶路,自己则留了下来,一个人呆呆地看着山下故乡。
我这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这么远远地高高地俯视我的故乡,而且是以一种饱经了人间风霜似的苍凉心态来俯视。
坐在高高的山崖上俯视着,故乡是那样的远,又那样的低,然而又那样的温馨。四周山峦环绕交错,坐落着我老屋的山坳中间,恰到好处存在着一块不怎么大但也不怎么小的坪子。山路弯弯,小河弯弯,故乡有如躺在上苍特意伸出的温柔的怀抱中。我第一次觉得,我一向引以为羞的故乡原来是这样的美丽。
此时正值春天。山上大多数树木们还处在一种麻木不仁状态,看着是枯黄的一派,而故乡田里油菜早已开成一派金黄,与碧绿的麦苗交织出一幅锦缎,像是有意打扮了,好迎接远行多年的游子归来。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而故乡的一切也在朦胧泪眼中越拉越近,越来越清析。哦,我见了,看见了我放过牛的小山坡,看见了我打过柴的小树林,看见了我洗过澡的小水潭,我看见了留下了无数欢乐与憧憬的故乡的所有沟沟岔岔,一草一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这个现在正高高地俯视故乡的我,一个一向自命不凡的我,一个自以为将永远生活在精彩的外面世界的我,说到底还不是由眼下这块贫穷的土地上的精微物质孕育而成?说到底还不是由这块贫穷土地上出产的所有能吃能喝的物质一点一点地养育而大?如果没有这个贫穷的故乡,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自命不凡的我。没有故乡,我至今也许仍是一粒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尘土,没有故乡,我至今也许仍然是一个不可名状的混沌的虚无。凭谁问,古往今来的,纵有掀天揭地倒海翻江能力的,有谁能从心中彻底割断故乡情节的?又有谁能真正地走出故乡的?
这样想着,我突然平添了一份深深的羞愧,紧跟着,群山一样连绵不绝的自责袭来。而此时眼下的故乡,分明花开着般地人间天堂般地美丽起来,温柔起来……
高高地俯视故乡,有如天上俯视人间,让我全方位地看到了生命的摇篮,看到了生命的根系,也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最终走向。我知道,此刻,眼下那个小岗儿背后的土地深处,正并排地躺着我的先人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我知道,或迟或早地,我也将步他们后尘,还原为土地的一部分。但我想,当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刻,无论我身在何处遥远的异乡,我的灵魂定会轻盈而急切地飞升起来,越过重重关山,飞临这个生我养我的故乡,就如现在我正做着似的,高高地俯视着她……
吕先觉,作家,现居湖北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