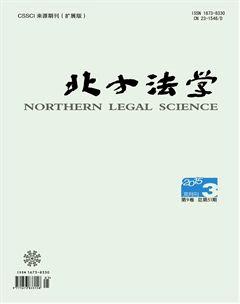论刑法中“应当知道”的教义学意涵
袁国何
摘要:析清“应当知道”的教义学意涵,应当区分其具备的三种不同意义:词源意义、语境意义和类别意义。在词源意义上,“应当”是一个多义情态动词,既可表示推测性判断,又可表示规范性命令;“知道”则具备多元时态面向,这共同决定了“应当知道”具备多元的词源意义。在语境意义上,级次混乱造成了“应当知道”含义探寻的难题,但厘清“应当知道”条款的证据规则属性后,即可将其界定为有间接证据证明的知道,系对故意的认识层面之描述。在类别意义上,“应当知道”是对知道与否的概率判断,而非对知道确切程度的判断,其与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的类别定性没有逻辑关联。
关键词:应当知道多元词义证明故意间接故意
中图分类号:DF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3-0139-10
《刑法》第14条第1款将故意犯罪的认识要素界定为“明知”,司法解释素来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记“明知”的内涵;①新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312条的解释》仍通过“知道或应当知道”来界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明知”。
“应当知道”情形下被告人的心理责任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其与“应当预见”是同一含义还是各自不同?实体法上又是否有别于“可能知道”?本文拟以区分词源意义、语境意义与类别意义为原点,从情态动词的情景语义分析的角度展开论证,区别实体规则和诉讼规则,以期窥得“应当知道”教义学意涵之一斑。
一、规范理解的实然争论与应然方向
刑法学界对我国刑法中的“应知”和“应当知道”究竟是何种含义有多种争论,张明楷教授关于窝赃、销赃罪中“明知”含义的考察拉开了“应当知道”的教义学解读争论帷幕。
(一)理论争鸣的学术演进
张明楷教授认为,“应当知道”本质上对立于“明知”,司法解释之所以将其规定为“明知”的一种类型乃是考虑到明知的证明难度。②新近,他明确指出,《刑法》第219条第2款规定的“应知”实际上是推定知道,而不是过失的不知道。③亦即“应当知道”原本是表征过失犯的认知状况的概念,立法者的真实意思是推定知道,而非要将过失犯纳入处罚范围。同样,陈兴良教授分析指出,司法解释实际上想表达的是推定知道,“应当知道”在文义上实际上是不知道,④不过,二者文法构造的类似性导致了将应当知道理解为过失的不当主张。⑤新近,他主张,需要将较多规定“应当知道”的司法解释还原定性为有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的证据法规则。⑥
与之相应,周光权教授认为,当前司法解释中广泛使用的“应当知道”包含着“实知”与推定知道两种情形,需要区分不同情形而分别借用“实知”与“应当知道”实现司法表述的剥离,实现明知的分级和内涵细化。⑦也就肯定了“应当知道”作为司法推定表征故意犯认知要素的功能,“应当知道”原本即非过失犯概念,而属故意犯语词。新近,王新教授指出,“应当知道”是一个“文不对题的空壳”,且存在与“明知”混搭使用的问题,对洗钱罪司法解释放弃“应当知道”这一富有争议词汇的新动向表示赞同,主张将采用“可反驳的客观推定”这一表述。⑧
就“应当知道”这一语词本身的含义而言,张明楷教授和陈兴良教授将其视为过失犯的语词表达,周光权教授则将其作为“实际知道”与“推定知道”的上位概念,故该词汇并非是过失面向的,而能够容纳故意于其中,赵秉志教授也表达了“应当知道”可以容纳疏忽大意的过失与可推断的故意。⑨除了语词本身是故意面向还是过失指向的争论外,“应当知道”是否包含有间接故意限定的意味也存在疑问。通过分析“应当知道”只能存在于可能知道的外延之内,于志刚教授提出了“‘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的差异与并存”的命题,⑩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可以引入概括性认识而对毒品犯罪进行定罪。B11
(二)实然阐释的三重维度
自“应当知道”首次被使用以来,尽管学界多有争论,但实际上是在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解读的,不少讨论是在自我界定的范畴内展开批评进而提出解决方案的,并未重视解释者的阐述定位,这导致“应当知道”一词的规范内涵至今未得清晰展现,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规范含义的探寻。
其一,在词源意义上探讨“应当知道”的含义,分析该用语在词源上是仅仅指向过失还是可以兼容故意。如上所述,张明楷教授和陈兴良教授即主张,在词源意义上,“应当知道”是指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的疏忽大意的过失,将“应当知道”的词源含义限定在单一理解范畴;B12赵秉志教授则主张,“应当知道”一词既可指疏忽大意的过失,又可指有间接证据因而可推断事实认识的故意,将“应当知道”的词源含义做二元理解。B13
其二,在语境意义上探讨应当知道的含义,探析具体语境下“应当知道”是归属于过失还是故意。周光权教授的主张即是指,在语境表达的意义上,“应当知道”是指推定知道,进而表征故意的认识要素;传统观点则认为,“应当知道(应知)”是指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表现着疏忽大意过失的认识要素。B14
其三,在类别意义上探讨应当知道的范围,争论类别归属上“应当知道”是指向直接故意还是勾连间接故意。于志刚教授即悄然转换“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并将“可能知道”置换为“知道可能”,由此将“应当知道”同间接故意相勾连。B15
(三)应然探寻的三项前提
“应当知道”一词可能存在三个维度上的不同意义,清晰界分学界在三种维度上的理论展开,是进行有效学术批评进而促进学术进步的前提;同时,准确展开“应当知道”在三个维度的本体定位,是获知应当知道的教义学内涵的必由之路;此外,有效分析“应当知道”三个维度间的矛盾冲突之有无及其大小,是探寻司法解释规范化改进与提高的应有前提。
1.区分词源含义与语境含义
“语词的含义不是其固有的,而是必须放在一个运用的背景中去把握。语境是任何理解活动都不可能挣脱的支撑性条件”。B16静态词汇和特定语境下的动态词汇可能存在含义差异,多义语词进入特定句子之后即受到语境制约,显现出确定的内涵与外延,例如,“共同犯罪”字面上兼容共同故意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但我国刑法语境下则专指前者。语境甚至具备改变独立词汇含义的机能,可以赋予词汇某些原本不具备的意涵,日本学者即长期将《日本刑法典》第109条第1项B17的“或者”解释为“并且”,B18形成同字面意思截然不同的语境含义。
立法者总是怀揣一定目的而创制规则、制度,但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使用的语言与欲达目标间可能存在空隙与跳跃,可能出现词不达意甚至文本与内心意思悖反的情形。同时,法条解释过程中也广泛存在着体系解释与个别解释的紧张冲突,有时候需要将同一词汇体系性地解释为统一含义,有时候则需要区分情形分别界定其内涵,进而,同一词汇在不同条文中可能表征迥然相异的含义。解释者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对不同的解释方案进行优劣判定和合理甄别,最终选取合适的解释方案。
因此,要准确发现“应当知道”的含义,必须首先区分应然与实然,弄清语词本身的内涵、外延和特定语境下的具体内涵的差别,前者是作为语词的“应当知道”能否包容故意与过失,后者则是指司法解释究竟是在故意还是在过失的意义上使用“应当知道”。
2.区分概率判断与类别判断
厘清“应当知道”的教义学意涵,还需弄清司法解释将“应当知道”作为“明知”下位类型的目标指向,是为了判断明知的可能性还是其程度?前者是概率问题,判断的核心在于是否明知,进而是否故意;后者是类别问题,关联的是确切与否,亦即究竟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在概率判断中重要的是结论的有无,而在程度判断中重要的则是认识深度基础上的故意的类型。需要分清楚可能性判断的对象指向,不能将概率判断混同为类别判断。
“应当知道”要解决的是对知道可能性的概率判断,是诉讼意义上的证据判断,是依据特定经验规则而对是否将特定自然事实肯认为法律事实的判断,其结论指向知道或不知道;间接故意中的可能性判断是对依证据规则确证的知道的内容确切性的判断,是依据刑法规则的规范分类而对明知程度的规范判断,其结论指向知道构成要件必然充足或可能充足。
3.区分诉讼规则与实体规则
对“应当知道”的理解,需要准确区分司法解释的诉讼规则属性与实体规则属性,即首先必须明白司法解释到底是为了解决程序或证据问题,还是权利义务问题。不同的规范定位关系到对“应当知道”理解的根本差异,可能导致迥异的立场变动。因而,厘清规定应当知道的司法解释的规范属性,是顺畅理解应当知道规范含义的理论前提。
如果将司法解释关于“应当知道”的设定理解为实体规则,理应认为其创设了实体性的行为规范,其使用的应当是祈使句,以表达出命令创设概念。此类规范中的“应当”就必须从规范要求的视角展开理解,义务性正是借由实体规范这一定位进入法律文本的含义之中。
如果将司法解释理解为诉讼法领域的证据裁量规则,即应认为其并未创设实在的法义务,过失论的理解就丧失了根基。证据裁量规则具有经验判断性和取舍性,其强调的是对自然事实的法律拣选,其职能不在于如何判断作为被告人是否具有某种义务,而在于将具备一定证据证明的心理事实归类到故意或者过失的概念之下。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将探讨如下递进式的问题:(1)“应当知道”的词源意义是单一指向的,还是可以容纳多种解释?(2)“应当知道”的语境意义是过失指向的,还是故意面向的?(3)“应当知道”的类别意义是什么?与间接故意有无内在逻辑关联?清晰地探寻“应当知道”的词源意义是判断其语境意义的前提,语境意义又构成类别判断的关联性肯否之基础。
二、词源意义的多元论主张
在词源上,“应当知道”可以做“理应知道”和“必然知道”的双重理解:“刑法中的应当知道也包含两种文义,一种含义是理应知道,强调知道的义务,即行为人预见的义务,是认定无认识过失的前提条件;另一种含义是必然知道,强调知道的状态,一般是故意的认识状态,是一种推定的知道”。B19
(一)“应当”的多重情态含义
汉语中的情态动词可以分为认知情态动词、道义情态动词、动力情态动词和意愿情态动词。其中,认知情态动词,包括判断类和推测类认知情态动词,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看法;道义情态动词,包括权威性道义情态动词和条件性道义情态动词,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使令和允许。B20作为情态动词,“应当”既可表示基于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测,强调“下雨天地应当是湿的”式的普遍联系性,具备认知情态动词的属性;又可表示基于一定权威而发出指令,强调必须承担规范义务,显出道义情态动词的特征。
将“应当知道”中的“应当”理解为道义情态动词,那么,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对行为人预见及避免结果的规范命令,如《刑法》第15条规定过失犯一般。在此意义上,学者在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的共犯问题上,将“应当知道”与行为人的形式审查义务相关联,B21这实际上将主观心理状态的问题转换成了客观注意义务违反的问题。B22相反,将“应当”视为认知情态动词,“应当知道”条款就仅具提示作用,是法官经验判断的书面标准,并不向行为人发出命令,而是对裁判者设定的规则。在此理解基础上,多数学者才认为司法解释实际表达着推定知道或者有间接证据证明知道。
此外,作为虚词的“应当”,具有多元解释面向,应通过考察特定语境中与其搭配的词汇和句子的整体意思,确定该多义词的真实含义,对虚词尤当如此。
由于“应当”具有认知情态动词与道义情态动词的双重面向,欠缺充足的理由在词源理解的意义上将“应当知道”限定为故意或过失,词源的对比分析没有界分故意与过失的充要机能,“应当知道”的教义学含义必须求诸建构在词源边界内的语境理解。
(二)“知道”的多元时态面向
应当知道中是由“应当”和“知道”共同构成的词组,因而,对其理解不能仅凭“应当”的多义性就否定“应当知道”的单义指向可能,如果“应当”之后搭配的是明显的判断性或命令性动词,解释者仍可通过词组内部的相互限定关系确定“应当知道”的唯一含义。然而,“知道”一词具备多元时态面向,否定了这种单义确定的可能性。
作为情态动词,“应当”可通过句式与时态的区分实现含义的特定化。祈使句中使用的“应当”表现出规范命令,是作为道义情态动词来使用的;认知情态动词则在陈述句中使用,以表现经验事实推断。不过,这种区分路径在法规范用语中无法妥当实现,因为法律所具有的行为规范属性使得多数条文都带有命令特征,句式的区分难以清晰界定“应当”的词源意涵。
规范命令总是对当下的人发出,要求人们此后依规范行动,因而带有强烈的未来面向性;判断则带有强烈的一般趋向甚至过去面向,因为判断类认知情态动词是依一般情形与规律而对现实状况进行的判断,推测类认知情态动词则是依据客观规律和习惯表现而对未来状况的预测。在刑事法领域内,推测是没有意义的,B23“应当”只能被作为判断类认知情态动词而面向过去与当下。人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搭配动词是否具有未来面向区分出“应当”的具体含义,然而,“知道”没有明确的时态指向,它并不像“预见”一般显示出明确的未来性,它的时态需借助不同的助词表现过去、现在或未来。于是,词源意义上的单一词义判断失败了。
此外,“预见”和“知道”是一对近义词,都反映着行为人主观的认识面,B24其区分需借由与其搭配的其他词语及上下文特定含义来实现。离开具体语境,没有上下文参照,近义词(“预见”和“知道”)与同一词汇(“应当”)连用时,解释者难以析清各用词的具体含义和个中区别。
三、语境意义的故意论肯认
抽象考察层面的语词多义性,并不意味着唯一意涵不可获知,将多元解释理由与语词多义性相互比对,多义词的确定含义即已时隐时现。规范总是有其表达的意思和其意图表达的意思,较之作为边界划定的词源意义,更重要的是“应当知道”的语境含义,后者真实地反映出规范的意涵,过失论和故意论即系该层面的展开。
由于《刑法》第219条第2款并列适用“明知”与“应知”,体系解释就使得二者成为并列的过失概念,B25这种解释符合刑法体系构建,将“应当知道”作为“明知”下位概念的司法解释应以刑法为准进行矫正,这也能通过将司法解释视为实体规则得到确证。因而,有观点认为,“应当知道”在语境意义上系指无认识的过失。B26然而,该种解释要面临三个诘难:(1)过失定位会导致故意犯与过失犯的同等处罚,违背刑罚同责任相适应的原则;(2)过失主张会导致同一罪名具有双重罪过的尴尬以及轻罪领域过失的不当处罚;(3)过失界定会导致共犯领域肯定过失共犯,违反《刑法》共同故意犯罪的规定。妥当的语境解释是,“应当知道”是指有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能推定其知道。
(一)级次混乱的尴尬选择
刑法规范中的“明知”与“应当知道”存在级次混乱的问题,司法解释未注意与《刑法》用语的位阶统一,二词在《刑法》和司法解释中级次难以协调。B27不同位阶上使用相同或相近词汇的规范,在客观上增添了“应当知道”规范含义的理解冲突,过失界定在此获得了养分。
《刑法》第219条第2款将“明知”和“应知”并列,作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识要素;然而,1992年《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的数个司法解释均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明知”的下位概念。“明知”和“应当知道”究竟是并列关系还是位阶关系,是必须厘清的问题。
级次混乱是清晰梳理“应当知道”体系性地位的最大障碍。将“应当知道”解释为过失的认识要素表征,解决了“明知”与“应知”在《刑法》第219条第2款上并列规定的解释困境,却难以说明司法解释将“知道”和“应当知道”作为“明知”的两大类型的缘由;将“应当知道”理解为推定故意,则难以释明《刑法》第219条第2款的逻辑。严格的同一律要求下,前述两种方案皆难形成完全合理的结论,在此,需要抉择的是,何种解释方案解释力更强且弊端更少。
单纯在语句逻辑关系层面分析,过失论欠缺逻辑上的排他性:解释者固然可以将“明知”解释为故意犯而将“应知”归为过失,但将“明知”界定为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知道,而将“应当知道”理解为有间接证据证明或推定被告人知道,亦能获得生命力。后一种解释既在文本上区分了“明知”和“应当知道”,又未形成前一方案的过失与故意的同等处罚。B28同时,后一方案尚可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B29相衔接,不至于根本悖反共同犯罪理论。
以各司法解释为理论原型的解释方案未必形成对立法的批判而违反教义学原理。《刑法》第219条第2款与司法解释的位阶冲突是由用语产生的,可以通过调整司法解释文字理顺逻辑,不会像过失论主张一样引发教义学的基本矛盾。
(二)同一解释的适用边界
“之所以理解为过失,是将‘应知(‘应当知道)与疏忽大意过失的应当预见对比中得出的结论”。B30亦即,理解偏差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体系解释上的“同一律”适用,即刑法典中使用的“应当”一词理应具备相同含义,这一暗藏逻辑是理解过失论定位的关键。然而,这种体系解释存在问题。
首先,“应当”是虚词。对实词的解释须尽可能遵从同一律,但对虚词的解释应首先考虑其文法,而非从体系角度解读。虚词解释中,重要的是语法结构基础,而非前后的语词照应。
其次,分则用语与总则用语、程序法规则用语与实体法规范用语的阐释,经常出现偏差,不能依据同一词汇的联系而将总则与分则规定、程序法与实体法规则混为一谈。例如,《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分则中也有大量的情节犯规范,显然,不能将但书的“情节”与分则的“情节”混为一谈,否则,要么总则规定成为不必要,要么分则的情节犯规定沦为赘言。程序法规则用语的解释与实体法规则用语的解释,也存在着类似的含义分歧问题。
再次,同一律解释不致重大偏离基本原理才是合规范的,否则,实质合理性将否定同一律之适用,这是一项矫正规则。将“应当知道”与“应当预见”中的“应当”混为一谈,必然导致部分过失犯罪的处罚欠缺明确的成文法提示,并导致故意犯与过失犯的处罚同等化,B31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多项刑法原则的违背形成反制同一律适用的强大力量,因而,必须否定同一解释方案。
最后,同一律适用以句式一致为前提。《刑法》第15条第1款是对过失犯承担责任前提的界定,过失犯在本质上是违反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的义务违反行为,因此,该款系以祈使句式对行为人科以预见义务和回避义务;《刑法》第219条第2款和若干司法解释则是对认知状况的事实描述,系属陈述句式。将后一情形理解为祈使句而呈现出规范命令特征,无法规避悖反前述刑法原则。
综上,就“应当知道”的理解,同一律原本即不应适用,将“应当知道”界定为过失没有逻辑根基。质言之,解释的同一律根本就不能合理反对故意论主张。
(三)证据规则的角色定位
如果将某一规定理解为实体规则,就势必肯定其创设了行为规范,这正是将“应当知道”理解为过失的隐藏设定,义务性正是借由司法解释的实体规范定位进入法律文本的含义之中的,“应当”的理解即应从规范要求视角展开。相反,若将司法解释理解为证据裁量规则,就必然认为其并未创设实在的法义务,“应当”植根于证据规则的经验判断性和取舍性,是对自然事实的法律拣选的应然规则之强调。证据规则的职能不在于如何判断行为者的义务存否,而在于将一定证据证明的心理事实归类到故意或者过失概念之下。在此意义上,“应当知道”是“明知”的一种证明方式,是区别于有直接证据证明的间接证据支撑。B32
笔者认为,应当将司法解释的“应当知道”条款理解为程序法上的证据规则。首先,“应当知道”大量出现在司法解释而非作为实体法的刑法典中,因而,其并不必然系实体法规范,而可能是程序法的认定规则。其次,刑法典中规定的“应知”应被理解为提示性规范,是为方便司法认定而将证据规则纳入刑法典。再次,大量司法解释都是在认定“明知”的意义上使用“应当知道”一词的,其功能目标在于为事实认定提供标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19条第1款即明确使用“认定”一词,B33其证据规范属性已表露无遗。“对于明知的推定,严格来说应该是一个证据法的问题”。B34
厘清“应当知道”的规范属性,能够实现从实体法规范视野向证据法规范定位的思维转换,使《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当知道”的规范含义不再矛盾重重。因而,学者指出:“如果把明知解释为是对这种主观心理的实体性规定,而把应知解释为对这种心理的推定性规定,还是能够对以上刑法规定作出合理解释的。因此,应当知道并非以不知道为前提,而是指并非行为人本人承认的知道,是通过推定所确认的知道。”B35
需要说明的是,司法解释规定一定的情形作为“应当知道”的判断基准,并没有扩大刑法处罚的范围,不存在将原本依据疑罪从无和罪刑法定可以判定为无罪的行为纳入处罚范围的问题。B36诸多规定只是阐明了诉讼法上的证明规则,法院原本即应如此裁断,大量的“应当知道”情形系指有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明知相应的事实,B37而不是纯粹的司法推定,亦非对证明的放松。
即便真正的事实推定,也没有降低证明标准。B38推定仅意味着原本应当被证明的对象被转换为与之存在紧密关联的前置对象,控方仍需依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对该前提事实进行证明,辩方则可针对基础事实和推定结论进行双重质疑与反驳。B39
综上,过失论的解释欠缺合理性,将“应当知道”视为有间接证据证明或推定行为人知道的事实认定方式,是词源范畴内唯一合理的语境解释方案。
四、类别意义的间接故意关联否定
学者从“应当知道”的推断属性出发,通过将“应当知道”限定在确定知道与确定不知之间的可能知道情形中,进而将其与行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或然性联系,B40“应当知道”与“可能知道”就在区分的基础上实现了并存。B41学者进一步指出,“可能知道”是对犯罪对象法律性质的概然性认识,标志着对自身行为的违法属性的放任心态,“应当知道”也就带有一定的间接故意面向。B42值得思考的是,在程度意义上,“应当知道”能否与“可能知道”等同?其是否表达着认识程度不确切的放任意思?作为有间接证据证明的故意的“应当知道”与间接故意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亲缘关系?这些都是“应当知道”教义学意涵必须回答的问题。
前述关联的基础在于可能性的双重含义,即“可能”一词既可以表征对构成要件具有认识的可能性,又可以表现对具体构成要件的认识程度,其借用“可能知道”与“知道可能”的语词顺位调整,将复杂多变的经验判断问题转换成结果相对固定的规范类别归类问题,存疑而可能无罪的案件进入稳定的有间接故意为最低保障的系统中。如果放到英美陪审团诉讼模式下,这实际上将原本应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问题转变成了需要法官裁判的法律问题。如此的设定,违背了法教义学的基本规则。
(一)语言学批判:表达顺位的恣意调整
间接故意主张似乎只是在“可能知道”的内部调换了语词顺序。调换乃是由于:“可能”作为情态动词具有表征估测的意涵,知道可能性判断只能发生在知道本身存疑时;而在知道本身存疑时,行为人对行为客体及后果发生可能性的知道程度也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能知道”与“知道可能”具备经验的同在性。
然而,此种恣意的语词顺位调换未曾顾及整体语义,导致“可能”修饰的对象发生根本变化,引致规范定性的本质差异。“可能知道”与“知道可能”分别描述的是裁判者和行为人主观认识状况。B43
结合《刑法》第14条第1款,“可能知道”的完整含义是“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可能”修饰的是“知道”,表彰的是行为人对结果(构成要件之充足)的知晓概率;“知道可能”则指“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可能”修饰的是“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表彰的是构成要件充足的可能性,是对知道确切性程度的表现。
因此,将“可能知道”还原到整个句子之中后进行的语词顺位调换,即是对主句与从句含义的重大修正。将“应当知道”与间接故意相勾连,面临着擅自变动主从句修饰关系进而改变文本含义的诘难。
(二)逻辑学批判:概率程度的不当混同
将“应当知道”同间接故意勾连的学者指出:“‘可能知道之所以叫‘可能知道,就在于它对特定犯罪对象的认识状况的非确定性,但是,这种非确定性表示的是行为人对特定犯罪对象的一种概括性认识,即有个大体性的认识,而不是毫无认识。”B44
只有真正将“可能知道”界定为知道的可能性,才有助于解决其与明确知道、不知道之间的逻辑衔接问题。论者一方面将“可能知道”界定为与“明确知道”相对的概念,另一方面又将概率性概念通过语词同一性转换为程度性概念,将证据判断转换为类型判断,将事实判断转换为法律判断,看似紧密相连,实则南辕北辙。这种转换导致原本的“对特定对象的认识状况的非确定性”丧失了,代之以认知的程度非清晰性,尽管仍系“大体性的认识”,但已成为肯定认识存在后的认识确切性判断。
间接故意强调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是因为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为放任提供前提性的认知基础。显然,上述的转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间接故意之中意识服务于意志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间接故意的定义是一个实体法本位的定义,其默认的前提是程序上已经有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来加以证实,因此,间接故意是建构在被确证了的认识基础上的放任意识!然而,将应当知道同间接故意相勾连的主张却意图将一个未经确证的认识转换成认识本身的非确切性,这本身就已经与间接故意的实体法展开的逻辑前提是不相符合的,这是对间接故意理论的逻辑误解。
刑事诉讼的精确性特征决定了“可能知道”概念在诉讼和实体上均无意义:法官不可能因为行为人有可能认识到某一事实而确定其故意,这违反疑罪从无原则;心理责任意义上,要么有认知,要么无认知,泾渭分明!可能有认知也可能没有认知的情形,必须分解融入其中。B45“怀疑的认识状态和‘应当知道的认识状态有着根本的不同,应当知道的认识状态归根结底还是知道,即对于行为对象的明确知道,行为人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能是间接故意,在个别犯罪中还可能是过失,而怀疑是对行为对象的不确知,行为人一般均是间接故意,所以不能将二者混同处理”。B46
(三)方法论批判:矛盾转移的非可行性
将“应当知道”同间接故意相勾连意图实现两项目的:其一,判断的简便化;其二,为处罚仅具抽象认识者提供根据。然而,前者欠缺可行性,后者则为责任主义所拒斥。
诚然,法教义学的目标之一在于法律适用的精准化、便捷化。将“应当知道”的经验事实认定通过语词变动转换成识别内容的确切程度的做法,使得原本不确定的结论变得相对确定,有无的判断变成了大小的确定。更为关键的是,此种转换使得抽象认识成为间接故意而应予处罚,即便最小程度的可能认知,如客观运输毒品但仅认识到运输的是违禁品,亦可纳入间接故意处罚。此种连环设定下,疑罪从无即无从谈起,这绝非法网的合理扩张,分明是类推入罪!
实际上,将以语词勾连概率判断与程度判断的主张,亦未导致真正的证明便捷,因为间接故意也存在证明问题。认识程度确切性固然是指对某一对象的认识程度,但此种讨论须以有充足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现实认识为前提,不论该现实认识的程度如何。将程序法与实体法联合表述的间接故意,实际上是指“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证明被告人认识到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此,前述转换意图实现的判断合理性与便捷性无处落脚: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被告人就是无认识的,无认识者即无所谓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有认识过失,裁判者只能考虑无认识过失或无罪。
仅就转换中必不可少的对抽象符合说的证成而言,B47间接故意主张也难以成立。故意的认识要素是意识要素的前提,只有明确知道行为符合某罪构成要件时,行为人才可能产生损害法益或违反行为规范的法敌对意志;相反,即便行为人有违反刑法的意识,但未清楚认识到其行为指向某罪名保护的对象,就不能被认为是故意。例如,如果运输毒品的行为人被欺骗告知其运输物涉及重大商业秘密或国家机密,为防泄密不能走公开路径,故给付其巨大报酬,行为人就难以认识到其运输的可能是非法物品;即便认识到运输的可能是违禁品,也未必意味着可依运输毒品罪处罚行为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行为的对象是毒品。如果要求行为人仅仅认识到行为对象是违禁品,这就违背了犯罪故意认识的基本原理,扩大了毒品犯罪的范围,更增加了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可能性”。B48只有当行为人明确认识到运输的是毒品时才具备运输毒品的故意,若其误以为运输的是珍稀文物,岂能定运输毒品罪!
前述论证并非旨在论证“应当知道”不能与间接故意并存,而是认为二者并无逻辑关联。“应当知道”的教义学意涵,与故意的类别属性无涉。
结论
清晰界定“应当知道”,应当从词源意义、语境意义和类别意义三个维度展开。“应当知道”在词源上兼容故意与过失,在语境解释下则仅指向故意论,其与故意类别没有逻辑关联。因而,“应当知道”须被理解为被间接证据证明的知道或推定知道。
实际上,司法解释包括两大类型:一是以法律含义具体化为目标的法律解释;二是以具体问题的法律定性归类为目标的刑事归类。前者是对法律规则的进一步阐发,后者则是对法律规则的适用。B49规定“应当知道”的司法解释,一方面是对证据规则的释明,另一方面也是对法律文本的司法情形展开。该类条款是交融规范与事实的提示性条款,能够制定或总结的判断规则的有限性与语词包含的现实情状的无限性矛盾,决定了立法应当更加注重抽象规则的建构,具体含义的阐释应通过司法的反复裁断不断建构。指导案例具备较之司法解释更强的连接规范与事实的优越性,更适合承担归类规则创建的职能,类似“应当知道”规则的对法律文本的司法展开,应更多倚重具体指导案例,这也可以减少不伦不类的兜底性解释,更加有效地实现法律明确化。
Abstract:The dogmatic connotation of “should know” should be analyzed by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 including etymologic meaning, contextual meaning and category meaning. As to the etymologic meaning, “should” is a multiple modal verb, which may either refer to presumptive judgment or normative order. The word “know” has plural tenses. Thus the phrase “should know” has multiple meanings in etymology. As to the contextual meaning, the secondary chaos has caused the predicament for exploring the conception of “should know”, but once the clause of “should know” has been determine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evidence rule, then “knowledge” can be decided as an indirect evidence so as to describe the deliberate conception. While as to the category meaning, “should know” aims to decide the probability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which thus has no logic relation with the category defining between direct deliberation and indirect deliberation.
Key words:should knowmultiple meaningsproof of deliberationindirect delib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