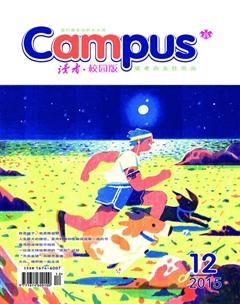我不愿停在这里
我就想谈谈,我是怎么样变成一个导演的。其实我写的第一个剧本《疯狂的石头》,当时叫《钻石》,被一个中戏的老师看到了。他说:“你的这个故事讲得很有意思,正好我带的这个班要毕业了,就把它排成毕业大戏吧。”我说:“好啊,你要是觉得有用,你就拿去排吧。”
我写的东西能被排成话剧,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我觉得原来我也可以进行完整的故事创作。但是当时的问题是,写完《疯狂的石头》也没人投钱拍。因为你算算账,怎么都得上百万元的制作费,所以我就想,那就干脆写个便宜的拍吧,然后就重新写,怎么不花钱怎么写,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故事《香火》。
临到毕业的时候,我说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拍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把我头两年攒的钱拿出来自己投资,开始拍《香火》。
拍完之后,我其实完全不清楚这个片子能够用来做什么,我只是把它拍完了、剪完了,往那儿一放。但是就在我准备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的那个摄影师朋友就跟我说:“有一个香港电影节的选片人来北京了,听说你拍了一部新的电影,你可不可以给他看一看?”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说:“能见人吗?那我就给他看看吧。”我记得当时他只看了一半,因为急着赶飞机,没看完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没戏了。大概一个月以后,我突然收到了邮件,他说想邀请我的电影参加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所以,其实这是我拿到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从那时开始,我觉得我要坚定自己的方向,我要开始做电影导演。紧接着后面我就拍了《绿草地》。当我拍完《绿草地》之后,我就开始在全世界进行第二次免费旅游。我记得那年我在柏林影展放《绿草地》,我数了一下,底下只有40个观众。然后我出来坐在台阶上,突然有个人坐到我身边,我一看是陆川。我们两个就在那儿聊影展,最后我们俩聊着说:“到底拍电影是给什么样的观众看?”不是说每年拍一部电影,跑几万公里去跟几十个观众交流,我希望我的表达能够有更多的观众看到。因为中国电影在海外毕竟是边缘化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拍电影能够给中国人看。我就想,我应该拍一些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这才是我的方向,于是,我下定决心再做一次改变。
回来之后,我在香港参加影展时遇到了刘德华。华哥看完我拍的《绿草地》后,说:“你其实是有做商业片的潜质的,你愿意拍什么电影我不管,我给你一笔钱。”一开始说的是500万,后来变成300万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一笔钱,你想拍什么都可以。”我当时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
所以,我在收到他的这个邀请之后,回去开始想拍什么。这时我把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又拿出来,叫《大钻石》,就是《疯狂的石头》,进行了4个月的改编,就开机了。
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被一个电话吵醒了。电话那头说:“我是韩三平。”他当时跟我说:“我看了你的电影,刚刚看完。我们决定发行。”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了商业电影的怀抱里。
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就是为了拍一部商业片去挣钱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电影是一种文化产品,不提炼出文化核心来我觉得它就是空的,它就仅仅是娱乐产品。
我想了很多,然后重新改组公司时,我说要重新换一个品牌。我在《无人区》的片头加了“坏猴子”的标志,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仅做电影,我们要开始做电影背后的文化。这“坏猴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喜欢好玩儿的东西,然后我喜欢可以改变、有创新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后面做的东西,都符合这样的标准。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导演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没有在我的人生计划当中。大学四年,我学的是画电影海报。毕业之后还画过一张,当时画的是刘德华。画完那一张,我就失业了,因为打印机诞生了。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迷茫是什么感觉,就是站在人生的“米”字路口,觉得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是又完全不知道走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我在金韵琴行,跟琴行的老板张敬云聊天。我说:“其实我挺迷茫的,我不清楚该去哪里。”他当时跟我说:“宁浩,我是过来人。做生意这件事儿呢,非常简单。一毛钱买了,两毛钱卖,你就挣了;一毛钱买了,五分钱卖,你就赔了。而且这件事情呢,对年龄没有要求,你到30岁的时候一样可以干。你现在还年轻,应该先去读书。”
然后临到毕业的时候我就问自己:“宁浩,难道说你就准备这么混下去吗?”我想,我还应该变,我还应该继续改变,我要开始做一个电影导演。
也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那么爱改变呢?为什么那么喜欢改变呢?或者说你就是没常性在一个地方待着?”
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旅途,而在这个向前走的过程中,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问题,我觉得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过去,不要停在这里。改变,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余娟摘自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