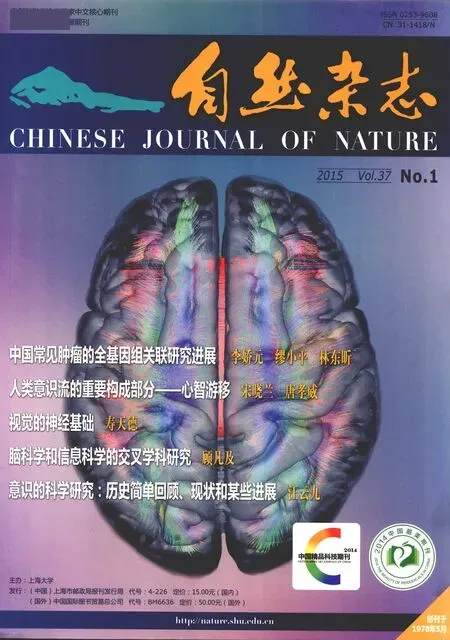意识的科学研究:历史简单回顾、现状和某些进展﹡
汪云九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意识的科学研究:历史简单回顾、现状和某些进展﹡
汪云九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自古以来人们就对灵魂问题感兴趣,但是对于灵魂问题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辨式讨论,到19世纪心理学中的内省式研究,一直到20世纪末的多学科多层次探求,灵魂问题才真正进入现代科学的研究范畴之内。现在意识问题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举出两个事例来说明意识问题的科学研究进展:灵魂出窍和视觉图象识别。
灵魂(意识)问题;灵魂出窍;祖母细胞
1 意识研究的简单回顾
人有灵魂吗?灵魂居住在人体的什么地方?人死后魂归何处?……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人们,但遗憾的是,至今未有人给出一个满意的正确的答案。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 Jung,1875—1961)调查了许多非洲的原始部落,这些部落还未被现代文明侵袭过,而且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通信联系,发现这些部落几乎都相信人有灵魂。虽然各部落的崇拜仪式有所不同,却都认为,世间有神灵。荣格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从而推断人类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考古学也证实,人类祖先远在没有文字记载以前,就相信人有灵魂。因此可以说,宗教和神学是最早关心和对待人的灵魂问题。人们对于灵魂问题的议论和关切程度,远早于现代自然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
意识和人体(包括人脑)的关系问题(brainmind problem)始终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处,brain代表包括人脑在内的人体的物质实体,mind代表情感、意识、智能等精神现象,中文把它译为“心脑问题”。此处的“心”不是解剖学上的心脏,而是泛指所有精神现象的总称,所以,仅把mind译为“认知”或“智能”是太过于狭隘了。文献中常把mind与意识(consciousness)、灵魂(soul)等混用。对于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的不同,哲学上分成二元论和一元论。简单地说,二元论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两码事,精神独立于身体(包括人脑),研究人脑无助于解决精神问题。一元论者持相反论点,认为人体(包括人脑)产生意识和精神,研究人脑可以最终解决精神问题。这两派之间的争论,自有哲学以来就存在, 直至今日仍在继续。
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对心脑问题有过相当深入的思考,并发表巨著《灵魂论及其他》一书。全书包括感觉与感觉客体(7章)、记忆和回忆(2章)、睡与醒(2章)、说梦(2章)和占梦(2章)。《灵魂论及其他》译成中文达453页之多,试想当时还处于羊皮纸和莎草纸时代,所以在当时该书可以说是宏篇巨著了。另一位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etes,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0年)最早认为“人类应当懂得,我们的喜、怒、哀、乐,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大脑”。他明白无误地宣称,情绪、精神来自大脑。希波克拉底可能是最早的一元论者。
中世纪数理科学家笛卡尔观察到人脑由左右两半球组成,而灵魂只有一个,因此不可能在大脑半球上产生;松果体仅有一个,却深藏于大脑深处,因此他推断松果体产生灵魂,由它控制支配大脑,并最后指挥整个躯体。哲学家虽然把意识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数千年来发表和出版了无数的理论和观点,二元论和一元论之间争论不休,但是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是思辨式的,从语言的描述到理论的阐述,没有试验结果和数据,所以只能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派系林立,取得的实质性进度不多。
19世纪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地把意识问题作为它的主要研究对象。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Wilhelm Wundt认为,心理学就是研究意识的科学。由于缺乏合适的仪器技术,心理学中研究意识的方法是“内省法”,即受试者说出当时的主观感受,记录下来加以分析和做出判断。这种方法类似于“黑箱理论”(black box),根据输入剌激和输出反应,得出规律,对于其中实际过程是不得而知的。当然这种研究方法比哲学中的思辨方法略为进步一些。20世纪20年代John B. Watson在心理学中倡导行为主义理论,他认为:“人从来没有看见过意识,摸过它,嗅过它,尝过它,动过它,……对于行为主义来说,意识与灵魂基本上是同一概念。”从而把意识问题排挤出心理学,一时间行为主义成为心理学的主流,无人再敢问津意识问题,这一趋势统治美国心理学达半个世纪之久。
20世纪中叶,由于控制论、信息论的理论影响,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所谓认知科学家,他们具备良好的数理基础,受过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训练,又会编程和使用计算机,在研究人的智力行为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数学中证明数学定理的计算机程序被编制出来,电子计算机与人对弈可以战胜世界冠军。一系列的智力行为的规律被研究出来,用计算机实现。于是,人工智能创始人Minsky当时断言,20年内可以造出模拟人脑的电脑。一时间人工智能专家和认知科学家欢欣若狂,认为人脑的一切功能将要被计算机复制和取代。但是1989年英国物理学家 Penrose发表《皇帝新脑》一书,对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提出质疑,认为计算机在人的逻辑思维方面可以模拟再现,但是在日常经验和常识方面却无能为力,更何况人的感情、意识等方面的问题,完全摸不着头脑,于是,意识问题又重回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中来了。
2 研究意识的现状
在谈到意识的科学研究时,不能不涉及它的物质基础——脑科学的发展。脑(神经)科学在20世纪从生理学内一个不起眼的小分支,发展成为一个壮大的学科,以致英国的《自然》杂志专门设立一个分册来报道这一方面的发展。回想100年前,人们对于人体中最神秘的器官(脑)的理解还是十分粗浅,只知道脑看起来像一团均匀的蛋白冻状的浆糊。1873年意大利组织学家Camillo Golgi(高尔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细胞染色法,叫做银染色法。用这种方法可以把神经组织中少数神经细胞着色,并呈现神经细胞的细节。西班牙组织学家Romany Cajal(拉蒙-卡哈尔)运用Golgi发明的银染色法,并加以改进,对神经系统进行了大量研究,创立神经系统的神经元理论。该理论认为神经系统并非连续一片,而是由一个个的细胞组成的,其基本结构和功能单元是神经细胞,也称神经元。1906年Golgi和Cajal两人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由于电测量仪器的使用,发现神经细胞有活动,神经信号在神经轴突上传播。Hodgkin和Huxley由于弄清了神经信号的传播规律而获196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John Careu Eccles,他的贡献在于证明神经脉冲到了突触(一个神经细胞与另一个神经细胞之间的接头部分)后,分泌神经递质,影响下一个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同样也是使用生理技术,Hubel和Wiesel因在感受野方面的贡献,获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全仗于物理技术手段——电生理技术的应用。
因此,到了20世纪末,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突飞猛进为意识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意识的科学研究历程中,1994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当年有两件大事作者认为值得载入史册:一是关于意识研究的多专业国际会议开始举办;二是Crick著述的《惊人的假说》出版。
1994年第一次“走向意识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TSC)”会议在美国Tucson市召开,这是第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会议开得热闹非凡,各种专家莅临大会,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而后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双数年在Tucson开,单数年在其他国家召开。至今已20年,一次不落。
1998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成立了一个意识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sciousness Study,CCS),该中心主任兼奠基者是Stuart Hameroff教授,合作奠基者为David Chalmers(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该中心成立的目的是联合哲学家、认知科学家、神经科学家、社会学家、医生、物理学家、艺术家和人类学家,共同研究人的意识问题。
1997年国际性学术联合会——意识的科学研究学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ASSC)成立并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此后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每次有一个主题。例如:ASSC-2主题是“意识的神经相关物”,ASSC-3主题是“意识与自我”等 。ASSC至今已召开了18次,遗憾的是,这一系列会议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召开过。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F. Crick发表《惊人的假说》一书。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本书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意识的奥秘。”此话表明,他想把意识问题从神学家的崇拜、哲学家的清谈、心理学家的内省中解脱出来,放到现代科学家的实验室中,通过显微镜观察、手术刀解剖、物理仪器检测,把千万年的世界之谜——意识问题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来研究。这一观点与1997年成立的ASSC学会的宗旨是一致的,与1998年亚利桑那大学成立的意识研究中心的目标也是相同的。他在该书第一章中的第一句话:“惊人的假说是说,‘你’,你的喜悦、悲伤、记忆和抱负,你的本体感觉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这句名言被许多期刊杂志和书籍所引用。他在这句话中表述了意识问题是神经系统(脑)的产物,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一元论观点。因此可以说,《惊人的假设》一书是对意识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旗帜和进军号。20世纪末意识问题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多个学科研究的焦点,其中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Eccles(发表7本著作)、Edelman (发表4本著作)、Sperry、Crick等,以及国际著名学者Pernose、Minsky等。他们原先各自在所从事的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后来关注意识问题,著书立说。Edelman是因为免疫学方面的研究而获奖的;Pernose是著名的数理科学家,他的《皇帝新脑》一书,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Minsky是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他们或发表演讲,或出版书籍,对意识问题的科学研究发表看法。在这些名人中,尤以F. Crick更值得一提。他是因为DNA的双螺旋结构与Watson一起荣获诺贝尔奖的,他们的贡献被誉为20世纪三大基础理论之一(其他两项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获奖以后认为,生物学中的遗传、繁殖复制和变异问题,基本上可以用他们的DNA模型解释,而意识问题是生物进化的最高阶段——人类的头脑的产物,为此,他要做充分的知识准备。他花了30年时间,恶补了神经科学、脑科学、解剖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到1994年才出版他关于意识方面的书籍。此时离他获诺贝尔奖的1962年已有30多年时间,期间他没有令人瞩目的工作发表,一直在坐冷板凳,酝酿孕育这本巨著的发表出版。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意识问题的科学研究方面,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从各个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进行探索,使用的技术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提出的模型理论形形色色。有从细胞内的微观结构来考虑意识现象的,也有从整体和社会角度研究的;有从单个神经细胞的活动来研究的,也有从神经集团的活动来考虑的;……。 一年两次的国际会议足够供他们交流和讨论。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一个“脑的十年”计划,这个由美国众参两院通过的科研法案,支持对脑科学进行研究。2013年美政府又通过一个BRAIN(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计划,每年投资1亿多美元,为期10年,开发试验对脑进行深入研究的技术。差不多同时,欧盟也每年投资1亿欧元,实施脑研究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HBP)。这些政府资助的大型研究计划,表明社会和民众对于脑研究的重视和关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意识问题的科学研究。
美国最著名的科普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也有《Mind》分册,专门刊登神经科学和意识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果你上网查找consciousness一词,就会跳出数万条条目;到Amazon查找“意识”方面的书籍,起码有上百本专著和科普书籍,其中不少已译成中文,如Crick的《Astonishing Hypothesis》、Edelman的《A Universe of Consciousness》、松本修文的《心灵之谜面面观》、Koch的《The Quest for Consciousness》等等,已有10多本。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参考文献中仅列出中国作者撰写的著作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译作[1-6]。
3 意识的科学研究的某些进展
在20世纪末开始的意识研究中,科学家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意识现象和病理现象进行研究,取得许多有意义的结果。本文仅从浩若烟海的研究报告中,选取两项作者认为有意义且有重大进展的成果介绍给读者。
3.1 灵魂出窍(out-of-body experience)
“灵魂出窍”一词常出现在民间传说之中,严肃的科学家好像避免谈这一论题。进入21世纪以后,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等国际顶尖科学刊物陆续登出一些科学家进行的实验工作,表明正常人在一定实验条件下会出现灵魂出窍的现象,并寻找出大脑主管灵魂的解剖组织的部位。《科学》杂志在2007年8月24日这一期上,刊出两篇心理学论文,描述灵魂出窍的实验。Miller G.为此在《本周新闻栏》上写了一篇短评——《灵魂出窍经验进入实验室》,简单介绍了这两个实验工作。第一个工作是瑞士的Lenggenhager 和 Blanke 等四人做的[7],他们令健康的成人头戴特殊目镜,目镜中只能看到摄像机拍摄到的和经过处理后的虚拟景物。实验时摄像机放置在被摄物体后2 m处(图 1)。这个实验在三种不同条件下进行:在第一种条件下,摄像机放置在被试者身后(图1(a)),被试者看到自己的后背——这个虚拟的身体;第二种实验条件下,摄像机放在一个假人背后(图 1 (b));第三种条件下,摄像机放在一个直立的立柱后面(图1 (c))。这三种情况下,被试者看到的分别是自己的背后、假人的后背以及一个立方体。我们权且把这三种见到的图像称为“化身”。实验进行时敲打被试者身体,而让被试者看到图像化身时也看到同步或不同步的敲打过程,当然,这需要用电脑稍作处理才能达到这一效果。敲打一分钟后,关闭摄像机,被试者看不到任何影像。然后把被试者拖离原先站立的地方,脱掉眼镜再叫他走向他原先站立的地点,有趣的情况发生了。在第三种实验条件下(即观看的是立柱图像),被试者可以毫无困难和差错地回到原点。如果敲打身体与敲打化身的节奏不同步,不论是第一种情况(真人)还是第二种情况(假人),被试者也能顺利地没有差错地回到原点。但是敲打身体与敲打化身同步情况下,被试者走到原先站立点前面几步的距离,这个距离正好在虚拟的“化身”附近。因为在这个实验条件下,被试者看到的视觉图像与他身体感到的触觉(敲打)信息联系到一起,自我感觉融入到化身中去,也就是他的灵魂从自己的肉体中出来进入到了“化身”中去了。
另一个心理实验是瑞典科学家Ehrsson做的[8]。实验条件类似于上文介绍的那个情况,也是头戴特殊目镜,目镜中只能看到摄像机送来的景物,摄像机放置在被试者身后,被试者仿佛在自己的身后。实验时拍打被试者的胸部,同时让摄像机也能拍摄到手的拍打动作。拍打几次以后,被试者感到自己仿佛进入到目镜前面的虚拟人体中去了。这是被试者的主观感觉,有没有客观指示来测定这种变化呢?Ehrsson把电极放置到被试者的手指头上,然后用榔头在镜头前虚晃一下,被试者看上去好像要打到自己身上,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及他,因为被试者已经把前面的人体看作自己的身体,他吓一大跳,手指的电极测到电阻的变化,表示这种心理感觉已经有生理学上的反应。

图1 正常人在清醒状态下诱发灵魂出窍现象的实验安排[7]。令被试者戴上特殊目镜,他只能看到从摄像机送来且经过电脑处理的图像,在三种不同情况下进行实验:(a)摄像机拍摄的是被试者的背影;(b)摄像机拍摄的是一个假人的背影;(c)摄像机拍摄的是一个长立柱
上面介绍的两个实验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对健康人清醒状态下进行的实验,使用的主要刺激是视觉并伴以触觉刺激,让正常视觉中止,而给予摄像机摄取的情景,同时给予身体上的触觉刺激,使得“灵魂出窍”过程有切身体验。而且拍打刺激与看到的节拍同步的话,会加速这种出窍过程。
Blanke等人在《自然》上发表论文,报道一位患者(43岁妇女)的头部电刺激实验,表明已经找到负责“灵魂出窍”的部位,它位于大脑的右角回区(angular gyrus)。该患者受癫痫病之苦已有11年之久,磁共振成像技术看不出器质性病变,因而找不到癫痫发作的中心,只好使用颅下植入电极以便精确定位。电极植入后可以通电刺激,患者可以口述她的感受。当植入角回电极通电时,患者说她好像“沉到床下去了”“从高处落下来”的感觉。增加电极的电流幅度,她报告说“我好像从高处看到自己躺在床上,但只看到自己下半身的腿。”后来她多次报告浮到空中2m高,靠近天花板。后来Blanke等人使用“透颅磁刺激”技术,发现大脑顶颞联结部(temporoparietel junction,TPJ)是负责“灵魂出窍”感觉的关键部位[9]。
灵魂出窍现象在正常人身上也会发生。中国著名电影演员李诚儒在接受访谈时说,每当他演一角色十分入戏时,他感到他自己仿佛从戏中出来,在一旁观看自己在演戏。在一些重大手术的患者报告中,常有人提到自己的灵魂从肉体中飘出来,在高处观看自己的受伤的肉体,或者抢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视觉好像仍在工作,躯体感觉和本体感觉也继续在活动,而其他感觉似乎退居次要地位。
人去世后意识丧失,民间认为是灵魂逸去。有的人死而复生,恢复了意识,俗称 “还魂”。这种幸运的人值得好好研究,他们经历了“濒死”经验(near death experience,NDE)。现在世界上有专门研究濒死现象的学术组织和出版物。这些死而复生的人,其中多数报告在临死前并非恐惧和恐怖,而是思绪平静,感觉像在黑暗隧道中飞向光明的远方,有的还感到亲人相逢时的幸福感。1976年唐山大地震24万余人死亡,16万余人受伤,其中不少人从死亡边缘被抢救过来。天津安定医院冯志颖和刘建勋对这些患者作了调查研究,结果发表在《大众医学》1993年第5期上。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3.2 视觉图像识别
眼睛是五官之首,人眼的功能之中,尤以人眼图像识别最为复杂精巧。婴儿出生后在没有语言能力前,就能识别父母亲和陌生人。许多野生动物,出生就会分辨敌我。这种神奇能力,至今仍未彻底搞清,虽然20世纪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中有五位科学家在视觉研究中获此殊荣,但距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距离。
20世纪神经科学从生理学中独立出来成为茁壮成长的一门学科,在视觉研究方面取得最重大的成果。首先,Hartline把感受野概念引入视觉研究。所谓感受野(receptive field,RF),就是视觉系统某一水平上的神经细胞所对应的视网膜区域,在这区域中给予光刺激,可以引起它的不同反应。根据它们的不同反应,可以分为三大类。20世纪50年代 Lettvin等发现在青蛙视顶盖上的神经细胞可以分为五大类,有的对小虫样的图形有反应,有的对巨大的阴影有反应……。总之,蛙视觉系统中的细胞对于它生态环境中有影响的图形更敏感。这些细胞天生就有的,处于相对高的地位,对于特殊图形才有反应,称为祖母细胞。20世纪中叶Hubel 和Wiesel 在猫的视皮层上发现神经细胞对于非对称性的图形边缘有反应,而且这些细胞在皮层上形成功能柱结构。1972年Barlow把这些实验结果总结为“神经还原论”,认为视觉图像功能可以由层次越来越高的神经细胞来完成。所以,部分学界人士和民众简单地认为,视觉系统某个高层细胞对应一个特定图形。但是,像人脸那样的复杂图形,在不同光照条件下、不同视角下呈现完全不同的形象,那么,一个人的面孔就应当对应视觉系统中许多许多个细胞。这样一来引起组合爆炸,人脑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要求,于是,神经还原论似乎陷入危机之中。
但是到了21世纪初,一些在人脑内用电生理实验获得的结果却使得老祖母理论死灰复燃,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电生理学方法因有一定的破坏性,所以绝大多数实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而动物难以精确表达对复杂图像的认知程度。事情到了21世纪初出现转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Quiroga等人,有幸在清醒的人脑上直接记录个别神经细胞的电活动,并获惊人的发现[10]。有的癫痫病人需要动手术切除发作中心,但用传统方法(脑电方法、核磁共振成像方法等)有时难以准确定位,在癫痫病人的脑中植入微电极可以精确定位癫痫发作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患者同意做一些附带的实验以便对科研做出贡献。Quiroga等人在8名患者身上研究,总共记录了993个单元(343个单细胞和650个多细胞)的反应,发现其中有132个单元对特殊图像有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反应,占总数的14%。这些细胞位于视觉系统的颞侧通道的较高层次上,有的还分布在海马区、杏仁核区、内鼻皮层区等部位。这些细胞中每个细胞(或一小群细胞),只对一系列图像中的某个特殊图像有反应。例如,有一个女患者杏仁核部位的细胞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素描和油画像有特殊反应,而对其他人物或建筑物或风景照片没有什么反应,而且不论克林顿穿什么服装或摆什么姿态,或者照相角度、大小都不能改变它的反应,甚至克林顿的英文名字出现在屏幕上也会引起这种特殊反应。可见这个细胞只对这个特殊“事物”有兴趣,而且存储了它最本质的东西,超脱了一些无关因素——背景、服饰、大小等等的影响。

图2 从一位患者的左后海马部位记录到只对演员J. Aniston的照片有反应的某个神经细胞的活动[10]。(a)该细胞对30幅照片的反应情况,每幅照片上的数字是该照片的编号,照片下显示该照片出现时这个细胞反应的光栅记录和组织图;(b)横坐标表示照片的编号,纵坐标表示该细胞对某照片显示时300~600 ms内神经脉冲发放数
这些实验具体进行过程如下。先在被试者颅骨上打孔插入电极。然后做预备实验,询问患者的兴趣爱好,在一大批被试者熟悉的人物、著名建筑、动物和物品中选出实验图片,数量大约100张。对这些有反应的图片,再制作一些它的“变种”图片,例如不同角度拍摄的建筑物,不同服饰的人物照片。在实验阶段随机显示这些图片。实验中,被试者不必用言语表达个人感受,他们的实验结果完全基于微电极上记录的电活动。图2是一个典型的实验结果。记录部位是被试脑中的左后海马区,这个细胞只对女演员J. Aniston的不同视角的照片敏感。图2(a)列出这个细胞对87张试验图片中的30张图片的反应。最上面一行是显示图片及其编号,中间一行是光栅记录,最下面一行是刺激后该细胞反应的组织图。图2(b)是这个实验结果的另一种表达,横坐标是显示图形编号数,纵坐标是该图形显示后300~600 ms内神经脉冲发放数。图中可看出,被试者左后海马上的这个细胞对女演员J. Aniston的各姿势和服饰的照片(编号在5左右和30左右)感兴趣,而对其他人物照以及建筑物只有很少或完全没有发放脉冲。有意思的是,该细胞对Aniston与男演员B. Pitt的合影不感兴趣(图2(a)中的第6、7、67号照片等)。在另一个被试者脑中发现对男演员H. Berry感兴趣的细胞,而且对屏幕上出现“Halle Berry”字母时,也有强烈反应,但该细胞对其他人物头像或者建筑物或者人名都不感兴趣。
这些结果表明,至少在视觉认知的高级部位和记忆部位可能用少量的神经细胞编码某个客观事物。Quirogo等人认为,这些细胞对事物的整体敏感,而忽略它的具体细节,而且对于文字和语言有相同的反应,因此可以把它们称之为概念细胞[11]。当初Lettvin估计一个人或物大约对应18 000个神经细胞,而Quirogo等用统计方法估计一个概念触发100万个神经细胞的兴奋。这个估计仅是上限,可能实际使用不到1/10,或许1%。这样就与Lettvin的估计相差不多了。一个人能够记住的概念通常不超过一万个,而内颞叶约有十亿个神经细胞,足够用了。可以想象,一个概念在脑中以稀疏方式编码,用比较少量的神经细胞表达一个概念,代表一个人、事、物,而且具体某个细胞又可以参与不同概念的表达。
精神病学研究从另一侧面提供了一些线索。1947年一位德国神经学家报道,一位男性患者在遭受头部枪击后丧失了识别家人、朋友甚至本人面容的能力,称之为面容失认症(俗称“脸盲症”)。早期记录在案的这种病人不过区区百人,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大约有2%的人患有这种病症,而且大多数病人本人不知自己患有这种怪病,他们依靠其他信息(例如声音、肤色、体形、个头、发型等等)来识别对象。此病的严重程度也各有差别,有的只对面容识别有困难,有的却对更简单的物体识别也存在困难。遗传学研究表明,有的患者具有遗传史;病因学研究表明,儿时眼睛疾病(例如弱视、斜视、白内障等)会造成此种疾病。心理学训练可以改善此种症状,神经系统的衰老可能会加剧症状的严重性。
到现在为止,人类对于视觉图像识别的原理和机制的认识,大约就到这一步,离开彻底解开这个谜团,尚有一段距离。
(2014年11月21日收稿)
[1] 唐孝威. 意识论——意识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 弗兰西斯·克里克. 惊人的假设——灵魂的科学探索[M]. 汪云九, 齐翔林, 吴新年, 等, 译. 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8.
[3] 汪云九, 杨玉芳, 等. 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研究及其意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4]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朱利欧·托诺尼. 意识的宇宙——物质如何转变为精神?[M]. 顾凡及, 译.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3.
[5]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第二自然——意识之谜[M]. 唐璐,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6] 杰拉尔德·埃德尔曼. 比天空更宽广[M]. 唐璐,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7] LENGGENHAGER B, TADI T, METZINGER T, et al. Video ergo sum: manipulating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J]. Science, 2007, 317: 1096-1099.
[8] EHRSSON H H. The Experimental induction of out-of-body experiences [J]. Science, 2007, 317(5841): 1048.
[9] BLANKE O, MOHR C, MICHEL C, et al. Linking out-of-body experience and self processing to mental own-body imagery at the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5, 25(3): 550-557.
[10] QUIROGA R Q, REDDY L, KREIMAN G, et al. Invariant visual representation by single neurons in the human brain [J]. Nature, 2005, 435: 1102-1107.
[11] QUIROGA R Q, FRIED I, KOCH C. Brian cells for grandmother [J]. Scientific American, 2013, 308(2): 30-35.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 Brief history, present state and some progresses
WANG Yun-ji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rian and Cognitive Science,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It is a long history for study of brain-mind problem. Since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a new era has been initiated to investigate consciousness by mean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are many progresses in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 In this paper, two examples of consciousness progresses are represented: out-of-body experience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in visual system.
brain-mind problem, out-of-body experience, grandmother cell
(编辑:沈美芳)
10.3969/j.issn.0253-9608.2015.01.00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27117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