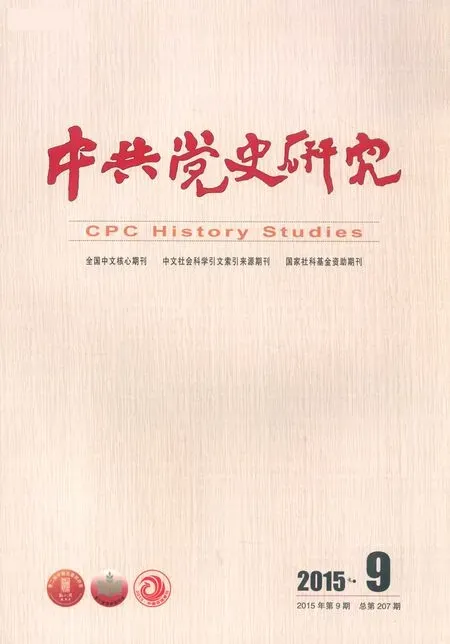追求教育平等的尝试:小学新学制改革及其影响(1950—1953)*
张 放
追求教育平等的尝试:小学新学制改革及其影响(1950—1953)*
张 放
1950年至1953年施行的小学新学制改革,以消除初等教育中存在的地域与出身不平等为出发点。但由于改革设计者最初未能考虑到各地教师人才储备情况、资金投入状况、学生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教学压力的突然增加使得基层教师意见很大,消极怠工,改革阻力重重,多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升反降。以消除不平等为鹄的的学制改革却拉大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间的教育差距,不得不提前终止。然而,新学制的实施从三个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小学教育文化:形成了超越个人义务层面的教育荣誉感;改变并统一了教学方法;重构了师生关系,提升了学校教育的地位。
小学教育;教育平等;新学制;教育文化
一、引言
中国的教育平等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许多学者给予关注。目前关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倾向于强调中国教育不平等现象的产生与学生所在家庭之间的关系,认为家庭的物质条件与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对学生的教育晋升之路影响甚重①参见Yuxiao Wu,“Cultural Capital,the State,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1949—1996”,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Vol.51,No.1(Spring,2008),pp.201-227;李习凡、何雨: 《阶层优势的代际复制:精英中学选拔机制的社会学分析——以南京 F学校为例》,《学海》2011年第5期。该路径显然是受到了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等人研究的启发,他们认为不同阶级对文化资本的掌控力不同,体现到教育领域,教育系统就被制度化为社会分层的工具。参见〔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著,邢克超译:《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商务印书馆,2002年;〔法〕P.布尔迪厄著,杨亚平译:《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二种路径则将研究重点对准国家政策,认为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产生了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超越了家庭所施加的熏陶①参见Zhong Deng and Donald J.Treiman,“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3,No.2(Sep.,1997),pp.391-428;Xueguang Zhou,Phyllis Moen and Nancy Brandon Tuma,“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1949—94”,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71,No.3(Jul.,1998),pp.199-222;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梁晨等: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以上研究主要将关注点聚焦于中等及高等教育,其隐含的预设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小学教育的推广和普及效果明显——研究者可以找到大量数据支撑这一预设②参见Martin King Whyte,“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64(Dec.,1975),pp.684-711;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研究者开始强调小学教育机会不平等这一问题时,目光已经对准了改革开放以后。参见唐俊超:《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但数据或许只能对历史趋势作出整体性描述,而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复杂面相则往往无法通过单纯的定量研究予以揭示。如若进入历史细节,我们恐怕会发现,1949年之后小学围绕教育平等的改革并非像数据显示的那般乐观,而数据更是遮蔽了改革中的文化意涵。针对上述研究存在的不足,笔者将以新中国第一次小学学制改革(即五年一贯制)为研究对象,分析追求教育平等尝试中的历史细节及其蕴含的矛盾与张力。
目前,即便是在教育学领域,研究者也基本是在学制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顺带谈及五年一贯制的推行③提及小学学制改革的多是教育通史类著作,例如苏渭昌、雷克啸、章炳良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页;卓晴君、李仲汉:《中小学教育史》,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42—43页;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卷,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95—96页;李太平主编:《普及与提高——中国初等教育6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张礼永、郭军:《筚路蓝缕1949—1960》,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42页。西方学者涉及该问题的研究,参见Suzanne Pepper,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2-193;Theodore H.E.Chen,“Elementary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10(Apr.-Jun.,1962),pp.98-122.,尚未涉及对小学新学制改革历程的专题研究,更谈不上对这一短暂改革的评价与反思。面对这一尚待深入开垦的论题,我们有理由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小学新学制是对国民政府时期学制的批判性继承,新制度的设立反映出执政者对于初等教育角色和功能的重新定位;第二,一场符合新中国教育精神和话语的改革,从试行到暂停不过短短三年时间,这意味着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超出政策制定者最初的预期,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们需要对其作出分析;第三,伴随小学新学制的实施,一系列涉及教育文化重建的工作在舆论宣传工具的帮助下同时展开,因此,尽管制度层面的实验提前结束,但文化层面的影响却不宜忽视,有待进一步梳理。基于上述考量,本文试图重新思考新中国成立初期旨在追求教育平等的小学新学制改革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并初步评估这场改革在新中国小学教育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小学学制变化与教育不平等状况
若要充分理解并评价新中国初期小学学制改革的意义和动机,我们须对1949年之前小学学制的变化以及小学教育的不平等状况作出简单梳理。近代中国对于小学学制的最初构想源自1902年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所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参考欧美和日本的学制系统,比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④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9—190页。,将初等教育分为蒙学堂(四年)、寻常初等小学堂(三年)和高等小学堂(三年)⑤参见陈青之: 《中国教育史》 (下),岳麓书社,2010年,第559页。。由于该章程并未实施,因此真正在实践层面产生影响的乃是次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将小学教育分为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⑥参见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第560—561页。。二者的定位与角色有所区别:初等小学堂属于义务教育之范畴,“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应强迫入学;高等小学堂则为“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而准备,未列入义务教育范畴①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93页。。该学制实施至民国元年后废止。
1912年中华民国首个新学制正式颁布,将小学教育分为初等小学校(四年)和高等小学校(三年),前者为义务教育阶段②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凤凰出版社,1991年,第59页。;但同时又作了补充说明,指出初小理应不收学费,但各初小可视具体情况,经过县行政长官同意后,收取学费③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446页。。初小学费限制在每月银圆三角以下,而高小学费每月则可高至银圆一元④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65页。。此时,限于地方经济状况,义务教育还处在一个“有名无实”的理念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学制公布前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合并初、高小,实行五年义务教育制,但在“义务教育年限,宜视人民生计酌定之”观念的影响下,被否决了⑤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13页。。该学制实施不久,就有人指出其弊端,认为初等小学的设立似乎专门是为升学而准备,国民义务教育的功能不够突出。袁世凯遂于1915年初颁布《教育纲要》,规定初小实行双轨制,国民学校专为普及义务教育而准备,预备学校则为旨在升学的学生准备,但该学制并未推广⑥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23页。。1915年夏,为了凸显初等小学承担普及教育的性质,教育部将其改名为“国民学校”⑦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466页。,规定公立学校学费为每月银圆两角以下,私立学校不受限制⑧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486页。。此时,教育部虽对学制作出规定,但地方在执行时却显示出很大的随意性,“六四制”“五五制”“五四制”层出不穷⑨参见李彦福、黄启文等编:《广西教育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7页。。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对学制作出一次重大调整,该学制基于对德、英、美、法、日五国教育体制优劣比较分析而制定。在学制颁布前,各省对小学教育与义务教育之年限,小学教育是否继续沿用初、高级二分制等问题争论不休⑩参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30—243页。。最终学制出台时,将小学教育规定为义务教育阶段,年限设为六年,其中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地方可根据自身情况,单独设立初级小学,并将义务教育年限缩短至四年。⑪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84—85页。
国民党执政时期,保留了1922年确立的小学初、高小“四二”划分的学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适当调整。1932年提出“完全小学”的概念,即包括四年初级小学和二年高级小学的学校⑫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凤凰出版社,1994年,第14页。。为涵盖普通小学所无法吸纳的失学儿童,尽快普及义务教育,教育部于1935年和1937年分别推出一年制和二年制短期小学⑬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631—633、638—643页。。1940年,教育部要求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每乡(镇)成立中心学校一所,办学经费以自筹为主。国民学校学制四年,相当于初级小学;中心国民学校学制六年,相当于完全小学。⑭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一),凤凰出版社,1997年,第421—427页。经过调整,完小位于区域中心、初小分散于区域边缘的地理分布格局得以巩固。此次改制对小学的功能和名称作出重新安排,但并未触及1922年奠定的小学学制。随着小学教育的发展,国民小学中亦开设高级部,但所占比例极为有限⑮例如,根据河南省方城县1948年的统计,全县国民学校有309所,共有673个初级班、7个高级班;而全县中心国民学校有35所,共有115个初级班、71个高级班。参见程国珍主编:《方城县教育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1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其统辖区域内展开了教育改革。1934年之前,中共所辖区域内的小学学制尚无统一规定。例如,湘鄂赣苏区最初采取“四二制”,后又改为“四三制”;闽西苏区选择“三三制”;还有一些地区推行初、中、高级各两年的“二二二制”①参见董纯才主编: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宣布小学学制改革,小学修业为五年,前三年为初级小学,后两年为高级小学。该学制为弹性学制,可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提前或延长。②参见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9页。然而,“三二制”并未成为共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部分采取“三二制”,其他根据地多采用“四二制”,个别地区沿用“二二二制”③参见董纯才主编: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四二制”仍是根据地的主流,之前缩短学制的学校也多选择恢复“四二制”④参见董纯才主编: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3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1—102页。。
概言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不管是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小学普遍采取初、高小两分的“四二制”。小学学制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基本上趋于稳定。但学制背后所隐含的小学教育不平等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30年初级小学的数量占到全部小学数量的 92%,共有 222545所⑤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558页。;1936年小学数量达到战前高峰,其中初级小学244398所,完全小学39034所,前者数量占86%⑥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第579页。。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持续的动荡环境使得小学教育发展缓慢。根据1946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小学290617所⑦参见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464页。,初小学生占全部小学生的83%⑧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65页。。初、高小比例失衡状况依旧。若将目光对准条件相对落后的革命根据地,情况则更不容乐观。20世纪30年代中期,湘赣苏区只有两所高小⑨参见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257页。。1938年之前,陕甘宁边区没有完小⑩参见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第241页。。经过六年发展,1944年,陕甘宁边区完小中的高年级学生占全体学生的14%,若加上初小学生,接受高小教育的学生比例更在1%以下⑪参见《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2页。。到了1946年,陕甘宁边区共有小学1249所,其中完小仅有62所⑫参见韩作黎主编: 《延安教育研究》,文心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关于延安时期的学制简介,参见Wang Hsueh-wen,Chinese Communist Education:The Yenan Period,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public of China,1975,pp.136-138.。
在“四二制”中,初小和高小的数量存在严重脱节,完成初小学业的学生大多数不能继续升入高小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更谈不上有进一步升学深造的机会。初小毕业生没有适当的晋升通道,只能返回家中务农或外出务工⑬参见《遵义县虾子小学志》,内部发行,2009年,第134页。。如果接受教育仅仅是为了提升国家的义务教育率,而所学知识既疏离于务工或务农生活,又难以成为向上流动的“敲门砖”——这与民众对传统教育功能的认知不符⑭到了1940年,还有很多生活在区域边缘的民众对新式教育持怀疑观望的态度。参见金湖县文教局教育史料组编:《金湖(老解放区)教育史料汇编》,内部发行,1984年,第114页。——那么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动力就明显缺乏,哪怕是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成为政府在推行义务教育时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受教育的不平等状况还与家庭条件有关。尽管从清末开始的学制改革都至少将初小划入义务教育的范畴,但囿于经济状况,公立学校被允许收取一定费用,私立学校更不在监管范围之列。而高小多设立在区域中心,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远途学生的负担。根据毛泽东对寻乌县的调查,该县高小维持在13个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⑮《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页。。而在30年代的华中地区,供两个孩子读初小,须家有良田30亩,50亩良田才能供一个孩子读高小①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69页。。例如该地区的昭明小学,在校学生中80%到90%都是富裕户②参见《襄樊市昭明小学校志(1903—2008)》,内部发行,2008年,第135页。。
有论者试图通过对精英人士追忆的梳理,展现民国小学教育中的优良传统③参见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同心出版社,2012年。。但这仅仅聚焦于民国小学教育的一个面相,即为数不多的高质量学校。在那个年代,绝大部分地处中心地带之外的初小或国民学校教育水平极为有限,有些地区的学校管理混乱,学生不分年级,水平参差不齐,甚至很多学校只有一位教师④参见《平顺县教育志(1529—1984)》,内部发行,1985年,第117页。。大多数学生无法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更失去了进一步读书的可能——这便是中共在接管教育工作时所要面对的局面。
三、新学制的试行、推广与停止
小学学制中存在的问题,使“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人民的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⑤教育资料丛刊社编:《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第91页。,这显然不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⑥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页。,与中共所秉持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因此,新政权认为学制改革势在必行。在“一边倒”的时代背景下,小学学制改革的最初构想受到苏联初等教育四年一贯制的启发⑦参见吴研因:《关于小学五年一贯制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52年8月24日。苏联于1923年开始实施四年一贯制。关于苏联基础教育学制的演变,参见Ronald F.Price,Marx and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7,pp.76-86.,决定“实行一贯制,取消初、高两级的分段制”。但考虑到中国幼儿教育的落后与缺失、中国汉字掌握的困难程度等因素,修业年限定为五年。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内部发行,1958年,第29页。为配合缩短教学年限的改革,并进一步凸显小学教育的新特色,新学制推进过程中还对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职责作出了积极调整,并通过多种媒体广泛传播。可以说,新学制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新中国小学教育文化的形成。
(一)新学制的改革试验
由于此次学制改革中小学学制的“变动比较最大”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第92页。,因此教育部门相当慎重,决定首先选择试点学校进行改革尝试,以观察其效果。1950年教育部发出文件,要求北京市文教局进行小学学制改革试验,选定北京育才小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小学,北京市六区中心小学、三区第二中心小学以及北京市立师范第一附小等六校作为改革试点(其中前三所学校系教育部直属小学,后三所系北京市文教局所属),在一至三年级进行试验。文件强调市政府应配合工作,适当增加经费,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⑩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示(关于参加新学制试验之市立小学编制经费等项希你局转请市府适当增加以利工作进行由)》(1950年9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5-104。
北京市制订了改革计划,规定各校进行试验的四项原则:第一,每年级学生数控制在45人至50人;第二,劳作课、政治常识课可以取消,高年级的历史、地理、自然可精简;第三,各年级的班主任要选择政治进步的教师担任,最好是党团员,并且文化程度高,教学经验丰富,有一定研究能力;第四,除制度和教学进度与非试验班有所差别外,其他方面尽量保持同步,不搞特殊⑪《北京市小学学制改革试验计划草案》(1950年9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5-104。。
从上述原则可以看出,五年一贯制主要通过课程和教材的调整以及师资的加强来实现改革目的。课程方面,新的安排突出实用技能,主次分明:国语和算术的平均课程量增加,而常识课⑫常识课包括政治、历史、地理、自然等,从三年级起单独开设,一、二年级在国语课中讲授。的课时比例有所减少。改革前六个年级国语和算术每周平均课时数分别为11节和5.3节,改革后变为12节和6.6节;改革前常识课在中年级(三、四年级)和高年级(五、六年级)所占课程比重分别为11.5%和27.6%,改革后在三、四、五年级课程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4.3%、24.1%和23.3%。然而,由于学习时间缩短一年,新学制中语文课的总节数较旧学制共减少228节,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用五年的时间达到六年的效果,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会更大。①参见《五年一贯制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间表》(1950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5-104;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内部发行,1950年,第31页。为了保证教学效果,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传统教学方法已无法适应时代需要,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方法乃是应有之义②在新学制试验前后,各地教育部门专门针对中小学教师编译出版了一系列学习苏联教学方法的小册子,这些书为处在学制改革摸索阶段的教师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借鉴,也为新学制正式推广之后全面推行苏联教学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参见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编审部编:《怎样向苏联学习教育》,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1950年;天津市小学教导研究会编印:《向苏联学习》,大众书店,1950年;东北教育社编:《苏联的教育》,中国儿童书店,1951年。。
师资方面,试点小学将政治和业务双过硬的老师分配给试验班,反映出官方对学制改革试点的重视,同时也折射出国家对新学制下人才素质培养的期许。若进一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安排背后的现实考量。从业务能力看,小学师资力量的分布非常不平均。由于初小的数目远多于高小,因此能教小学高年级的教师数量不足。以北京为例,根据1952年全面推广五年一贯制前的不完全统计,全市教师中仅能教一、二年级的有427人,占9.3%;能教到三、四年级的有1840人,占40.1%;能教到高年级的有2326人,占50.6%③参见《北京市小学实施五年一贯制的初步意见》(1952年8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2-246。。在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能够胜任完整小学教学的老师也不过刚刚过半,教育落后地区的比例恐怕更低。可五年一贯制又恰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方不得不集中优势资源来完成试点任务。而对教师政治素质提出要求,乃是因为在新学制下,一方面政治课取消后,教师通过日常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被突出;另一方面教师还要对学生的全面成长负责,过去通过简单粗暴的体罚教育学生的方式已不再适用,教师的管理范围有所拓展,课后与学生和家长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经过一学期的试验,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操行成绩尚能维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以北师大第一附小为例,该校有甲、乙两个试验班共100人,在学期末测验中,国语常识得分在4分(满分5分④五级分制学自苏联,用以代替传统的百分制。五级分制的满分为5分,最低分为1分,分为五个档次。分数只反映档次,不显示具体成绩。关于五级分制在新学制改革过程中的推广情况,参见教育资料丛刊社编:《成绩考查与苏联五级分制》,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广东教育与文化月刊社编: 《学习五级分制记分法》,华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中国教育工会广州市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编:《五级分制记分法实施经验介绍》,华南人民出版社,1953年。)以上(含4分)的有84人,而算术则有98人。在学生操行考核中拿到5分的有49人,拿到4分的有43人。⑤参见《1950年第一学期师大第一附小试验班工作总结》(1951年3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5-108。与此同时,学校在教学改革、师资培训和学生生活方面也都有所改进。例如,为尽可能保证教学质量统一,北京市第三区第二中心小学建立集体备课制度,成立集体备课小组,每天上课前一小时进行集体备课,教导室随时抽查教师的笔记与备课情况⑥参见光明日报社编印:《小学五年一贯制学习资料》第1辑,内部发行,1952年,第45页。。北师大第二附属小学成立“试验工作委员会”,由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与任课教师组成,共同完成“选编教材”与“研究试验新教学方法”两项任务,形成标准化备课流程;建立汇报制度,定期由教师向校长或教导主任汇报工作;同时完善班主任工作,要求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智育培养”“品德教育”“纪律教育”,并要全面了解学生及其家庭情况,师生关系得到有效提升⑦参见《小学五年一贯制学习资料》第1辑,第48、50、51页。。在随后新学制全面实施的过程中,试点学校所采取的这些方式都被作为先进经验在全国推广,悄然塑造着小学的教育文化。
试验工作取得进展使官方坚定了继续推行五年一贯制的决心,教育工作者认为五年制的小学毕业生可以达到六年的水平,甚至更高①参见张健:《为什么小学要实行五年一贯制》,《教师月报》第1卷第9期,1951年11月15日。。教育部根据试点取得的成绩,相信只要全盘复制试点的做法,五年一贯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推行。但教育部所忽略的是,试点成绩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试点是在北京顶尖的小学中进行的,学生素质普遍较高,而试点班级又集中了学校最优秀的教师,并有充足的资金保障。可以说,试点工作是在汇聚了各方优势资源的前提下才取得成功的。一旦全面铺开,教师水平、学生素质、地区差异、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状况就会迅速呈现,成为普及新学制的羁绊。
(二)新学制的宣传推广
1951年8月10日,政务院第九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随后召开的全国初等教育会议确定了计划实施的时间安排②参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6页。。这表明五年一贯制的试验正式得到国家肯定,并将进入全国推行阶段。
《决定》出台后,官方首先着重阐发新学制的意义。钱俊瑞在分析中国教育领域面临的诸问题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生活上得到了改善之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就迫切要求上学,学文化”,而新学制就为工农群众提供了一个在正规的学校系统中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③河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初等教育科编:《小学怎样实施五年一贯制》,河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页。。张健认为五年一贯制是完全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情况和需要的“人民基础教育最好的学制”,“为祖国培养各种建设人才打下最广泛的基础”,“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创造良好的条件”;五年一贯制能够从“教育制度上巩固工农联盟”,并为“国家培养大量中级技术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小学毕业生打开了宽阔的升学和就业的道路”,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④张健:《为什么小学要实行五年一贯制》,《教师月报》第1卷第9期,1951年11月15日。。各地教育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召开学习新学制精神的会议,并及时表态拥护新学制⑤参见《上海三万余教育工作者热烈拥护改革学制决定》,《文汇报》1951年10月5日;《学制改革符合新中国实际需要本市教工一致热烈拥护 各中小学校长致函本报表示意见》,《文汇报》1951年10月6日。还可参见《教师月报》1951年第9期上发表的教师笔谈系列文章。。这些宣传逐渐改变了民众对教育的看法。他们发现,新政权鼓励工农子女进入学校;也只有通过教育,工农子女才有可能打破身份的“循环生产”,获得晋升机会,取得更大成就——如今,新学制的实施使上升渠道得以畅通。
1952年8月2日至10日,中小学行政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叙伦在会议开幕式上指出,除部分边远落后地区外,“全国小学,从今年秋季新招的一年级起,开始实行五年一贯制,以后逐年顺推,争取在五年内全国小学基本上实现五年一贯制”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 讨论了大量发展中学的准备工作和小学实施五年一贯制等问题》,《人民日报》1952年8月19日。。
由于之前对新学制优越性的阐释多集中于价值观念层面,一旦具体执行,各种问题便接踵而至。教职工面对创新,显得顾虑重重,改革阻力很大。以北京为例,市文教局对14所小学进行了调查。调查后发现,教师们的态度并不像预计的那么乐观。有的老师认为五年一贯制增加了师生负担;郊区教师认为新学制并不适合农村小学的实际情况;能力稍差的老师担心改制后自己会失业;而高水平教师又不愿意拉下面子教低年级;不少教师消极对待改制,认为“不改教书,改也教书”,一副无所谓的态度。⑦参见《关于调查九、十三两区的报告》(1952年8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1-2-246。
针对教师中间的消极反应,文教部门在组织各校继续学习新学制实施之重要意义的同时,舆论宣传的重点发生了明显转向。之前偏重价值层面的宣传几乎不再单独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学制执行中具体问题的指导。此类指导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聚焦课堂,一方面对教学方法、教学经验予以介绍,敦促各校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举措,例如,1952年8月31日至9月5日每天20∶30至21∶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推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讲座,讲座嘉宾均为试点学校负责人或新教材编写者①讲座内容包括:“小学五年一贯制一年级开学的准备工作”;“小学五年一贯制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的特点和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我们学校的五年一贯制实验班是怎样进行同年级语文课生字教学的”;“我教小学五年一贯制实验班一年级算术的几点体会”;等等。参见《协助推行小学五年一贯制 中央人民电台广播有关节目》,《文汇报》1952年8月31日。;另一方面对教师在新学制下应具备的教学态度予以塑造,包括鼓励积极参加各种学习组织、自觉学习、集体备课、互帮互助等②参见任浩然:《青浦县普遍举办小学教师自我教育的“星期学校”》,《文汇报》1952年9月29日;朱杰:《余姚县小学教师星期学校介绍》,《文汇报》1953年2月9日;边忆萍: 《新成区小学教师的业务学习》,《文汇报》1953年2月10日。。另一类聚焦课外,指导教师如何有效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关心学生生活,全面了解学生,用自己的行动感化、引导顽劣学生,放弃体罚手段,促成良性师生关系之形成③参见曹书端:《我们在儿童生活指导工作中的一些体会》,《文汇报》1952年9月12日;熙修:《访内蒙优秀教师吴淑媛》,《文汇报》1953年5月21日;笑生:《热爱儿童钻研业务的好教师张淑庄》,《文汇报》1953年6月14日;陆钧:《我将更好地照顾住校学生》,《江苏教育》1953年第14期。。地方教育部门要求各校组织教师集中学习讨论,并对其进行重点检查④参见《本市小学教师将开始学习小学五年一贯制》,《文汇报》1952年8月28日。。用具体的指导替换抽象的说理,以便一般学校模仿,有利于激发教师对五年一贯制改革的热情和兴趣,从而能更好地形成拥护改革的氛围,促进新制贯彻。
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宣传攻势下,刚刚试验两年的五年一贯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推行。多元化的宣传为新制实施提供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指导,尽管不同地区的学校情况不尽相同,但舆论机器所集中呈现的方向正确的指导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板,使其能够紧跟主导趋势。大量关于新学制意义、先进教学方法、优秀教师典型的宣传报道,为新型小学教育描绘了一幅理想愿景,逐渐改变着人们对小学教育功能和作用的认知。
(三)新学制的暂停
此时,各校都聚焦于如何尽快彻底实现新制,而新制下的教学效果如何,多少已经暂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或者说大家普遍认为试点学校在学生成绩上取得的成功已经说明了新制与教学效果之间的自洽关系,而忽略了试点学校所具有的优势和特殊性。实际上,当全国都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新制时,教学进度和质量已经出现了一些隐患。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教材难度明显增加,这让多数低年级教师感到吃力。以语文教材为例,新学制第一册语文课本的生字量,与1951年全国各地区使用的课本以及民国时期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社的著名教材相比,平均高出50%;而且课文篇幅超过了历来的同级课本,总字数是最短篇幅版本的2.9倍⑤参见刘御:《介绍小学课本语文第一册形式方面的五个特点》,《人民教育》1952年第9期。。课程量突然加大导致老师不得不加快讲课节奏,以识字数作为完成任务的硬指标。新教学法也无法完全消化内容增加带来的压力。有些地方甚至延长了课堂上课时间⑥参见《登封县教育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8页。。尽管如此,很多学校仍然不能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学期末教材内容讲不完成为普遍现象⑦参见俞济民: 《对复习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的一些意见》,《文汇报》1953年6月19日。。
1953年5月中下旬,在正式推行新学制一学年之后,北京市教育局组织调查组对城区代表前门区和郊区代表海淀区不同类型的小学(包括市立小学、私立小学,城镇小学、农村小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调研。正是在这次调查之后,北京市教育局作出了暂缓施行五年一贯制的决定,后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
此次调查涉及的内容包括师资质量、教材和学生成绩。通过对师资的调查发现,前门区能够教到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的教师比重分别为7%、36%和57%;而海淀区的比重则为15.5%、42.5%和42%。虽然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调查组认为能够胜任四年级及其以上教学任务的教师数量超过了80%,而能力稍差的教师也可以通过各种学习培训提高水平。因此单就北京市来说,师资质量对新学制的影响不大。⑧参见《北京市五年一贯制重点调查报告》(195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4-2137。但在其他地区,教师能力短板已经严重影响到五年一贯制的执行①参见东初:《五年一贯制为什么暂缓推行?》,《文汇报》1954年3月6日。。通过教师座谈会,调查组了解了教师对教材的具体意见,语文教材方面主要包括:课数过多;课文有些太长,有些还过于抽象,学生不易理解②因教科书内容不易理解,有些地区学生甚至出现了缺课现象。参见文教科:《怀宁县小学实施五年一贯制检查报告》,《安徽教育》1953年1、2号合刊。;生字偏多,导致师生疲于应付,达不到预期效果;课文难易程度的编排顺序不精当;各校对教材要求标准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数学教材方面,难度超过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尤其是应用题错得最多。学生成绩方面,经调查组出题测试,发现语文和数学成绩不及格的情况较为严重(见下表)。而对城区学生461人进行的默写测试(共40字)中,全对的仅有8人,答对20个以下的有103人,还有8人全错。另经统计,入学年龄偏小的学生不及格率高(语文50%,数学51%);人数多的班级学生成绩差。③参见《北京市五年一贯制重点调查报告》(195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4-2137。

北京市不同类型小学新学制改革后成绩对照表(1953年)
根据这一调查,调查组发现新学制实施之后,普通学校和前述试点学校的学生成绩无法相比,而且城乡之间、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相当大,由此得出结论,建议“五年一贯制暂不推行”。教材方面,由于新教材具有思想性强、生动、题材多样等优点,因而决定继续使用,将“新教材加以改编,分六年进行”。④《北京市五年一贯制重点调查报告》(195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53-4-2137。北京市教育局的这份调查报告对国家取消推广五年一贯制的决定有较大影响。在教育资源、师资条件都相对优越的北京市,师生面对新学制都无法适应,其他地区的适应程度可想而知。1953年11月26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正式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一律暂停推行五年一贯制,要求“小学学制仍沿用四二制,分初、高两级”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文汇报》1953年12月15日。。至此,这场试行三年、正式推行一年的教育改革运动宣告结束。
四、塑造教育文化:新学制改革的影响
新学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不过一年,即便从试行到终止也只有短短三年时间,但此次改革远非缩短入学年限那么简单,而是包括了改变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的一系列举措。宣传推广新学制的过程也是中共对其所秉承的教育理念集中传播的过程,而学制贯彻中产生的课堂内外变化对新型教育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些变化甚至经受住了历史长河的磨砺,影响至今,其意义已不仅局限于对教育平等的追求。
(一)形成超越个人义务层面的教育荣誉感
前文提到,义务教育推行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被压缩在了个人义务层面,缺少必要的向上流通渠道,个人受教不能与晋升联系在一起,与传统“学而优则仕”之观念无法契合。小学新学制的实施,从理论上填平了学生读书通道上的沟壑;而政策上的倾斜使得在旧社会本没有多少读书机会的工农子女进入了新社会的学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固有“偏见”促使工农阶级很快就认同了中共所作出的普及初等教育的努力。通过舆论建构,读书与贡献祖国建设之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唯有认真学习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祖国,个人价值才能得到社会认可。这一导向使家长又一次看到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读书所具有的荣誉性得以重建。
“读书—改变命运—荣誉”三者构成的逻辑关系很快就深入人心,这从北京市1953年暑期开始的小学升学危机中学生和家长的反应就能看出。此次危机爆发并非北京一地个案,其主要原因是“学生的志向远远超过了经济所能吸收他们的能力”①〔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而在北京,由于要照顾华侨子女和外来少数民族子女等,这一危机尤为严重。入学紧张的困境引起了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初中入学考试成绩出来以后,就有4000多人到教育局上访,表达愤怒;市委、市政府也收到了500多封投诉信,要求解决子女入学问题。一时间民怨沸腾,出现很多过激言论:“小孩子不上学就成流氓了,难道政府看着不管吗?”“爹妈打一顿骂一顿,也不像政府这样狠心!”“为什么盖那么多办公室、宿舍、礼堂,不盖教室?”“解放后,我对政府什么都满意,就对这点不满意。”“这么多人失学人民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没有两样!”“什么工人当家做主,我儿子都上不了学。”②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档案馆编研处编: 《北京教育档案文粹》上册,华艺出版社,2008年,第91页。这些言论表明了普通人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需求的迫切性,给执政者带来了巨大压力。官方不得不通过重新建构劳动之于儿童的荣誉感来弥补读书之荣誉无法实现时所形成的心理落差。但这种新的逻辑关系缺乏传统思想资源的支撑,甚至与之相悖,其稳固与接受程度远不如“读书—改变命运—荣誉”的逻辑关系。
(二)向苏联学习:教学方法的改变与统一
1950年《人民教育》发刊词中强调,“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学习苏联新的教育科学,对于新中国教育的建设有着巨大意义”③柳湜:《为建设新中国人民教育而奋斗》,《人民教育》第1卷第1期,1950年5月1日。。苏联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获得了“唯一科学的、正确的”地位④曹孚:《苏联先进教学基本原则(小学教育讲座第二讲)》,《文汇报》1952年12月18日。,其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高等教育层面⑤关于苏联因素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参见陈兴明:《中国大学“苏联模式”课程体系的形成与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Jeremy Brown and Paul G.Pickowicz eds.,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88-308;Thomas P.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1949-Present,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0,pp.303-325.,也体现在基础教育层面。五年一贯制从制定之初就借鉴了苏联基础教育的学制,但对中国基础教育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在新制贯彻过程中对苏联教学方法的吸收和借鉴。
新中国成立前,教学方法没有统一,不同方法之间亦无明确的优劣之别。例如,有些地方高、中、低年级教学方法均不相同,体现出不同教学法之间的博弈⑥参见《桂林市教育志(初稿)》,内部发行,1994年,第29—30页。;有些地方采用美国的教学方法⑦参见《河南教育史志资料选编》第3期,内部发行,1986年,第89页。,并强调自学的重要性⑧参见《焦作市教育志(1898—1985)》,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1949年之后,教学各自为战的局面逐渐改变,中国教育界开始有意识地借鉴苏联教育模式,尤其是随着五年一贯制的实施,苏联的教学方法被系统地引入中国的小学教育。在新学制实施过程中,官方通过媒体敦促各学校系统地、全面地学习苏联教育科学理论与教学法,认真领会苏联教学的基本原则、课堂教学制度,并以此衡量教学质量⑨参见王昭:《怎样备课和进行课堂教学》,《文汇报》1952年9月6日;顾少明:《贯彻教育原则 提高教学质量》, 《文汇报》1952年12月21日;曹孚:《苏联先进教学基本原则》,《文汇报》1953年12月18日;王志成:《参观北京市几个小学学习苏联课堂教学后的体会》,《文汇报》1953年1月19日。。首先,科学主义(Scientism)思维⑩这种思维的基本预设是:教育者将学生放入一条标准化生产线,能够得到规格相同、质量一致的无差别产品。参见Donald J.Munro,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0,p.77.主导下的教学标准流程被引进,课堂被严格划分为组织教学、检查复习、讲授新课、巩固联系和布置作业五个教学环节,教师须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一“仪式”,以增加上课效率①参见王昭:《五年制实验班三年级一课语文教材的讲授》,《文汇报》1952年11月1日;曹孚:《苏联课堂教学制度(小学教育讲座第三讲)》,《文汇报》1953年1月3日;《西城区普通教育志》,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79页; 《商丘县教育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其次,为保证不同教师教学内容和进度的一致性,减少教师个人差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在试点学校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纷纷学习苏联成立不同级别的教研室(从地市级教研室到年级教研室),定期进行集体备课、听课、教学方法交流等活动,强调教学的计划性和目的性②参见《香山小学志》,内部发行,2011年,第101—102页;《登封县教育志》,第115页;《黄冈县教育志(1875—1985)》,内部发行,1987年,第139页。。最后,课堂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联加强。苏联模式本就强调通过教育培养学生“最优美的道德——政治品质”③〔苏〕格鲁斯捷夫、彼特洛夫等著,王易今等译:《苏维埃学校中的共产主义教育》第1分册·共产主义教育基本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第1页。,加之在五年一贯制实施过程中,政治课被取消,因此“结合各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新学制推广中着意宣传的观念④参见《怎样在低年级的语文课中进行思想教育》,《文汇报》1952年9月10日; 《不能忽略思想教育的要求》,《文汇报》1953年4月21日;《向一年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些经验》,《文汇报》1953年2月20日。。例如,新学制语文教科书的教师参考书就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指导教师结合课本内容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⑤参见茅谷澄等编:《备课参考资料》,上海童联书店,1953年。。在新学制停止实施后,这种观念不仅没有随之结束,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⑥例如,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小学语文课本》四册中,相比于新学制使用的教科书,政治化内容明显增加。参见张放:《新人新语:建国初期政治语言的传播与习得(1949—1956)》,《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三)师生关系重构,学校教育地位提升
如前所述,在五年一贯制实施过程中,教师的职责范围已不仅局限于课堂之上。新学制鼓励教师在课后与学生多沟通交流,关心学生成长——概言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正逐步建立,教师开始与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严父”形象脱离,“慈母”形象渐入人心。这一转型的完成主要通过两个环节实现:
第一,赋予体罚以污名,逐步废止体罚。在中国传统社会,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并不罕见,甚至司空见惯。鉴于“板子底下出秀才”“严师出高徒”的观念,家长和学生认为体罚乃天经地义,不觉有何不妥。民国时期,教育部虽然屡次规定不得体罚,但又强调须对儿童加以儆戒,以弥补教育手段之不足⑦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445、464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一),第449页。,这一模糊的规定就为体罚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中共所辖区域内,打骂学生的现象在30年代普遍存在⑧参见董纯才主编: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167页。,后来边区政府明确规定“小学管理绝对禁止体罚”⑨《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小学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但体罚在一些地区远未杜绝⑩参见《金湖(老解放区)教育史料汇编》,第13页。。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教育领域开始批判体罚制度,并树立正确对待儿童的教师典型⑪参见陈钧、放野:《滁县部分小学教师应改变体罚儿童的现象》,《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8日。,但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手段也层出不穷,花样翻新⑫参见亳县文教科:《小学中的体罚与变相体罚的检查报告》,《安徽教育》1952年第2期。。新学制实施以后,废止体罚成为制度改革的一大任务。尽管有教师发出不同声音⑬参见吴正礼:《我不同意绝对废止体罚》,《小学教师》1952年第11期。,并引发一场关于是否彻底禁止体罚的讨论,但讨论结果是超过96%的教师同意废除体罚⑭参见本刊编辑室:《体罚问题讨论会结束语》,《小学教师》1953年第6期。。经过这场争论,体罚的正当性被彻底击垮。不管今后体罚是否依旧会发生,其“反动落后”的性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反对体罚”的观念既是师生关系融洽的催化剂,又是学生用以反对教师体罚行为的潜在武器。
第二,“教师—学生—家庭”新型共同体开始形成。在新学制实施过程中,一种新的师生关系被有意识地塑造起来。一方面,教师应主动和学生接触交流,让他们感受到母爱般的温暖、舒适和无拘无束,并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积极表扬学生的长处,少公开揭发、指责学生的过错;另一方面,教师被要求与学生家长沟通联系,定期家访,全面了解学生出现问题的原因,配合家长共同帮助孩子成长,由此,新教育进入了家庭这个曾经相对独立于校园之外的系统,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加①新学制实施过程中,介绍学校与家庭相联系的文章刊印在各类教育刊物上面。参见《小学五年一贯制学习资料》第1辑,第41—46、54—74页。。家庭和学校形成联系之后,家长的实际权威地位会有所削弱。建立权威秩序的传统手段,如打骂等,已经在新社会失去了正当性地位——不仅在学校这一公共空间如此,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内亦然,私人空间因与公共空间建立直接联系而不再封闭。家长打骂等私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暴露在公共空间面前,因此会受到干预和限制。学生已经成为社会的新人,而非家庭的私有品②参见吴晗:《保卫儿童权利,做好儿童工作》,《人民日报》1950年6月1日。。
五、结语
本文尝试从微观层面提供一个个案研究,希望绕到丰富而细致的统计数字背后,审视被其所遮盖的历史细节,进而展现追求教育机会平等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从小学新学制改革努力的失败之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凭借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制定出来的政策,很可能会走向初衷的反面。研究者在观察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机会获得这一问题时,往往对宏观政治进程和国家政策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印象深刻③参见周雪光著,郝大海等译:《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66页。,但我们应该对其面对固有社会结构时作用的局限性充分保持警惕。以这次新学制改革为例,当代表国家意志的五年一贯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时,由于在政策制定环节并未充分考虑各地师资力量、财政力量、地区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改革反而拉大了学生之间的受教育水平差距,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城市区域中的好学校成为了改革的核心受益者——这些学校具有相对完备的师资结构和相对充足的财政支持,能够迅速凸显出来,获得从中央到地方权力的进一步青睐,从而赢得更多资源支持其改革进程。我们遗憾地发现,尽管这次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其教训并未被认真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之前,在激进思想的鼓动下,缩短基础教育学制的改革屡次发生④参见《周口地区教育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8页;《桂林市教育志(初稿)》,第24页。;改革开放以后,各种以“素质”之名推动的教育改革也不排除重蹈五年一贯制覆辙的可能——虽说两者目的不同,但逻辑中存在的盲点却惊人相似。
相比之下,小学新学制改革对教育文化的塑造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这一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贯彻新学制时的舆论宣传,使得人们再次将读书与改变命运关联在一起(科举制度废止之后,二者之间的断裂始终未能缝合),并将受教育之意义提升至宏观的国家层面,完成了对个人义务层面的超越。在这种整体氛围中,课堂内外的文化都发生了改变。课堂上,统一教学流程的引入以及集体备课制度的建立都显示出新政权生产“标准化”学生的雄心壮志,这些标准包括了基础知识、价值观念、言语表达、思维逻辑以及情感方式等诸方面的内容。课堂外,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加强,改变了传统社会学生生活空间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融合实际上凸显了学校教育的功能和地位,而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权威秩序的体认。可以说,新学制的短暂实施,尽管在追求教育平等的道路上遇到挫折,但影响已超越其改革初衷,在新中国小学教育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上海 200083)
(责任编辑 赵 鹏)
The Attempt to Pursue the Education Equality:The Reform of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in Primary School and Its Influence(1950—1953)
Zhang Fang
The new school system reform implemented from 1950 to 1953 was aimed to eliminate the inequality of region and origin in primary education.But as the reform designers failed to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eacher talent pool,capital input conditions,and the students’quality in different regions,the teaching pressure suddenly increased.Therefore the grassroots teachers had objections and slacked off,the reform was confronted with much resistance,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majority of the schools didn’t rise but fell.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system,aimed to eliminate the inequality,widened the educational gap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schools,and had to be terminated.However,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ystem shaped the new Chinese primary education culture from the three aspects:forming a sense of education honor beyond the personal obligation level;changing and unifying the teaching methods;reconstru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school education.
D232;K27
A
1003-3815(2015)-09-0080-12
* 本文是2014年度上海市“晨光计划”项目“思想与实践:中国共产党对小学教育的革新(1949—1957)”(14CG3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