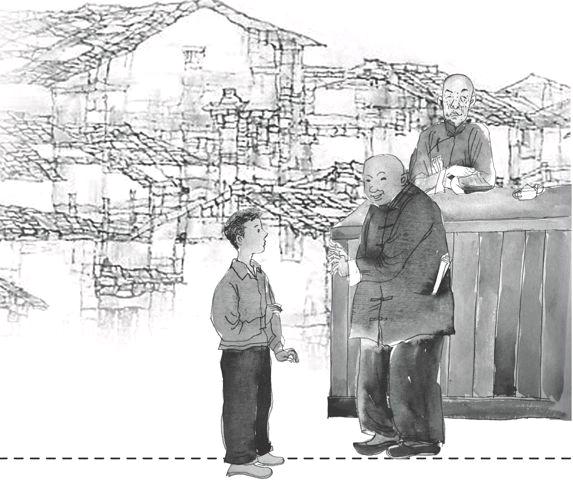时牙行
陆璐
很高兴,在“新年”这个时间节点上讨论关于时间的问题。
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迷人的东西。时间有无数的岔道,我们生活在迷宫中。时间组成人和万物,时间又让人、物分离。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深深陷入这个迷宫——身处其中时,自己不知晓。过了那个时点,回头再看,虽然明白了,但再也回不去。不知不觉,又进入一个新的迷局,不能自拔。
时间是多变的,难以捕捉;人性是永恒的,牢牢恪守。
这篇小文远不能承载这样大的主题,但我还是想把它提出来,这个问题关乎每一个人,希望有人能因此产生这方面的兴趣。
两栋大楼之间,有条不宽不窄的夹缝,正好临着街。本可以利用起来,盖个门脸儿,但两座楼的主人起了纷争,谁也动不得,只好由着它落满垃圾,谁看了都觉得可惜。
不知何时,垃圾被清空,夹缝当中起了间房子。青砖墙,小黑瓦,门是那种一片儿一片儿往上装的板子,古香古色。开张那天,噼里啪啦放了鞭,挂起一块掉了漆的牌匾——“时牙行”。
现代人已不晓得牙行是何物了,但老辈儿的还有些印象。这玩意儿打明朝起就有,专门撮合双方买卖,大抵跟现在的中介公司差不多。什么样儿的牙行都有,买卖丝绸的有“丝牙行”,买卖水产的有“鱼牙行”,买卖粮食的有“米牙行”……
时牙行的门口立了牌子——
专营时辰
代买代卖
稍抽微利
童叟无欺
时间还能买卖?
这年头儿骗子太多,防不胜防,没人敢去试试。偶有胆儿大的,也只是躲在门外向里张望。高高的木柜台后面,杵着俩穿长褂儿的,一个圆脸,另一个是麻子。圆脸还好,那麻子永远冷冰冰的,瞅着就叫人腻歪。
时牙行开张大半年,那两个穿青蓝布大褂儿的庄客,见天只做三样事情——卸门板儿、傻站着、上门板儿……
这天,终于进了个客。
来的是位少年,瘦瘦的,从衣着上可以看出他没钱,从神情上还能看出他有些自卑。
他走进大门,抬眼看见二人,扭头就要朝外走。不过还是有股力量把他拉住了。他又回过身来,勉强挤出一丝笑。
“这位客,有何贵干?”圆脸忽然笑了。尽管是皮笑肉不笑,但还是给了少年不少勇气。
“我……我想问一问,买一天时间需要多少钱?”他说完,长出一口气。
圆脸说:“不等。大年三十儿至正月十五是一个价,春上是一个价,冬里又是一个价。看这位客要哪一天了。”
他捏了捏衣兜儿,里面有一厚沓——零钱。他酝酿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2015年2月29日,我想买今年的2月29日。”
圆脸“噗嗤”一声,笑了,这次不是皮笑肉不笑,“阳历?这位客,您回去查查日历吧,今年可不是闰年呐。”
他嚅嗫起来,喃喃地说:“所以才要买嘛……”边说边往门外退。
“等一下。”一旁的麻子发话了,“我去问问周登,看这买卖他接不接。”
说着,他掀帘子进了后堂。
圆脸沏了茶,递过来,“请用。”
“周登,”他接过茶碗,闻到一股异香,“是谁?”
“你这事儿挺棘手,怕只有他们弄得了。”圆脸本就是个热心肠,“四值功曹,晓得不?值年、值月、值日、值时,四个人。管日子的那个值日神,便是周登。”
他摇摇头,心想,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麻子出来了,还是面无表情。看看圆脸,看看他,说:“贵。”
他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掏在柜台上,“我只有这些。”
麻子拿了算盘,往柜台上一推,几枚镍币被碰落在地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别!我送了一暑假的水。”他心疼,忙蹲下身子去捡。
“可以不用钱。”圆脸说,“稍等,给您算一下。”
圆脸从柜里拿出本大红册子,翻到一页,麻子歪过脖子,瞅了瞅,开始噼里啪啦地打算盘。
少顷,麻子清了清嗓子:
“咳!这位客。今年阳历2月29日子虚乌有,需专门为你订制,所费自然不菲。既然你没有钱财,那只能以物易物。经查,你今年实岁一十四,此生算是高寿,能活八十五岁,余年七十有一。你可用余年的一半,即三十五年来换取一日,加上本牙行抽佣钱一年,两项合计共三十六载。盈亏与否,自行衡量,一旦成交,盖无反悔。”
“专门……订制?”他问。
麻子点点头,“是,这一整天归你独享。”
他挠挠头,“我可以带个人吗?我俩过这天。”
麻子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那就是七十年,外加佣钱翻倍。”
“少点儿吧……按你说的,我余下总共才七十一年,怎么够换?”他还价。
“不二价。”麻子摇摇头,“双方开价,牙行居间,我说了也不算。”
圆脸看看手里的册子,侧头望着麻子,“要么再跟周登说说?”
“谁说?你说!”麻子没好气。
圆脸不吱声了,显然那个叫周登的很难缠。
“这样吧!”少年一巴掌拍在柜台上,下了决心,“佣钱少收些。我这辈子全换了!”
麻子翻着眼睛,想了想,点点头,对圆脸说:“照他说的,造约!”
圆脸笑了笑,又摇摇头。
“居然还活着。”
她刚被查出绝症,开始懂得为活着而感恩。她的生日是2月29日,她这辈子只过了三次生日。她想在有生之年再过一次2月29,可医生说她剩下的日子不多。怕是等不到了吧,真可惜。
她瞥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
2015年2月29日08:10
一愣,又从枕头下摸出手机——
2015年2月29日08:11
开什么玩笑?
“叮咚叮咚”,门铃响。
“宋妈妈,爸,妈,来人啦!”她坐在床上喊。
屋里没人答应。奇怪!这个点爸妈应该在家才对。怎么连保姆也不在?
她披上衣服,从床上起来,穿过走廊,下到一楼,打开门。
是他!
她有些意外。他很久没来了。
她和他,七岁之前都住在乡下,天天一起玩。后来,她爸爸进城搞建筑发了家。他爹娘也进了城,他爹在超市当搬运工,他娘在酒店洗洗涮涮。两家原来是邻居,进城后住的也不远。她放了学还去找他玩,放假时他也去她家。她爸不高兴,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他爹也不乐意,说,去她家干个啥子哟,没出息。
两人只敢在上学路上,做贼似的说上两句。
他手里提着一个蛋糕,站在门口,两眼放光,“生日快乐!”
她笑了,嘴上却说:“别闹!”
鲜奶蛋糕当早餐,她并不觉得腻,一口气吃下好大一块。吃完问他:“今天怎么会是29号?”
他没回答,用大拇指替她抹掉嘴角的奶油,说:“出去转转呗。”
步行街上,招牌在转动,音响在叫唤,五层楼高的大屏幕正播放着新闻。除了没人,看不出和平时有什么不同。
他挺挺胸膛,说:“走,给你挑件生日礼物去。”
他们牵着手,在光天化日下走。
商场里,东西还是那么丰富,可今天的服务质量可不好,逛了半天,没一个人搭腔。正好,不用看营业员那表面谦恭,背后却是“谅你也买不起”的臭脸。
他们自己动手,爬进柜台挑首饰。他为她戴上一条钻石项链,手有些抖。
从一楼到七楼,“买”的东西拿不下了,他俩累得腿发软。
“去电影院歇歇吧。”他提议。
顶楼影城,爆米花、可乐随便拿,没人检票,他俩舒舒服服地窝在椅子上,包了一场。
真爽,出了门,3D眼镜还忘了摘。
“啊!”她看他一眼,惊叫。
她把3D眼镜甩得老远,揉揉眼睛,再看,又惊叫一声。
他莫名其妙。
她拽他到镜子前,他忍不住也惊叫——他长个儿了,下巴上爬满胡茬子,看样子,足有二三十岁。她站在他身旁,像个小妹妹。
“好吧!到你坦白的时候了。”她拽着他,坐进一旁的咖啡吧,“今天的事儿,如果不是做梦,那就肯定和你有关系。”
他搓着手,掂量着,把来龙去脉说了。
她出奇冷静,呆呆地望着他,许久从鼻子里笑了一声,泪珠闪动着晶莹,默默地从腮边滑落。
“好了,快不说这个。好容易得来一天,唉声叹气地过,实在太浪费啦。”他宽慰她。
她甩甩头,像是在努力。再抬起头,果然平静了许多,“接下来干什么?”
“没想好,干什么都可以。这样静静地坐着,也不错。”
“我想回到小时候。”
“那……咱们回乡下吧。”
“好。”
出了商场。迎面看见大屏幕,屏幕上那个人……
“本台消息,我市作家……《今天的明天 明天的昨天》获得茅盾文学奖。”
“快看!那是你耶!”她向上指着,双脚蹦了起来。
就是刚才镜子里那个青年,满脸胡茬子,厚厚的眼镜片,呆里呆气。
他笑了,原来以后的我,这么厉害啊。
路边有辆车,他上去试了试,居然会开。也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儿不懂驾驶的,不多。到乡下需要八个小时,他们从麦当劳拿了汉堡、鸡腿和可乐。
高速路插过田野,风吹麦浪,一地金黄。
他们把车横在路当间儿,四门敞开,蘸着麦香吃东西。他专注地啃一只鸡腿,她专注地望他。午后的阳光洒下来,他的两鬓有些斑白,背似乎开始驼了。
车载收音机里传来主播兴奋的声音——
“本台最新消息,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205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
吃了一半儿的鸡腿凝在他嘴边。
“你五十五了啊。”她爱怜地抚摸他的后背,似乎自己比他的年龄还大,“你真了不起,能得诺贝尔奖。为了换这一天,后悔吗?”
“嗯!”他又开始吃鸡腿,“后悔!”
将最后一点肉吃进嘴里,他吮了吮鸡骨头,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这么精彩,后悔没跟他们好好还价,兴许能多换几天。”
“净说漂亮话!”她拍了他一巴掌,“你懂我问的意思。”
他摇摇头,很严肃。
终于到了乡下,天已擦黑。
她和他家在这里都已没亲戚,房早就塌了。一群还没回窝的鸡,在砖缝里寻找吃的。
他的步履有些蹒跚,需要靠她搀着,才能走好。他像一个离家很久的游子,在孙女的陪伴下回到故乡。他们抚摸着门口的那株桃树,似乎还能感觉到光滑,那是当年被他们用屁股打磨过的枝桠。
他走不动了,他俩在打谷场的稻草垛上躺下。
天空如洗,繁星一览。
“我们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吗?”她问。
“嗯,当然。”
“不是,我是说最好最好的那种。”她说。
“是最好最好的。”他老胳膊老腿,但心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那……要不要表示一下?”她又说。
“好!”他费力地抽出枕在脑袋下的胳膊,双手在嘴上拢了个喇叭,冲着高高的夜空,大声喊,“……是天下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
她笑了,“你这个笨蛋。”
他也笑了。
两人挂着笑,睡着了。
3月1日的阳光照在脸上,他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她没有醒过来。
有乡人路过。他用那辆车给她换来葬礼和墓碑。
“你先睡在这里,我马上就来。”他想。
他借了根拐杖,搭车去城里,找到时牙行。
“店家,你们弄错了。”他进门就嚷,嚷得急了,连连咳嗽。
圆脸瞅瞅他,认不出来,“你是谁呀?”
“咳咳咳咳……”岁月真的不饶人,这副老皮囊,怨不得别人认不出,“是……咳咳……是我,二月二十九。”
“哦!”圆脸恍然大悟,“您安好。”
他顾不得寒暄,“错啦,错啦!时间已经用完了,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是不是忘记扣佣钱了?”
圆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占了便宜还不好,还有上门儿退便宜的?”
“不不不!”他急了,又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我不占你什么便宜,到时间就是到时间了。”
圆脸看看麻子,麻子点点头。圆脸从柜中拿出一本黄册子,翻到一页,抬头看了看他,说:“本不该跟你说,但现在起了纠纷,就不得不说。你的余年本是七十一年,但在你之前——也就是你来的那天晌午——来了位女客。她有一载余年,她说她得了病,要那一年也没用,不如送给她的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你。”
“所以,我说过,佣钱要翻倍。”麻子插过来,“七十二年,其实你付得起。你非要还价,我也不能揭破,只好给你个实惠。我们牙人,童叟无欺。”
他老了,腿脚是不行了,晃了两晃,差点摔倒。圆脸忙绕出柜台,把他扶到墙角的太师椅上坐,麻子送了杯茶来。
“看看吧。”圆脸从黄册子里抽出一张夹页,“你的时间也不多了,可以给你瞧啦。”
他才看了一眼,手就剧烈地抖了起来。那是她娟秀的字迹——
再也不能见面了。
没等到2月29日,实在可惜。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渴望过这个生日。你总是这么自以为是,谁说这一天只是我的生日来着。你去查查日历吧,知道“女性表白日”吗?
这一天,四年才一次。做女孩子,真难。
算啦,既然等不到2月29日,我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我走了,剩下的时间托时牙行转给你。
你的作文写得真棒,将来一定能出书。我把这一年送给你,希望你能多写点文章。愿你的笔下,能有一个我。
他没再说什么,在圆脸和麻子的注视下,走了。
她的墓旁,搭起个茅草棚。一个白头发老头儿,佝偻着背,日夜住在那里。
晴日扫满地落叶,雨天遮一片浓荫。
插图/常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