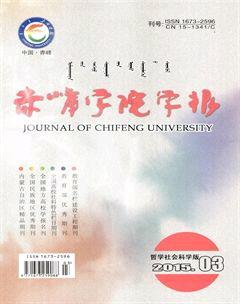女性小说到影视生成的性别文化整合
马丽敏
摘 要:自编自导的“女性电影”经常会表现出文化传达上的孤立和边缘,由女性小说改编的女性电影,表现出了性别文化向大众化表达迂回靠近的努力,而女性小说与男性导演的合作更可能走向性别文化表达的和谐与整合。以目前“共读”研究重整合的思路,关注并赋予女性小说影视生成的价值和意义,寻找影视媒介传达性别文化的有效路径,打开女性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女性小说;影视生成;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144-03
“女性意识”,作为女性文学研究中不可跳过的关键词,在女性小说影视改编中被过度强调。女性小说影视改编的不少研究,大都表达了对女性文学在目前改编现状中的不满,似乎在这种“主体性失落”、“性别意识妥协”的论调中做了过久的停留,可再生的话题已经所剩无几。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由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览,势必要求主体之相应改变。”[1]本文以重互文与整合的“共读”研究作为审视问题的视野,希望女性小说的改编能让性别文化传播找到更适合影视媒介,更符合当下时代发展的路径和表达机制。
一、女性电影的失效表达
选择是否以一部适合改编的女性小说为蓝本,决定了影视文本在性别文化的表达路径选择的狭隘与开阔,封闭与开放。由女性自编自导的女性电影还在依然故我地走着女性文学传统中自我言说的“消解——建构”;而在以女性小说为蓝本的影视改编中,呈现出了认可视觉时代的文化融合以及影视媒介的大众和商业化特性,在输出性别文化时,讲求在妥协中再生,缓冲中前行,确实让女性文学影视改编获得新的生机。
(一)女性的自编自导:在坚守自我中滑入角隅
打着“女性电影”旗号的电影,从女性视角、女性形象到女性意识的强烈表达,无不是对女性话语权的理想建构,但作为商业化特征明显的文学形式,她们过于注重传达自我,忘记电影更重要的本质是大众的消费产品,这在性别文化的传达和输出上从结果来看并不尽人意。
《无穷动》自始自终没出现一个男主角,女主人邀请三个女友来家中过除夕,和气的表面在女主人的质问中被打破了,“寻找狐狸精”的主题就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每一个漫不经心的镜头面前,看似围绕着追问“谁勾引了我老公”,但大家又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其他,女主人也并不懊恼这样的非正面回答,而就在她们的回避中享受着女人在一起的种种:大声吧嗒着吃凤爪,随后无聊地看着春晚。最终让我们意识到,男人在此完全消失了,他们从来都是不在场的,他只是生活的一个无聊的消闲。在逻辑不佳的镜头排列下,女性的世界被着重凸显了,但是要说什么呢?男人的变心,男人的失踪,女人在形式上给予了一些配合式的寻找,但终究不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女人们在一起。这样的主题在并没有女权思潮兴起过的国家,确实激进了些。不仅如此,作为大多数受众,她们认为电影缺乏叙事,情节乏味,觉得仅仅是女人之间的一次毫无故事的相遇,无聊的开始,寂静的结束,掀不起一点涟漪。受众在这里没有共鸣,就连起码折影视文学理应具有的娱乐作用也消失殆尽。到这里,性别文化的建构再次成为了行为艺术。
《我们俩》深受评论界的推崇,认为是中国影片走艺术路线的成功案例。作为女性电影,导演选择了生活中边缘的小人物老太太和女学生作为讲述对象。与《无穷动》相似,电影没有男性。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的叙事要顺畅很多。一个温情小故事,在老奶奶和女学生之间展开,从最初的房东和房客,一个老女人与小女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出现在观众视野,但最终陌生猜忌转换为一种彼此的照顾和思念。影片清新温暖。当然,作为一部艺术小电影,它是成功的。而从性别文化表达的有效性来考证,这样的电影,只因为缺乏一种“双性和谐”理念的融入,性别文化选择中抛弃了当下还远远不能逾越的主导。作为电影,你不能忽视大众,更不能急于求成,毕竟不卖座也不是为艺术献身的光彩借口。
李玉导演的多部女性电影,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从《苹果》到《观音山》再到近期的《二次曝光》,每一次都是在述说着女性特有的性别经验,或者说女导演就是在进行创作上的“私人化”。但是,文学的思维,放在电影这个媒介中,就发生了一种难以融合,甚至两相背离的现象。观众作为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创造者,在看了这样的女性电影后,势必会造成观影后的失落。因为这里有太多导演自己的“私人话语”和个体经验,女性意识的鲜明带来的却是观众的不知所云。而导演期望的“受众”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接受”,普通观众没有感受到“寓教于乐”,而是“头疼欲裂”,受众群体最终成了一个缺失了能指的符号。
(二)以女性小说为改编文本,走出“她”的世界
女导演在改编女作家的文本时,在性别文化表达上依然很难实现大的弥合,缺失了“双性”的交流和互动,女性意识这个鲜明的符号也仍然桎梏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输出性。但潜意识中突破创新的创作心理和一种影视生成的内在审美机制决定了二次编码的必然,呈现了影视生成中努力追求的大众接受。
陈冲改编严歌苓的小说《天浴》和以上两个文本相比,性别文化的表达有所转变。电影《天浴》基本尊重了原著的精神,但女性意识在电影中并不表现出有意强调。从电影文本中的视角转换来看,原著一直采用女性作者全知者的视角,电影中转换为男性讲述,最先从秀秀的初恋男友,再次转换为老金,来讲述秀秀的一生。这两个男人的视角尽管对剧情的发展起不到大的转折,但从文本视角看,这样的安排,导演是有意将原著那种女作家的女性视角向男性视角转换,吁求实现一种性别文化的融汇。当然,小说本身的性别文化的和谐观也决定了导演在影视编码中的顺手推舟。小说起笔是以秀秀看老金,最后收笔却以“老金感到自己是齐全的”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对男性生命的关怀。所以正是因为女性小说本身具有的性别文化表达的明晰,在影视生成中,它才能把握得明确顺畅。从小说的销量和电影上映后到目前为止的改编评论(研究成果)来看,性别文化的表达在这部电影中已经成功地被传输了。
综上,我们看到这些女导演自编自导的影片,文本叙事都比较虚空,少了很多文学性的元素。话语的内在封闭性导致了影视文本意义的再生性疲弱。作为审美源,这样的女性电影不能赋予观众更多元的审美想象力,女性意识仅仅成为了符号性的存在,根本上没有进入一种电影生成前,就应该具备的一种文化建构逻辑。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捷径就是选择一个好剧本。影视改编以“共读”审视作家的文化思考,追问小说文化意蕴的价值,导演在将文学思维的拿来和商业化元素的兼顾下,自然而然地铸成了电影的完善。其实,商业化的元素本身并不是一个负符码,但是在内陆电影的研究中,很多时候将商业化元素看成一部有深度的电影的天敌。于是,这样就有了今天女性电影,一则缺乏文学思维的清晰,再则因一味形而上地追求女性意识的执着,忘记尊重大众文化时代影视作品自身的规律。性别文化在影视媒介中的表达转换理应提升大众的审美品位,但更应该做出视觉时代中弥合与融汇的选择,这样让女性文学发展的每一步都能在性别文化建设的路上留下一个印迹。
二、女性书写与男性导演的“双性和谐”
之所以将女作家和男导演的合作视为有效的文化表达机制,是因为这里突出了改编影视剧本身的“共读”特质,即当一本女性小说被改编后,影视的男性编导就在进行着主流文化的审视与创造,在一种历史与现实、主流和非主流的合谋中铸成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共读”。从目前发展来看,性别意识的表达依然是自言自语,受众面窄。当女作家的作品被男导演改编后,其女性意识尽管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是有所滑落和冲淡,但对于性别文化的表达来说却真正是一次有效的输出和表达。纵观当下几部成功的改编电影,他们其中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性别话语的表达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电影文本在性别文化表达层面的新叙事,值得考证。
(一)《生活秀》——温和与理解的转换
《生活秀》由男性导演霍建起改编后,电影线条明朗,叙事紧凑,有了一种温和与理解的意蕴。尤其在男女关系上以理解和大爱打开了电影生成的普泛价值。这种转化的内在路径表现在:(1)原著来双扬的妹妹来双瑗是个较有个性的人物,池莉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是想极力突出来双扬的能干、善解人意、母性情怀等等,总之将来双扬的魅力竭尽全力地凸显,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来双扬的中心化。而电影中导演删掉了来双瑗这个人物,这样从客观上少了一次美丑对比的安排,更加温和。(2)小说在对来双扬和卓雄洲的故事中,对男性角色的着笔并不多,读者对他的男性魅力印象也不深刻。到了电影,导演在对卓雄州的塑造中增加了魅力值,演员陶泽如将一个具有成功的商人和军人气质的男人塑造得很成功,这样观众看到了这里的爱情不只是小说中数次强调来双扬答应约会,更多是因为“毕竟买了两年的鸭颈”这样的世故;小说写到床上的卓雄州时,强调了年过50的男人的无力、干瘪和丑态。电影改编将这个做了融合的处理,男性的魅力、主动和女人的感动、欣赏,爱情的味道渐渐浓郁起来。(3)电影对两人的分手做了创造性的编码:小说中的卓雄州是无情的,等了两年的女人一夜之后就扔掉了,这一点不近乎人情;电影中卓雄州是因为妻子的背叛不愿意再踏足婚姻,而来双扬坚持结婚致使两人分道扬镳。饶有意味的是,电影里卓雄州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说“下次,你想我了,我们再来”,忽然意识到这里的主体性问题,改口为“不,不,是我想你了,我们再来”。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导演的一句台词里承载的是文化的命题:男人其实本能上可以放下的,但社会性让他们不得不扮演。这样,将矛头指向的是男权中心文化,而并非这一个男人。对男性的理解之心可见一斑。导演在这样的双性话语的相互照映和关怀下,让电影更多了一种性别文化的弥合与融汇。尽管其中女性意识有所淡化,但在商业化大众化的处理上,男导演的性别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文本性别文化表达上有所控制,不会过于急切,这就使作品原本的浓烈而边缘的女性意识打上了一种“双性和谐”意蕴的符码。
(二)《金陵十三钗》——从展示女性到体验女性
以下从性别文化输出的有效性这个视角来关注两部影片《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这里并不涉及两部电影的价值比较,只是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来研读。
同样的题材,相似的故事,由男性导演、编剧的《南京,南京》,女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女教师和妓女小江以及其他两位女性,都被导演赋予担当拯救一座城的意向,主题的颠覆性可见一斑。影片确实能看到第六代导演的锐气和突破,选择这样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当导演理念先行地想表达女性在历史中伟大的举动时,具体的叙事却让人看到了女性的被侮辱和承受。镜头告诉我们的只是个展示的动作。影片一上映就引来评论热潮,两年间中国期刊网的研究论文就有15篇之多,但其中只有1篇是写到女性形象的人物分析,这就更能说明这样的电影看似为女性打了个翻身仗,但其中缺失了男女对话带来的互动交流,也缺乏了一个“文本固定”的场域,致使它不能享有更为持久的文化影响力。
不同的是,在《金陵十三钗》里,从电影上映后,中国期刊网对《金陵十三钗》的改编研究一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有10篇。这些文章都是对改编后的电影和小说做文本比较,评论中都涉及了性别文化的内容。先不说男性导演和女编剧为同一个故事商榷创作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次双性和谐的实践,即使就在女性作家做出让步,主线从女主角书娟和玉墨的故事换成了男牧师的成长,但欣慰的是影片的视点做了恰当的位移,让我们看到女孩成长中的身体秘密,女性的言语,女人之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女性之间微妙的情谊,女性伟大的母性之光,也看到了一个妓女在最后关头的后悔、犹疑和恐惧。这里就不仅仅是导演在展示,而是也跟随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女性视角在体验。不仅如此,当观众对影片中故事的叙述尤未尽兴,他们可以重回小说,寻找原典,弥补审美缺失。正如王菲在她的《21世纪新媒体与文学发展》一文中针对当下先影视后小说的现象,提出了“文本固定”的概念,尽管,本文所提到的改编现象从逻辑上并不符合这种先有电影后生产文本的顺序,但我们可从中看到,目前对于新媒介时代,电影和文学的关系并非更加疏离,而是更加亲近。最终不论电影运用多少科技,多少艺术手法,观众还是想通过转化到读者拥有更多收获,因为 “书写还鼓励读者形成批判性的思维:文字被固定在书页上,读者因而可以对文字反复思量、回到前面的段落并重新考查论辩的来龙去脉”[2]。由此可见,以女性小说为改编文本的电影都或隐或现地要求导演和编剧保留原著的一些性别文化的传输因子,这就让当下影视剧女性文化缺失的现象多了一次性别关怀的引入;另一方面因为影视改编中性别文化有效的大众化处理,仍在大众视域边缘行走的女性文学让观众潜在地成为了读者,从影视改编到原著,传统的阅读心理让读者更为尊重原著,这对女性文学来说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收获。
三、结语
在图像时代女性小说虽被电影作了视觉化的转型和奇观化的扩张,但也在传播上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实则给处于生存尴尬中、仍处在边缘行走的性别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系列的变化和转向中,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创作观念和叙事方法也随之渗透到电影中去,在无形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引入电影作品,女性文学的文化基石以别样的方式在电影中承续下来。
在这个视觉文化难以阻挡的时代,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介下的文学生成形态,并能从中寻找相应相生的合作机制。但“视觉与听觉,图像与语言,是我们生活所借助的符号,人被这些符号所包围,归根结蒂,人仍然会成为这些符号的主人”[3]。无论在小说还是改编的电影中,这种符号间的转换,抑或是一种重新解码,编码的过程都是将文化进行了一次激发和创新。相信有意识地介入影视生成文化整合的理念,无论对传统的纸质文本还是当下视觉文化的影视艺术都是一种推动和促进。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与电影又一次紧密的结合中,更多地建设优秀的文化,昭示更加真实的本质的人的生存图景。
参考文献:
〔1〕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J].中国社会科学,2004(5).
〔2〕王菲.21世纪新媒体与文学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24.
〔3〕堂圣元.读图时代[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77.(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