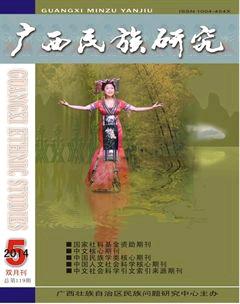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葛政委 黄天一
[摘要]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族群认同
[作者]葛政委,三峡大学民族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黄天一,中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湖北宜昌,443002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5-0106-005
两湖西三角高地尽管高山谷深,交通不便,但邻近长江中游平原,中央王朝很早就在这里经营。公元前223年,秦在此设黔中郡。公元前205年,汉又设武陵郡。到宋朝时,湘鄂西高地一带的“徼外之民”、“蛮”逐步内化为“熟蛮”、“土人”、“土丁”了。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带实施土司制度,以此稳定“内地边疆”和防御西南潜在的动乱。容美土司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被政治建构起来的。在这一政治建构和“再边缘化”的过程中,“熟蛮”、“土人”的族群边界重新得以塑造与强化,土司之内的“土民”对国家的认同得以建构、发展、成熟与升华,土司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繁荣。从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历史与事实出发,分析其本质、内涵、特色与价值,可以深化“边缘”凝聚于“华夏中心”历史经验的认识,其所展现的理念与经验对我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本质:多民族国家认同
元明清时期,我国已发展为成熟的多民族国家。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在两湖西三角地带设置了大量土司,容美土司就是湖广四大土司之一。在这一进程中,容美土司国家认同逐步成熟,并展现出从策略性的王朝国家认同发展到内心深层的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中央王朝只有使自己成为多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的代表,才能让容美土司认同为“正朔”或“正统”。只是元朝和清朝因受统治者出身以及实施了不利于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民族歧视政策,从而让容美土司在国家认同上表现出相当的策略性和矛盾性。
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容美土司对不同时期王朝的认同表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两湖西三角高地实行羁縻制度,选用地方“蛮酋大姓”治理地方。《鹤峰州志》载:“宋嘉泰中,湖南安抚赵彦励请择素有智勇为蛮夷所信服者,立为酋长,借补小官以镇抚之。五年之间能立劳效,即兴补正,从之。”自元代起,中央王朝又对这些原羁縻地带实施土司制度,但在土司制度实施初期,王朝难以管控容美土司地域的“蛮酋”。元至大三年(1310年)四月,容米洞官田墨纠合蛮酋,杀千户及戍卒八十余人,俘掠良民。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夔州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为寇。泰定三年(1326年)四月,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结十二洞蛮寇长阳县。容美土司并不惧怕蒙古人主导外大中虚的中央王朝。这一阶段容美土司对王朝的服从更有胁迫的味道,内心对元王朝并不认同。明代,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域贯彻土司制度较为彻底。自永乐年间至明末以及南明政权时期,容美土司对中央王朝国家的认同不断强化。容美土司在明代进贡次数居西南诸土司之首,还屡次参与王朝征调,在平定水西土司、播州土司的叛乱,打击叛乱的农民军以及入侵东南沿海的倭寇,防卫苗区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进入清朝后,容美土司对于这个满族主导的政权始终抱着矛盾的心态,只是迫于压力,容美土司不得不在清初各种势力中周旋。容美土司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投降了清军,此后,容美土司与清王朝就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祝光强、向国平先生认为容美土司对清廷政权存在狐疑之思,即:“清朝定鼎中原后,开初并未有将明朝已经完善的土司政策延续实施,这使得容美土司大为愤懑。”尽管康熙二十年(1681年),容美土司田舜年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披陈忠赤疏》大力宣扬对清王朝的认同,但是其在行动上又处处防备清朝。容美土司对清王朝的矛盾是因为在当时清王朝还不能成为多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不被容美土司认同为“正统”。这正是说明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在内心深处已经转化为对代表整体利益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可见,容美土司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逐步加深的。这其中,明代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一时期,在容美土司的努力以及中央王朝的用心经营下,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基石不断夯实,许多有利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因素在容美地域族群中沉淀下来,国家认同的内涵变得充实。容美土司对清王朝的矛盾性认同更说明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已经超越了族群利益,更加注重多民族国家整体的正义。
二、内涵: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
经过长期与中央王朝的交往与互动,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内涵逐步完整与深化。到明代中叶以后,容美土司国家认同逐步超越族群策略性特征,真正建构起国家认同的基础、核心与表征,容美土司国家认同也不再停留在族群认同与王朝认同上,而是追求对“王朝正统”的认同。此时,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内涵也才真正丰满。在这里,文化认同是基础,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
容美土司夯实了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有学者认为国家认同体现为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认同。这一观点尽管不全面,但其强调国家认同的文化属性是正确的。容美土司国家认同之所以能超越族群认同与王朝认同,是因为其在与“华夏中心”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培养起独立的“正统”、“正朔”意识。自田世爵整顿容美土司后,汉地的文学、艺术、戏曲、宗教迅速在容美土司传播。容美土司在吸纳大量外地文化的同时,又积极创新,发展出土、客文化融合的土司文化。容美田氏“文学世家”以唐诗为叙事模式,大量叙写土司内外情境,并在多首诗歌中表达对王朝正统的忠诚与热爱。这些诗歌深深地蕴含着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就是说,容美土司与汉地的文化接触、磨合、采借、融合与创新真正夯实了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基础,这也为容美土司国家认同境界的升华起了奠基性作用。
身份认同的转换意味着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核心的形成。身份认同是指对自我特征以及属于哪个群体的认识。清代文人顾彩在《容美纪游》中说:“其(田舜年)先世田弘正,唐魏博节度使,土司若忠峒、忠孝等宣抚司,多田姓,故田亦巨族,然皆土人,惟君先世系中朝流寓,不与诸田合族。”也就是说,容美土司田氏统治者努力划清自己与“蛮田”的身份界线。明代,容美土司田氏统治者在“弃蛮名、取汉名”、“再造家谱”等一系列运动中,把先世追溯到在施州担任长官的陕西关中汉人田行皋。《容阳堂田氏族谱》载:“皋公从高崇文讨平刘辟,授皋公施、溱、溶招讨把截使,后加兵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施州刺史,仍知溱、万、溪、溶州诸军事。”这种族群根基历史的重塑和改造彻底地建构了土司“主体性认同”的核心,身份转换也真正建构起容美土司认同“华夏中心”的心理根基。
政治认同是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表征。著名民族主义研究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政治认同体现在对政治制度以及相对应的权利义务的履行上。一般来说,政治认同是可视的、策略性的和表征性的。容美土司对明王朝和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也表现出这些特征。容美土司认同明王朝,超一般地履行土司职责。明人田汝成所说:“其所以图报于国家者,惟贡,惟赋,惟兵。”尽管不需要向明王朝纳税,但是容美土司积极从征和纳贡。根据《明实录》记载,容美土司几乎参加了中央王朝在武陵民族走廊所有的平叛征调,数千土舍、土丁、土妇还远赴闽浙一带抗击倭寇,并取得重要战功;容美土司在明代进贡40次,所属椒山玛瑙长官司、五峰石宝长官司、石梁下洞长官司、水尽源通塔坪长官司分别进贡27次。容美土司并不认同清王朝。在明末清初容美土司主田玄和三个儿子在同一晚上创作的40首《甲申除夕感怀诗》中完全可以看出容美土司的内心真实想法。在政治认同中,认同者的话语权力可能是被压制而得不到表达,也可能是想表达而不让表达。因此,容美土司政治认同行动只是表面现象,有时表达的是土司的真实意思,有时仅仅是策略。
可见,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与政治认同并不总表现为一致性。历史上容美土司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朝着多民族国家认同方向发展,但是容美土司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有时候也表现出巨大的矛盾性,这会困扰容美土司的族群策略和行为,甚至引发自身与王朝的危机。从容美土司的历史看,明朝中后期,这三者较为统一;元至明初以及清初,这三者存在局部矛盾。但在这种曲折与历史变迁中,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内涵才真正成熟和稳定。
三、特色: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
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在发展丰满过程中,逐步显示出特色。在容美土司存在的相当长时间里,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机结合,和谐共生。在当今世界我们既可以看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割裂的现象,也可以看到族群认同向国家认同升华的有益实践。容美土司提供了一个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处并有机结合的案例,其显示的边缘族群凝聚于多民族国家的关系机制值得探索。
容美土司的族群边界是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在著名族群边界论者福雷德里克·巴斯那里,“族群是一个归属性和排它性的群体,它取决于边界的维持。”而容美土司的族群边界却不是巴斯所描述的那样。明代中叶,关公信仰已成为容美土司最重要的信仰。清初文人顾彩在容美游历半年之久,他在其著作《容美纪游》中曾写道:“土人最尚关公”。他曾目睹:“十三日以关公诞,演戏于细柳城之庙楼,大会将吏宾客,君(土司主田舜年)具朝服设祭,乡民有百里来赴会者,皆饮之酒,至十五日乃罢。”在地方史志以及田野考古中,笔者发现容美所有重要土司衙署、集镇都布局有土司官修的关公庙。关公信仰一方面有强化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的功用,这是因为土司社会的军事性质以及土司尚武的习俗与关老爷的气质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关公信仰也表达了国家权力在土司社会的“在场”以及族群在多民族国家中的位置,这是因为关公信仰也是中央王朝大力推崇的。因此,关公作为族群边界与认同的符号也在表达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
容美土司文学主位表述中的族群与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容美土司文学并不是“纯洁的少数民族文学”,而是土、客文化交融与创新的结晶。在土司时期的田氏五代九位诗人以及改土归流后田氏后裔的诗文中,这些文化的主位撰写者不仅表达对家乡的认同,也时刻不忘记心忧天下。田泰斗在描述其故乡时写道:“风无淫靡政无苛,鸡大桑麻尽太和;问是桃源君信否,出山人少进山多。”而当国家处于忧患时,田玄写道:“亡国音同哽,无家路倍岐;烽烟匝楚甸;惊跸远京畿。”在告别南明重臣文安之时,又写道:“尔来关塞惊风迫,为恐篮舆更远迁。”明代中叶后,容美土司的主位表达把“家乡”与国家命运联结在一起。
土司的内部斗争不能危害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基于土司制度“不相统属”的内在分立特性,两湖西三角土司结成了普遍的联盟和世仇关系。湖广四大土司的永顺、保靖、容美、桑植之中,保靖与容美联盟,桑植则与永顺联盟。其他小土司则受大土司的摆布。顾彩认定容美地位时说:“惟桑植,永顺,保靖,及蜀之酉阳,势位与之相埒,其余忠峒、唐崖、散毛、大旺、高罗、木册、东乡、忠孝等名目,不可悉数,皆仰其鼻息,而凛其威灵。”康熙十九年(1680年),容美土司主田舜年在《情田洞碑记》中写道:“三年之内,报桑人欺侮之仇,平悉洞负义之仇,雪东乡以完先世未了之恨。”尽管土司内斗不断,但当国家需要时,容美土司与世仇土司又联合起来,服征调、抗外敌、纳大贡、除叛乱。明清两代,湖广四土司在平播州宣慰司、水西、永宁土司的叛乱、“夔东十三家”、闽浙倭寇、贡楠木等王朝国家大事上保持高度一致。
容美土司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上所表现出来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土司制度体系中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示范性。容美土司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与容美土司所呈现的族群符号、文学表述、政治制度设计等因素有关,但其完整机制还需进一步探讨。
四、价值:国家与族群共创繁荣与发展
容美土司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机结合,相互促进,这既赢得了族群文化的繁荣和族群本身的发展,又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族群与国家都是受益者。容美提供了一个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共创繁荣与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有多个要点。
族群要在国家认同中拓展其发展空间。族群若过分强调地域认同,就会大大压缩族群生存的空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容美周边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和巡检司,并采取“土蛮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的边地政策,严格限制土司的对外活动。在容美东、北缘地带,中央王朝在白石关、梭草关、旧关堡、蹇家园、渔洋关、长毛关、百年关、菩提隘、连天关、石柱关等十个关口设立了巡检司。在容美东南缘地带,中央王朝以九溪卫为核心,千户所、百户所为节点,在湘西北的澧县、石门、张家界、慈利、桑植等地建构起狭长的防御土司的卫所带。政治建构强化了容美土司的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也约束了容美土司的发展空间。然而,容美土司在认同王朝国家的过程中,采取多种策略,打通与汉地以及中央王朝的经济文化通道,边缘族群的“向化”之心逐步为王朝所理解、包容和赞赏,也逐步为王朝国家所倚重。正是如此,容美土司在军事、文学、戏曲、建筑等方面,无论是其成就,还是其影响,都大大超出土司地域,容美土司也为族群自身发展创造了无限的空间。
族群要在认同国家主体民族情景下分享国家主流文化和物质资源。国家主体民族构成国家的主体,并承载着国家主要的物质和文化财富。认同国家主体民族,边缘族群才有可能分享国家的主要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才能在与主体民族共享资源中走向繁荣和发展。历史上,容美土司就深谙这一要点。从物质上看,容美境内物产丰富,但也不能自给自足。《宋史》载:“蛮无他求,唯欲盐尔!”顾彩在《容阳杂咏》一诗中也写道:“与人钱钞都抛却,交易惟求一撮盐。”从文化上看,容美土司早期行为甚至为族人所不齿。明代前期,容美曾发生一起争袭案,土司主田秀之庶子白里俾弑父杀兄,独自里俾之弟田世爵逃出魔掌。田世爵认为文化上的“野蛮”是这场惨祸发生的根本原因,“公痛惩乱贼之祸,始于大义不明,故以诗书严课诸男,有不嗜学者,叱犬同系同食,以激辱之;以故诸子皆淹贯练达,并为成材。”明代中叶后,容美土司努力打通与汉地的地理、经济和文化通道,土、客互动频繁。中原动乱之时,容美土司又收留了来自中原的一大批官员、僧侣、工匠、艺人。正是如此,容美土司才能在与国家主体民族的交往中获取资源,提升自己,创造繁荣。
国家对族群认同应是包容和引导的统一。土司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凝聚边缘的重要机制,曾以其包容性与建设性的特殊优势,大大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延续、稳定与发展。土司制度既照顾到边缘族群的特殊性,也不忘以建设性的方式引导边缘族群进入“华夏”。容美土司族群认同的历史变迁表明,族群认同需要得到王朝国家的包容和引导,这是因为族群认同置入“国家在场”和“族群在国家位置”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非常漫长,需要时间来磨合。容美土司早期族群认同中很难有王朝国家的因素,而到了王朝更替之时,族群认同中置入新王朝因素时又需要更多时间。也就是说,国家不能放任族群认同,而应该在容纳的前提下加强引导,让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逐步消除隔阂,相互置入理解因素,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
总之,容美土司提供了一个国家与族群共创繁荣与发展的典型案例。在族群与王朝国家的互塑中,容美土司逐步消除了中央王朝对她的误解,中央王朝也越来越倚重和赞赏容美土司。容美土司在这一进程中创造了令人称赞的“文治武功”,国家也得以在容美土司的繁荣和发展中受益。改土归流后,这一地域的“土民”迎来了大量外来族群,此时“土人”的族群性已具有国家大局观念和主体民族的包容气质,“土民”与“客民”也得以在此和谐共居,共同开发原来人烟稀少的湘鄂西山区。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