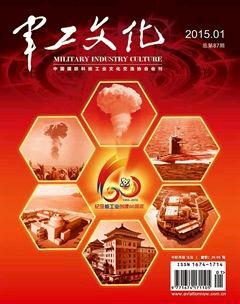快堆是国家的需要
一生中,父亲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1921年,他还没毕业就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领导点名要去工作。后来,祖父过世,父亲要担负家庭重担,才被迫回到母校教书。此后,去科研单位工作,成为父亲的最大愿望和永远的遗憾。这在他年纪大时,还念念不忘提起那段往事。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去科研单位工作很光荣。
父亲回扬州教书时,还处于抗战时期。当时,父亲知道日本人正在抓学化学的人为他们做炸药,父亲就装手抖无法做实验转教数学。父亲在扬州中学是很有名的数学老师,但他热爱化学,不仅热爱,还有知识分子面临国难民灾时情不自禁的爱国情怀。这种对一门科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从小我就耳濡目染。我们家里有三柜子做化学实验的器皿,我三岁起,就开始拿着那些烧杯、试管,倒来倒去,不许倒在手上,培养细心。高考前,我曾有想到杭州大学学纺染专业,因为父亲说学纺染专业很容易转去做炸药,一旦国家有难,就可以去研究炸药,报效祖国。但是高考那年,清华大学的老师来扬州招生,我数理化综合成绩好,老师想挑我去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相比去清华读物理,当时我个人更想去北大读数学。父亲得知清华工程物理系是因国家需要而设立的,就劝说我去清华。
清华毕业后,我被分配到401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父亲得知后,特别高兴,跟我讲:“能到科学院研究所工作最好不过了。”
说起扬州、说起家、说起父母,我有个遗憾。就是1979年和1980年父母相继去世,我都没能见他们最后的一面。
父母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怎么做人:对国家要做贡献,对别人要和谐,不争不吵,自己要不张不扬。
在清华读书时,清华校长蒋南翔教导我们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当时,每天下午4点半后,同学们都会去操场上锻炼身体。读好书,锻炼好身体是我这些年来最简单朴实的一个想法。1961年从清华毕业到今年,我已经健康工作了51年。
清华的教育,使我有这样一种思维,就是一个工程,要先从物之理讲起。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介绍快堆,总会引用上世纪40年代意籍美国科学家、反应堆之父费米的两句话:“会建增殖堆的国家将永远解决它的能源问题”、“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前一句是从物理的道理讲快堆能使核能利用的时间更长,这个道理入手讲起,会更容易让人接受和理解。第二句再去讲快堆能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
在原子能院工作这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钱三强、戴传曾、朱光亚等老一辈科学家们及“401精神”。
我刚刚到原子能院时,钱三强先生就对我们年轻的同志们提出要求,如果5年之内不能带领师弟师妹们做研究工作、10年之内不能掌握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带领一帮人工作,就不宜留在院里继续工作。
我还记得我们晚上从工作区办公室回住宅区,每每看到老专家戴传曾先生挑灯夜读。他从生活区到办公区都是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他们对学术的高要求、对生活的简朴、能经得起艰苦条件的考验等品格,对我影响至今。
搞快堆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是一个团队。
在快堆工程部,我是总工程师,要作决策。但每一次的决策都不是我一个人在作决定,是集体的智慧。
我们这个团队经常会开会进行集体讨论。每次开会前一天晚上,我会事先针对问题心里有一个结论。在会议讨论中,我认真听大家的意见。如果有一种比我之前设想更好的结论,我就会马上调整自己的观点。如果是有两种意见的话,我会认真听,认真分析,使大家意见统一起来。不管是老同志们还是年轻同志,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只要是言之有理,我都会采纳。相信科学是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也是我对这个团队的一种态度。
事实上,就是物理与情理的交融。物理是道理,情理是一种和谐关系的处理。物理经过讨论清楚后,大家对快堆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工程只有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才可以完成。
我喜欢称快堆工程部的每一位同事叫作同志。同志就是有同一个志向。我有时也会跟大家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拥有同一志向——替天行道。快堆是国家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人民就是天。
现在快堆并网发电了,但离真正的大批量商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快堆商用才是真正为国家作出贡献。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令我欣慰的是快堆是一个团队,一个正朝气蓬勃的团队。我自己想了一句话:“天道首步人易老;登天喜见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