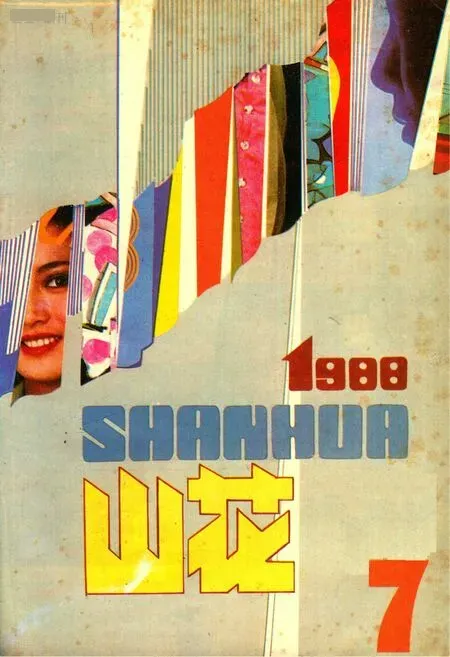土拨鼠的生活


陈寒还没有死的时候,我给他发过两条短信。那个下午,我们离开了大马岛,在大马岛的时候,我们习惯朝风略疏的西北方眺望,那个方向灰暗、金黄,像一条鱼线,却牵引我们往岸上走去。遥远的是我们更年轻的时候,穿梭在浙赣线、湘黔线的火车上,像无业青年,我们这一船人的爱情,多是从那时候开始。
“9月27,就这么定。”洪易算准日期,那时退赤潮还能望见海岸线,我们很累,陈寒说,要离开他妈的海壳船了。离开船上的“福拉莫斯”,陈寒早早开始准备,直奔烧烤店。无边无际的海上,鱼虾现成,眼下多的是青蟹,陈寒又最爱吃烤蟹,他喜欢橙黄的焦肉和膏黄,一股嗓子熏燎后几近冒烟的快感。
不想刚靠岸,陈寒就不辞而别地走了。听王梵说,陈寒一下船,背着麻布袋,装束像个老矿工(为了遮人耳目,说在昌吉老山挖石头),走的时候头也不回,他只跟王梵说半个月后汇合,也没说离岛,王梵转达给我和洪易。
“估计去洗脚店会相好了。”王梵一离开福拉莫斯,又变回了原来爱爆料的王梵。不过,出乎我和洪易意料的是陈寒,他有什么事从来只和我和洪易说,陈寒不和王梵说事。
晚上9点,我和王梵、洪易,找准一家烧烤店,我们仨撸着一瓶瓶啤酒,由洪易负责提酒,虽然我们彼此不想再见到对方,可是啤酒喝光四箱,直到洪易再去提酒,我和王梵到阳台上抽烟。
烟这种东西,到这个年龄,我和王梵都少不了,相比我的四元一包,王梵抽的是顶贵的盒子,先前他负责一个鞋坊,把一张张牛皮钉成一双双鞋子,他一辈子没抽过廉价烟。
我们就这样没根没底地抽,熟悉的海上将近鱼肚白的前夕,闪出一线红霞的光芒的时候,王梵烟也抽完了,王梵拍了拍我肩膀,很无趣地自问自答说,“诗人,你说陈真上哪?”船上,陈寒的诨号陈真,霍元甲徒弟陈真的那个陈真。
这时洪易上来了,他平静异常,“他不是跟你说了吗,收了一袋牡蛎交他女人了?”也只有洪易自己回答,“没经常看到他,真告诉你王梵了?”
我没有说话。看着远方那线扩大的红霞,内心陷入死静。我正有点生气,来店里喝酒也是为了驱散霉晦生活带来的不快,不是为了陈寒,而是为家里我的情人李华。船在阿加尼亚,电话与往常一样,由女儿丽子打过来,丽子拼命催。我内心琢磨,心里发悚地想,丽子看到了什么?也许李华真出事了呢。
李华是我女儿的母亲,我还没结婚的情人。李华出事,是一件天大的事,我心里奇痒无比。可是,眼下我才刚上岸。
就着洪易的话,我说,短信我发过,上次自从和他女人口角,陈寒就喜欢关机,我上岸后,也不知道他刮哪里去了。洪易接着拨陈寒电话,也没拨通,他抬起头来说,接下来咋办?
聊罢,我和洪易都要下阳台回家。王梵笑了,讥讽说,有可能和女人留大马岛呢。我说,怎么会呢,还听你说他要离婚呢。王梵说,那就更有人去岛上看他,你要知道他老婆的脚腌得不行。这时,洪易不再想说陈寒了,他打开了我们聚会最后一个啤酒盖,他可能是要赶回去和女人孩子看早上的打折电影吧,他走之前说,我们走,要给陈寒带几串烧烤,带不走,也要用泥巴捏几个。
我说当然可以,然后想想我们的福拉莫斯,我笑了。最小的洪易也三十八九了,相聚在这座城里。那年的午夜,我在火车站寒气逼人的站台碰到陈寒,然后依次碰到洪易、王梵,洪易、王梵都是招募而来的,那时,疲倦、折腾写满我们的四张脸,然后,等我们再次碰到陈寒的时候,陈寒说挣脱吧,远走高飞,我和洪易、王梵一拍即合。只是,我们的挣扎不能向上。而对于熟悉海上的我,离开铁路后干过一阵偷渡客,帮助大连、温州人去日本,更远是连名字都报不出的太平洋上的小岛,而这一切都从那张开呈鳝鱼口的海岸出发。
“早应该看清了。”那年的车站,陈寒他递给我一根烟最后说。
——于是,我又吸了一根烟。在人流穿梭的街道上,我回到我和情人李华的家。
早晨7点零6分,不需摁门铃,直接用钥匙插进锁孔。锁去年才换,托陈寒买的专业防盗弹簧锁。锁口有露水,李华和女儿丽子还没起床。我不想打扰。虽然我知道,一旦李华醒来,将有一场暴风骤雨,史无前例的争吵会打破李华的日常生活。然而,我仍担忧,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毕竟她是我爱人。
我拧开了门,很轻微,再换鞋,可是抬起头来走进客厅,我差点吓了一跳。
李华坐在家里的布艺沙发上,偏着头注视门口,眼角惺忪,神形凝重,看似愠怒。我不应该发声,琢磨着这次回来该怎么过。
出海前,李华是一把左轮手枪,我是土拔鼠。左轮手枪精准,每次射向可爱鼠类的弱点,射准男人所有虚无、飘渺的毛病,不过,她李华不是一个铁心的女人,她手里拿捏的那一颗颗铜锰子弹只是证明——她李华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即使他性情飘浮。十年前,她跟我生下女儿丽子,却不愿意跟我领结婚证。
我很认真地看了看李华,也许,刚才开锁的那一小声“咔嚓”把她弄醒。我笑了一笑,“醒了?”
“没睡。”
“怎么没睡?”我坐到她身边,揉揉眼眶,心里在预备台词。
“你说呢。”李华却看向我的脚。
我问,“丽子呢。”
我朝内室里喊:“你应该起床,好上学了,高一也很紧。丽子——”
这时李华用手抹了一把脸,“别喊了。”
我说怎么了。
“我打了她。”
“然后呢?”
“跑到同学家里去了,说再也不回来了。”
“你怎么能打她?你坐这就为等?”
“你要回来。”
这时她离座,洗了一把脸。回来后再次看向我的脚。没有再说话。
我没有和她辩,我去洗了脚。我在洗浴间一直观察她,像看一个陌生女人,连她的下意识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沙发上的李华一直纹丝不动。等我出来后,她给我倒了一杯柠檬水。我坐下重重咽了口,她已经打开了电视,平常李华喜欢看电影频道,她打开的是《早间新闻》,她仍没有离开沙发。睡醒的暹罗猫从卧室里出来,这时她示意我将脚抬起,还是与以前一样,去死皮,修指甲,按摩全套。已经十二年,李华一直在洗浴城工作,现在她是经理,她的工作是公关,为高端客户。李华为我修指甲的时候,匐下身去,噌噌噌、茨茨茨,全力以赴。
我在焦急地联系丽子。丽子上高中,李华给她买过一部手机。然而,嘟嘟两声。“关机。”我说,与给陈寒打电话一样,可是,丽子这还是头一遭。
我瞬间想到人际关系的万能大师陈寒,陈寒是找人的天才,要不要找他帮忙,可陈寒一下船,就离开福拉莫斯失踪了。我干着急,这让我蓦然陷入寻找亲人的地步。这让我好好想了想,莫非我又败回原点了?
“你怎么不看好她,万一她学样呢?”
我的口气显示我生气了。
李华在继续修脚。
我喊,“李华!”
我挺不耐烦,拒绝李华修脚。
“呵,你女儿你哪里管过,她连自己都管不好还管大人的事,对,她是你家人,我算服了……”
李华扔掉修剪钳。
到这,我也不想再多话。
李华去上班了。我一直在等丽子,我联系过丽子常来往的同学,找过班主任,才发现,丽子没上学。就像某一天夜里我突然在这座城市不辞而别了?我想大骂作为母亲的李华,在家里,我满脑子开始是丽子没向我讲完的状况,仿佛有个黑影让我看到了,他坐在马桶上,他靛蓝色的裤筒在衣柜出现过,都是似曾相识。李华还没下班,我疯狂地找,阳台上、雨棚上、厕所。然而我失败了,我知道他存在,或许一样爱吸烟,习惯坐在阳台上,朝城市更远的方向眺望。
我把失败归咎于李华。李华坐在床上看电影,我做我该干的事,她没有拒绝,摸手机,手指有节奏地撸暹罗猫的尾巴,吧啦、吧啦、吧啦啦。也没有生气。卧室只有“喵”、“喵”起伏和我的蠕动、撞击声。
我知道丽子是个好女孩,肯定没事。
公安一大早帮助我们找到了丽子,丽子用自己刚办的身份证,住宿在我家街道附近的小旅馆里(她哪来的这么多钱,这让我再次怀疑李华),她闭门不出。丽子回到家,我又喝了酒。反正李华不管。趁着酒性,躺在床上,灯没关,我想和李华好好谈谈,对于我们的事,早在诞下丽子的时候,我就有所察觉。
我神秘的模样映在镜子里。
李华说,“你想说什么。”
“我想来支烟。”我去阳台。
说什么好呢?那只猫让我打消了念头。
我去阳台上浇花,然后给洪易、王梵一一打电话。洪易刚接电话,看也没看就说,“他妈的谁打电话?”,“洪易,我马上重操旧业了,”我话还没说完,洪易就挂了,也不听是我。我说,唉,估计他公务员的火爆毛病又犯了。
王梵则说他在宾馆里,和一个女人在幽静的走廊上,他在反复地重复,没盼头了没盼头了,鞋坊能起来吗?鞋坊还能起来吗?王梵自问自答,当我是他旁边那个陪他过夜的人,听得让人烦,我又试着拨陈寒,还是没通。我把手机放回兜里时,我本想迁怒于李华,可是,我们再次做爱,然后,她起床做早餐、洗碗、买菜,仿佛她是一块任我摆弄的抹布。
李华没有拒绝让我产生了冒险的冲动。我知道作为情人,李华圆滑如珍珠,她内心脱离于我,然而,我又不太怪她,这是一种奇怪的不知羞耻的想法,我又不适合再找情人,我厌恶和其他女人上床,我选择了另一种极端的出路,回到海岸线蜷曲的小港上,去寻找另一种彼岸。
海风是无情的,绝望的海岸线更是狰狞、绵长,延续千里之外,不适合诗人表述。海带来的一场火灾,每天都恰到好处,无边无际的海上,每天仍旧只有丽子的报告电话。这一阵我脑子里只有李华。
这次对于我的提前离家远行,我临走前,李华嘴角出现一抹难得的愧疚,她包下所有家务,停下来后和我商量,说我可以上洗浴城工作了,有家投资商找她,至少,我可以给她打工。我摸了摸刚理好的后脑勺整齐的新发,然后说,李华,请你相信我。李华笑了,揶揄地笑,相信你?相信你混什么福拉莫斯?
“猪朋狗友!”
“无耻下流!”
“狼狈为奸!”
李华怒了。这里,关于我和陈寒的“福拉莫斯”,暂且需要澄清一下,首先从称谓上,是这样的,除了当初在车站提议秉持真理的陈寒外,我们叫“陈真”,其余包括我都叫“A先生”、“B先生”……“福拉莫斯”里流行暗语,人性、仁爱是唯一标准,而不是军事化管理,逢人都是“您好”、“请问”、“贵兄”,上厕所也是“出恭”,我们从来不把排泄物倾进海里,对于我们来说,海是高尚的、纯白的、比所谓的有机蔬菜、有机瓜果等更干净、纯净……甚至还要说一件事,在上次上岸,到烧烤店喝酒的时候,我们还协商,船上准备招聘一位小姐,我们尊称,给她的暗语是“C小姐”,她应该是一位志愿者,行为高尚,允许出生低微,我们要在艰苦、乏味,然而人情味浓重的船上,建立一个理想的性别协调;
洪易说,可以找李华。
陈真也就是陈寒说,李华做菜蛮好。
我却说NO。她晕船,我说。
我仍在寻找那个影子。那个像表演帝,像乙醚遇到酒精,现在,我要把它的分子、原子一点点提拎出来。
这个季节,有一点风,裹着裤腿,让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精瘦得像根筷子。那些天,像以前青年时期无所事事的游荡一样,我找不着任何人,包括洪易、王梵、陈寒,每天在小吃店点一碗三江源牛肉面,而不是每顿必有的鱼、虾。我选择在一家临时旅馆落宿。后来女儿丽子告诉我说,她呆在小旅馆里人肉那个影子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领导姓名。包括影子送给李华的那块蓝绸布。她一定能找到。但是公安先找到她了,并且告诉她人肉搜索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丽子说,警察叔叔有时也是不对的,只会糊糨糊——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留在了我所住的街道,算是故事发展,出海的前奏吧。我告诫过丽子,丽子也保证过,她担当着维持我们关系的职责。她很听话,她怎么会挨打呢?
所以,这次也可以这么说,出门前,允许我违心,我对李华以及丽子都说了谎。我没有立即出海,我在我家所在的街道上,学丽子藏在小旅馆里。不是我不相信丽子,而是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出马。
可是我没找到想要找的人。
最后一天清晨,正当我准备离开街道,又不太想返回小港码头的时候,意外碰到陈寒。那时,陈寒戴着鸭舌帽,像一只伪装过的野象,从热带雨林出来,周边的人群只不过是丛林。在我所住的街道见到陈寒,我几乎叫了起来。
“你个鬼样,消失哪里去了。”
“还用说,回家看女人孩子呗。”
“骗得了其他先生,骗不了我。”
“上岸了?还改不了海上的生活啊。”
我们就这样说着,到了我家对面的一个废弃的车库。我望着我们家的阳台,上面有李华刚晾晒的我的衣服。
“我说,在大马岛,也不吭一声?”
“吭一声与不吭一声,有什么差别呢?”
陈寒一句话就卡住了我。
我说,“来,吸支烟吧,别想了。”
“是啊,想也是舔人屁股。”
接下,陈寒执意邀请我和他同住希尔顿酒店,他执意请我。
对于我这样胆小的人,我受宠若惊,我搞不懂陈寒请我的缘由。在废旧车库上,因陈寒的到来,我给洪易、王梵打电话说碰头,只是他俩都拒绝了,说我太闹心,家庭生活是不是无聊之极……这时,我看见了对面的李华,她在阳台上发呆地喝水。陈寒也看见了她,他说,你在车库上站这么久,只为看李华啊。“多亏你,去年帮忙买了把锁。”我低下头去,陈寒伏下身去大笑着说,“我们四个,可怜虫。”
我若有所思,这时问,“时间多久了?”
陈寒看表,故作姿态的大声朗读:“世界公历,10月3日7点零3分!”
车库上,我继续打电话,还是给洪易,打电话时我有个怪癖,就是有洪易和王梵的时候,通常打给洪易。我说,“洪易,我可能早点上福拉莫斯。”洪易很火爆,数落我,说他上公交车了,去市里办保险不能回来,你们急着是去赶死吗?你们急着是去赶死吗?
酒店就这么住下来了,陈寒买单。
从后来开始算起,和陈寒在岸上是最后一次碰面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天是陈寒跟他老婆的离婚日。早在之前的半年多,陈寒像蜗牛壳一样神秘。酒店里,陈寒始终都没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想说的时候,打死也不说,他最爱说以前的铁血事件。
我从侧面观察陈寒的脸庞。以前我多次观察过,比起我的柔弱,他脸孔粗放,他是西南边陲汉子,有青铜的轮廓,颌下还留一小撮平整的扫帚一样的胡子。早年的时候,他没少在浙赣线奔波,后来开地下博彩,给市办公室主任送过情,舔小官员的屁股,舔出了油,蒸出了花,再继续舔更大的屁股,他每天幻想和官员们就当是情人一样眉来眼去。
这就是陈寒的过去。然而这些是岸上的事,谁没有一身骚呢。人,一旦出了海,过去就是鱼离开了水,一整个人,完全蜕变,清洗干净。
当然谁都有烦心的时候。何况在这岸上。海上的陈寒也不只是宋江大哥啊,我们买下的这艘一千吋的船,他出力最多,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说,“我正烦着呢。”
陈寒就笑,“别说了,还有比我更烦的?”
这时,我认真地说的,“我女儿要叫别人爸爸了。”
陈寒很不相信。
“你女儿要叫别人爸爸?”
“是的。”
“这世上真没天理了。”
“……”
“那李华呢。”
“你今天看见她出来了?”
“你不是让我看了吗。”
“我在想她。”
“嗨,想哪?”
“陈寒,要不再上那个废旧车库去看看?”
“你说呢?”
“……”
作者简介:
叶临之,1984年出生,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