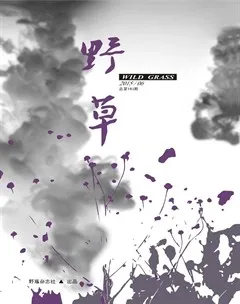风的事情
十三年前,搬到小城嘉善。
头一夜,我躺在尚未装修的房子里。廉价席梦思一翻身便嘎吱作响,来不及拆开的行李堆在床脚。江南的夏夜即便黑到最深处,底子也是透明的。箱子们在稀薄惨淡的天光里,制造出大块大块的暗影,层层堆叠在一道。我担心这间空房子容纳不下这么多东西迟迟不能睡去,而身边人早已经发出轻轻的鼾声。正是在失眠的当口,我第一次留意到嘉善的风。
一阵一阵,像很远处有人吹响了嘶哑的哨子。体量巨大的风,拖着尾巴,尾梢打着小旋,呼呼刮起来,越来越近,就在要撞到窗户的一刻,倏地抽身而退。接着重来,一遍又一遍。正是八月,明明是盛夏,距离上一个太平洋台风造访的日子也有好几天了,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是西北风正在酝酿一场暴动。这不免让多愁善感的人对此地对前景生出几分茫然,我迁居嘉善的第一晚便在惴惴不安中度过。
磕磕碰碰住下几年,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所谓的杭嘉湖平原,在嘉善这一带才算名副其实。这里一马平川,四围没有一座山丘土包,楼群和人口密度也不高,只要有风,即毫无抵挡无遮无拦,肆意刮成任何形状。不过究竟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也是瞎猜的。嘉善四季的风声始终存在着,顶多有些量级变化,夏天的东风和冬天的北风,从声音的角度讲,穿过耳廓的一刻感受不出有季节与温度的分别。
然而。
关于风的事情,只有外人才意识得到。几乎在每个被大风洗劫过后的早晨,当地人总是那么平静,不仅是习以为常,仿佛他们充耳不闻。当我拾掇完毕出门上班,小区的老人一个衔着一个,鱼贯而出。他们的衣袖和裤管里含着风,或者风支撑起了他们的轮廓。在他们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夜晚的风声鹤唳。这时常让我一个外地人怀疑,这份自给自足的安乐从何而来。
有个吃素的朋友,每到陌生城市总爱去当地的菜场转几圈,还老是说,感受一下市场里花花绿绿的蔬菜果子,闻一闻讨价还价的烟火气,就像穿越回清明上河图,那才是清晨最美好的开始。菜场?难道不该是污水横流馊味弥漫?买菜?超市不是更加明码标价干净便捷?至于扯到清明上河图么,是不是还要拍成套滤镜的美图配上康熙字体?对这种文艺兮兮的偏好,我时常嗤之以鼻。
母亲经常从杭州来嘉善小住。每每周日起得晚,她就说要去菜场看看有没有落市菜,还问我要不要一起下楼走走。相比超市,母亲一直更喜欢到菜场去买菜,勤俭持家惯了的主妇,尤其喜爱逛菜场、路边摊。一路上,母亲告诉我,她喜欢逛嘉善的菜场,不光是小菜比杭州要便宜,人情味更足,她去得多了,还有了几位相熟的摊主,总会给她留着实惠好货,从不缺斤少两,反而主动抹零,有时候还要多送把香葱呢。仿佛就是为了验证这番话,我们刚跨进菜场,门边摊位上一个四十出头的妇人便“大姐,大姐”地叫住了母亲。对我来说,在嘉善这些年,确实还不太习惯这镇东打一枪镇西就要吓到人的微小格局。尤其是当人们走在老街的樟树浓荫下,一路都会碰到跟他们打招呼的人,不是一道逃过学的小伙伴,就是隔壁太婆的远房亲戚,不是小叔小哥地笑脸相迎,就是叫声伯叫声婶随便怎么叫都没有错。那些和善的脸,好像逢年过节般热闹甜美。叫我时常怀疑,并在心里默默画三个字,至于么。
母亲也停下来与她招呼,更令我吃惊的是,一年也就在嘉善住一回的母亲,居然能叫出妇人的名字。妇人在卖藕,长相拙朴,身前摆着几大盆洗得干干净净,嫩得好似小孩手臂的莲藕。她问母亲有没有忘记她家地址,怎么不来家里坐坐,一个个问题迫不及待丢过来,简直像久别重逢,又是他乡遇故知,在乡音以外还努力添加着普通话的语调。说着说着随手从盆里捡出几段藕,甩甩干,拿袖管擦擦,一定要塞给对方。在我外人看来,这热情凭空升起,仿佛小小一朵白云,温柔悬垂着,如果硬要说给人某种圣洁的想像,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修辞过度。自从搬来这里,就经常遇见这种几乎可以修正我三观的情景。这热切地想要表达,想要把好东西无条件跟人分享的心思,可以是奶可以是蜜,还有那架势,既令人意外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吧。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像个置身事外的人,讪讪站在旁边,看二位你拉我扯,大声推让,客气得好像在闹架。结果,莲藕还是装进了我们的袋子,直到我们转身离去,妇人还在说,大姐常来啊,我家里地址记得喔?一定要来坐坐……
离开摊位,母亲就不再笑了。她说,常去这家买菜,知道那妇人先是被远房亲戚半哄半骗从苏北拐来,后来丈夫重病瘫痪,全靠她一人支撑全家老小,以前送过她几件旧衣服,当时还怕她嫌弃,没想到,一直记牢的,每次走过她摊位,一定要给我几段藕,还要请我去家里做客,实在是不好意思,下次来从另外的门进去好了。我心里被旁人的不幸身世牵扯着,而那些已经不算微弱的不幸并没有充分地在那妇人全身上下体现出来。我呵呵干笑着,碰到难过的东西,有时候笑一下比添加同情的举动更合适。可又以为笑得不妥,被由先前的偏见所裹挟而来的难为情包围起来,充溢着鼻腔的菜场气味,也被另一种超越其上的陌生而温暖的情意替代了,渐渐开始理解爱逛菜场的那位朋友的心。诚然,超级市场整齐明亮干净有序,但这舶来的物事,终究不是小城原初的宗教。线条笔直的钢制货架,取代不了弯弯曲曲的藤条菜筐,流水作业的收银机,取代不了讨价还价的世态人情。菜市场、小集市不光只有脏乱差,它们背后有一声声鲜活的心跳,偶尔会被掐断,却总是能在最后时刻自动复苏。孩童时代的我们都随母亲去过菜市场,只要挖掘一下记忆,我们能轻松地回想出集市的气味:那儿有鸡飞狗跳,有三教九流,有历史,有群,有自在,那儿有历经沧桑千疮百孔却依然是滴溜圆润的一粒良心,经年累月摆在秤砣上,那儿是琐屑,有丑恶,是哲学,那儿也有真实,是吞吐了风暴之后积蕴起来的处世态度。
这么多年住在嘉善,渐渐和当地人一样,不以风只以温度来感受四季,慢慢对经年的风声习以为常。眼见着街道越来越宽却越来越堵,蓬勃的住宅区生机盎然拔地而起,而且个个有着响亮拗口的名字。不知从哪个莫名其妙的时刻起,风的痕迹偶尔会失踪不见。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温暖的深夜里,侧耳聆听,虫子持续的鸣叫,以一条平行线的形式悬挂在地表之上,谁家犬只要是忽然狂吠,那条声线就垂直地向半空升起,这些时刻,风都不在。导致后来几年,住在小城里,却并没有住在此地的感觉,好像存在于这里,又好像存在于任何一个和此处相似的所在。唯有一处地方,微妙地还暂时没有被城市化的手臂拉扯到,或许能够在那儿找到些什么。
沿着小城古老的中山路往西走,过了绿草如茵的新小区,过了闹哄哄的学堂,没走几步,会遇见一座拱桥。弧度高,长度随之便短,用高大全的眼光去看,它很不合时宜。那些年,桥边总是堆着一滩黄沙,随着节气的变化,颜色深了又浅,每天都有人拖来车铲上几勺,它却像会变戏法一样,从不曾少下去过。他们告诉我,这个地方叫黄沙滩。为什么叫这个名儿,谁也说不清。不知道是先有黄沙还是先有地名,不过肯定没有哪处的黄沙能像这儿一样,大大咧咧地躺在路边,洋洋洒洒地恣意飘扬,骄傲地存在着。过了黄沙滩,再走一小段路,西门就到了。
顾名思义,西门,是小城的西城门。过了西门,后面就是通向远方的铁路了——请暂时允许我把目光放在这一狭隘并过时的城乡分界线上。走进西门这一段不足百米的老街,熙攘活泼的一个小世界,毛茸茸地跃动出来。烧饼油条店、凉粉店、玻璃店、杀鸡店、金店、鞋铺、肉铺,平板三轮、贩夫走卒,传统的生活形态藏在这里,缩略的清明上河图凭空复活了。有一阵,几乎每日要路过西门老街,停车很难,推着三轮车在路边卖菜的大嫂却主动给我让路,还一脸歉意摆摆手,仿佛理所当然是她的错,难道路边都应该是汽车的占领区么?如此却叫我羞得满面通红。那家曾经不知路过多少次但从没有进去过的小吃店,应该叫茶馆更合适吧?总是黑洞洞的不怎么亮堂,因为长条凳上时刻坐满了密密麻麻的老人,他们闹嚷嚷地在同一频段上发出声音,沉沉地显得昏暗,也算是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吧,不管外面天旋地转,我自在此岿然不动。那边走过来的大爷,他是在走吗?如此缓慢和僵硬,每一步都定格在似动非动的瞬间,恨不得要人在他身上找出某个快进开关——可你看他脸上,眉毛松松,眼目舒展,笑意含蓄,微微昂起头,风千方百计灌进稀疏的发丝,灰白色头皮在底下若即若离,他分明有股不管怎样皆要享受每时每刻的好心态。可西门的小狗们再是闲庭信步,都永远忙碌碌地走得比人快,那些叼着一根骨头或一段树枝匆匆赶路的劳碌命,从来都不是没有,你要是说这些无聊吧,我就觉得你无趣了。生活,他人的生活,即便是一条狗的生活,都够不着外人来指手划脚呢。
比如他们说西门尽头的那幢四层楼里住着一个女人,他们说那是一个关起门来经常挨丈夫打的女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每次说起那个女人,总是欲言又止。他们总是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欲言又止。有的人会摇摇头,有的人索性沉沉叹息。他们跟圣人似的,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什么事情都知道又装作什么事情都没说起过。我见过那个女人,有一次我见到她穿着运动鞋沿街跑步。随着步伐的起落,两颊的肉微微甩动着。她把辫子扎得很高,下巴抬得也很高,宽阔的额头上,汗珠在暮色里亮晶晶。她的神态,跟所有跑步的人毫无二致,诚恳而认真,头顶冒着热气,仿佛跑步就是她向昨天背转身去,面对明天抬起头的某种最好的方式。即使他们说的是真的,我依然看不出她有什么地方需要同情的。
比如他们还说那幢四层楼的顶楼上住着一个男人,他们说那是一个养鸽子的男人。他们说那不光是一个养鸽子的男人,那是一个娶了鸽子的单身男人。他们说那个男人每天吃过晚饭,就会爬上楼顶。他在楼顶插上一面红旗,等待风把红旗吹起来,他会盘腿坐下,指挥一群信鸽像乌鸦一样,一遍遍飞过头顶。我见过那个男人,有一次我在遛狗时遇见他。养鸽子的男人蹲下来,像抚摸信鸽一样抚摸长得和乌鸦一样黑的狗。狗原是一条以凶猛著称的狗,狗没有躲闪也没有扑咬,狗甚至迎着手掌自喉咙深处发出咕噜咕噜的呜咽。我不知道养鸽子的男人是怎么做到的,即使他们说的是真的,我更加觉得他是一个无比神奇的人。
如果在西门住一辈子,大概每天晨起都会遇见各色各样的人,那些人在前一天夜里正住在大风里,正活在我们和他们的嘴边。半大的孩子提着早点跨上自行车,歪歪扭扭骑向严苛的学校,他们的父母礼貌地互相道别,把纠缠不清的烦恼关在家门内。微笑的农妇,挽着一篮湿漉漉还透着新鲜魂灵儿的蔬菜,阿婆们颤巍巍走过,随手挑拣一番,随口问个价钱,不管买不买,有来有往的和气随时奉送。你不知道也没法知道每个人昨夜前夜乃至前半生的真实境遇,你只要能看得到此时此刻,这实在算是种古意乃至诗意盎然的存在了。而在西门的每个黄昏,人尽皆知的傻子阿强穿戴整洁,永远怀抱塑料小板凳,像孩子恋着心爱的玩具,在那个固定的路口,雷打不动地凝望着旷远天空,表情安详。在他周围,人力车、电瓶车和农用车川流不息,彼此间仅仅差距几毫米而最终相安无事,一切都乱糟糟的,一切却都秩序井然,远方暮霭沉沉,在风的反面,一场大雨正在酝酿。像某种亘古以来的仪式,像有某种宗教的力量,这些细小的事物在此一瞬具备了恢宏的神性存在。
又一年冬天,风一如往常呼啸肆虐。
母亲待在嘉善,晚上抱着暖水袋看电视,看着看着跟她女婿说,小黄,你听这风,怎么会那么响。那一夜的北风出人意料,竟变做尖利的哨音,还撞得窗棂发出了摩擦声,咔嚓咔嚓,听得冬夜更加凄凉。女婿应声而来,凝神驻足片刻后,伸手把窗户轻轻推上。咔嗒一声,随着这一细小的动作,没关严实的窗缝被彻底封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呜咽着哭泣的风,立刻在耳边消失了。隔着一片玻璃,室内的暖意又可以从四面八方发散开来。这可能不过是一种生活中的空气力学问题,但我此时要写文学性是不爱细究科学性的。
隔不多久,我们重又听见风。风在很远处,像是有人吹响了嘶哑的哨子。
而这一切,再也扑不到我家的窗户,于是好像瞬间变做了我们屋外广袤平原上的其他事物,司空见惯的身外之物。第二天醒来,不光是我们脸上,只要我们想,大概我们心里都可以不留下风声鹤唳的痕迹了。
里尔克说,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高中时,我把这句诗抄在课本扉页上,以为这里有御风而行与广阔天地共沉沦的少年意气。其实何必呢,风,本来就是天上的事情,本来就是外面的事情,认出风暴不过是启蒙主义的功课,最终有什么好激动的,又何必激动得跟大海一样,激动得跟过去一样便已足够。因为我听说,我也可能在胡诌,真正的大海制造风暴,吞噬风暴,气息吐纳之间,依然沉静如鉴,圆融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