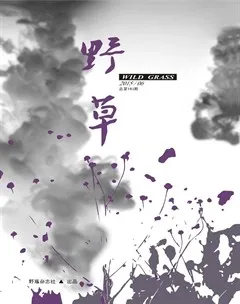我们的宇宙和自我
谈论江离的诗歌对我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虽然我们同是野外诗社的成员,但从一开始我们的诗歌写作就不在一条道路上行进,坦率而言,我的诗歌在某些地方尚能与胡人和飞廉的诗歌找到相通之处,但江离的诗歌或许与古荡的诗歌更加相近。诗歌经验的不同,是造成我谈论江离诗歌的困难之一,但经验的背后,我们之间知识结构的不同是我谈论他的作品的更大困难。
虽然我和江离有彻夜谈论诗歌的美好经历,但很明显,和他的深入对话让我感到吃力,我明显感觉,他的冷静、理性和推理能力走在了我的前面,他对知识的掌握和分析已经到达十分深刻的地步,这种深刻使他从来不会草率地对一件看起来是非明显的事情展开评论,由此我也发现江离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即:他从未对所谓重大的社会事件发表诗歌上的观察和观点。这在当下诗人中间是不多见的,尤其在我们这代尚属年轻的诗人中间十分少见。从功利论的角度来说,是江离对自己诗歌的自信和信念让他放弃了这种投机。但这样的事实并不说明,江离对我们这样的时代没有意见,相反,我以为他意见甚多。所不同的是,江离放弃了对一事一议的兴趣,也放弃了斩钉截铁的道德判断,他希望站在一个更加高远的地方,一个能够脱离感性影响我们的判断的地方,对这样一个时代和人群(包括他自己)做整体性的观察,得出一个超越个人经验的结论;又或者,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通过自我辩论或自白的方式,将经验逐渐抽象,上升为一种理智的思考,从而将自己的经验置于一个巨大的普遍性中。
因此,我和江离的诗歌写作之两种道路或许可以表述为:我是经验主义者,江离是理性主义者。从这样一个角度,江离的诗歌适合纳入哲学范畴考察。所以,谈论江离诗歌的一个基础,我认为就是要具备比较充分的哲学常识,这对于不事学术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然而,诗人的敏感既然已经让我对江离的诗歌有了这样的印象,所以,即使力不能及,我也愿意翻箱倒柜,穷尽所有谈一谈他的诗歌。至少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我还没有见到有谁就江离诗歌的这一特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所以,我愿意勉强一试。我以手边江离的诗集《忍冬花的黄昏》中几首诗歌试读。
江离的诗歌出现在诗界时,便展现出很高的成熟度,仿佛省去了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并且,他的诗歌始终都有一个稳固而坚定的内核——智性的内核。
《贝壳》是一首早期的诗歌,我认为它可以视为精神层面的某种象征。
我将它放回水中
清洗
给它沙
整个夜晚,我们
相互厮守
告诉它我的一生
拥有的秘密
我的贝壳,这样
在一个恰当的时刻
它会让我进入它的灵魂
大片大片的海浪和延伸到远处的海岸线
一个人走在沙滩上,并将它捡起
“放回水中”、“给它沙”,都是继续维护贝壳生存环境的举动,而“清洗”是将让贝壳浮现它本来的真实面目的动作。前三句诗都属于让贝壳逐渐呈现的行为。“整个夜晚,我们/相互厮守/告诉它我的一生/拥有的秘密”,这是“我”单方面尝试与贝壳对话的努力。“整个夜晚”,以强调的姿态指出了时间长度,同时“夜晚”的属性加深了“厮守”一词所传达出来的亲密感,这使“贝壳”具有了拟人化的异性色彩。“秘密”是不可告人的,“告诉它”表明“我”信任它,更暗示了“我”与“贝壳”交换秘密的需要。我认为这四行诗都是在写“我”向“贝壳”主动靠近的过程。“我的贝壳”是一次称呼,它可以让叙述对象暂时由“它”转换为“你”,这也是一次语调的停顿和转换。“这样”一词让“我”前面所做的一切,成为接下来两行诗的条件——“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它会让我进入它的灵魂”。“我”进入贝壳的灵魂,超越“相互厮守”构成的亲密关系,让“我”与贝壳的关系成为相互对话的关系。“大片大片的海浪”和“延伸到远处的海岸线”是对贝壳之灵魂的描述。实际上这一描述只呈现了一种空间特征,它包含了一个近景和一个远景:前者是巨大的重复的意象,后者则是遥远弯曲的无边的意象。从这个姿势来看,描述贝壳灵魂的这一空间特征具有庞大而恒久的终极色彩,那么,“我”与贝壳的对话,就是“我”与某种终极意境的对话。
江离有着对终极概念的兴趣,这样的兴趣在他早期的诗作《老妇人的钟表》中也有体现。这也是江离广为人知的一首诗,在这首诗的诗题里,“老妇人”和“钟表”皆具有时间的属性,钟表是绝对的客观时间,而老妇人则是相对的主观时间。所以,我以为,在这首诗歌里,他既谈论人世这个生命有限的主观世界,更谈论了这个主观世界在无边的终极世界面前一种不可捉摸的虚无感。
有时我们从深夜回来
看到她屋里的灯火
她怎样将钟表调快或调慢
像穿越一次次漫长的谈论
她需要理解,一个听众,使她的生命降落
或者一扇窗
来收集孤独的标本
在我们的心脏有一个精密的仪器
一个陀螺旋转
轴心倾斜、不可接近,时间的
玻璃器皿,靠近它的星辰、光线
你说出的每个词语都经过了小小的弯曲
“深夜”是一个最佳观察时机,“有时”一词说明这样的观察不是一次单一的偶然事件,而是具有持续性、固定程序的事件。“灯火”而非“灯光”调暗了并缩小了观察对象的空间,使“老妇人”的孤独形象进一步浮现出来。“将钟表调快或调慢”便是老妇人固定程序的一件事情,它使老妇人具备了某种持久不变的恒常形象,像一幅静止的画面。这无疑是悲哀的。把钟表的调校比喻为“穿越一次次漫长的谈论”,既形容了调整动作的缓慢姿势,更打开这个恒常意象的内部,把钟表的客观时间转换为老妇人的主观时间。“她需要理解”是“我”对老妇人的一种主观理解。“一个听众,使她的生命降落/或者一扇窗/来收集孤独的标本”,这是对有限生命的悲哀陈述,是人世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将这一陈述简单处理,把它降落在具体的某个形象身上,比如“母亲”的角色,那么我们对老妇人的悲哀就变得更好理解。但江离避免了这么做,因而,也使得“老妇人”这一处境具有了普遍性,由个人变成了人群,升华了我们的悲哀。
孤独让人变得轻盈,“生命降落”未必指生命由高处向低处滑落,我以为是指孤独的敞开,向人群、大地概念的回归。而“听众”所具有的倾听、对话性质,说明这样的回归是双向互动的结果。“收集孤独的标本”是处理孤独的另一种方式,而以一扇窗来收集,申明了一种开放的姿势,但与前一处理方式不同的是,孤独制成标本,表明孤独只供陈述,而不是对话的对象,这是孤独的赋形,并且具有精致、缓慢、不被时间侵蚀的意味。
“在我们的心脏有一个精密的仪器/一个陀螺旋转”,这是对孤独感知的工具和方式。如果我们超越自我,把人视为客体,那么心脏作为“一个精密的仪器”的容器就比较容易理解,并且心脏具有永动的色彩,就如同诗人在《贝壳》里写到的“大片大片的海浪”一样,是我们身上最接近第一推动力的地方。“陀螺旋转”是我们处理孤独的方式,也可以视为心脏持久跳动的转换,它的出现使心脏里的这台“精密的仪器”忽然成为宇宙中的一颗星球,是“旋转”的、“轴心倾斜”的,以及“不可接近”的,就如同“我们深夜回来”时看到的黑暗中的灯火一样,它和老妇人的孤独已经建立了同构的关系。
接下来的两行诗,我认为是对孤独本身的描绘,诗人以浩渺而黑暗的宇宙中的星球和光线,比喻了灵魂的孤独,把孤独形容为幽暗、透明、精巧而永恒的事物。“时间的/玻璃器皿”是孤独的借喻,由于和密度与空气不同,透过它的光线必然“经过了小小的弯曲”。但在这里,“星辰”和“光线”编织了一个宇宙中的图景,使“时间的/玻璃器皿”成为独自漂浮之物,既指出了孤独的时间性,更形容了孤独在灵魂中的形态。而“你说出的每个词语”则有别于“星辰”和“光线”,自成独立的一组,与后两者形成并列关系,提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相似性,即:词语,这个被孤独激发出来的事物也像光线一样,当它再次经过孤独本身时,将遭遇必然的变形。这也说明,我们试图描绘的世界,在真实世界面前仍然具有虚构的性质。
对孤独的观察或叙述,有时成为主体的自我确认方式。《1662年的雪》同样是一首十分优美的诗歌,作者仍然谈论了孤独,并在孤独中加倍谈论了“我”——
1662年的雪落了下来
这是冬天,在我拥有的小小孤寂里
有一盆火在跳跃
从我的窗口看到的夜晚
单一而简朴
并且每一个都会是双倍的
多么熟悉啊,帕斯卡尔
我就是那个死去已久而今天
抖落了轻雪来造访我的人
1662年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逝世的时间,他就是一个创造了“精密的仪器”的人,是科学家,也是追寻上帝的人。在短暂一生的后期,帕斯卡尔隐居于修道院,撰写了著名的《思想录》。在这首诗歌里,作者设计了“我”与帕斯卡尔,以及我与自己的对话。帕斯卡尔死于当年8月,但诗人追忆的却是冬天——“1662年的雪落了下来”。这是有意的设计,将“我”的沉思和追忆与外部世界屏蔽,使“我”的思想幽居于自我的狭小空间里——“我拥有的小小孤寂”。在孤寂的状态里,“一盆火在跳跃”,其意象是温暖而突出的色调,增加了诗的丰富性,同时也可以象征在孤寂而冷静的精神状态里的某种激情。“从我的窗口看到的夜晚”,这是设计了空间场景之后,再次设计了时间的场景,夜晚和雪的时空组合,共同消失了外部世界纷繁复杂的细节,因而“从我的窗口看到的夜晚”是“单一而简朴”的。如此,更大的普遍性主题通过简化的过程被显露并强调出来。“每一个都会是双倍的”这一句令人费解,但回溯“单一而简朴”这句诗,它实际上已是双重属性的一种转换描述,“单一”是客观的,而“简朴”却具有主观色彩,因此我大胆假设“每一个都会是双倍的”指的其实是“从我的窗口看到的夜晚”中的一切都具有双重属性:它们既是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面貌,同时更包含了它们如此呈现的自然规律和推动力,也即数学和物理学背后的一切真理。这也是帕斯卡尔这样的哲学家所必然思考的。
“多么熟悉啊,帕斯卡尔”,这一句唤起了朋友般亲密的对话场面,其中所谓的“熟悉”可以视为之前描述的总结,认为窗外夜晚里的一切皆是帕斯卡尔曾经透彻研究的对象,是被他掌握了秘密的一切;但这一行诗同样也可以视为启下之句,让接下来的诗句与帕斯卡尔发生关联。
最后两行诗颇具神秘主义色彩,“我就是那个死去已久而今天/抖落了轻雪来造访我的人”。这里的“我”被一分为二,同时被设计为死而复生,创造了自我对话的可能。在这两句诗里,被造访的“我”实际上诗歌里未曾描述的“我”,他与“1662年的雪”无关,也与帕斯卡尔无关;而前来造访的“我”,则是处于前述“我拥有的小小孤寂里”的“我”,这一个“我”,也即是“死去已久而今天抖落了轻雪”的“我”。两个“我”来自于不同的“时间”而相逢于同一个诗歌未曾提及的场合,那么,这个被造访的“我”即1662年以外的人,也是一个需要“被造访”的人,一个“在这个贫乏的时代”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造访”的“我”,乃是这个时代需要被精神救治的人,是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我”。
自我对话,从来都是重要的沉思方式,反求诸己,也是靠近真理的主要途径。如果“轻雪”被视为纷乱的遮蔽之物,那么“抖落轻雪”则相当于《贝壳》里的“清洗”动作,是浮现主体的行动。“我”对“我”的造访,也是一次映照自我的行为,从被造访的视角来看,“我”通过对“我”的观照,才发现了“我”曾经“死去已久”的事实,以及曾经浑身“轻雪”的状态,我认为,这就是失去自我,以及自我被蒙蔽的状态。所以,这样一次造访,就是借助帕斯卡尔的沉思方式,对自我精神上的一次刮垢磨光,是自我的确认,也是对真理的靠近。
借助沉思,我们更加靠近了真理。但沉思的另一种结果,也是使我们处于一种相对论或怀疑论中,在曾经令我们感到确切的概念之间,找到了新的联系方式。我以为《几何学》就是这样一首诗歌。
风雪过后,我把房屋搬到山顶
每天晚上漫步,在这些蓝色和白色的
星球中间,它们缓慢地移动
像驼队在沙漠,像一个树林里
我们从来没有访问过的古老种类
衰老的橘红色,一个我们不再熟悉的邻人
离开了这里,我感到担心,这也是多余的
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忠实地记录下
这些诞生、死亡
和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似乎存在着一种结构:它们中的每一个
都在另一个之中,孤单
必然成为更大的友谊的一部分
为了永恒,就必须把时间再次分割
在我的房间内,混乱的桌椅
恰好构成对清晰的另一种表达
《几何学》的诗歌命名让我想起了康定斯基的绘画作品,那些处于不断流变、变幻中的点、线条和色块,是构建纷乱中的规律的作品。但我认为,江离的这首《几何学》呈现了相反的意图,是试图在秩序里寻找与混乱的联系、让“混乱”得以安放、最具有辩论色彩的一首诗。
“风雪过后”,是一个宁静与简洁的时空,“我把房屋搬到山顶”,建立了高远的观察视角。“每天晚上漫步”,是一种规律可靠、不断重复的个人行为,犹如康德准点散步的习惯,“漫步”因而具备了工作性质。“在这些蓝色和白色的/星球中间”,我以为可以认为是雪后群山的比喻,也可以认为是类地球行星的指称。“驼队在沙漠”是对“缓慢地移动”的星球的形容。“驼队”是复数,说明类似的星球不止一个,但相对于广漠的宇宙——沙漠,依然是孤独而荒凉的景象,这是一个宇宙视角,类地球行星作为被观看的客体,被揭示出了它们在宇宙中各自孤悬的处境。
接下来的比喻使观看的镜头由远至近,“我”进入了被观看对象的世界——“像一个树林里/我们从来没有访问过的古老种类”——整体转换为局部,进入了一个内部的生态世界。这两行诗仍是对“缓慢地移动”的星球的描述,但它着眼于“缓慢地移动”所营造的自我环境,它们共同组成了“树林”这样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无疑是在缓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古老种类”充满了时间感,它是“树林”这个生态系统的成员,描述了“蓝色和白色的星球”之于宇宙的关系。相较于“驼队在沙漠”,这个比喻的角度实际上更高一层,并且态度相反,在更广大的时空范围证明了宇宙的生机。“从来没有访问过”预设了一个“已经知晓”的前提,同时隐含了对话的渴求。“衰老的橘红色”是恒星死亡前的表征,是恒星的比喻和死亡的象征,接下来的“邻人”依然是个比喻,但它更着力于揭示我们和宇宙之间存在的联系,通过它,宇宙被描述为一个村落,也因此,从这一句开始,诗歌中的观察视角继续转换,从沙漠、树林,再到村落,宇宙的喻体不断缩小,但宇宙本体的幅度却在不断扩张,在概念与人、人群之间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离开这里”,指的是离开山顶,山顶是诗歌的观察视角从大地升向宇宙的起始之地,所以“离开这里”也是离开宇宙被比喻的沙漠、树林和村落,放弃对驼队、古老种类和邻人之间的关切——这种关切构造了彼此相连的系统。所以诗人说“我感到担心”就是对这一系统可能发生的不稳固的担忧。但诗人很快就展开了自我说服——“这也是多余的”,并在接下来的诗行里进行了论证。
“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忠实地记录下”,这是一个工作场面,“忠实”与谦卑近义,是“我”作为一个居住于“山顶”的人在永恒主题面前的基本姿态。“这些诞生、死亡/和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诞生和死亡是生命的两端,“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之结果,是使得诞生和死亡保持了一种恒数的状态,并具有相互转换的可能:“似乎存在着一种结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另一个之中”。从诞生走向必然的死亡,又在死亡里萌发新的诞生,这是宇宙间的定律,诗人以“结构”来表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另一个之中”,这指明,诞生和死亡并非异时存在,而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生与死相互包蕴,彼此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属性,甚至任何处于两端的事物都是相互包蕴的——“孤单/必然成为更大的友谊的一部分”,这就是上述结构在人间存在上的呈现。
“为了永恒,就必须把时间再次分割”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另一个之中”的延伸和深入,把诞生和死亡这一对具有终点性质的组合上升到了“永恒”这个无限的概念。为什么“时间再次分割”能够成就“永恒”?我以为,这和飞矢不动的芝诺悖论同构:时间分割的无限性创造了“永恒”。接下来则是另外一种悖论:“在我的房间内,混乱的桌椅/恰好构成对清晰的另一种表达”。“混乱的桌椅”带有生活过的痕迹,因此,尽管它呈现着混乱的状态,但却可以追溯生活的各种线索,一定程度而言,每一个“混乱”背后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自此,诗歌通过雪后的山顶上升到了宇宙空间,而通过对宇宙的观察和想象,对诞生和死亡、孤单和友谊、混乱和清晰等等概念相对的组合构建了终极意义上的范式。
把自己设置在一个孤独隔绝的空间里,在自我的对话中获得想象和自我对话的自由,《1662年的雪》是如此,《几何学》、《寒冷的光线》等等,也是如此。《寒冷的光线》几乎就是《几何学》的副篇,“我”活动的空间仍是狭窄的山上,并且“我”获得了“气象观察员”的职业身份,使“我”对星空的思考变得更加细致而深刻,通过显得专业化的天文学知识的谈论,“我们”论述了永恒的微弱和孤独。
“316号房间”是江离大学时的宿舍,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拥挤的群居空间里,他仍能凭借想象建立一座自我的园地,把喧嚣挡在外面,找到自我对话的愉悦——
在我的果核里,我喂养着我的马群
和不同的自己交谈
并不断增加着他们的数目
虽然有时候说“是”,但不知道
那被肯定的是什么,在上空燃烧的
究竟是星辰还是看见它们的眼睛
当我的手指敲在琴键上时,是不是
我的灵魂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在旷野上我想到元素们,是因为孤寂
而结合在一起,多么美妙!蓝色和黄色
我的石头脸恰好和世界上
所有时间的一面相互吻合
《哈姆雷特》里有句台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霍金因此将他图解宇宙学的著作命名为《果壳里的宇宙》,所以作者把“316号房间”想象成一枚果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它是一个隔绝外界但仍然具有充足空间的场所。“我喂养着我的马群”,把“我的果核里”的世界带到了一个辽阔、孤独的地带,这个地带,几乎是与“316号房间”平行的另一个时空。多重时空带来了多重的“我”,“我”和“不同的自己”对话,“并不断增加着他们的数目”,说明了多重时空的不断繁殖,像有一面镜子,竖立在“我”和“我们”之间。这样的多重性质,使我们陷入相对概念的怀疑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缺少一个可靠的坐标进行衡量,因此我们既不能分清,当我们说出“是”时的肯定意义,也无法确认“当我的手指敲在琴键上时”,是琴键发出了声音,还是“我的灵魂发出了低沉的声音”。“旷野上”正是适合喂养马群的地方,但在这首诗歌里,仍然是在果核——这个独立的世界之中存在。“元素们”,是最基本的物质构成,它们运动不息,却依然像宇宙中的星球一样,凭借第一推动力联系在一起,组成更加显著的物质世界。在诗歌中,这样的第一推动力被认为是“孤寂”。但如果我们把视野始终围绕“316号房间”来谈论,那么“元素们”也可以视为宿舍成员的比喻,他们因为孤独而走到一起就具有温暖的意味。“石头脸”是一个凝固的表情,是属于时间的,而同时,它也是可以镶嵌在旷野之上的物质,属于空间,那么于此而言,“石头脸”就是旷野中的永恒表情,是对人类精神世界里的最基本情感的陈述。
江离诗歌中的冷静和理性主义色彩,并不是指他的诗歌缺乏情感的力量或叙述,而是我认为,他把自我及其情感当做了沉思的对象,成为被观察的客体世界的一部分,这使得他在谈论爱、悲伤、和孤独等情感元素时,始终保持着收敛的态度。
《颂歌》是一首不一样、值得注意的诗,它充满了激烈的感情
起风了,因为这是夜晚
一阵突然的悲伤
像雷电,击中了屋顶,因为起风了
我将把我的悲伤献给谁呢?
没有人来问候我弄出来的声响
没有人,那么请风静止一小会吧
我将为你们朗诵,以一种严肃得
有些滑稽的方式,还有你们
这些台灯、书本,被扔得远远的
我的臭袜子
我如此爱你们,因为这是夜晚
请你们坐好,我将告诉你们我的理解
像我的老师做过的那样
像今时今日,这悲伤所教导的
必须去发明一种新的逻辑
必须用一种酒后的语言才足以
对生活说话:请你喝,请把我熄掉。
这是江离少有的情感张力十足的诗歌,几个排比的铺陈增加了情绪张扬的力度,被设置的抽象的“你们”,成为情感倾泻的对象。然而,“颂歌”的命名已经告诉我们,这并非简单的抒情诗,情感倾泻也绝非诗的主题,相反,情感本身正是诗歌的写作对象,通过向“你们”的叙述,“我”内心的情感不但被激发出来,并且得到了谈论,具有了普遍意义。诗歌中的情感起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一阵突然的悲伤”、“没有人来问候我”,这是消极悲观的姿态;“为你们朗诵”、“我如此爱你们”,则是积极而开放的姿态。从悲伤到爱,正如诗人在《几何学》中所说的那样:“似乎存在着一种结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在另一个之中”,既是情感状态的两端,也是相互生长的同时因果。事实上,对自我而言,悲伤和爱可以导致相似的结果:缩小甚至取消自我,将自我奉献出去。而这种将自我降低并奉献出去的姿态,正是“颂歌”的基本内涵。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诗歌的结束部分,“悲伤”作为一种启示再次出现,紧接着呈现的,便是诗人意图奉献并取消自己的欲望——“必须用一种酒后的语言才足以/对生活说话:请你喝,请把我熄掉”,而诗歌中提到的“新的逻辑”,在我看来就是《几何学》中谈到的“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打破了泾渭分明、斩钉截铁的观念和判断,从而类似与酒后麻醉的语言。
《爱之后的爱》继续谈论自我的情感:
我用一种漫长的距离
一种不带任何细节的空白爱你
因此就没有凝视,也没有
过多的激情和迟疑来破坏它的纯粹
这就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
一座庙宇
不再有人去修整它,参拜它
而获得了应有的敬意
仿佛晨雾消散之后,草叶上的露珠
显现,一个清澈的小世界
仿佛我们——在两座山峦之间
终于有海水填满了深谷而变成了岛屿
这是一首可以和米沃什的《礼物》对照阅读的诗歌,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历经痛苦后的澄明意境。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西川译
米沃什在诗歌中设计了一个劳动的场面,地点是在他的花园;而江离在这首诗歌设计了一个“爱你”的情节,其中有一座破损的、比喻中的庙宇。米沃什的诗歌是纯粹的自白,而江离的这首诗却有一个对象可供倾述。在《礼物》中,“蜂鸟停在忍冬花上”是一个易碎的幸福时刻的形容,而在这首《爱之后的爱》中,“草叶上的露珠”同样一个是晶莹而易逝的画面。当米沃什说“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江离的这首诗里同样有一个表达恒定和秩序的静止画面——“在两座山峦之间/终于又海水填满了深谷而变成了岛屿”。
在这首诗歌里,诗题“爱之后的爱”中,前一个“爱”是动词,后一个“爱”是名词,似乎表明,诗歌所谈论的“爱”是一种冷静状态的爱,因此如诗歌中所说,“没有凝视,也没有/过多的激情和迟疑”。在诗人看来,凝视、激情和迟疑都像是破坏爱的纯粹的举动,因此可以说,在诗人的眼里,纯粹的爱应该是它们的反面——是坚定、冷静而平常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两节诗歌里,诗人阐述了他对纯粹之爱的理解:不是刻意的,像无人修整的庙宇;克服迷惑的,如“晨雾消散之后”;洁净明亮的,如“草叶上的露珠”;坚定,彼此相连却保持适当距离的,仿佛“在两座山峦之间/终于有海水填满了深谷而变成了岛屿”。诗歌中对话的“你”是不确定,这里的“爱”却是比较明确的情爱之爱,但即使如此,此“爱”仍然是抽象的,构造了作者理解中的理想之爱的普遍形态。
不议论具体的事件,对情感和自我的呈现也不停留于对细节的表达,甚至说不停留于表达,而是抽离出来,以保持一定距离的眼光,以回望、眺望或俯视的方式,对自我和情感展开观察和思考,考察其基本,并最终与诸如宇宙观念、自然律等终极思想建立联系,我觉得是江离诗歌写作的一大特点。所以,在江离的诗歌里,宇宙星球和自然气象经常出现,并且可以视为人类生活和自我精神的投影。
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个神
从这里退场
在星的栅栏之后不知所终
我们深知奇迹不可信赖
而回到事实本身——
一头狮子的沉睡就是它的沉睡
一口井中不再有月亮升起
在一场雨之后,是植物裸露的根茎
它的光泽正在消退
一切都变得清晰了,但没有什么
可以称为礼物
在哥伦布和笛卡尔之后
是一个新的世界,在它的完整性中
没有一种命运可以称为我们的命运
《日落》也是这样一首诗,其命名本身就是一个终极场景,因而它宏伟得与星空产生了关联。这是诗歌第一节呈现给我们的思考和想象。在这一节里,日落还有十分强大的象征性质:“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个神/从这里退场”,这是神性逐渐消亡的意象。“在星的栅栏之后不知所终”,说明神性的赋予来自于星空,而“不知所终”的现实表明,神性逐渐消亡之同时,大地与星空之间的隔绝也日趋严重。在这一节,诗歌设置了一个巨大的谈论环境。第二节,对日落的思考和叙述回到了我们自身,一个更小的场景。“我们深知奇迹不可信赖”,这是以否定的姿态对神性消亡进行了再次确认,并且开始谈到这种消亡与我们的关系。“回到事实本身”是一个降落的姿态,接下来的两行诗——“一头狮子的沉睡就是它的沉睡/一口井中不再有月亮升起”,就是神话退场的隐喻性描述,也意味在神话退场的现实面前,世界已经没有隐喻的容身之地。第三节“雨后”的时空,类似于江离其它诗歌中多次出现的“风雪之后”、“雾散之后”,依然是历经迷惑、狂暴或痛苦后的宁静境界,这是一个拥有前提的冷静而理性的场景,“光泽正在消退”重新描述日落神话的退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是“植物裸露的根茎”和“一切变得清晰”的另一种真理浮现之场景,它可以代表一种自我发现的情形。但很快,诗歌语言再次出现了否定——“但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礼物”,所不同的是,此否定是对自我发现的否定。到诗歌的最后一节,便是对此否定的进一步阐述。“哥伦布和笛卡尔”代表了两种发现,前者是地理发现而后者是精神层面的发现,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便是自我发现的经典名言。联系上一节,诗人似乎认为,不论是我们眼前所见的客观世界,还是自我体察的主观世界,“在哥伦布和笛卡尔之后”,都已经没有巨大的秘密未被发现,所有世界的秘密皆被一个更加庞大的阐释结构所笼罩,如诗歌所言“在它的完整性中”;并且,在此结构的笼罩下,自我被抽象出来——“没有一种命运可以称为我们的命运”。但这样的结果未必是幸运的,“哥伦布和笛卡尔之后”的“新的世界”,可以理解为古典主义终结的世界,它与“日落”的神性消亡之象征几乎同构,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放弃了对秩序和终极世界的思考和重视,有序正变得混乱,清晰变得模糊,长远也被暂时取代,成为一个由量子力学建构的不确定世界,自我的命运因而变得更加难以捕捉和掌握。在诗人看来,这无疑是悲哀的。
《沙滩上的光芒》是我们在“哥伦布和笛卡尔之后”的世界里再次寻找神圣安慰的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对《日落》的积极回应的诗。在这首诗里,诗人再次通过对相对概念的辩论和自我的再认识,发现了秩序之美以及自我的光辉。
春日的沙滩上,一片交织的
光芒在流动
有时它也流动在屋顶
高过屋顶的树叶,和你醒来的某个早晨
那是因为,在我们内心也有
一片光芒:一种平静的愉悦,像轻语
呢喃着:这么多,这么少
这么少,又这么多
像一阵风,吹拂过簇拥、繁茂的
植物园——
但愿我们也是其中的一种
并带着爱意一直生活下去
这使我们接近于
那片闪烁的沙粒,以及沙粒中安息的众神
光芒流动带有神性色彩,而“春日的沙滩上”,以及光芒流过屋顶、树叶和清晨,恰是与日落场景相反的灿烂画面。这是欢乐而积极的色调。而这种色调来自于对自我的信任,如诗歌中所说“在我们内心也有/一片光芒:一种平静的愉悦”。于是诗歌中出现了两种光芒:春日沙滩上的,以及内心的。“平静的愉悦”是一种心理状态,愉悦通常是激动的,但诗人以“平静”来界定,正指出了愉悦的静态和持久性,使得这种心理状态上升为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精神姿态。“轻语”是“平静的愉悦”的比喻,它的“呢喃”构建了自我与光芒的对话:“这么多,这么少/这么少,又这么多”。依然是与相对概念的辩论。从自我之外的世界回到对自我的叙述,到第三节,诗歌再次走出自我,并且试图构建客体世界与自我的和谐关系:“但愿我们也是其中的一种/并带着爱意一直生活下去”。与《日落》一诗的巨大不同是,这首诗歌里的“光芒”兼纳了现实生活和超现实生活的内容,因而它对内心“平静的愉悦”具有更加强大的说服能力,它是日常的,也是神圣的,正如诗歌的最后两行诗:“这使我们接近于/那片闪烁的沙粒,以及沙粒中安息的众神”。
对经验和自我进行诗歌上的概括和抽象,这让江离的诗歌呈现了超越的姿态,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经典的缓慢语调让江离的诗歌具备了某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在诗歌技术上,他不会沉浸于对具体事件的再写作中;而在处理日常生活,他更有一套独立而稳固(自信)的观念支撑。《宴席之间》这首诗可以视为他阐述自己如何对待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诗歌。
窗台上,花木迎来了夜露
你知道,软弱时
连轻寒也能钓起一片悲伤
席间,贵宾们锋利的目光
又一次检视了我来自小镇的谦卑
和不为人知的骄傲
作为回赠,我用冷漠
匹配了清谈
只有无知的天使,仍在即兴表演
我知道我已错过太多
在感官的真知和自我的信念间
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信徒
那就让我回到花木前
用灰烬后剩余的
热情,裁剪出一方合适的黄昏
第一节,“窗台”、“花木”和“叶露”共同设计了一个独处的场景,但这样的独处是被动的,因为诗人说:“软弱时/连轻寒也能钓起一片悲伤”。“软弱时”,也即对自我的心理状态不能控制之时,在这种情形中,“悲伤”因此显得泛滥,以至于“轻寒”也能诱发。这一节诗,是“我”在“宴席之间”尚未能得到自我确认时的情景。第二节,“我”由独处来到了人群之中,“贵宾们锋利的目光”让“我”显得格格不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展开了对自我的确认——“来自小镇的谦卑/和不为人知的骄傲”。第三节,是“我”在人群中的回应:“用冷漠/匹配了清谈”,“我”在这样的骄傲和冷漠中,获得了某种上升至高处的自由和怜悯:“只有无知的天使,仍在即兴表演”。第四节,是阐述“我”之所以如此回应,其背后的理念辩论,但依然显得不牢固——“在感官的真知和自我的信念间”,“我”是迟疑的。第五节回到了第一节的独处空间,但格调完全不同,是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选择。“灰烬后剩余的热情”是所剩不多的热情。我们周旋于生活和人际皆会造成巨大的损耗,这是悲哀的,但仍幸运的是,尚有“剩余的热情”供我们在独处时“裁剪出一方合适的黄昏”。
稍微仔细阅读,就能发现江离对某些相似意象的兴趣,日落和黄昏是一种,海岸线和波浪是一种,风雪、群山、积雨云是一种,但星群、星球、星辰和光线出现得更多。这些意象几乎都是巨大而稳固的,在诗歌中大多也与我们相隔遥远,是我们观察的对象。尤其是星空中的宇宙意象,更是不属于经验范畴,而属于推理的世界,一个属于数学和物理的世界。这个世界,也是笛卡尔、帕斯卡尔、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沉思对象。在他们身上,科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于此而言,江离的诗歌也有运用形而上学的推理或辩论的方式,理解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的兴趣。或者说,他能够运用星空的遥远视角,使诗歌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具有超越的姿态,以及一种强大的综合、概括和升华的能力。这样的超越,使得他即使谈论孤独,也持有充足的自信,因为就算孤独是人世间的情感元素,在推理和辩论之后,便与人世间的欢乐和幸福一样,具有同样一个恒久的终极架构。这样的结论,也许是让我们的情感以及诗歌保持宁静的最终原因,这种宁静也是江离的诗歌最让我感到折服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