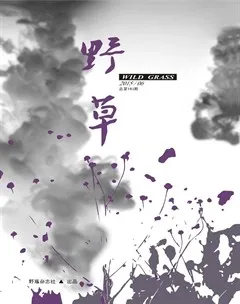在啃光的桃核上再用力咬一口
走走:你的小说与历史羁绊很深,涉及抗战、解放、土改、反右、文革、计划生育、暴力拆迁……这些历史元素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契机,开始影响你的人生观的?因为在我看来,个人对“历史”的建构只能出于服务自己的现实需要,而很多80后的写作者,活在当下,活在“历史”之外,没有你这样的历史感。
郑小驴:我理解你说的活在“历史”之外,其实是我们这代人对历史的一种回避,倘若我不写作,我对那些沉重的话题也没有半分好感和兴趣。时代在飞速变化,那些看上去很重大的东西,也不过是在时代的万花筒里浅浅一瞥就过眼云烟了。时代之“快”抵消了历史之“慢”。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很多东西是无法总结的,因为在总结的时候,新的东西又很快覆盖过来。惟有放下包袱拼命跑,才能不被主流所抛弃。这就是为什么阎连科老师前些日子说,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找不到80后的声音的原因所在。再倒过去回顾当年那些沉重的主题,其实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写作策略。
走走:我觉得未必是回避,不是每个写作者都能明明白白体察到历史对现时的影响。这里还有一个叙述的野心。
郑小驴:这种体察,也可以说是历史对现实的“投射”。至少回顾我自己的家族史,和阅读《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记事》、《古拉格群岛》时,我会体验到历史的悲凉和沉重。很多人不会知道历史对现时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应该知道。这是你起码的职业良心。是你道德的底线。苏轼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当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历史和他所处的时代带给自身的痛苦感也就越强。在一个有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历史之“重”不应该被刻意“轻”化。作为写作者体验这种痛苦并将其准确表达出来,不仅仅是叙述的野心,也是其职责所在。
走走: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过你的“故乡苍穹下”专栏,写你的祖母“在三年饥荒时期,用冬瓜救济过奄奄一息的邻居”;写她在1951年春,身怀六甲,膝下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在刑场目送了年轻的丈夫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清脆的枪声过后,一道影子栽倒于地,背上绑着的木板上面写着‘地主恶霸田某某’的字样。……不久,她两个哥哥也被五花大绑,以同样的方式押往了刑场。”祖母留下的诗歌藏在一只高筒雨靴里,被你读到,是不是这样的家族往事让你很早就意识到记忆、苦难与文学的关系?
郑小驴: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会贯穿你的灵魂,融入你的血液中,所谓大悲无泪。我从未见过祖母,在我出生前十二年,她就已经去世。家人平时也很少言及她。但我后来偶然知道她的这些生平事迹的时候,仿佛我和祖母之间的精神一下子贯通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也许这个家族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但是我的家族的不幸,和当时千万个不幸的家庭来比又算得了什么?还有更多悲惨的故事,它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可能性,落入历史的尘埃中。我好几次读杨显惠先生的文字流了泪。我们重返现场,打捞历史的记忆,面对一大堆让你无语凝噎的资料时,要做的可能并不是站起来批评、谴责、控诉,而是保持冷静、悲悯,因为只需客观呈现,就有足够分量说明问题了。
走走:正好刚才我还在和双雪涛聊他的新小说,也是涉及“文革”等等,我就觉得,历史这光一定要打在人物身上,才能形成阴影。
郑小驴:对,我很喜欢你说的这句话。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是历史必须要聚焦于当时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来,历史的画面感才会清晰可辨。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要写他出生前的事,其实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因为历史之光很难对准那个具体的人,很难看清他的轮廓和模样,我们都在说“文革”之恶,控诉远多于忏悔,因为这东西已经达成了共识,控诉容易博得同情和眼泪,而忏悔意味着需要付出代价。这就会造就人人都是受害者的假象。作家需要逃离这种假象,要从众多的控诉声中分辨出其中微弱的忏悔声。
走走:我自己也关心历史,但就像你说的,我们都不是历史的亲历者,“我的那些历史观,很多来源于后来重新获知的历史真相”。可以这么说,你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是你对自己历史认知的第一次“祛魅”,但对这所谓的真相的展现,会不会本身也是一种矫枉过正?就是,我对这种历史真相,本身也不信任。我可能苛刻了一点,我觉得你把历史之谜处理成了个人传奇,比如《秋天的杀戮》,枪支走火造成的误杀事件从游击队时期一直拉扯到“文革”再翻旧账,最终却还是如先锋一代,落进神秘主义氛围下个人欲望的窠臼里。
郑小驴:像《秋天的杀戮》我觉得里面的历史背景只是小说里的面纱,和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完全不同。那时我刚开始写作,迷恋先锋派的技法,需要借用历史来和现实拉开一段距离,需要一个能尽情虚构的空间,于是我设置了1942年这个时间点。所以这里的“历史”并不等同真正的“历史”。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要彻底还原当初的现场是不可能的事,好比侦破一桩凶杀案,我们只能从在场的证人、物证、凶手入手,却无法唤醒被害者,问出个所以然来。我也看过你写的一些文字,涉及到人物、史料、史实时,只能在这些二手资料中“祛魅”,这里得出的真相,也许只是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走走:写作者摹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观念,是这个意思吗?
郑小驴:是这意思。历史是由无数个细节、瞬间和人构成的,它有具体的所指,就像你说的历史之光必须打在具体的人物或事物身上,才能形成阴影。就像摄影,必须聚焦于某个点,否则就很容易脱焦。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历史的观念里,或者一些已成定论的假象里,“书上都这么写的”“电视里就是这么说的”,自己却没走出这个洞穴,观察外面不一样的事实。这些年,我自己也在历史观念的误区里徘徊,我在怀疑那些定论,又没有付诸实际的勇气,最后也就成了仅仅在洞穴前徘徊的人。
历史和现实两者彼此纠缠,有时甚至充满黑色幽默。历史告诉我们,在专制和自由之间,我想没有人选择专制;在独裁与民主之间,没人希望生活在独裁者的阴影下;在战争与和平面前,相信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后者。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人在现实面前往往却做出了有悖于内心的选择。我们总是选了一条自己不愿意走的但现实中又被迫去走的道路。历史和现实构成了一个悲哀的死循环。
走走:我很喜欢《没伞的孩子跑得快》这篇小说,涉及很多大的话题,比如年轻的叔叔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为民众振臂高呼牺牲了生命,民众却因为他的暴死拒绝他进入祖坟;女孩对叔叔的世界充满向往,却没有行动的能力,险些被人诱拐;女孩常去的黑老太的零食店又牵扯出黑老太自身经历过的更久远的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去触碰一个时代的禁忌?事实上,你很多篇与历史有关的小说都会选择一个孩子的视角,这样处理有一个便捷之处,就是人物因此不需要具备反思历史时所要求的思考的高度,而是只需要呈现出局部。
郑小驴:采用孩子的视角,的确给叙事带来便捷,但绝不是回避某些东西。宿离的童稚、天真刚好和时代之“重”形成反差。采用孩子的视角,其实也是很多电影的叙述策略,《穿条纹衫的男孩》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成年人眼中犯忌的雷区,在孩子纯真的目光和懵懂的追问下,反而会与成年人彼此心照不宣的“沉默”形成艺术的张力,达到反讽的效果。比方宿离问黑老太古币为什么在今天不能使用了、她的儿子为什么会饿死等问题,换成大人去问就大打折扣。我并不觉得这样的小说换成大人的视角,就能提高思考的高度,面对这样的题材,作家所要做的,其实是站在作品的背后,让读者主动去思考。福楼拜说,小说家是努力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其实你说的那些阅读感受,正是我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如果不是借用孩童的视角,这种力量反而传达不出来。借用孩童的视角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和宿离在小说中属于同一代人。
走走:有没有读者和你互动反馈过,看完你的这个小说,他们是否有所思考?
郑小驴:金理好像也很喜欢这篇小说。“比如说小驴的近作《没伞的孩子跑得快》,小说碰触的是当代中国的话语禁忌,小驴之所以不想让这一历史事件因为被赋予禁忌色彩而成为一代人的‘意义黑洞’,可能是觉得‘80后’尽管并不是直接当事者,但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态度所遗留的症结其实很难彻底消除。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自我主体的想象、甚或今天依然身陷其中的价值困境,未必不和当初相关,尽管当年只是不涉世的旁观者。在当下世俗社会与日渐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往的有生机、有意义的价值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公共生活和文化社群割裂,在外部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世界面前被暴露为孤零零的原子个人。当下青年人创作中一再出现的上述单薄、狭隘、没有回旋空间的个人形象,与当年知识分子广场意识与启蒙精神膨胀到极点的溃败后,再无法凝聚起批判能量,未必没有关联。通过《没伞的孩子跑得快》,我终于看到青年作家直视历史暗角、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在自己身上的烙印。”这是金理的分析。
走走:“都是以前的钱了,放在家里还能干吗!”所以小孩子偷去换话梅吃,你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情节?
郑小驴:权力左右着资本,权力一旦失去,所有的秩序都会打乱重新组建,资本也随即发生改变。换了朝代货币就变成一堆废纸。放开点讲,不仅是货币,连律法、社会风貌、教育、人格、精神等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恰恰这些东西,在几岁的小孩眼里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她才会天真地用失去了交换和流通价值的钱币去购买话梅。
走走:小女孩崇拜的小叔叔是村里唯一去北京上大学的大学生,当年高考全县第一名,所以我的解读是,想追随对知识分子崇拜的道路,却步履维艰,铩羽而归。
郑小驴:“战争时代我们流尽最后一滴血,和平年代我们寸步难行。”这是电影《颐和园》的台词。小叔白白牺牲,和鲁迅的《药》里悲哀是一样的。
走走:《七月流血事件》是我觉得很令人绝望的一篇。专科学校毕业,没家境没背景的小曾,只能做个推销员,底薪刚够付完房租勉强吃饭,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被交警查扣就成了生活中一件特别大的事情,为了弄出车不得不将借来打算交房租的钱买了烟酒,拜托人走后门。在如卡夫卡《城堡》般的手续面前,感觉自己即将被碾压成齑粉的他再次偶遇骗了他烟酒钱的骗子,于是拔出了刀子。小说里出现的所有情节都是硬邦邦的暴力,我觉得你非常冷峻地推演出了整个年轻一代在残酷的物质现实面前撞得粉身碎骨的过程。“他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排山倒海一般朝他袭来,要将他挤成齑粉。那一刻,他又看到了黑色,那么纯粹,那么深沉,没有一丝的杂质。”综观你的大部分小说,都集中笔墨于物质生活困境,非常“务实”,探讨精神生活困境的“务虚”作品大概只有《可悲的第一人称》这样为数不多的几篇。你一直在各种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从事的是形而上的工作,为什么能如此切身感受到新底层的戾气?
郑小驴:我很多小说主人公都游离于“务虚”和“务实”的痛苦中,两者间不停摆渡。《七月流血事件》可能是最务实的一篇小说,写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燥热和不安,那时我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区,身边有许许多多像主人公小曾那样的年轻人,有做销售的,有跑业务的,也有长时间待业的,我和他们成为了朋友,一起打球,一起喝酒,后来还成立了一个篮球俱乐部,有的现在还保持着联系,称得上是哥们。我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无产、无望、无为的绝望与迷惘(其实我又何尝不和他们一样)。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出路,也没太多的自主意识,受到时代残酷挤榨的时候,他们能作出的反抗必然滋生戾气。我觉得物质困境是精神困境的基础吧,就像我同事赵瑜说的,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差距永远缺五百万。
走走:你曾说过,你的很多小说都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人,今天怎么办?这个问题你现在有答案了吗?
郑小驴:没有答案。我曾经以为,我生活和工作安定下来了,会有答案。我一次次否定了自己。你看过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吗,他说过,一个艺术家从来不可能在一个理想中的完美环境下生活,除非有某种苦难在纠缠着他的心灵,否则他将毫无灵感。艺术家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一旦世界完美无缺,艺术将变得毫无意义。
走走:十八岁上大学之前,你一直在乡村生活,所以你的写作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乡村经验的,如《鬼节》、《少年与蛇》、《等待掘井人》;基于城市经验的,如《和九月说再见》、《赞美诗》,这样的生活经验给你的小说带来不一样的视角,你可以在两种经验中观察、对比,并在这之间的来来回回中拉出张力。但是乡村如今正被城市同化,你是否担心你笔下的乡村,也许跟真实的乡村已经没有关系,它成为虚构出的湖湘民俗文化载体,带着题材的稀缺性,承担猎奇的眼光?
郑小驴:坦白说,我顶烦那种动不动把“乡愁”挂嘴边的人。文字里也挺烦“乡愁”这二字的。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乡愁就不复存在了。就像我回到故乡,童年的一些记忆在此能得以归位以外,真正的故乡已经死去。甚至它已经变得不宜怀旧。其实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沈从文、鲁迅他们笔下的故乡也已经死去。我也很烦那种故意表现民俗猎奇的东西,全世界都在商业化,连西藏都不能幸免,再用民俗文化载体承担猎奇的眼光有矫揉造作之嫌。《鬼节》里我虽然表现了湘西南民俗风情,但那只是我借用的一个载体,我原意并不在此。乡村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溃败,暴露出的问题,比城市的问题要严重得多。那种还在发出旧文人似的感怀的人,是真正不了解乡村的人。
走走:所以《鬼节》的原意是什么呢,纪念那些因计划生育而夭折的婴儿的亡灵?我看上次加拿大记者提的采访问题,是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很好读的农村全球性系列之一,觉得你强调了农村生活的魔幻和苦难(尤其是女性的代表母亲),其实还是有猎奇的解读角度。
郑小驴:就怕他们把这个当猎奇小说来读。他们很多人是在把中国小说当社会学文本来解读的,试图通过小说家来了解中国当前的现实,对于小说的艺术性则索然无味。其实我觉得残雪老师说得对,这个小说体现出来的是“黑沉沉的力量”。《鬼节》我并不是仅仅提供一个猎奇的视角,里面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因为那天人和亡灵之间是可以生死相通的。
走走:阅读你的小说,即使是写乡村生活的,我也总是有种感觉,这个作者很焦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像《少儿不宜》里对蛇的恐惧,像《蚁王》一开始引用的《马太福音》,“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小说结尾,犹豫的善被纯粹的恶杀戮。这种焦虑和恐惧其实是非常道德化的,因为它们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小说营造出的世界缺失了人和人某种光明的伦理关系……
郑小驴:真正的艺术也许都是令人不安的,至少我喜欢的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三岛由纪夫等作家的作品都给我带来过不安。小说应不应该承担道德的职责和功能,给读者指明方向,带来光明?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卡夫卡说,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和捅我们一刀的书。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问世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道德伦理关系的讨论,有人指责这是一本伤风败俗之书,建议查禁。我的这些小说,呈现出的焦虑与痛苦,并不是特意的艺术渲染和强化,而是来自现实世界真实的反馈。
走走:我读你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蚁王》,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小马的道上大哥的独苗被残酷虐杀,小马无意中发现了杀人者,那也是一个小孩。“小孩被他的突然而至吓了一跳。他颤抖的眼神,让他想起当年在街头被人劈砍时的自己。……小孩畏惧地望着他。”于是小马“想着让那小杂种走算逑。越快越好,他再也不想看见他”。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小孩等着小马的惩罚时,一只黑蚁的蚁王爬上小孩的手臂,“小孩伸手将那只蚁王捏住,只见嘴角动了动,轻轻一搓,蚁王顿时化为了黑粉。接着他又低着头,做错了事等着挨罚似的”。然而小马没看见这一幕。于是在他转过头去后,“当他感觉脑后有风时,尖锐的疼痛也紧随而来了。不用猜他也知道那小杂种在干吗。小马一下一下地忍受着钝击带来的创痛。栽倒在地的时候,他看到一道歪斜的身影,手中正握着一块滴血的石头。一个略有些稚气的声音在上面说,‘老子还未满十四岁,杀人不犯法。’小马想笑,却怎么也动不了,他的眼前漆黑一片。”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列维纳斯的书,他提出“他者”的伦理哲学观:“看到脸庞就是听到:汝不可杀人。”小马看见“他者”——小孩的脸庞,于是就对这样一个外表弱势的“他者”产生了伦理责任,他也因此下不了手继而送了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对人和人的关系的想象是相当消极的。为什么你会让更年轻的——孩子——对他人的脸庞视而不见,漠视自己身上应有的人性本质?为什么你要赋予更年轻的一代如此黑暗的未来?
郑小驴:列维纳斯的书我没有看过,不过他提出的“他者”的哲学伦理观和我在小说中引用的马太福音里的“凡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都不要惧他”是有共同之处的。小马不过是想惩戒一下小孩,来平复他内心涌动的愧疚和不安。他并没有要杀小孩的念头。在这里,他是受伦理责任的约束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讲究秩序和规则的成年世界。而小孩要自立,必须得先打破这种规则,他是藐视一切法则的。所以我觉得,让小孩来干这事,是很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特征的。一个男孩反抗世界,首先是从反抗大人开始的。所以他杀小马,并无突兀之处。因为他尊奉的处世哲学,是尚未“入世”的哲学。谁要欺负他,他必反抗,甚至杀戮。而成年世界里的小马,思想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为黑疤的死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另一方面黑疤唯一儿子的意外死亡,更是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自责和忏悔心理。小马身上既有善的东西,也有恶的东西,他是集善恶于一体的人,是活生生的人。
走走:你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他们看起来全都怒气冲冲。和你同龄的许多80后写作者,文本气质相对温和、宁静,甚至有一种死水微澜的沉沉暮气。你的人物这种被压抑因而总想爆发,总想像刀子一样把自己扎出去的劲儿来自什么?
郑小驴:痛的时候,人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反抗。因为痛和这些有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像刀子一样扎自己,正是源于主人公他们和周遭的紧张对立关系。我的小说中,主人公们都是一群现实中灰头土脸的失败者,在社会规则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的人,他们活在时代的夹缝之中,唯一能伤害的人就是自身。刀子扎得越深,意味着越痛,他们反抗的力度也越大。我喜欢有力量的文字,因为这意味着和现实短兵相接,带着点血腥味儿,但绝对很真实。
走走:“坦率讲,我就是我娘偷偷躲出来的,不好意思,拖了计划生育的后腿,原谅我娘觉悟不高。那些暴力标语伴随着暴力行为,和凋敝的乡村四处所见的砸墙揭瓦的种种惨状(好比鬼子进村)是我漫长的童年见证。”计划生育这个问题落到一个乡村家庭的实处,确实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经历是不是构成了你个人的创伤性体验,导致你的长篇小说《西洲曲》完全直面这一问题?
郑小驴:是的,这个小说很多经验其实直接来源于我少时的所见所闻,给我带来过创伤性的体验。我记得无数个不安的黑夜,被狗吠吵醒,那是计生组的人深夜来了。当时城市里可能文明点,而且有工作单位等限制着,在农村完全是一种野蛮粗暴的执法状况,我在河南有次听一个干部讲,那边的情况更惨烈,医院里抓来引产的孕妇已经人满为患,实在住不下了。那些人后来抓到孕妇,用一块布围着,直接在现场就给人做了引产手术。
走走:我觉得你所有与计划生育主题相关的小说都可视为创伤小说,原因之一是受到困扰、折磨的是失去孩子的那些亲人,而不是那些强制结扎、流产的执行者。像《鬼节》中,必须面对鬼魂、亡灵不满的是“窝藏”超生大姐的母亲(大姐后来因动了胎气,早产了一个死婴),而逼自己六个月身孕的大儿媳妇去流产并最终导致她因引产而死在医院的八伯却不需要承担面对鬼魂的罪恶感。这样处理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小驴:我们是没有忏悔文化的一个民族。不像西方相信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儒家思想里的忏悔,也不是表面上的,而是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羞耻”和“不安”,这个东西,即便他有忏悔的心理,他也不会与任何人分享,表现得更为内敛和克制。《鬼节》里采用的主要是受害者一方的视角,意在表现这项政策给人性带来的戕害和创伤,小说母亲一家对八伯的警戒、冷漠,其实可以理解为受害者的症候反映,母亲最后嫁给他,可以视为借助强者来保护这个家庭,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特征。八伯虽然着墨不多,他同样有自己的苦恼,因为他是执行者,儿子憎恨他,周边人的蔑视他,只不过他的痛苦表现得更内敛些。
走走:你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有一个从失望到绝望的过程,但希望的成分不多。我觉得他们是对既有的秩序不满,但另一方面,并不知道自己追求和需要的是什么。像《少儿不宜》中的堂哥,大学毕业却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被逼跳楼后只能瘫坐轮椅。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小说主人公游离也只能继续无所事事。为什么你选择不去指出一个努力的方向?
郑小驴:我觉得这符合生活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清楚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是如此。作家不是道德家,也不是人生规划师,他负责提出疑问,但不负责指出方向。我不喜欢虚假的温情,因为一个温暖的结尾,需要作家在现实面前撒谎、妥协,他为了一个看似光明的前景,向读者强颜欢笑,告诉他们去相信也许并不存在的光明。当然这个世界一定存在温暖,这是客观的事实,未来也许我也会成为那样的写作者,但现在不会。我的写作希望能呈现一部分事实,不赞美,不粉饰,也不刻意夸大人性之恶。我希望坚持一种怀疑的立场。
走走:你的回答让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的话,小说所要代表的人物,是“生活着的怀有深刻不确定性的人”。在你这里,文学不是逃离现实的手段,它是理解现实的手段,但却不是和现实拉开距离的手段。那么你喜欢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吗?
郑小驴:说实话,关于这个时代我并不大喜欢。我时刻在想着逃离,但是又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时和朋友开玩笑,我是一个从不写诗的诗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我和它保持着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有时咀咒着自己,心里向往着美好,身却驶往万复不劫的黑夜深渊。我很不喜欢这种缠绕的现实关系。
走走:在你新作《你知道的太多了》自序部分,你提到自己在长跑。“每次跑十公里,或者更多。……这几年,社会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我不安、悸动,有时甚至惊魂动魄,不知所措。惟有在跑步的时候,我才能彻底沉静和专注,将那些繁芜杂念抛弃身后。”你以前也将写作比作马拉松,我一直觉得你的写作手法非常沉重,据说长跑过程中会达到某一个临界点,那之后人会有飞起来的感觉。希望有一天,你的沉重中会多出超越性的轻灵一笔。
郑小驴:你说得很对,我觉得一直在背负着十字架在长跑,跑得特别笨拙,特别别扭,特别累。聪明的人都选择回避某些话题,轻装上阵。这就是我和你说的,我为什么写《蚁王》这类故事性的小说时,非常轻松愉悦,而写《天鹅绒监狱》等中短篇时,总感觉在推一座山向前走。很多作家总爱将人性摆出来替自己开脱,我想说,人性才是最好写的,往阴暗里写,或往温情里写就是。人性就像水蜜桃,谁都可以上去咬一口,而我崇拜的是在啃光的桃核上再用力咬一口的人,鼓着腮帮子嚼出它的涩和苦,紧锁着眉头,却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