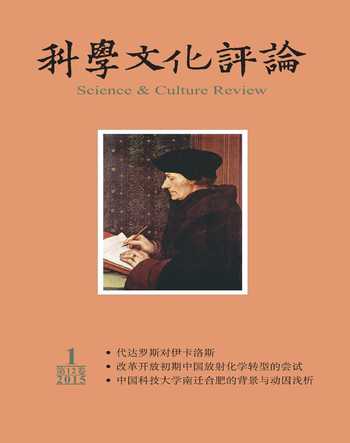西方科学史家与全球转向
冯晓华 高 策
摘 要 近些年,全球转向正在成为西方科学史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够缓解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困境,开启西方科学史家写作与生存的新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史家开始重视地方研究,地方研究的重点放在技术知识而不是自然哲学知识。科学史的全球转向正在改变这个学科的地理轮廓和操作模式,正在促成各种研究方法的转变和重塑。同时,科学史是什么的历史、科学史家应该研究什么以及共同交流的语言平台应该是什么等难题再次摆在西方科学史家面前。
关键词 西方科学史家 全球转向 地方研究 技术知识
18世纪以来西方大致形成了三种主要的书写世界史的模式:第一种是由进步史观主导的世界史,这种世界史实际上就是欧洲文明的传播史;第二种是由平行史观主导的世界史,这种世界史是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历史;最后一种是以民族国家为本的世界史,这种书写方式也是源自进步史观。
这三种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在历代世界史著述中都有所显露,针对世界史学中所存在的学理争议,伴随新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相应的新帝国史、比较史、微观史、跨民族史、区域史以及后殖民史学,20世纪60年代以“文明互动说”为核心理念的全球史观被美国学者引进史学研究,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反思与批判;但自90年代以来全球史以其全新而开放的理念,与各民族日益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形成互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如今全球史已经发展成一个新的史学流派,成为撰写世界史的一种方法论。
史学界的这种全球转向也影响到了科学史,科学史的全球转向,不仅会改变这个学科的地理轮廓,也会改变其操作模式,西方科学史家需要对过去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和理论工具都特别注意。有西方科学史家开玩笑说科学史现在需要被切除内脏,应该审慎地对待它;也有人认为决定如何重铸历史的时刻到了,他们开始改造自己适应新的标准,尝试提供新的方法和角度来重建非欧洲知识体系的科学史。近些年,对全球转向的持续讨论表明:全球科学史已成为西方科学史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全球转向正在促成世界各地做科学史的各种方法的转变和重塑,全球化正在成为定义科学史的核心术语。
一 选择全球转向
科学史要不要进行全球转向的问题根源于历史学界在转向问题上的犹豫。历史学界一直在很缓慢地领会全球化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世界史家一般认为全球史(研究全球化)将会弱化世界史已经确立的地位,造成混乱局面,所以各国的世界史家一直致力于维护世界史的身份,他们往往要么忽略新的全球史,要么说他们正在做的研究已经包含了全球史。至今,到底什么是全球史以及什么是世界史的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即使承认全球史不同于世界史,有关全球史的研究是否可能的讨论也是无果而终。
这种困扰也带到了科学史界,不过西方科学史家面对的问题不是定义类别,而是选择。对于西方科学史家,全球科学史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早期的自然史家和自然哲学家都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重视地理区分会缩小科学本身的思想,所以他们解释的可信度往往与其理论描述全球的程度相关。将世界化分为西方和非西方有很长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科学”作为与“现代科学”相当的概念确立起来。一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已经宣告了西方科学的成功,并假设其他地方科学的失败。在这种基础上确立地狭隘的时间和领土的科学史观,塑造了这个学科的分类和范围;再加上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相互作用期间发展起来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偏见,导致欧洲人对非欧洲世界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产生了极大的贬低。
全球转向开启了西方科学史家写作与生存的新历史。历史实践向来是由多个叙述声音确立的聚合对象,鼓励和支持多个声音才是该领域的生机。全球转向使得西方科学史家有机会克服他们一直以来研究框架的限制,从以欧洲为中心转而面向多个科学史的声音,认真对待不同语言和国家的文献。全球转向促进了科学史在空间上的延伸,通过将时空上分散的对象建立关系,西方科学史家致力于塑造越来越丰富和多个声音的科学史。它的确是一种积极的运动。
对欧洲边缘的关注可以说是全球转向迈开的第一步。1999年7月巴塞罗那举办了“欧洲边缘的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uropeanPeriphery))论坛,边缘是一个非常含糊地字眼,它包含有历史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和人类学的起源等意思。与会者认为:对于科学史家,当前最具挑战性的一件事情是地理上的扩展和文化的多样性,他们应当决定如何重新撰写历史。在欧洲边缘的科学编史学研究中,概念变化和文化调整使得科学作为全球现象出现在欧洲边缘中。
后殖民主义促使全球转向在欧洲边缘成为一种合法化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全球现象,而不是欧洲遗产;科学史是一个全球史,不仅因为它被嵌入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还因为它没有特权起源地,它是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结果。后殖民语境中的科学史与欧洲外围的科学史相结合,进一步扩展了两个领域的解释性范围。民族主义的科学史成为全球转向的集中反映。
对全球转向最好的宣传来自科学史会议与期刊。2005年,北京召开了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主题是“全球化与多样性:历史上科学和技术的传播”(Globalizition and Diversity: Diffu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outHistory)。2006年,克拉科夫举办了欧洲科学史学会第二次国际会议,主题为“全球与地方:科学史与欧洲文化整合”(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The History ofScience an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Europe)。2010年,著名科学史杂志伊西斯(Isis)第101卷专门辟出大幅版面约有63页用于发表全球科学史的研究。2012年,雅典举办了欧洲科学史学会第五次国际会议,主题是“全球现象与地方特殊性:东西方科学思维精英与手工艺知识持有者之间的渠道”(Global Phenomenaand Local Specificities: Conduits Between Scientifically Minded Elites and Holdersof Artisanal Knowle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西方科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可能是西方科学史家进行全球转向的最无奈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科学史旨在用简短的历史解释来巩固统一科学知识的目标。到了70年代,科学似乎太过多样化,甚至在同一个分支学科中就会有太多变化,已经不能涵盖在一个简单的模型下。科学史家也很少有兴趣提供简略的例子来证实或否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图景,他们转向了由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提出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尽管呼吁全球科学史不是灵丹妙药,它可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但是拒绝全球转向将会导致科学史成为一门僵化的和摇摇欲坠的学科。科学史正在转型的风口浪尖上,所有科学史家需要考虑的是他们的工作如何融入全球的轨迹,重塑这一学科。
二 地方研究受到重视
20世纪后半叶,殖民地科学史成了西方科学史家突出的研究重点。在这一时期,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科学的本质进行了辩论。由于社会构建主义强调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地方或然性特征,渐渐地,盛行的实证主义让位于构建主义,以欧洲的真理和理性为标准的分析让位于非欧洲地方地更丰富、深刻、厚重的科学解释。西方科学史家作为回应,加入志同道合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行列,他们从古典现代主义概念转身离去,走向地方研究。
地方研究正好与科学史的全球转向相契合。地方可以是国家、地区、城市甚至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就是在一个地理区域内也允许地方分层次解释的灵活性;地域界限只是所需之一,地方也可以是制度上的,如期刊、大学、大型合作项目、或卓越的研究中心;地方还可以被有形资产所界定,如社会经济情况、合法性、地形和技术;抽象的还有对时间、空间和进步的信仰,它们进一步被种族、性别、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所塑造,地方标志着历史、环境、语言和文化的交点。地方与全球知识被一视同仁,没有一种知识系统凌驾于另一种知识系统之上。地方研究还原了知识的完整性,通过简单的标记成科学史的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被整合到相同的历史中,而不需要在现代科学思想中涉及它们。地方性解释转向可能是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哲学近三十年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
地方研究,重点放在技术知识而不是自然哲学知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力量的天平偏向自然科学,早期的科学史家只是将欧洲以外其他地方那些以数学或经验方法为基础的东西算作科学,将所有那些不适合这种模式的技术知识列为非科学或干脆忽略。而实际上,早期富有实践头脑的知识分子与善于思考的工匠之间分享了他们在理论与实践、思考的知识与技能等方面不同的知识,作为知识的生产。对此,西方科学史家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由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工作启发的实践理论是过去几十年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展,其中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品,而是实践,是一种技能,存在于地方日常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现在,技术科学正在成为文明重力的中心,技术科学文明开始覆盖全球。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历史,西方科学史家越来越重视将地方个案研究、微观史与比较史作为通向全球史上更多声音的科学和无所不包的科学叙述的路径。个案研究能成功的整合科学内容和历史语境,将自然研究放置在它们的内在和外在语境中,重建历史解释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通过相互作用,根据自己的条件,形成对自然世界的知识结构。微观史是对一般事情的特定细节进行展示的例证,它能够挖掘地方故事,引出某个时间、地点下标志科学的过程、价值、符号的微妙的内在联系,促成地方特色的科学记录,形成科学叙述的连续性。比较史通过提供不同文化基础上科学知识生产的启发式的比较分析,扩展了科学知识生产的参与者的范围。三者积聚地方中的个别点,把个别故事交织到一个共同的全球情节中,给出一个更全面的科学史。
地方知识与全球科学之间的翻译有一个张力,即地方知识如何移动,穿越边界,进行地方密集交流,形成全球广泛流通,最终融入全球科学。这些地方交流与全球流通以及它们形成的相互作用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史中塑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效的整合科学史与全球史,来解释地方性知识成为全球科学的过程,透露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演化中更多的东西。近几年,最有影响的有关全球化科学史的研究,就是知识散布到世界网络的想法,每个地方都有能力成为中央,成为信息交流的节点。相应的,批判和推翻巴萨拉的科学从西到东传播的三种模式,成为近些年来西方科学史的一个重点。
一旦赋予地方交流和全球流通在科学发展和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接触区(contact zone)、流通(circulation)、挪用(Appropriation)便成为很有用的术语。全球不同地方接触区的独特复杂性形成了全球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和它与物质进步历史联系的基石,接触区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确认。流通能够实现从对西方优越必然性的简略表达到纠正全球关系不平衡观点的转变,这个词已经在科学史的全球转向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使用。挪用能够解释科学的普遍性是如何通过跨地方的思想交流和实践而获得的,通过关注挪用而不是发现、发明、或转换和适应,科学史家可能带来重新发明、概念变化和文化调整的最前沿。挪用已被欧洲外围和殖民地科学编史学广泛采用;不过挪用现象不是限制在欧洲外围和殖民地,它涵盖了全球。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地方间的挪用仍然是地方的;但是它们能够通过不同的速度,使地方知识和文化形式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超越地方性生成一个普遍合法性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挪用能使科学史家将科学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地方过程来研究。“放眼全球,立足本地”将不是一句空话。
三 全球转向面临的难题
但是,对于那些渴望通过仔细核查地方性文本与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联系来讲述一个更具全球性的故事的科学史家,除了有这些机会,也有很多挑战。
首先科学史的全球转向意味着这个学科需要重新定位。非西方和西方人之间的冲突是他们的知识系统不完全按照相同的内部真理的或一致的标准运作,科学史家想要在欧洲、北美与其他地方的科学史之间建起桥梁,并且保持连贯性,就需要与相邻学科的学者如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符号学、区域研究以及文学家重新对话。科学史越来越成为实用主义的、地方定位的一种;而不是一个从它的学科问题获得特殊性的、特定的学术事业的表达,科学史作为服务于科学的一种事业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科学的共同表示与科学史家研究材料大杂烩的不匹配,使得确定一些主题或话题是否属于科学史变得不是那么简单,科学史是什么的历史变得不怎么可识别。过去几十年,公度欧洲和非欧洲的知识成为科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科学史家是什么或应该研究什么再次成为问题。科学史家不清楚自己应该研究什么这件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世纪研究者和早期现代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就讨论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是将世界化分为西方和其他地方。在很多方面,科学史本身就是从问科学是否是西方文明或西方的特殊产物开始的,科学史学科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全球舞台上,科学不再是西方的特殊产物,科学与非科学的类以及边界需要重新审视。
非欧洲视角文献的缺乏是西方科学史家的一个共同抱怨。全球转向很重要的是接近各种地方文献,事实上在欧洲和北美之外有很多很好的科学史研究发表在一些当地期刊上,但是这些期刊一般不会被西方科学史家参考。为什么呢?举个例子,一个西方学者要撰写16世纪中国的自然史,他首先必须熟悉中文或古文,以便能阅读中国古典原始文献;其次他需要在许多语言中识别相关文献资料:如英语、法语、德语,他还可能在意大利、葡萄牙或其他语言文献中发现重要资料。这种挑战的难点还在于他不是在几种语言文本中而是几种史学语境中遨游。如果不这样,西方科学史家如何从有限的档案资料库中提炼出新的全球史?
全球转向并不仅仅是转向新的领域,西方科学史家需要重新思考西方模式的科学史,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分期问题,同样重要的是重新考虑全球化科学史中某些关键时期的分类。一直以来,西方史学如此依赖一个神圣的历史时间框架以及它自己看似无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的进展,地方时间概念已经对西方的线性时间范式提出挑战,全球科学史应该采用一个什么时间线,建立这样的时间范式应该依据地方的还是欧洲的标准,仍然是问题。
对科学史研究的评价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比如有3篇相同的有关本草纲目的论文:一篇是中文医学史期刊上的,主要由援引原作者的陈述组成;一篇是日文论文,主要是跟踪和整理各种文本版本;还有一篇英文论文,主要是解释文本中药物的现代作用来确认它们是否起作用。这3篇论文分别象征着科学史的地方风格,依据不同价值体系,通过各种方式参考一手和二手文献,阐明一个观点。当这3篇文章被提交给一个重要的国际期刊后,同行应该怎样审查?拿一个西方标准审查来自不同地方的编史学的工作显然不公平,问题是如何实现评估工作的全球标准。
全球转向还需要一个新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基础。长期以来科学史期刊鼓励用全球主导语言英文写作与研究,这可能会扼杀了地方差异,使人们很难感受到科学史的地方特色;同时翻译的民主性也受到质疑。这种情况下,需要发现一种新的方式,它能够将地方差异翻译成一种有意义的共同交流,实现科学编史学和认识论中的地方多样性。如果不是英语,这种有意义的共同交流的平台能是什么呢?
国际科学史学会同样面临问题。原则上,国际科学史学会是一个多种语言的组织,但实际上科学史学会主要由北美实体经营,它的年会总是在北美举行,会议的讨论语言是英语,它的管理主要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完成,它是一个讲英语的实体,在它旗下知名的科学史出版物伊希斯和奥西里斯(Osiris)上的大部分书评和所有研究论文是英文。在很多方面,这是有道理的:在以英语为主的一个多元化学者的组织中,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为什么不是英语呢?但这些又如何实现全球转向呢?
总之,科学史要实现全球转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种转向,有一点可以肯定,用全球化的视角写科学史,看法会很不一样。
——博弈论
——“科学史上的今天”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