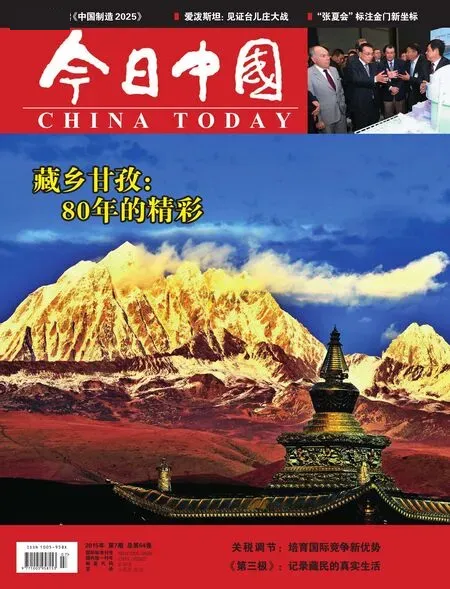《第三极》:记录藏民的真实生活
文|本刊记者 龚 寒
《第三极》:记录藏民的真实生活
文|本刊记者 龚 寒
镜头下的青藏高原美景震慑人心,但真正吸引曾海若的,是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极地环境下人和自然的关系。
“看我在这里找到了什么?”美国人乔治夏勒摊开手掌心,是一只其貌不扬的黑色毛虫。作为国际知名的雪豹专家,夏勒的乐趣和工作,是在青藏高原寻访珍贵的雪豹足迹。但此次行程,让他印象最深的却是这种黑色小虫。
在从青海玉树开往杂多的路上,夏勒看到,有一段路面上爬满了这样的毛虫。几乎每一辆当地的车经过那里,都会停下来。人们下车,弯腰将这些毛虫小心捡起,放进桶里,走到路边的草地深处放生,之后才驱车离开。
纪录片《第三极》记录下这个片段。这个最近热播的关于青藏高原的纪录片,前后拍摄了500天,行程遍及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60多处秘境,是迄今为止投入成本最大的涉藏纪录片。
青藏高原,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被称为除了北极、南极之外的第三极,也是唯一有人类丰富生存活动的极地地带。这里覆盖着雪山、冰川、湖泊、沼泽,物种丰富,宗教氛围浓厚,充满着神秘色彩。

玛旁雍措,藏医次成取圣湖水用来煮药
在青藏高原,最能体现人对自然的善意的,是人和动物的关系。农妇救下受伤的黑颈鹤,村民们为下山的猴子让出居住地,主人真诚地把洁白哈达披在自家藏獒或马匹身上。
“我没打算拍成解密的片子,藏民原本的生活是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导演曾海若说。
镜头下的青藏高原美景震慑人心,但真正吸引曾海若的,是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极地环境下人和自然的关系。
片子播出后收视率超出了制作团队的想象。首轮播出后,累计观众规模达8334万人次,平均收视率达到0.37%,比同时段电视剧还高10%,也成为中国首部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直接采购并推送到其全球电视网络的中国纪录片。
当下的真实生活
10年前,曾海若第一次拍摄长纪录片就在青海藏区。40多天的拍摄最后被剪成30分钟的片子。再次拍摄西藏是他的一个心愿。然而这次的感受与上次大不相同。
“第一个,我没有想到现在的西藏还是比较现代的,手机很普及,基本都在用微信。另外,他们的观念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传统,而是对新的东西很有兴趣。”曾海若说。
他最初想拍的是西藏的传统风采,但在拍摄前搜集故事的过程中,发现与西藏有关的书籍,集中在历史和游记,关于西藏人民当下日常生活的内容少到几乎没有,尤其是2010年后的西藏日常生活部分。
于是,回归到极地环境下西藏人的真实生活,成了这一纪录片中40多个人物故事的内在标准。
外界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藏民一生只洗三次澡,出生,结婚和死亡。
“他们比我们想像的要现代得多,虽然在牧区确实没有澡堂子,但有很多温泉”,曾海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待上好几天,甚至一天洗好几次澡。”
少有人知道,温泉是藏医的治疗方法之一。老鹰泉有20多个温泉池,患有疾病尤其是骨骼病的藏区人,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
这里俨然是第三极的一个公共空间。人们赤裸着身体,在雾气缭绕的温泉里聊天,交换看法,言谈间不时以石头叩击泉眼,泉水便会汩汩而出。
每天都有从外地赶来的人,每天也都有离开的人。温泉外面,病人们丢弃的拐杖交错堆起,温泉的神奇疗效可见一斑。人们泡完温泉,裹个毛巾或罩个棉袍,一字排开,坐在墙角晒太阳,聊天,吃药,娱乐,孩子们赤裸着身体在其间嬉闹。
在拍摄完温泉返回的途中,摄制组发现了住在帐篷里的一家人。这家人正在用新鲜的羊肉喂养6只捡回的小狼崽,它们可能是因为风暴而走散的。而这些羊肉,来自家里当天被狼咬死的20多只羊。“狼崽小时候很可爱,长大了就很可恶。”这户人家笑着对摄制组说。
在青藏高原,最能体现人对自然的善意的,是人和动物的关系。农妇救下受伤的黑颈鹤,村民们为下山的猴子让出居住地,主人真诚地把洁白哈达披在自家藏獒或马匹身上。
曾海若认为,藏族人对动物的善意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一种祖辈传下来的传统。
“爷爷奶奶这样做,妈妈也这样做。在那样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生存极为不易的高原环境,他们自古以来形成了对于生命、对于万事万物的平等的感激之情。对待虫子也是,并不去区分益虫害虫。”曾海若说。
他拍摄过的一个村庄,村民每年都要去寺庙求高僧加持过的象征赎罪的解脱丸。这机会一年只有一次,但村民们却选择将药丸溶在水中,喂给不得不杀掉的羊,并为它念经超度,以此赎罪。
“在藏族文化里,人的地位似乎不像其他地方那么高,力量那么大。他们有一种观念,在高原上人类是客人,高原、环境才是主人。客人不能随便乱拿主人的东西,主人给你提供了多少,你就享用多少。牧民们绝对不会去养超出这片草原承受能力的牛或羊。”曾海若说,“他们只是把人当作万事万物中的一环来看待。”

喇嘛穿过一片沙丘去寻找制作坛城的原料

敏珠林寺,僧人用沙粒制作坛城
瞬间消失的坛城
摄制组去敏珠林寺拍摄,被这里的佛学院学生所吸引。他们是一群身着红色袈裟的顽皮年轻人,做鬼脸,小恶作剧,嚼口香糖。因为他们,摄制组得以近观寺庙的仪轨,并在这里遇见了“坛城”。
坛城,梵语mandala,是诸佛菩萨聚集的空间,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这种仪式传统上只在灌顶过程中开放给受法弟子看,很少示众。
萨卡达瓦节,敏珠林寺的40多个僧人怀着极大的虔诚心,分布在四个不同的位置构建坛城。他们用手指捻着色彩斑斓的细砂,沿着勾勒好的白色图案,轻轻落下,渐渐构筑出一个结构严谨却又瑰丽无比的图案。据说,当年佛陀也是这样和弟子一起作画。
令人震撼的是精心建立坛城之后,僧人们一齐跪在地上,以极快的速度用手扫走砂砾,随即用湿布用力擦拭。不到1分钟,坛城完全消失,赤色的石地板上空空荡荡。
“除去信仰,这几乎可以用来比喻任何事情。”曾海若说。
修行,是第三极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雪山脚下的湖边,两个瘦小微驼的背影是一对年老的双胞胎姐妹。姐姐在附近的岩洞中修行长达20多年,从没回过村子,吃喝全由妹妹供给,陪伴她的只有吃死尸的秃鹫。相比富态的妹妹,修行很高的姐姐虽然面容黑瘦、衣衫破旧,却备受妹妹和村里人尊重。
她们坐在山坡上,瘪着嘴聊天,议论村里那么多老人为什么要拍她们,搞不清但也不在意。姐姐对摄制组说,你们拍电视太苦了,还是修行好,“只有善念是最好的陪伴,有了善念的陪伴,才不会感到困惑与烦恼。”
摄制组第一次进入藏医次成的工作室—一个简陋的洞穴时,意外地发现这里有很多现代电子产品。次成正烦恼于IPAD最近出了小毛病,互联网已经成为他研究藏药的方式之一。
次成研制藏药的重要材料是石头,为了完成师傅圆寂前嘱托的每年配制12味藏药的任务,他跋山涉水寻找各种合适的石头和药材,再去圣湖玛旁雍错采集圣水蒸煮,配制出的药丸只留下一小部分,其余均赠送患有疾病的村民。
无论是次成的IPAD,还是帐篷里的各种电器,现代生活方式正在这里越来越普及。
“打嘎”,是一种集体劳动,大家在屋顶上排着队,拿着工具踩着节拍,对屋顶进行整修。打嘎的年轻男孩子全都穿着现代服装,戴着棒球帽,有人热情地邀请来拍摄的编导一块跳,“come on,come on!”。
曾海若曾问一些当地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城市生活,喜欢外面的世界,你们有没有担心?
“许多喇嘛以及传统文化的学者跟我说,他们觉得世界一直都在变化。变化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特点,一点都不可怕,如果几十年都不变,才是有问题的。而普通藏人则当然喜欢便利的生活。”曾海若说。
传统与现代也会在年轻人身上实现奇妙的结合。斯塔多吉,西藏的一名大学生,性格真诚腼腆,每天和其他学生一样上课,打篮球,回宿舍睡觉,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格萨尔王》口述艺人。
《格萨尔王》,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青藏高原的多个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唱了千年,仅韵文就超过100万行。它讲述的是生灵涂炭之时,格萨尔王下界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的故事。
斯塔多吉是一位神授艺人。这类艺人通常有过奇异的生活经历,绝大多数不识字,却记忆力惊人,能够说唱《格萨尔王》一二十部,如同“神授”。
学校要用摄像机记录斯塔多吉说唱《格萨尔王》的情景。斯塔多吉穿上繁复的服饰,双目微闭,进入状态后立即变了一个人,犹如被沧桑老练的说唱艺人附体,富有节奏地快速念诵着:
湖似圣水,神山(桶拉)开火花上面的宝座上似有格萨尔,罗布占堆(格萨尔)邀各地神仙,灭除妖魔鬼怪,为失去的妖魔祈福,为了更好的来世。

甘孜巴塘,一对恋爱的年轻人
《格萨尔王》,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青藏高原的多个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唱了千年,仅韵文就超过100万行。它讲述都是生灵涂炭之时,格萨尔王下界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的故事。
人只是自然中的一环
高原环境的严苛,令摄制组初到高原的兴奋很快被冲散。除了极地美景,这里更多是荒凉的无人区,崎岖的山路,无数次塌方泥石流。
摄影孙少光曾经在藏区呆过2年,但此行依然备受考验,“我经历中,没有比这次更艰苦的”。他说,这里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60%,相当于背着一袋40到60斤的大米行走,并且需要经常这样徒步穿过五六公里的结冰湖面。
高原上的意外,常常令创作人员们感到无力。多部航拍器失灵报废,电池使用时间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一,汽油烧得特别快。
“这就是高原,你必须得清楚地认识到人在自然的面前是非常渺小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当作自然中的一环。”曾海若说。
压力之下,摄制组首次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湖泊冰潜拍摄,首次在雅鲁藏布江岸200米悬崖悬空拍摄,首次高清记录羌塘无人区的动物生态链,积攒了超过1000多个小时的4K超高清素材。
当地人常常安慰他,没必要着急,其实什么都会拍到的。这种不着急的性格给曾海若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我在这里呆了一年多,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着急。除非亲人或羊群有危险时,否则他们都非常平和,生活节奏也非常慢。每天早上起来,慢慢地喝喝酥油茶,吃吃糌粑,然后去干活。”曾海若说。
他认为,这当然和信仰有关,也和农业生产方式有关,但最重要一点,是对利益的权衡。
“我们为什么总那么着急,容易紧张,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时刻在计较,例如我会不会就比别人差一点,少拿一些钱,总是处在一个自我评判和自我要求之中。看起来是一个特别上进的人,但也恰恰因此情绪变得糟糕,不耐烦,对大自然,对身边的亲人的关怀,那些比较细腻的感情就没有了,或淡漠了。”曾海若说,“这里的人们当然不是什么都好,但这点比我们做得好得多。”
他说,这一年多的拍摄,让他见到了熟悉又很永恒的一些东西,也对生活和工作有了一种新的视角,“不要那么紧,松弛一点。”
“拍过10多年的纪录片,见过各种各样的人,西藏让我觉得最舒服。这里的人们对我们、对摄像机抱着极大的宽容态度,他们无视我们的存在,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孙少光说。
《第三极》是曾海若“青藏高原三部曲”的第一部,未来两部将把重点放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
“不管是人对动物,还是对河流山川,母亲对孩子,邻居对邻居,都有一种很尊重的感觉,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人与自然、人与人平等的感觉,就是我想传达的。”曾海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