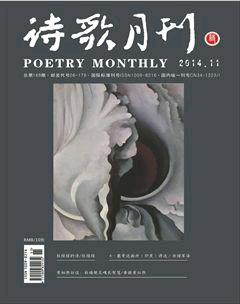夜的风景线(组章)
夜的风景线
黑色,加重了夜的深沉,我轻轻扶起你的影子,在月光下踯躅。
千万次的承诺,似乎成了荒置多年的一片废墟。季节在无声中泅渡了年龄,而流逝,却永恒不变。留给你的,或辉煌,或惨淡。
这注定是一个寂然无助的时刻。
我们把心事都交给黑夜吧。任凭泪水都滴在花瓣上,看着它一天一天消瘦。
轻风浮云,荒原阡陌。夜空仍是昨天一般高远。经年不变的顽石,习惯于选择自己的色彩。
不再转身看清泪滴落,不再回首看你,看你被泪痕冲刷的容颜和蹒跚而来的眷恋。
从此,再也走不出潇洒的步伐,也不愿日渐佝偻的背影摄进你的眼眸。
让我挥挥手,走出梦境。
深夜蝉呜
挥手那瞬,是要告别么?
你摇曳成婷婷的凤尾竹,几乎要被风托起来,在空中,看一个人的舞蹈。夜,如此神奇,如此清醒。一个身影,终日徘徊,酝酿着,灵光四射,把最后的一丝希望,交付给蝉鸣,与黑夜对弈。
空谷寂寂。往事零星的片断在脑海中不断闪现。再来寻觅时,已不见你秀丽的身影,唯有长长的足迹与怅惆的追忆布满山中。
多少年过去,我们在熟悉的歌谣中长大,变老。如今,在这飘流的余韵里,颤音和回响像尘埃一样荡去,且渐渐蒙上大地的眼睫。而那多年以前的渴求,如同日日莅临的晨光,依然这般年轻。
失眠或渴望的表达
没有你的黑夜,有我蜷伏的寂寞。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走进意念的黄昏,甚至许下一句月上枝梢的诺言,我相信,到那时,会有一盏真实的灯火点亮心的幽空。
你不要延长默默的期待,只作远距离的眺望;你应朝我徐徐而来,作一缕轻风,嗅我幽幽情怀。
久别的蛙鸣,似沙漠中的一眼清泉;柔情的披纱,勾勒出黛青的山峦。风,带着喘息,听树叶喃喃私语。
呢喃是隔夜的诗句,遗忘在山之一隔,被雨声解离。
我要一遍一遍地重复着,直到将你从我的视线中移开。正如失眠者的夜晚,一遍一遍地数着,直到梦的边缘。
凝,秋的怀念
只听见一阵沙的响声,秋,就迈着碎步来了。
荒漠的原野,只剩下一棵孤独的树和树上一片孤独的叶,孤独得发不出半点声响。
遵照你的诺言,我走了一整夜的路,眼前仍是那条熟悉的古巷,依稀可见青苔,还有给我一个陌生的背影。
既然留不住秋的黄昏,只好让没有结局的秘密沉人心底,并且细细打捞,在断断续续的日子里。
沿古巷仰望黎明,成群结队的心事飘絮般乱舞。隔着枯叶一样的岁月,听那远去的雷声,然后,面对自己流泪。
秋风唱着古老的歌从身边飞速掠过,一个无法诉说的秋天在遥远的地方沉默。
临窗而望
时光在焦灼的月空中,特别漫长,就像蜿蜒曲折的山涧小路,在我等待的瞳孔里,陨落。
夕阳已经散成流动的惆怅,夜的脚步溅起我的叹息,让无尽的明天,无尽的长路,把我无尽的孤独丈量。
我已隆冬,你正春浓。
唯有早已合流的心泉,想参人大海的澎湃,昼夜淙淙,淙淙。
流逝的岁月,已把心灵絮语化作一支洒脱的过旅。惊醒睡梦沧桑的夜鸟,会不会再度重来?
记录在细密竹叶上的情愫,依旧摇曳不停。每天,如烟云一样的心绪,是溢满遥望远方的双眸。
思想瞒着记忆,让灵感悄悄地走过;思想撇开时光,让渴望静静地回忆。
探寻一段路程,在日落里吟生命不屈之诗。至此,便有一个绿色的季节,在朔风中款款而来。
有风的日子
风已无法将你挽留。
当一披秀花飘出视野,开在游子行吟的泽畔,开在伊人微茫的叹息中,仿佛冬之序曲,穿过长长的雨季,悠悠而来。
我以柔弱的目光轻抚童年的梦。就像我把自己的手轻轻举起,让阵阵山风,还有滴滴晨露随花瓣滑落。山,早已潮湿。
一枝绽放的花,穿越冬天的极限,从你深深的脚印里,破土而出,并且噙着喜悦的泪滴。
在那绿色丛林的边缘,我站立好久,为了倾听夜的钟声,我在痴情地等待。
纷纷扬扬的愁绪,如一枚清新的执着,雕塑一个个闪光的形象,在这个沉思的季节飘然。
从此,一种洁光,开始明亮着一首诗的意境。
也许有意,我把它凝成彩翅,向着北方渲泄。
居住在你的诗里
溪边嫩绿的表情,已枯黄在无可奈何的季节里。而今,对你的膜拜,必疯长成一片绿荫。
相信雨季已经远去。隐逝的群山,有风从你的双肩滑过,秋蝶飞来的时候,千年的灯火,绮丽翩翩。
此刻,亘古的乡村,在你烟萦雾绕的秋天下,云淡风轻,落寞缤纷。
风,不永远干枯。
雨,不长久冰冻。
当其最后一抹夕阳涂尽,当其最后一颗星辰隐去,当其晚秋封冻在伊水河边,那时,我正看见,一位诗人在深巷的路口张望一一
深巷没有阳光。
我木然地呆望着,空荡的是你远去的行迹。深沉的树影,倾诉着我无声的表白。
主持人语:
这一期我们选用的稿件带着某种“冒险”的尝试。这种“冒险”,当然不是指三色堇和王猛仁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保持着当下大多数读者对于散文诗的审美认知。这两位都是诗坛的实力派。三色堇已经逐渐实现了分行诗与散文诗的双翼飞翔,而王猛仁多才多艺,是当代中国散文诗界的资深作家。然而,中间代代表诗人安琪和承德诗人北野的作品究竟该如何看待确是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究竟“散文诗”作为独立体裁的边界在哪里?这本来就是困惑人们一百多年的问题。波特莱尔把《巴黎的忧郁》命名为“小散文诗”,然而,散文诗就应该是那样的吗?包括后来的鲁迅、帕斯等人的作品也存在同样的质疑。那些作品与散文、小说、独幕剧、甚至杂文、恩想随笔等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然而,同样被人们作为散文诗看待的纪伯伦、兰波、圣琼·佩斯等人的作品却不是那样写。当代的中国散文诗作品,大多数偏向于通过对分行诗节奏的改变,场景性、情节性的诗性呈现后所造成的“散文诗”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对,许多当下的分行诗也越来越“散文诗”化。也就是说,以流动性的铺展替代跳跃性的节奏,只是通过使用回车键让作品在形式上还保持着“分行”的外表,仅此而巴。在这种分行诗与散文诗的界限日益模糊的当下诗坛,像安琪和北野的作品,其作为散文诗似乎可以唤醒某种传统,丰富人们对于这种体裁的美学恩考。
一一灵焚 爱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