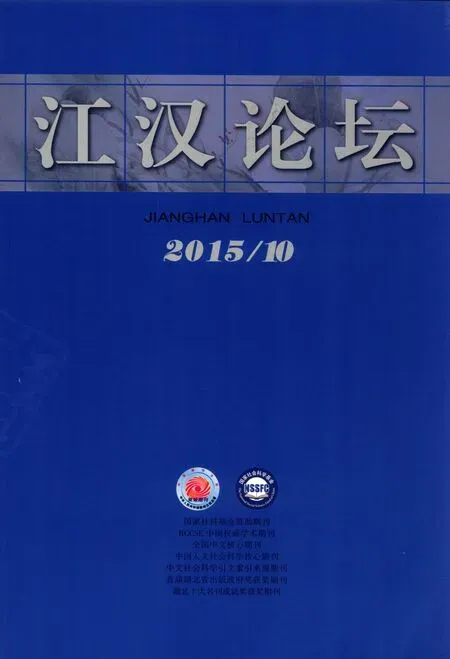论忠孝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历史演变
於可训
在近一个时期兴起的 “国学”热中,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倡言忠孝成为一时的风气,甚者希望以此重建国民道德,重整伦理秩序,使传统的忠孝观念,在现代中国发扬光大。随之而来的是,有论者认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断了忠孝伦理传统,造成了忠孝文化的断裂,因而接续这一传统,修复这种断裂,是当今道德伦理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笔者无意在此讨论忠孝观念本身的问题,只想针对这种意见,结合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对与忠孝观念有关的文学题材所作的艺术处理,和不同时期的作家对忠孝观念所持的态度,说明忠孝观念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并非一味地被批判打倒,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忠孝观念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也逐渐在向现代发生 “创造性转化”。
一
了解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五四时期,一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曾对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其中就包括作为儒家伦理文化核心的忠孝观念。这种批判的现实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日见式微的国运,和列强蚕食鲸吞、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其思想武器,则是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及于19世纪产生的诸如人文主义,和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乃至科学、进步等一些主流的思想观念。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贫穷落后、挨打受欺的根源,其近因在腐败的朝廷,其远缘是专制的制度,而这种专制的社会制度及君主的统治权力,几千年来得以维系,又有赖于儒家所提倡的“忠君”观念。这种 “忠君”观念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同样是为儒家所提倡的 “孝道”。家国一体,忠孝同源,被有的学者称为 “超稳定结构”的封建专制统治,就是建立在这种完全同质同构的忠孝文化观念之上的。这种文化观念同时也压抑了人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造就了民众的麻木与愚昧,培养的是没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奴才与顺民。以这样的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与从西方传入的启蒙文化理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和对立,必须施以批判的强力,才能为思想启蒙扫清障碍,进而使国家民族振兴图强。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所以,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的批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矛头所指,锋芒所向。无须列举更多的例证,只要看看被胡适称为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言论,就可见一斑。他说: “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彻始终而不可动摇。”①“其实他们就是利用忠孝并用、君父并尊的笼统说法,以遂他们专制的私心。君主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 “麻木不仁的礼教,数千年来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②
五四时期对儒家伦理文化这种激进的批判,得到了正在兴起之中的白话新文学的积极响应。作为现代白话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就把他的 《狂人日记》的创作题旨定位于 “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③。他稍后的作品,如 《祝福》、 《孔乙己》、《阿Q正传》等,也借助不同题材,从不同方面,暴露了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宗法制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生的压迫与毒害。受鲁迅影响,五四时期的白话新小说创作,多以对封建家庭和专制家长的反叛、抗争为题材,或以封建礼教所造成的迷信、愚昧与麻木为暴露、批判的对象。前者以 《斯人独憔悴》等 “问题小说”,和 《终身大事》等戏剧作品为代表,后者在早期 “乡土小说”中的表现最为突出。
受一种激进的文化思潮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在肯定上述创作 “反封建”价值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另一种情感走向和价值取向的创作,即那些不以家庭为人生的束缚,不以家长为专制的化身,不以宗法制家族社会为罪恶的渊薮,相反,却对之充满了留恋和温情,甚至不无歌颂和赞美的创作。这类创作在鲁迅回忆故乡的小说、散文中,就已露端倪;在冰心歌颂母爱的诗歌中,达于极致。鲁迅在 “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同时,却对宗法制乡村社会的人事充满留恋和温情;冰心在描写父子冲突的同时,却对母爱 (包括父亲和其他长者)极尽歌颂赞美之能事。前者在早期 “乡土小说”作家的 “回忆”和 “乡愁”中,有同样的表现,许钦文的 《父亲的花园》是其中的代表。后者在五四时期某些女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发扬,苏雪林的作品堪为典型。她不但不以家庭为专制的牢笼,相反,却以家庭为幸福的港湾;不但不以母命为专制的权威,相反,却以母命为温情的呵护。当这期间的诸多作家受 “娜拉主义”影响,让他们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和青年,离家出走,奔向外面的世界,苏雪林笔下的人物却认为外面的世界“是狭窄的,家庭在她却是最宽广的了”。到了废名笔下,则整个宗法制乡村社会,无异于人间乐土、世外桃源。从纯朴善良的三姑娘 (《竹林的故事》),到广施仁爱的浣衣母 (《浣衣母》),在在都是亲亲孝敬,处处尽现仁爱和平。在他笔下,不但没有家长的淫威,礼法的森严,即使是面对那些有悖礼教的行为,作者也不给家长施展威权的机会。如长篇《桥》中的小程与两个女孩子的感情,作为长辈的史家奶奶,也只看着他们任其自然地发展,并未运用长辈的权威横加干涉,如此等等,与上述创作侧重表现家庭所反映的等级秩序、家长所显示的专制权威不同,这类创作侧重表现的是家庭所反映的血缘关系、家长所显示的人伦之情,是平和、宁静、充满温情的。
五四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新旧文化观念杂糅的时代,无论是作家的人格构成,还是其文学的创作理念,都处在一种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的表现,是许多激进的反传统的作家,并不排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依然信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的传统道德观念,例如鲁迅,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孝子。他与原配朱安的关系,也表明他在不满于旧式婚姻的同时,在处理家庭问题上,依旧十分传统。胡适在婚姻问题上,也恪守孝道,不敢违抗母命,最终与江冬秀厮守一生。同样,他们的创作在激进地反传统的同时,也割不断他们与传统的天然联系,也不排斥对传统仍有所留恋和依傍。即使是就他们所持的激进的西方启蒙文化理念而言,其中既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相抵牾、相冲突的一面,因而不免要将传统文化作为批判、打倒的对象,如鲁迅所暴露的 “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与西方启蒙文化理念暗合,而需要为之张扬发挥的一面,如冰心所歌颂的母爱,苏雪林所眷恋的家庭生活,废名所向往的人情、人性和乡村社会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潮所追逐的一种理想的人性和生活状态,因而也是五四启蒙思潮在批判了旧文化之后,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忠孝观念,则其中虽有压抑人性、束缚人生的一面,但也有合乎自然、顺乎天道的一面,前者遭受激进的批判,势所必然,后者受到温情的守护,在情理之中。二者相反相成,构成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两面,都是五四启蒙思潮所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不可有所偏废。
因为忠孝观念的发生,起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它在现实中所发生的作用,也见之于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而五四时期涉及忠孝观念的文学叙事,多以家庭生活或家族社会为题材。作家对待忠孝观念的态度,也表现在其对待家庭关系或家族社会的认识和评价之上。视忠孝为 “吃人”的道德,则视礼教为 “吃人”的盛宴,家庭 (家族)为罪恶的屠场,故多反抗、逃离之声;视忠孝为血缘所系,则视礼教为人伦之常,家庭 (家族)为温柔之乡,故多依偎、留恋之情。正因为如此,考察五四时期忠孝观念在文学中的表现,宜从家庭或家族题材,和表现由此构成的宗法制乡村社会的作品入手。
二
从五四时期,到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乃至3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经历了从 “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明显标志,是影响五四新文学的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启蒙文化思潮,逐渐为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的革命文化思潮所取代。因为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一部分作家,主要是左翼作家,在坚持五四激进反传统立场的同时,又把传统文化纳入了阶级和政治的视野。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也有意无意地被作家作了政治的和阶级的区分。这种区分在创作中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五四时期批判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主要是以西方启蒙思想为武器,这期间则连创造这种武器的西方资产阶级,同时也受到了批判。 《子夜》中吴老太爷的死,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述。作为作者笔下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信奉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吴老太爷,不是死于正在中国乡村兴起的农民运动的风暴,而是死于资本主义都会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刺激。封建主义的 “僵尸”,遇到了资本主义都会的 “灯红酒绿”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香风毒雾”,就会发生风化,而作品的题旨,同时又要否定让封建主义 “僵尸”发生风化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存活的可能性,可见,这期间的左翼作家,在文化问题上是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面作战。这一象征性表述,同时也说明,在左翼作家眼里,封建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腐朽的文化,因而像吴老太爷这样怀抱 《太上感应篇》,以默念封建道德戒条,来应对儿孙以 “舞的旋风”和 “肉的盛宴”所表示的欢迎,所尽的 “孝道”,就不免滑稽可笑。他的气绝而亡,也表明,相对于五四时期受到正面攻击的封建文化的顽固和强大而言,这期间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更加不堪一击。
其二,五四时期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的批判,具体的矛头所指,主要是家长的专制和家庭的束缚,文学作品也多以此为题材。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大多为觉醒中的男女青年,或因为包办婚姻,或因为理想受阻,总之是感到情感和思想上的不自由,却较少涉及生存问题,相反,主要人物多为衣食丰足的青年知识分子。即使是标榜“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作品,如鲁迅和早期 “乡土小说”作家的某些创作,其所暴露者,也主要是民众精神的愚昧和麻木,即所谓国民的劣根性,而不是直接的生存问题。到了左翼作家笔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涉及忠孝观念的文化问题,不但有了贫富的区别,而且还被巧妙地转换成了一个现实的生存问题。以柔石的 《为奴隶的母亲》为例,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本是中国人一个极为传统的思想观念,但作品中这位贫穷的农妇,已经有了传宗接代的儿子,尽了自己应尽的孝道,但为了家人的生存,却要典出自己的身体,再去为他人传宗接代,以尽孝道,作者揭示这种野蛮的 “典妻”习俗,显然不在暴露 “礼教的弊害”或国民的麻木、愚昧,而在关切弱者的生存。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左翼作家笔下,由传统的忠孝观念所维系的道德伦理秩序,已经为社会等级和经济地位的差别所取代。忠孝观念也因此而褪去了它所特有的普遍伦理色彩,被打上了特定时期的阶级和政治的烙印。
其三,因为上述变化,在五四时期的创作,尤其是在 “问题小说”和 “女性小说”中较为流行的代际冲突和叛逆、出走的情节模式,其结构和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就代际冲突,尤其是父子冲突而言,在五四时期,为忠孝观念所维护的父亲或长者的权威,被视为专制主义的象征,而反抗这种专制权威,争取自由解放的年轻一代,无论是情感态度还是文化立场,本质上都是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伦理秩序的一种叛逆,二者之间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到了左翼作家笔下,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理念的影响,一部分左翼作家悬置了五四时期构造的代际之间的文化对立,而将这种文化观念上的对立,转换为一种实际斗争中的共生关系。叶紫的小说如《丰收》、 《火》、 《电网外》等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些作品中,代际之间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伦理关系,被作家有意无意地悬置起来,而为着生存的目的而斗争的 “伙伴”关系,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在这种 “伙伴”关系中,父辈虽然在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家庭秩序中,仍保有被 “孝敬”的尊严和地位,但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却常常因为思想保守,生性软弱,胆小怕事,忍让退缩而退居“跟从”的地位。相反,年轻的一代却以其敢拚的精神和行动的勇气, “带领”父辈进行反抗斗争,并在斗争中以事实的力量,促使父辈发生思想上的觉悟和转变。虽然在这种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激进与保守的冲突模式,但相对于五四时期而言,激进的年轻一代与保守的父辈的冲突,不是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伦理秩序的叛逆,相反,却是为维护这种伦理秩序所维系的家庭、家族和整个贫苦农民阶级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叶紫的小说中,激进的年轻一代克服父辈的 “保守”、 “忍让”,通过斗争,为包括父辈在内的家庭成员争得生存的权利,仍不失为一种 “孝悌”的表现,甚至是对父辈一种更大的 “孝敬”,因而从根本上说,无悖于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
与此相联系的是,某些左翼作家笔下所表现的“背叛”、 “出走”模式,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如殷夫在 《别了,哥哥》中说: “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主人公所背叛的并非像五四时期那样,是旧式的家庭和家长所代表的一种专制的文化观念和伦理秩序,而是他们所隶属的一个阶级。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这期间一部分左翼作家笔下,忠孝问题不但为生存问题所取代,而且出现了阶级的分野,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不但高于文化启蒙的诉求,而且为该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所左右。
与左翼作家不同,这期间有些作家仍然坚持五四时期的文化立场,在创作中继续致力于 “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如曹禺的话剧 《雷雨》、《北京人》和巴金的小说 “激流三部曲”等。但相对于五四时期纯粹批判性的表现而言,在这些作品中,与激进的文化批判相伴随的,还掺杂有一些异质的文化元素和世俗的温情,前者如 《雷雨》在暴露 “封建”家长周朴园的专制的同时,却让他为自己种下的 “罪孽”寻求宗教的 “救赎”,在控诉侍萍遭受 “始乱终弃”的 “礼教” (所谓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荼毒的同时,却让她接受宿命的安排;后者如 《家》中的觉慧从旧家出走时的留恋,和在祖父临终前所表现出的温情,包括 《北京人》中的愫方在出走前,与旧家的周旋所表现出来的宽厚与容忍等等,无疑都对这些作品激进的文化批判起了一种稀释和缓冲的作用。因而相对于五四时期持同样立场的创作来说,无疑也减弱了这些作品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的批判力度。
三
1930年代后期,全面抗战爆发,整个民族的现实生存和文化传统,同时都在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启蒙文化观念,和后来兴起的革命文化思潮,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也同时在接受检验。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在经受了五四时期的“价值重估”和激进批判、30年代的阶级区分和生存转换之后,再一次把它的价值和功用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在整个抗战期间,乃至紧接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现代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主要表现,是由五四时期 “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到这期间努力发掘乃至张扬其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挖掘其中蕴含的更深广的精神文化元素。
如前所述,儒家所构造的家国一体、忠孝同源的文化理念,既有加强专制统治,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功能,也有维护国家统一,家族 (家庭)安宁,凝聚人心人力的作用。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要反抗专制统治,破除等级秩序,争取个性解放,实现人生自由,自然要对维护这种统治秩序的忠孝观念施以批判的强力。左翼时期的革命文化要以工农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然不能把他们认定的这种腐朽的封建文化遗产,归属于革命阶级,所以要对忠孝问题加以必要的区别和转换。到了抗战时期,因为要增强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感情,动员全民抗战,凝聚民心民力,需要一种文化上的支持,以形成广泛的精神感召力,忠孝观念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文化资源,正应了这种需要,同时也为这个血与火的时代所激活,重新显示了它特有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是忠的观念凸现于历史的前台,忠于国家民族,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理念和主流意识。忠的观念发生质的蜕变,并非始于抗战期间,而是近代民族危机和民主革命。民族危机促成了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民主革命废除了专制君主,传统的 “忠君”观念失去了具体的对象,忠的观念于是发生了一种对象性的转移,由自认代表天下国家 (“朕即天下”, “朕即国家”),视天下国家为一家一姓之私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王,转移到了君王所 “拥有”和 “代表”的国家民族本身。这种思想也培养了近代的爱国观念,使爱国主义成了近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五四以后,在郭沫若、闻一多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以及早期普罗作家和某些左翼作家的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的观念,更成了一种普遍的民族意识。忠诚和背叛、爱国和卖国,不但是现实的人格试金石,也是检验文学人物的人格标尺。郭沫若的话剧 《屈原》虽然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但突出歌颂屈原的爱国和忠诚,反对南后的卖国投降,却集中体现了这期间民众和文学的一种共同的心理诉求,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这期间题材最为集中的直接反映抗战活动的作品中,无论何种派别的作家,也无论何种文体,一无例外地都把歌颂精忠报国、英勇杀敌的抗日英雄作为首要之务和鲜明主题,即使涉及党派问题和政治倾向,也不舍忠于国家民族的大义,认同守土抗战、保家卫国的宏旨,对汉奸走狗的卖国行径,皆敌忾同仇。这样的创作题旨,到滥觞于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蔚为大观的抗日英雄传奇,都有较集中的表现,如 《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 《铁道游击队》、 《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 《苦菜花》等。这类 “新”英雄传奇有一个突出特点,是善于利用和转化 “旧”英雄传奇的文化资源,尤其是 “旧”英雄传奇普遍张扬的家国意识和忠义观念,更是这类 “新”英雄传奇培养爱国感情、高扬民族意识的精神资源,其中“新”英雄人物的成长,也往往是沿着从报家仇到雪国恨的路线逐步上升,直至最终获得确定的民族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受特定时期的政治影响,这类英雄传奇同时也培养了另一种忠诚意识,即对组织和领袖的忠诚,这种忠诚意识在同时或稍后兴起的革命英雄传奇中,发生了一种本质性的蜕变,由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观念,蜕变为一种狭隘的政治伦理,这种政治伦理成了后来兴起的 “造神”运动的文化基础,对当代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家庭 (家族)伦理的价值得到了正面的阐发,家庭 (家族)由禁锢人生、压抑人性的专制牢笼,成了砥砺人格、凝聚人心、抵御外侮、共度时艰的坚强堡垒。老舍的《四世同堂》是这方面的代表。与同样可以称为“四世同堂”的 “激流三部曲”中的 《家》比较,巴金着重表现的是家长的专制和礼法的约束,阐发的是家的 “负面”的文化价值,即为五四从西方引进的启蒙思想所批判和否定的那一部分价值属性。但在老舍的 《四世同堂》中,家长却一改五四以来的形象,从他笔下的这个大家庭 (家族)中,不但看不到家长的专制和礼法的威严,相反,却充满了一派宽容祥和的气氛。像祁老人这样的家长,不是靠专制和礼法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威信,而是靠他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家道德信条所建立起来的德行和人品。同样,儿孙对他的服从和尊重,也不完全是出于礼教的规约,还有他的德行和人格的感召。正是祁老人所恪守的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精神的感召,凝聚了众多家庭 (家族)成员的向心力,才使得这个 “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家族)得以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不失操守,不堕人格,患难与共,唇齿相依,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难时世,保持了应有的民族尊严和气节。从这个意义上说, 《四世同堂》改写了五四以降 “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批判历史,使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的积极价值,得到了正面的阐发,成为抗战期间民众精神伟力的深厚蕴藏。
此外,是由五四时期偏重对家族伦理的文化批判,到这期间突出家族精神的影响和传承,扩展了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的观照视野。端木蕻良的 《科尔沁旗草原》和路翎的 《财主的儿女们》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两部作品分别以倒丁字形和正丁字形的结构形式,讲述了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小说的主体部分都写到了大家族的衰落,但这个衰落的大家族却无一例外地把它的精神影响,留给了它的后代子孙。无论是 《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还是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蔣纯祖,都打上了他们所在家族的精神烙印。与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批判把家庭关系简化为以忠孝问题为核心的伦理关系不同,在这些作家笔下,除了伦理关系之外,家庭关系还存在着更深层更复杂的精神结构。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和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者,丁宁和蒋纯祖从现实的文化属性上说,应该都是各自家族的叛逆者,但这种叛逆并非忠孝伦理意义上的反抗家长的专制和礼教的束缚,而是一种纯粹精神意义上的蜕变和追求,即企图从旧家的躯壳中蝉蜕而出追求精神的超脱和新生。但在这追求的过程中,旧家的阴影又像无形的鬼魅,时刻在纠缠、咬噬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永堕精神的炼狱不得超生,终致成为孤独的堂吉诃德和毕巧林式的畸零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作品无疑超越了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为反抗 “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叛逆出走的模式,把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命运,由反抗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引向更复杂深广的精神领域,为此后反映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和心路历程的文学叙事开了先河。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这期间的创作中,也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逆子形象,这种逆子形象既不是五四时期反对家长专制和家庭束缚的叛逆者,也不是上述追求精神蜕变和人生解脱的不肖子,而是传统意义上的不遵家训,违拗父命,挥霍家财,辱没家门的败家子和浮浪儿。如张天翼的 《包氏父子》中的小包、张恨水的 《现代青年》中的周计春,和巴金的 《憩园》中的杨梦痴等。对这种 “不孝子孙”的批评,本身便表明,作家对待忠孝问题的立场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化同时也表明,在经历过五四时期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的激进批判之后,作家与儒家伦理传统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向 “了解之同情”。
四
从上世纪40年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同其他 “封建思想”一起,被文学作为表现民主改革和 “反封建”斗争的批判对象。尤其是家长利用孝道和专制手段,阻挠子女追求进步和包办子女婚姻,以及乡村社会的恶霸势力利用宗法制家族制度的残余,反对新政权的民主改革,更成为文学批判的众矢之的。这类情节,在赵树理的 《小二黑结婚》中,有较集中的表现。在稍后兴起的土改小说中,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 《暴风骤雨》等,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宗法思想,进一步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土改斗争和分化瓦解革命群众的重要武器。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由此也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 “专利”,农民阶级尤其是其中最具革命性的贫下中农,不可能滋生这种思想,只会接受这种思想的残余影响。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宗法思想所作的这种阶级的定性“分析”,也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尤其是创作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占有相当份额的合作化小说,更把坚持宗法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作为阻碍合作化运动、破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危害,此后又进一步上升到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从 《创业史》到 《艳阳天》乃至《金光大道》,成为合作化小说的一条核心的主题线索。即使是像 《三里湾》、 《山乡巨变》这种侧重从家庭矛盾和民俗变动的角度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宗法制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也因为这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而趋向瓦解,乡村社会在文学中从此结束了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宗法时代,成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角逐的生活舞台。
宗法制乡村社会和家庭伦理的政治化,也改变了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传统所维系的父子(长辈和年轻一代)关系。相对于前述五四时期和左翼文学中所表现的父子关系而言,这期间的文学所表现的父子关系,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叛逆传统,但一般来说,主要限于 “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为着追求进步而背叛本阶级,与代表本阶级的父母划清界限。这种叛逆模式,在这期间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虽然在涉及出身 “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问题时,也有同样的表现,但在合作化题材和其他表现当代生活的题材中,却主要强调的是划清思想政治上的界限,而不是归属不同的阶级阵营。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承接了左翼文学的 “引领”模式,即由激进的年轻一代引领保守的老一辈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相对于左翼文学而言,这种引领不仅仅是依靠事实的力量,同时还要依靠说服教育和 “思想斗争”,激进的年轻一代对保守的老一辈的这种 “叛逆”,因而不是一种反向的激烈对抗,而是朝着同一方向的转变和提升。在 《创业史》中,梁生宝引领梁三老汉走合作化道路,就是典型的一例。经过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 “文革”期间的文学中,革命阵营内父子之间的忠孝伦理关系,就被新旧思想斗争,和进步与保守或先进与落后的政治等级关系所取代,父子之间虽然依旧保持固有的血缘联系和亲情关系,但同时也成了不同阶级和不同路线在思想意识方面的代表。
“文革”结束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首先把文学引向对 “文革”中流行一时的 “三忠于”、“四无限”所造成的 “个人崇拜”的反思。以 “天安门诗歌”为发端的新时期文学,开启了反对专制与迷信,提倡法治与民主的 “新启蒙”。这种 “新启蒙”接续了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传统,但重点却不是 “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是变相的 “忠君”观念所造成的现代迷信。由于 “人”从专制和迷信中获得了解放,因而人道主义和人情、人性的合法地位,得以在文学中重新确立。普遍人伦关系逐步取代政治和阶级关系,在文学中得到恢复和重建。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忠孝伦理仍被归属于旧的封建文化范畴,但在对 “文革”伤痕的揭露和政治历史的反思中,人与人之间特殊的政治关系和 “阶级感情”,实际上已逐渐在向普遍的人伦关系和血缘亲情回归。如 《伤痕》中王晓华最后的悔恨,就是由 “阶级感情”回归血缘亲情的表现,其中无疑也包含有从政治伦理回归忠孝伦理的成分。
同样是追溯历史文化之源,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 “寻根文学”,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的态度,与上述反思文学完全不同,如王安忆的 《小鲍庄》。在作家笔下,小鲍庄人在 “文革”的政治风浪中,仍然能够保持固有的平和与宁静,不是靠别的东西,而是靠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亲亲孝敬,以及建立在这种人伦关系之上的 “仁义”二字,尤其是舍己为人的少年英雄捞渣,更是 “仁义”的楷模和典型。捞渣的 “仁义”不是抽象的 “爱人”,而是建立在孝悌亲敬之类的日常情感基础上的高尚的伦理精神。作者褒扬这种“仁义”之风,认同这种 “仁义”的典型,意在表明,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仍然可以成为日常生活一种精神支撑,仍有其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王安忆在 《小鲍庄》中,褒扬了小鲍庄人的 “仁义”,那么,同样可视作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莫言在 《红高粱》中,则突出了民间抗日英雄的 “忠义”。余占鳌式的抗日,虽然是一种自发的反抗,但作家着力表现的,正是这种自发的反抗所传承的古之英雄义士的“忠义”精神。这种 “忠义”精神在古代虽然染上了 “忠君”色彩,但通过近现代民主革命和民族战争的淬炼,已成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表征。余占鳌式的抗日,就是这种建立在古之家国一体,全孝尽忠 (作为普通百姓,在毁我家园的日本强盗面前,奋起反抗,不辱没祖宗先人,是谓 “全孝”,作为中华民族子孙,在占我河山的外国侵略者面前,冒死对敌,是谓 “尽忠”)的观念上的现代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的表现。凡此种种,上述 “寻根文学”的这种创作题旨,同时也表明,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特殊的生活情境中,也可以向现代发生 “创造性转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为抵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化现实,致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建,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同其他中外人文思想一起,再度成为文学创作的文化资源。就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论,大抵有两条追求的路线。一条是以陈忠实的 《白鹿原》为代表,对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的历史审视,一条是以张炜的 《家族》为代表,对从儒家伦理文化中蜕变出来的忠诚意识的历史还原。就前一条路线而言,陈忠实对儒家伦理文化的审视,一反五四启蒙思潮的思维路线,不是首先确立一个启蒙思想的西方标准,而后对儒家伦理文化传统进行 “价值重估”,而是把儒家伦理文化传统,置放在一部“翻鏊子”式的动荡不安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之中,让它经历磨难,接受检验,而后考量其意义和价值。虽然就个体的命运而言,不免于许多悲剧性的因素,但在国家动荡、民族危难之际,白鹿两家儿女或投身革命,或抗日救亡,为国家民族,竭尽其忠,如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等;或在人性迷失、人生颠踬,沦为浪子之后,仍不忘回头,复归孝道,学为好人,如黑娃、白孝文,更不用说鹿三对白嘉轩的耿耿忠心,包括朱先生发表请缨抗日宣言,白嘉轩为传宗接代,延续香火, “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等等,都不失忠孝二字,而这一切,又都与朱先生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乡民,白嘉轩力践躬行儒家的忠孝节义有关,都是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规约和影响的结果。就后一条路线而言,张炜的 《家族》等作品,几乎完整地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理想的精神历程。如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这种追求是以对理想的忠诚为前提的,但却不附带古之 “忠君”意识,也剥离了现代变相的忠君观念,而将这种忠诚,还原为儒家知识分子为追求理想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精神。宁珂和曲予就是这样的典型。联系前述近代以来,忠的观念由 “忠君”向忠于国家民族的转换,可见包含在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中的 “忠”,是存在着多种转换的可能性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多样形式的转换,以忠孝观念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才有可能成为当今社会文明建设取用不竭的精神资源。
注释:
① 吴虞: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② 吴虞: 《说孝》, 《星期日》1920年1月1日。
③ 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