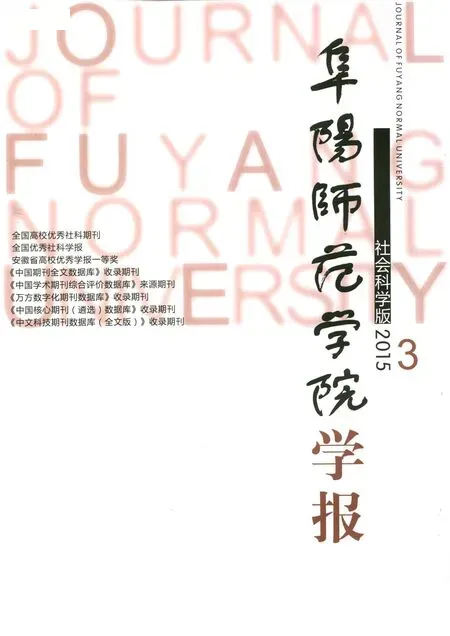“风人深致”与清人所至
——从《人间词话》看作为自觉转型期士人的深与不深
张兆勇,方 霞
(淮北师范大学a.文学院;b.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风人深致”与清人所至
——从《人间词话》看作为自觉转型期士人的深与不深
张兆勇a,方 霞b
(淮北师范大学a.文学院;b.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人间词话》作为以词话论词的殿军之作,诞生在清末国门被打开士人普遍以西土为先进的所谓心态转型时期,王国维以倡“风人深致”显其高端;以“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显其逻辑思路的清晰;以“境界”显其理论的谨严。然把这些理论置于唐五代宋词背景上反观其理论,能发现静安有“真”“深”的理论成就,更有真亦不真、深亦不深可加以追寻的诸漏隐匿,读《人间词话》者对此若心知肚明,也许更有滋味。
入乎;出乎;境界;情景;风人深致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字静安,近现代之交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一般认为他是从1901年起研究哲学与美学的,在这方面成就主要有:1904年著《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1905年著《论哲学家及美术家天职》、1910年撰《人间词话》[1]、1912年完成《宋元戏曲史》,此后转入史学与古文字学。1927年阴历五月自沉昆明湖,其遗嘱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要是研究其他学人也许不必这样追述其生平次第,但王国维必须例外。一在于王国维可算是最后的清儒,二在于王国维是研究美学的。在笔者看来王国维的自沉不仅是个人行为,他的死可以看成一代人所追求的人文理想的湮灭,亦可以看成是一代清儒最终转到了他们的死胡同。诚然,王国维倡导“风人深致”,然我们不禁要问王国维对之究竟体之多少。
王国维美学著作代表作无疑是《人间词话》,虽从总的内容上看《人间词话》是承传常州派论词的,但由于王国维引进西方学者的思路,故该书又可以看成是他试图以新思路而对常州派乃至清初以来各家论词的总结与反思,《人间词话》可以视为其人生感悟聚焦于以词为平台而对人生发掘整理的结晶。
流传至今的《人间词话》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齐鲁书社版滕咸惠注本是文革后较早的版本,也是较权威的版本,注者在其卷上收录《人间词话》稿126条,据滕咸惠讲这其中包括比王静安手定稿多出的十三条删稿。卷下收录《人间词话附录》稿28条。另外,王国维的《文学小言》亦是以词话的形式收在文本里,笔者是和《人间词话》联读的。所谓删稿者与其说是写作意义的修改,毋宁说是他内心世界的不稳定、不自信。
《人间词话》的逻辑思路很清楚:
一、“真”“深”标准与“出”“入”格调。
王国维认为一个好诗人、一首好作品其意义在于“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对此,王国维首先是从“入乎”“出乎”来展开思路的。其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100由此可见在王国维眼里诗人能以“入乎”而真且其风范如此,又能以“出乎”而深,其意义亦在于此。一个诗人若能如此,王国维称其有“风人深致”。
因为五代两宋词贯穿着道学的历程,若从道学的视域看(1),此命题意义在于,所谓“入乎”和“出乎”给人感觉在于能联系起来指涉性命在宇宙范围内的创造施展,换言之,表面上看王国维在这里是将宇宙、人生,诗内、诗外一滚重叠于一起讨论,主体化起来,眼界很扩大。只是可惜得很,由于王国维并没有真正将命题融入宋学再充实,所以其内涵显得飘忽。换言之,王国维虽有意追求厚实但没厚实起来。比如对于一个具体的诗人,若实现“入乎”和“出乎”,王国维认为其要经历三种境界,可以说此三种境界将“入乎”“出乎”做了更细致的分化。此三个境界分别是这样的,其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惘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1]5
在王国维看来“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2)。而所谓有人格者就在于他们人格之中包融有此三个境界沉厚之印迹。他们的诗文则是“入乎”“出乎”的真实体现。王国维论述到这里本来是很有气魄的,只是他用“意境”转语,再用他的“真”“深”思维充实之,于是,境界越来越空洞,气象越来越萎缩了。
其次,在王国维看来,所谓能以高尚伟大人格铺垫的伟大之文学者即是那些文学家能“出乎”与“入乎”,而若换一个角度看即在于这些文学家能从“出”“入”深刻地调动着“意”与“境”者。其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
这里所谓“意与境浑”即是所谓的“有意境”,如果说境界是他从主体意义上所呵护的核心,那么意境之说则又是境界反照下他对词研究展开的核心,这本来逻辑亦清晰谨严。只是可惜在于境界仅是在广泛借鉴西洋哲学所建立的人格论而汇总的,及于论词虽一变而为意境,但对于唐五代宋词来说显然失真值得加以推敲。换言之,他关于词的意境说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这就要我们读《人间词话》时需要从真与不真、深与不深加以辨析开始。本着此思路先看什么叫有意境,王国维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3)17(《人间词话》第2条 原稿26条此所谓意境)。
这里有几层涵义:
①在情景关系上,讲究以不隔转动真性;对情景描述讲究语语都在目前,据此王国维还批评了清真的那种如“隔雾看花”,以为其病在于失真。显然王国维这是在强调“真”。
②在涵容上又以境界大小指证其“深”。其云:“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推测一下可能在王国维看来,高下之分在于境界所涵容气象是否精纯。可惜由于没有道学内涵,故显得飘忽。比如他已在此将大小与高下含混了。
③艺术效果上就是有意境。王国维用体现在词作或词人的创作中的“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来指证意境的落实。到此我们除了要感动于他所做的细致,还应当为之惋惜,惋惜的是所谓“真”“深”者其内涵在这里显示其苍白,此也许是对于王氏“意境说”追问的应有姿态。
二、“真”“深”的还原思路与还原力度
王国维曾推举一些作家来指证他所标举的“真”性。总结起来观点有这么几个方面:(1)真性情,(2)少阅世,(3)没被染污。今天看起来王国维在此确实发掘出“真”所以能助人直达人生之性情特质的隐秘,只是实在值得推敲什么是他所谓的“真”,一个词人如何才能保持其真。在此最著名的是两则对后主的定语,如:“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1]94“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1]94由此可见他的真性情无疑是显得浮泛,脱离背景,且渐与自己实际要表达的意念相错忤。以至于《人间词话》给后人留下纳兰词高出一代宋词的公案(4)。
与真的标举相对应,王国维无疑也强调深,在笔者看来,理解王国维所标举的深主要把握两点:(1)深于何处;(2)从宏大的中华文化背景来说王国维之所论深为什么不深。以此两点几乎可以梳理王国维的贡献与缺点。
首先,“深”于何处,或换言之,即静安之深深否?在我们看来,在王国维之前,阳羡以豪放标举南宋辛张,浙西推崇醇雅标举双白,常州派比兴深美闳约标举飞卿,仅云间标举南唐,这些词评家或理论不系统,或力弱不符。与他们相比,王国维能动地继承了介存斋、冯煦、刘熙载走出一条标举南唐君臣、联络北宋、刻意区分南北宋差异的追寻之路。在此王国维的创造性尤在于以乐工之词士大夫之词将词按照他的思路安排于几个序列,要说深,深在于此。即是说他的深在于以标举南唐强调真,只是真者不真。是因为王国维并没能将自己的思路或者将自己借评词寄托的理想与五代、北宋、宋初至有宋一代的社会思潮相对应,因而还原不了历史,此即所谓苍白者。可悲在于王国维自己似亦没注意于此,可以说他所强调的境界说是抛空掏出的,因此是缺乏历史感的泛论。
例如,王国维特别重视所营造的境界说在小到一首诗词,大到《红楼梦》等作品中的意义。
其云:“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二者随之也。”[1]46“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1]33王国维论词的一切思路均围绕境界的营造而拓展,比如:在造境的方法上,他将意境分成造境与写境;以造境的方法,他又把诗人分成客观诗人与主观诗人。从造境的方法,他又把境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认为虽为意境但是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物皆著我的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1]3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虽对意境作了如此细致的划分,但他并不有所偏执,比如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境、写境,甚或有句无篇、有篇无句,虽做了区分,但无所偏执。即并不如同自张綖以来的以婉约豪放论词思路那样,而是尽可能找它们的共同点,王国维所找的共同点即是真之与深。他认为真、深是一首词无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共同拥有的,这是不能区分高下的原因,只不过对“深”来说“真”乃第一关键,对真来说深则是必须要在意的事实。
也即是说王国维虽以意境对诗人作上述划分,但并没有再以意境区分高下的偏见,因此其所强调意境者勿宁是方法气质的不同,他是将目标锁定在创造意境的另一层面上的真之与深上[1]39,特别是锁定在由真与深所创造意境的高浑和谐效应上。显然这并不符合五代两宋词变化展开的实际。王国维虽称此为气象。但境界最多是他在此意义上思维的重要环节。“境界”说在此被细化了,也被泛化、格式化了。
再比如王国维对与意境有相当关联的情景观点也吸引人,在这里,他有两个基本认识,即第一指出情感亦是人心中的境界,第二指出一切情语皆景语。对于这些今天评估之,当然可断言静安意在强调所谓情感、情景均是探讨意境、衡量意境的切实之物,但在此同样会发现,王国维关于境界的思路有灵性无神气。
其次把王国维的深放到他关于五代两宋词讨论的成果上说,究竟深否也是必须要指出的问题。
在《人间词话》中我们发现他利用境界对唐五代两宋乃至清词进行了他细密的批评实践,从而完善他的阐释学体系。
在此理论体系中最关键亦是他最推崇的词人主要有三个,即冯正中、李后主、秦少游,可以说王国维是以这几位的精神境界与词风和他的理论相对应、相诠释的。在此既可见出他理论深化、系统化,又能见出他所暴露的浅识。
对冯正中他所重点强调者是其作为士大夫的堂庑特大,也即在他看来冯正中的意义在于以自己内涵广袤、“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以为此最是“风人之致”[1]10。其第四条中王静安特别指出“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
又第六条云:“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在此点上王国维认为“中、后主皆未逮其精诣”。
若说他在这一点上的意义在于正好准确地把握了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谓“冯延已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2]107,从而呼应着刘氏之学,让世人找到清代词学学人间上下沟通的路径。比如与静安同时代的蒿庵有“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贯,短长之流别”(5),即是为读者提供的关于真深境界以至于“风人深致”的又一个解释实例与静安相呼应,但也不必讳言“北宋一代”含义是丰富的,而王静安对之实在有些含混、草率。
对后主王静安重点强调者在他以任真直达神秀,王静安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强调后主词以任真表现出对人生极处的深刻思维,这就使得“入乎”与“出乎”在后主这里变得更是具体。其次,静安是从比较的角度得出后主的这种独得。比如“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已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1]93。此所谓“神秀”由任真导致,是独得,再次,他又认为所谓神秀则在于“词至李后主而眼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1]93。以后主“神秀”而显示其深刻。又静安是从后主为人君的特别处来得其结论的,其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也”[1]94。王静安想要说的是词到李后主有一次异乎深刻的跨越,如果说“境界”是他理论的核心,那么以士大夫词对后主的认定才使境界与厚重的历史联系起来。如果说从开始起词人即实显赤子之心,那么王国维更看重后主的担待意识,以为这才是深。无疑王国维在后主这里又将真与深思维推进一步。只是在于他所谓的“真”“深”又显然不是越来越浓的道学氛围。
由上看来,王国维对南唐君臣词的批评的确是在遵循着他的真深思维,感悟他们的风人深致的,从常州派标举温飞卿到他终于以后主取代飞卿是他的深刻。只是与其说他是回到历史毋宁说是回到自己的理论。亦因此可以说他真者失真,深亦不深。
王国维的这种五代思维及结论也直接影响着他对北宋士大夫词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他从晏殊欧阳修到苏轼的结论也是脱离宋代历史抛空而出的。比如对苏轼品评,我们当然钦佩王国维所概述的诸如“有句有篇”“雅量高致”“词中之狂”“旷而神”等的概述,然恰在此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他对这些概念是含混不清的,其原因在于受自己标显的概念迷惑以致于遮蔽。
在宋代词人中无疑王国维最推少游,静安推少游主要是从词之特性,从词所包容性情的表现特征上来看的,其云:“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1]73我们认为静安对少游的评价应是对冯正中、李后主评价的展衍,因为标准的一致。只可惜他的理论正因这一点已更不能探测少游之深而相反暴露他自己的浅了,因为浩瀚的元祐文化已远远高过李后主的忧患。如果说到此“真”已经不一样,那么“深”有更多不同的内涵。由此可见出,从中华文化角度说王静安在此的浅,在于他没有继续将思路扎进宋学大营。
综合上面的论述看,静安于五代、北宋间,更在南北宋间以“真”“深”设置了层层界线,以此为思维铺垫,他也的确找到理由过高地抬高五代北宋,尤其所幸在于由于以营造的底蕴,故虽然他有南北宋的门户之见,有关“真”的执拗,但还是超越了张綖,也成功地传承了常州各家比如蕙风与白雨斋等,从而理论中彻底没有了婉约、豪放的相隔壁垒。换言之,王国维以他所具的优势,终于打破了明人的“正统观”、派别论等,最终归整到把词放到本然的平台。这是他的深。只是所不幸的在于,王氏此种方法其致命缺点在于,王国维和陈廷焯、况周颐一样,始终没能深入于宋学的具体背景。尽管他强调词品格、强调境界气象等,但无一例外,由于离开了宋词背景显得空洞苍白,又是其浅了。
总之,在《人间词话》中,我们除了从理论上不讳言这种没“深”,还应从词史角度上看到他实质上没有理顺正中、永叔、小晏、东坡、少游的关系;理顺美成和南宋诸家为什么不是第一流,对于这些他虽有刻意的强调,然他的说服力实质上也还是不透彻。这是因为他没有从文化背景上还原从五代到两宋词的变化背景,因此可以结论为真者纤细、深者空洞。
三、一种表达“真”“深”的特别方式评估
在文章的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王静安《人间词话》的创造性在于他往往用词人自己的名句评词人自己,亦很有见地。其深沉意蕴在于①回到以词人自己来自呈其词;②回到以其词来定格其格调;③回到试图以总感觉来导人逆推(6)。有的几乎就是该词人的定格,据此还可推论很深。试举几条看:
如第十四评梦窗以“映梦窗凌乱碧”
评玉田以“玉老田荒”
第五十七评飞卿以“画屏金鹧鸪”
评端已以“弦上黄莺语”
评冯正中以“和泪试严妆”等
甚或模仿此,我们还可以作一些类似的评语,如评苏轼以“人生有味是清欢”,评少游以“杜鹃声里斜阳暮”凡此种种。这些几乎是讨论这些词人的起讫点。且不说静安这种思路所包含的内容,这种从词人精品词中找寻词人精神的独慧与准确性,即说到这种方式,就已经具有其深刻的魅力。尽管他同时代人刘熙载的这个方式方法就很具启发性。但无疑王国维在这一点上比刘熙载做得更自觉。他几乎将其做成贯穿的系统。我们所要就此感慨的是作为一代清儒静安正在默享着传统文化的营养。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远从《周易》始即定调思维为立象尽意,此后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均以不同方式倡导“尽信书不如无书”,倡导“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目击道存”。禅宗更在意反观得意之主体、言语道断,追求以无念为宗,“说是一物即不中”。总之在大中华文化传统中,广大的士人思考世界如何往往崇信以世界自我证之、呈之。所谓“打坐之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打坐之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青原惟信语),可以说自宋代以来广大士人均是在感悟与默享这种把玩方式的乐趣。静安的思维推究起来也不例外,即在于他实质上是期待无缝地以词人自己评价自己,此无疑亦是其“深”者。
静安在这里当然也有其“浅”,在于他在找寻其词时由于受到对词人“先入为主”的“真”“深”观遮蔽。这样一来就无疑掩抑了他找寻的视线,就是说,有的不是被表达了反是被遮蔽了。
总的说来,王静安的《人间词话》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真”“深”思维框架,此框架的宏伟、系统在于静安的悟性;框架的空疏,则是静安乃至自乾嘉以来清儒之悲,它至少残留了清儒试图刨去宋学的背景来论宋词、论五代向宋词迁变等的历史进程的印迹,说明王国维没有还原道学以宋词之产生为背景来重新感悟“天人一体”的自然观念的费思、费力,暴露了王静安所谓真深者难以圆融其原因何在。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阅读《人间词话》必须要有二种心态:一者,入得进去,知道常州词派者到了王国维这里是一种什么状况。二者,出得出来,即摆脱《人间词话》的空框架从而再寻机会将宋词带回到宋词滋生自己的宋学土壤,弄明白宋人是从什么意义上利用形式上说依然是词,但士人完成的却是对词的新跨越,明白宋儒在内容上是怎样用词来铺陈对性情的探讨等凡此种种。
注释:
(1)在笔者看来,宋词穿越了宋代道学的历程,也是道学家表达自己性情的平台。此观点可参阅拙著《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
(2)选自《静安文集续编·文学小言》。转引自《晚清的最后一个文人》,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3)王静安《宋元戏曲史》云:“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
(4)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纳兰词没有受汉文化的熏染,故也没有能符合词越来越文人化所担负起的厚重人生使命意识。因为这一点纳兰词也就全面低于宋词的价值。可参见拙稿《中华文化氛围下的纳兰词试析》,《三峡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5)唐五代词选序 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6)在中华累代批评家的眼中,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始终是批评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批评目的。
[1]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
[2]刘熙载.艺概(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Refined Pleasure of Poetic Minds and the Arrival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Qing Dynasty——From the Ren Jian Ci Hua to Weigh the Profundity and Unprofundity of Intellectuals in Self-conscious Transformation Period
ZHANG Zhao-yong,FANG Xia
(a. School of Literature; b. School of Education,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Anhui 235000)
As the las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i comments,"Ren Jian Ci Hua" was bor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as so called mentality transformation period when the closed-door was opened and western learning generally was regarded as advanced by intellectuals. WANG Guo-wei advocated refined pleasure of poetic minds to show his high-end, used “See who is true, know who is also deep” to highlight his clear logical thinking and applied “Jing-Jie” to reveal the rigorousness of his theory. However, if we put these theories back to the background of Ci in Tang Dynasty,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Dynasty and reflect his the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WANG did get achievement on the theory of “True” and “Profoundity”, and had more defects and loopholes over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fact it is not true and profoundity needed to question. If the readers of "Ren Jian Ci Hua" are aware of these, perhaps they will understand more .
purifying within mentality;comprehending beyond mentality;Jing-jie;emotion with scenery;refined pleasure of poetic minds
I207.23
A
1004-4310(2015)03-0065-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3.015
2015-02-27
张兆勇(1965-),男,安徽五河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等论著,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