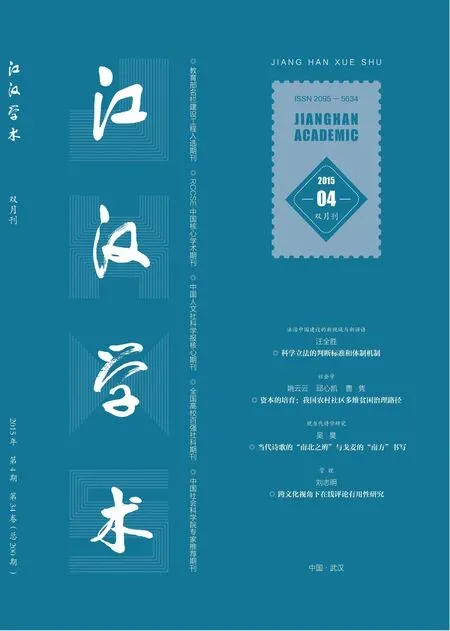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过程、困境及消解
董敬畏
(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杭州311121)
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过程、困境及消解
董敬畏
(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杭州311121)
摘要:流动人口因其自身的流动性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导致其文化认同处于错位和困顿状态。流动人口常年工作和生活于城市,但囿于种种原因无法定居和认同城市。流动人口群体的借位文化认同不仅困扰二亿六千多万流动人口,更带给未来中国发展以隐忧,让中国社会结构难以优化,社会转型潜藏不确定性风险。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错位和困境形成既有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制度的原因。要解决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困境,必须通过认同在地化方式加以解决。实现流动人口认同在地化要从三方面入手:宏观层面社会制度的在地化;中观层面城市政府和城市居民的在地化;微观层面流动人口的在地化。只有如此,中国社会秩序整合不确定性问题才能最终得以解决,中国公共性重构问题才能得以实现。
关键词: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社会转型;在地化
中图分类号:C912. 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4-0049-05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一、问题的缘起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3085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3525万人。而在这些流动人口中,外出农民工有7739万人跨省流动,8871万人省内流动,分别占外出农民工的46.6% 和53.4%。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以省内流动为主,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以跨省流动为主。[1]
当前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大潮中,这些以数字反映出来的流动人口,无论他们是基于何种原因而流动,也无论他们是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流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出现对于故乡的眷恋和对于工作地陌生感的问题,也即文化认同与否的问题。这些流动人口常年工作和生活于城市,但囿于种种原因无法定居和认同城市;他们已经不在故乡生活和工作,但现实却要求他们认同故乡,在多年的“打工”生涯后不得不返回故乡。流动人口群体这种借位的文化认同困扰着二亿六千多万流动人口。政府也认识到这一问题,提出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要解决这“三个一亿人”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流动人口错位的文化认同问题。由此,流动人口的错位文化认同便成为新型城镇化时代理论和实践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文化认同及其过程
认同或社会认同是现代社会学关键术语之一,它涉及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他首先使用自我身份(Ego Identity)对青少年心理进行研究[2]。围绕认同或社会认同,后来衍化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偏重以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解释社会行为的研究;二是偏重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意识的研究[3-4]。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首先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结合起来考察。他认为现代性不断形塑自我,反思性地投射自我,又带来自我的各种两难困境[5]。
对于当代中国流动人口的认同问题,国内学界主要从流动人口城乡分割和城市融入的视角切入
研究。这些研究或者从社会制度建构的城乡二元分割的身份出发,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进行研究,或从群体心理学角度分析农民工群体的群体认同①。尽管对于流动人口认同的研究成果众多,然而从研究视角和层次考察,众多有关流动人口认同的研究依然是一种结构、制度和宏观政策视角,微观、机制视角的研究缺乏。而且现有研究中,流动人口只是被化约为一些统计数字和被动适应和融入主体,他们如何在既有结构下,主动建构文化认同以应对结构却被忽视,由此现有研究呈现出见结构不见人,见物不见文化的特点。
学界提出的文化认同概念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研究的缺点。文化认同概念强调行动者对于人们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文化认同的主要依据是使用相同的语义符号、遵循共同的理念、持有类似的行为模式和规范[6],其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放大个体身份从而涵括一个群体,建立我群意识;二是限定与排除某种身份,树立我群与他群的分界标识[7]。尽管有所弥补,然而已有研究多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民族、族群的文化认同,对于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研究却几近于无。
在笔者看来,文化认同与其他类型的认同共同源于英文的Identity。查阅英汉词典发现,认同内涵包括以下三重:一是使等同于、认为……一致;二是同一性、一致;三是身分、正身、本体、个性、特性。从其内涵考察,认同是一种动态建构而非静态过程,是一种个体在具体文化场域中实践的结果。这种实践是在个体与外界客观和主观条件互动的背景下发生的,个体的文化认同也产生在这种背景中。个体从一种文化场域中到达另外一种文化场域中,通过逐渐改变自身原有的文化特征,消除与流入地文化场域的差异,从而最终实现一致和同一。这是文化认同的过程。
文化认同也呈现三个过程和特征:文化震惊—文化类化—文化认同或涵化。首先,从一个文化场域到另外一个文化场域,流动人口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适,这是文化震惊的阶段。中国作为具有高度复杂文明的社会,其地域文化各有特点,这种各有特点却又和而不同的文化认同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格局。各个文化地域的民众既对自己所处地域文化产生认同,也对国家层面的文化有一致认同,这是古代中国的天下文化观,它是一种同心圆式的文化认同格局。这种同心圆式的文化认同能够求同存异,共同生存和发展。②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虽然几经变迁,依然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天下文化观的特征。其次,在经历了文化震惊阶段之后,文化类化阶段开始出现。即以同一种地域文化为中介,习得这种文化的个体总能够聚集在一起,形成某种社会组织,即某些学者所谓的我群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根据某些标准,将自身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进而形成“异—己”的群体划分。无论是历史上各地的会馆还是现代的同乡组织,都是文化类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类化阶段可能与认同或涵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会融入个体所处的地域文化之中,成为地域文化大圆包涵的小圆。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化认同或涵化。作为流动的个体与流入地群体接触,总是流入地群体的地域文化居于支配或主导地位,流动个体的文化处于从属地位,从而出现流动的个体被流入地群体的地域文化涵化或流动的个体主动接受流入地文化,融入当地。流动人口融入当地之后,故乡原有文化形态的烙印逐步消除,而流入地文化形态的印迹逐步加强。
三、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特征与困境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认同总是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联系。在流动人口未流动之前,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流出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相一致,他们的地方文化认同是稳定的。然而,流动人口因为各种原因流动到异地,他们实际上处于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从稳定到剧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前述文化认同的三个过程开始发挥作用。作为认同主体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处于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撕裂”、“文化震惊”状态。这种文化震惊和撕裂状态我们可以透过个案访谈材料加以证实。
案例一:文化撕裂和震惊的王JH。
王JH,河南平顶山人,在H市某足浴馆做足浴师,2012年经初中同学介绍到H市学习三个月足浴技术,后在H市足浴行业就职,直到今天。
(问:您对这里还习惯吧?)
不是特别习惯,这里的气候、风俗习惯和河南完全不一样。河南人吃面,这里人吃米。这里的人特别精明,很会做生意,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钻。相比之下,我们河南人就差很多。太老实,只会给人打工。我一直想着在这里赚点钱,回河南老家去,这里的人情风俗与我们那里差太远。
(问:那您在这里呆了多久了?您喜欢这里吗?)
我从2012年到这里,到现在已经两年了。说实话,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只是单纯为了生存,为了赚钱。河南老家没钱赚,这里经济发达一点,能赚到钱。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喜欢河南。但为了赚钱和生存,我不得不适应这里。不过我肯定不会在这里呆太久的。③
王JH在H市工作和生活了两年,然而依然无法认同H市。根据他的说法,他还是喜欢河南,H市的风俗习惯与老家差别太大,他不习惯。只是为了生存,他才勉强适应H市。王JH的个案可以证实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撕裂和震惊阶段的存在。其实不仅是王JH,所有的流动人口在流动初期都会经历这一阶段。
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的逐渐稳定,他们开始试图寻找某种自己能够信赖的组织,而现阶段,血缘和地缘组织是他们最为依赖的,他们通过血缘与地缘方式结群应对各种问题,这是文化认同的第二个阶段。
个案二:李M,湖北襄阳人,2005年就到H市,至今已有9年。在H市先后从事过多个行业的工作,现在H市一间连锁茶馆做前台经理。
(问:您怎么会到H市来的?)
我老家是襄阳,襄阳地处湖北和河南交界。那里农村教育质量不高,我高一读了半年,觉得还不如出来见见世面。恰好我们村里有个人在H市,我就跟他一起来了。来了之后最初是在一家民营企业打工,一年之后觉得没前途,辞职了。后来换来换去,才走到今天这步。外地人在这里混出个名堂,真是不容易。
(问:那您见了世面了吗?)
当然了,这里还是比老家繁荣,比老家发达。在茶馆工作,自由度比工厂什么的大一些。我利用空闲时间,跑了周边很多地方。我眼界什么的开阔了不少,不再是以前的见识了。
(问:您平常都和谁一起玩?在这里朋友多不多?遇到事情找谁帮忙呢?)
我平常多和湖北、河南的老乡一起的。因为我们那里刚好是湖北、河南的交界,我湖北话和河南话都会说,因此我在这里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插问:本地朋友多吗?)本地朋友吗,呆了这么多年了,好歹有几个。遇到事情时还是湖北、河南的朋友帮忙多。我参加了两个QQ群,一个是湖北人在H市,一个是河南人在H市,我有事情求助就在群里发帖,就会有热心的老乡帮忙的。每年这两个地方的老乡在H市的聚会,我也都参加的。
(问:那您的日常交往还是以老乡为主了?)
是的,风俗习惯什么的比较一致,不会犯忌。这里可不行,风俗习惯不懂的话很容易犯忌的。
从李M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尽管在H市已经居住了长达9年,然而他的日常交往还是以同乡为主,H市的朋友也有,但在李M的日常生活中并未占据主要地位。李M也知道了H市文化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忌讳,也与当地人开始交往,这说明他已经开始逐步适应当地文化,开始融入当地文化。与同乡交往既是惯性,更是方便求助。
个案三:徐M,安徽大别山人,在H市生活已经17年,现担任某社会公益组织负责人,很少回老家,小孩在H市出生和成长。
(问:您喜欢这里吗?)
最初来这里是因为家里穷,想外出赚钱养家。后来在这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结婚生子都在这里,工作生活也在这里,因此慢慢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太愿意再回老家了。
(问:现在您的本地朋友多吗?)
多的,我自己从事公益组织交往的一些本地朋友,孩子交往的本地家长等,有很多。
(问:你现在遇到问题谁会帮忙多一些?)
我基本上找本地朋友帮忙的,他们关系多,人缘广。甚至一些同乡有时也通过我帮他们办事。
(问:您现在还经常回老家吗?)
很少回了。小孩在这里出生和成长,他的朋友同学都在这里,回去已经很不适应了。我回去也有点不适应了。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了,我已经把家安在这里了。
(问:那您在这里买房了吗?)
这里的房价这么高,我的打工工资哪能买得起?我现在租住在城中村里,慢慢熬吧,总有办法的。
徐M已经开始逐步融入到当地,他的朋友圈开始以当地人为主,孩子已经和当地的孩子没有差别,这是文化认同的第三个阶段。在笔者访谈的其他个案材料中,甚至有流动人口将老家的父母接过来与自己在流入地一同居住,这种举家迁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上述个案大略显示了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通过这三个个案我们可以回答当代有关认同的一些问题,即认同是由外界环境影响和塑造的,文化和社会是影响认同形成的主要因素,认同既是差异也是一致,不经过差异就无法达到一致。
然而,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也存在现实困境。在全球化和资本追逐利润逻辑的影响下,在社会的
制度限制中,流动人口无法形成整体的群体意识和阶层意识,反而表现出一种个体化状态[8]。个体化的流动人口很难应对强势资本家对他们的盘剥、应对流入地政府和居民对他们的政策性歧视和社会歧视等。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制度设置导致作为认同主体的流动人口与作为认同客体的城市及城市居民之间产生了巨大差异,乡村与城市不是作为一种职业区分,而是作为一种身份区别在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差异化的认同。这种身份区别带给外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异化认同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仅在社会方面产生距离,在心理方面也产生了距离。这种差异化的认同还不断通过社会制度进行固化。这种固化使得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过程难以为继。
尽管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工作与生活,作为认同主体的流动人口与认同客体之间社会和心理距离会缩短,但现行条件下并未消除。尽管流动人口为流入地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依然视流动人口为他者,作为他者的流动人口依然很难得到与流入地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久而久之,流动人口群体的被歧视和被污名化成为他者的典型表征,同时也是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地方政府之间矛盾与冲突激化的表征。长此以往,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消除、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都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导致流动人口认同困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在于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政府把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化约为市民权,造成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普遍认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城市居民的关系是利益博弈和竞争的关系。这是限制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和认同形成的外在制度原因[9]。二是流动人口与农村的客观联系在减少,重新回到农村的主观意愿在降低。尽管与农村产生脱离,但在城市他们的市民权和公民权又囿于外在制度原因,无法在流入地城市落地生根,进而在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完全消弥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差异。正是上述两种原因导致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出现了困境。
四、在地化:流动人口文化认同困境的消解
当前,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工作日益稳定,收入持续增加,家庭化的迁移趋势日益增强[1]。基于此,流动人口迁居城市的意愿十分强烈,这种强烈迁居城市的意愿既是流动人口文化认同形成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公共性重构和重新形成的契机。通过流动人口的城市迁居,我们不仅短期能够逐步消除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长期还可以实现公民意识的提升、公民权的实现、中国社会公共性的重建等目标。在笔者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在地化不可避免。
在地化一词用来描述流动人口实现文化认同的过程。在地化过程本质也是实现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认同主体的流动人口通过在地化过程,跨越文化撕裂和震惊阶段,实现类化和文化认同。与此同时,作为认同客体的城市政府、居民和整体社会制度主动消除流动人口在地化的各种制度障碍,实现认同主体与客体的良性互动。只有通过认同主体与认同客体的良性互动,文化偏见和差异才能首先得到承认,在承认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差异,最终达到同一。真正实现认同,当前迫切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首先,宏观层面社会制度的在地化。一是在国家层面还权与民,把属于流动人口的公民权还给流动人口,通过制度赋权实现流动人口在地化;二是探讨流动人口流出地与居住地之间的财税结算政策,从而为流动人口在居住地享受同等待遇奠定经济基础;三是消除涉及流动人口的各项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为认同主体与客体差异的消除奠定法律和政策基础。
其次,中观层面城市政府和城市居民的在地化。一是城市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将流动人口纳入到本地财政公共服务的预算项目之内,从财税层面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比如为流动人口提供公租房和廉租房,让他们能够安居。甚至可以为他们购买流入地城市的商品房提供便利。城市政府还要为流动人口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创造条件和机会,推动他们对于流入地的文化认同。如果能赋予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举权当然更好。二是城市政府和居民要认识到流动人口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他们独特的贡献,不再将其视为地方利益的竞争者和蛋糕的分割者。如果没有流动人口,当前许多城市的蛋糕未必能做得这么大。三是城市各种媒体不再污名化流动人口,反而要多宣扬流动人口也是城市劳动者,他们也为流入地城市做出巨大贡
献,在社会氛围层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上述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在地化是消除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外界障碍和客观限制因素,而最为根本的是微观层面流动人口的在地化。一是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消除异乡心理,把流入地城市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对流入地城市产生文化认同和融入的动力。二是流动人口主动参与流入地的公共活动,努力与流入地居民增加互动和交往,消除异乡感和孤独感,从而消除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差异,最终实现同一即文化认同。
注释:
①国内相关研究中的代表性作品可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整合》,《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3期;张莹瑞,等:《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郭星华,等:《社会认同的内在二维图式》,《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张广利,等:《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范式的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邓巧:《白领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邹美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②相关论述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0页;王铭铭.《作为世界图式的天下》,赵汀阳编:《年度学术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社会》,2010年第5期.
③楷体部分均为笔者在H市的访谈资料,根据学术规范,地名与人名均做了处理。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R/OL]. (2014-05-12)[2015-02-10]. http://www.stats.gov.cn/tjsj/ 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 html.
[2]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1.
[3]Michael A Hogg,Deborah J Terry,Katherine M. White,“A Tale of Two Theories: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5,58(4):255-269.
[4]Tajfel H,Turner J.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M]// S Worchel,W Austin.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apter 1- 3. London:Academic Press,1978.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5-8.
[6]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4).
[7]张淑华,等.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 (5).
[8]董敬畏.个体化:新生代流动人口新趋势[J]浙江学刊,2014(4).
[9]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 126. com)
作者简介:董敬畏,男,陕西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浙江行政学院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流动人口网络社区的文化认同研究”(13CSH060)
收稿日期:2015 - 04 - 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