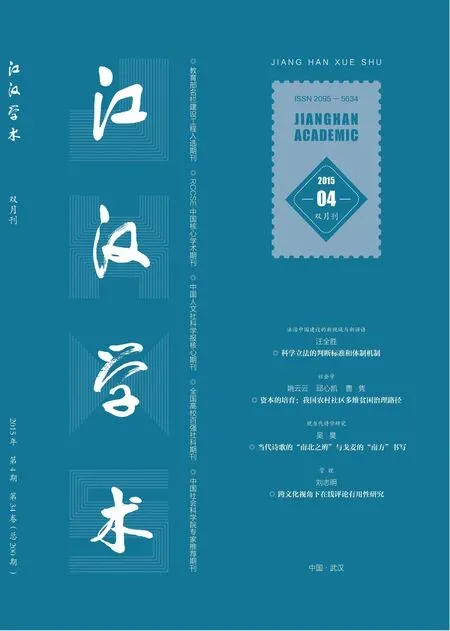知识与行动——雷蒙·阿隆基于“或然决定论”的“合理的政治观”
李 岚
(浙江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杭州311121)
知识与行动——雷蒙·阿隆基于“或然决定论”的“合理的政治观”
李岚
(浙江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杭州311121)
摘要:雷蒙·阿隆是二十世纪法国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我们主要旨在厘清其基于“政治社会学”视角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概貌。具体来说,他主张建立一种基于对社会结构均衡分析之上的“合理性的政治观”,即认为政治既是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又是“一种不可逆的选择的艺术以及长期的谋划”,它朝向的结果未必不同于最初的规划,却最终由众多历史参与者的判断和选择所共同决定。由此,从凸显人的自主性的立场出发,在马克思提出的“形式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概念框架基础上,他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接纳,并最终得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而支撑其非教条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正对人性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期盼。
关键词:合理的政治观;形式的自由;实质的自由;政治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4-0121-08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雷蒙·阿隆是法国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早先进入著名的孔多塞公立中学和巴黎高师求学,1928年便获得了国家哲学教师头衔,被认为是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哲学家。他几乎经历了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法西斯上台、二战爆发、冷战、1968年学生运动等等,并且凭借他冷静的头脑和达观的分析,在事件发生当下都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然而,与他的“小同学”萨特的名望相比,他似乎在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看作是法国知识界的“局外人”。对于这一点,阿隆有其清晰的认识,在《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他说:“在知识界看来,我之所以应该受到谴责,正是因为当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之前,我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们谴责我的另一个依据,是我没有指出通向良好社会的道路,未能传授进入这种良好社会的方法,对此,他们并不准备原谅我。”时过境迁,当人们重新发现阿隆曾经如此言之有理时,他的很多理念都已经成为现实。
他在其博士论文中所倡导的历史的“或然决定论”既反对一种完全的历史决定论,即认为人类历史按照既定设想来展开,但又不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它在承认历史多样性的基础上,保留了人类行动的价值导向,为人类的自由和有责任的行动开辟了可能性。显而易见,阿隆对历史客观性以及人文科学中的因果分析,不仅仅指向建立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正如他自述的那样,它又可被视为其政治哲学的引论。可以说,知识和行动的结合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而政治领域作为“从受境遇所限的可能性中作选取”的历史行动的典范,自然就成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
具体言之,进入到实际的政治领域,他强调行事者在面对具体场景时的理性选择和行动,与绝大多数意识形态的争论保持距离。因而,他的政治理论并不致力于建立于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反而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事件的分析。他在担任《费加罗报》主笔期间,写过上千篇的社论,用自己的解读引领读者去了解他所处的云谲波诡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他并不醉心于用华丽的言辞去激起情绪,平实的语言和严谨的分析是他最常用的方式。性情和旨趣的相异也注定了他和他的“小同学”萨特之间友谊的短暂。其实,两者分道扬镳,早在1928年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便可一窥端倪。那一年,阿隆在题为“理性和社会”的笔试中一举夺魁,而萨特惜败;次年,萨特问鼎首席,而那年的笔试题为
“偶然性和自由”。理性和自由,两个并不必然冲突的概念,其矛盾性在阿隆和萨特的命运中尤为凸显,克制的理性还是绝对的自由,在学生时代,两者似乎就已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总的来说,他主张一种基于对社会结构均衡分析之上的“合理性的政治观”(une politique raisonna⁃ble)。这一主张,既相异于“理性的政治观”(une politique de la Raison),即总是试图对现实作出调整或反抗以使其符合理想社会的模型;亦相异于韦伯所倡导的“理解的政治”(une politique de l’entende⁃ment),即认为政治中充满了偶然,身处其中的人们如同不知将驶向何处的海上舵手。在他眼中,这两种类型的政治观都是源于现实的理想化状态,现实政治必然同时包含两者,即它既要求某种前瞻性,又离不开摸索的精神。政治,究其根本,是“一种不可逆的选择的艺术以及长期的谋划”[1]。这种“合理的政治观”同时又是一种“渐进的政治观”(une politique progressiste),它试图在将理想强加于现实和对变动的厌恶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阿隆认为,政治首先是历史的,这就意味着行事者在具体事件中作出的选择和行动也是历史的,没人可以知道事件的全部状况,也没人可以提前知道后果,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行动是完全非理性的,因为即便我们无法全知,至少我们能够知道部分的现实。正如历史认识只能是或然决定的,政治亦是一种渐进的活动,它朝向的结果未必不同于最初的规划,却最终由众多历史参与者的判断和选择所共同决定。
一、何为“合理的政治观”?
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政治”对于阿隆的意义。总的来说,阿隆并不赞同用单一维度,比如经济—社会维度来分析社会现实,而忽略了政治因素对社会的影响。事实上,后者在其眼中显得更为根本,这是因为就人类这一群体而言,人际合作是其最大的特征,而政治代表了“权威的施加模式,比起其他社会因素,对个体间的关系的形成具有更大的影响”[2]24-25。事实上,它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永恒范畴出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治因素对于阿隆而言是首要的,但相对于经济现象,他对政治现象往往表现出更高的关注,但是这种政治的首要性并非是因果序列上的,而是价值层面上的。
首先,它并不等同于政治决定论,他强调说,他所赋予政治的,不是教理上(doctrinal)的而是方法论上的优先性。事实上,他本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单一社会决定论,他坚持认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很难以单一标准来衡量的。无论是经济的因素或是政治的因素抑或其他因素,在现实社会的运作中,会呈现出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状况,它们实际上都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发展的独特视角。①此外,从纵向看,各种因素此消彼长,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他们的重要性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比如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期,经济因素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小觑的。然而,阿隆并不认为讨论历史的第一动因(primum movens)之类的问题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除了上述提到的理由之外,我们事实上无法证明为何某种经济制度只能和某种政治制度匹配,正如他的历史哲学批判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时候,我们能建立的只是一套历史进程“为何如此”的事后的解释体系,我们并不能证明,历史演进具有“本该如此”的必然性。
其次,就政治在价值层面上的优先性而言,阿隆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在经济领域,比如在生产工具和技术等方面越来越具有同质性,而根本的差异往往体现于政治领域,在涉及到权力的组织和行使等方面,并且,恰恰是因为后者,各个工业社会间从生产的组织方式到生产资料的分配等才会显出差异。在这一点上,阿隆并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从人的本质上来界定政治的意义,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他的结论更多地来源于一种经验的判断。他说,我们活着,就是要跟人打交道,因而,就政治是权力的组织形式而言,它更直接地与人的生存相关联。
总之,阿隆所倡导的“合理的政治观”具体表现在他所采用的“政治社会学”视角。“政治社会学”,顾名思义,他是带着社会学家的视角去切入政治的,这就使得他的政治分析并非停留于抽象地对比各政体的优劣,或是对政权合法性原则的讨论,而是更多地与社会状况分析等现实状况相连。并且,和韦伯不同,阿隆认为,人文科学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某种既有的价值观进入研究,因而他的“政治社会学”并不把前者所谓的“价值中立”作为社会学的标准,而是以“不偏狭”(équité)为要求的。
实际上,阿隆分析的出发点,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的基本判断,即所有的工业社会都趋向于民主,
然而“民主”一词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统治模式,而只是一种社会类型,一种社会状态,它是以“条件的平等,代议制和民众智性的自由”为基础的。然而,民主的趋势并不必然预设一个自由的社会,换言之,民主本身并不决定权力的具体运作,而后者才是决定现代社会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根本。而这一点,阿隆无疑是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影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后者第一次对自由的民主和专制的民主作出了区分。相应地,阿隆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亦是基于此种两分法,一是多元宪政体制,一是垄断体制,分别以多党与一党作为分界。他认为,主权在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各工业社会的差别不在于经济组织模式,而最终体现于政治建制上的差异。
具体来说,能够体现多元宪政体制特征的国家各异,然其基本特点不外乎公私域的界分、社会团体和政党等的多样化和宪政的存在。以此为对照,阿隆以前苏联的政体为例,总结出两者间宪政和革命,社会团体的多样性与官僚体制下的专制主义,政党—国家与党国一体(l’état de partis/l’état parti⁃san)的分异。虽然阿隆对前者的偏好显而易见,然而,他并不宣称前者就代表了最好的政体,他认为,各种政体其实各有利弊,武断地否定一个而肯定另一个是不合适的。垄断体制的存在适应于某个历史发展阶段,比如在财富积累阶段以及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需要指出的是,阿隆同时认为,即便“我们有理由说,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会更倾向于某种政体,然而这并不是说,某个特定的工业社会只能对应于某种政体”[2]346。
在阿隆眼中,并不存在所谓完美的政体,即便是自由的民主国家,也需要面对官僚作风的增长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还需时刻提防多元诉求下对规则的僭越和寡头集团的出现。而对于专制的民主国家,更多地存在“需要不断地为大多数人服从小部分人的统治的正名”[2]107的问题。然而,即便同样作为不完美的制度,后者的弊端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它缺少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尊重,比如“安全、思考的自由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等。
以此为出发点,阿隆的政治社会学按照他自述的那样,首先用社会学的方法确定此两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然后分析两者的宪政的建制和运作,以及政党体系等[3]340-341。因而,他的“政治社会学”并不试图从人类希冀良善政体的美好愿望出发去构建一个完美的政体,而是在意识到现实受到的种种约束之后进行客观地分析。而这个态度,实际上贯穿了他的整个报社和学术生涯,与他的个人秉性密切相关。我们常说,阿隆的谨慎保守,与各种激情澎湃的政治运动天然保持距离,倾向于改革而非革命,因而在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版图上,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二、雷蒙·阿隆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
如上文所言,阿隆的历史批判最终落脚于“人类就是未完成的历史本身”这一结论,落实到实践层面,面对未知的历史,我们所能做的,并不是去幻想一个乌托邦,或者将现实强行塞入一个理想的模型,而是通过每个人理性和负责任的行动去接近这个理想社会,换言之,他用或然性替换了一个强定义上的历史决定论,实际上凸显了人的自主性,为自由留下了地盘。在此意义上,正如Franciszek Draus在一篇名为《阿隆和政治》的文中所说的那样,与其说阿隆的自由观接续了某个自由主义的传统,不如说,这是由他的历史批判而来的一以贯之的推论。因而,他所持的自由观,除了具有现实意义外,更兼有哲学存在论层面上的深意。
具体言之,阿隆的自由观并非自成体系,观点亦散见于他对各家的评述,尤其通过他对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自由观的比照以及对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思想的分析和批判,我们才得以窥见其思想的原貌。
1.“形式的自由”与“实质的自由”
在阿隆看来,对形式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的区分是抓住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之间思想差异的关键。他认为,在出发点上,两者都不否认民主和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只是在对“什么是民主”以及是“什么样的自由”问题上,两者发生了分歧。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民主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状态,一种平等的趋势,在他的时代,地位的日趋平等是民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而民主的社会并不必然是自由的,因为开明的专制统治者的设想是可能的。就对自由的定义而言,托克维尔在《法国1789年前后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一文中说,“……自由就是人生来就有独立于他人生活的不可被约束的权利,以及自己选择命运的权利”。在阿隆看来,这个定义兼有自由的消极和不明确的意义,同时,它也
包含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此一自由的“积极意义”。而对于马克思而言,民主首先是一种体现了“主权在民”并代表了“人的解放”的政体,在其中,人可以既是劳动者又是公民,即兼具其存在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他而言,公民身份代表了人的“形式”上的自由,而社会人则代表了人的“实质”上的自由,只有在民主社会,两者才能得以结合。然而,现实社会中人的劳动是必然的而非自由的,只有实现后者对前者的超越,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真正”的人才有可能实现。并且,形式的自由并不能使得人成为“真正”的人,因其并无法改变社会结构,民众所得到的选举权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存境遇。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人才可以说真正获得了自由。
基于各自的判断,两者虽然都预见一个自由的时代的到来,然而在它的实现方式等问题上各持己见。对托克维尔而言,他希望借由个人自由(尤其是政治层面的)呼唤代议制民主的到来,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变革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没有它为前提,政治自由仅仅是一个幻象。在两种观点之间,阿隆显然更倾向前者,同时他认为至少在三层意义上,托克维尔的想法是极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首先,用条件的平等来定义现代社会;其次,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或然的视角;再次,拒绝用经济因素来界定政治。[4]34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托氏的看法非常契合阿隆自己的想法,从根本上,他坚信,只有政治才是那个能够体现人的价值的因素。然而,阿隆同时分析说,马克思的论断也不无道理,后者也并没有否定政治自由的重要性的意思,他只是认为经济自由是在先的。并且,政治之所以在他眼里是抽象的和“形式的”,是因为对于贫苦的人民而言,选举权等形式上的自由并不具有很大的意义,而后者是必须由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来保障而得以实现的。
阿隆站在与托克维尔相同的立场,认为马克思寄希望于革命来改变经济结构,而后再实现政治自由的想法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未曾看到的是,当劳动者交付所有,臣服于某个集体名号下的权力,并甘心将经济生活也政治化的时候,他们获得的也许并不是解放,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劳动者实际上无以自卫和维权,只有国家才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样的社会仍然维持着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等级分明的状况,剩余价值也只是从资本家手里转移到了一群以集体为名义享有巨大权力的人手中。由于缺乏权力以外的制衡的力量,国家机器最后只能流于某个党派,甚至某几个人之手。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的那样,“权力倾向于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此意义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阿隆所一直倚重的政治自由或者形式的自由的重要性。
对阿隆而言,对应于马克思所提的“形式的自由”和“实质的自由”的区分,我们还可以用自由的积极义和消极义,“做什么的自由”和“避免什么的自由”等来对举。除此之外,阿隆本人还提供了一个切入自由问题的视角,形式的还是实质的自由还可以被解读为“有权利去做”和“有能力去做”之间的区分,或者“有自由”(free)和“有能力”(able)之间的区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被赋予权利,而是没有能力或者缺乏条件去做一些事,比如,法律赋予每个孩子接受同样教育的机会,然而受经济条件所困,一些孩子也许根本上不起学。
即便如此,马克思的思想仍被阿隆视为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实际上促进了该制度本身的改进,比如对民众福利的重视,对平等诉求的兼顾等。而他的错误在于,将政治自由视为奢侈品,而没有看到,形式的自由实际上反过来又是实际自由的坚实后盾,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实例,提醒我们注意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国家公权力的过度扩张、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等带来的危害。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政治的和经济的自由,其实呈现出一种互补和共生的态势,缺一不可。并且,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形式的自由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因为仅仅依靠实质的自由不足以保护我们抵挡外来的侵犯,只有依靠形式自由才能够保护我们历经艰难才争取到的权利。
在阿隆看来,民主社会只是预设了主权在民,而并没有具体说明权力的运作和行使。托克维尔看到了这一点,希望借由一套完善的建制将这一原则真正落实下来,而马克思,或者马克思的解读者们却直接从主权在民过渡到了“集体行使权力”的概念,而并没有在操作层面作更多的说明。
在阿隆对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两者思想的比照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两者除了对民主社会的界定和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以外,对平等的看法也有差异。对于托克维尔而言,现代社会所
体现的是这样一种平等,“对贵族制的否定,特权等级的消失,社会地位差异的消失,生活方式的同质性以及经济上的趋向于平等”;而对于马克思而言,他所设想的,无疑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绝对平等,一个不存在贫富差异,人们自由劳动和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而这种绝对平等的诉求与自由的概念就产生了矛盾,首先,在阿隆和托克维尔那里,条件的平等并不包含经济的平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改变并不能改变实际的经济运作,无论权力是交到了“无产阶级”还是“人民”手中;其次,绝对的平等实际也是没办法实现的。即便可以通过国家的手段实现某些条件的平等,然而对于由运气或者天赋等造成的结果的不平等实际是无法被消除的。
对阿隆而言,自由是首要的,而某种程度的自由就意味着某些不平等的存在,片面将平等的逻辑推至极致,就会导致个体丧失自由,落入受奴役的状态,这是阿隆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他说,“片面追求实际自由的人们很有可能一方面摧毁了形式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没法实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或者从参与公共事务中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追寻形式自由的那些人们,将一方面取得更多的实际的自由,另一方面,在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中获得更多的权力”[4]62。事实上,片面强调自由和平等这对二律背反中的任一方,都是不可行的:一味强调自由,则会使得弱势的民众失去保护,人类社会将无异于丛林社会。阿隆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他眼中的理想社会,应该试图是一个在自由和平等间求得一个平衡的社会,在那里,首创精神将受到鼓励,同时,通过民主程序的设计,避免大多数人的暴政,并且,贫富分化将被减弱,弱者将得到保护,并且有条件参与同等竞争。
2.与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其他理路相照
如果说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的对照反映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对现代社会认知的差异,那么阿隆对哈耶克的评述则反映了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路的不同。可以说,阿隆的自由主义相异于后者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另称个人式的自由主义。
具体来说,哈耶克对自由的讨论不再以政治—经济或者自由和平等的关系等为讨论的主轴,他将视角转移到了公私域的区分。在他那里,自由被定义为无约束(l’absence de contrainte),它旨在保护私域以及个人权利不受侵犯,而并未涵盖阿隆所说的政治参与的自由。可以说,哈耶克将经济领域(代表私域)的自由视为是首要的,政治自由只是为了保护个人实现经济计划而存在的[5]。
需要指明的是,阿隆赞同哈耶克对自由价值的倚重,他认为,保护私域,防止国家的过度扩张是必要的。同时,他对哈耶克提出的“民主和自由主义实际分属人类社会的两套理想体系”的观点也颇为认同:和民主对立的是独裁统治,与自由主义相对的是极权统治,因而,一个民主的社会有可能是极权的,并且,一个独裁的国家也有可能与自由主义的原则共存。这一区分提醒我们注意到,自由主义与目标相关,旨在限制公权力的范围,而民主则是切实保障自由的手段。阿隆进而补充道,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之所以是民主主义者,是因为他首先是个自由主义者,反之却并不如此。
然而,对于哈耶克对自由的界定,阿隆持不同的意见。首先,前者用无约束来定义自由有其逻辑上的困境。用“约束”(contrainte)一词,哈耶克指的是“一个人的行动受到了除非出自自身的另外一个的人的意愿的干涉和威胁(menace)”[6]而造成的不自由,而自由指的就是这种约束的消失,“给予个体以保护私域不受侵犯的手段”。因而,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是必须的,它严格划定了可为和不可为的界限。可以说,法治下的自由,个体据此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是哈耶克最终追求的目标。在阿隆看来,这样的推论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因为将不自由定义为“受约束”或者“受威胁”,自由意味着对法律的服从的看法,实际上是将不自由的含义大大窄化了。阿隆认为,如果依照哈耶克的定义,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比起遵从普遍法律的约束,我们更常服从于某些具体的指令,比如士兵服从调度,职员接受工作指派,而对某些指令的服从也许并不与我们的意图相符,甚至相悖,然而面对丢掉工作的危险,我们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们就是不自由的么?并且,如果讲这种逻辑推向极致,我们很容易就得出,哈耶克谈论的自由也许并不属于所有人,而只针对于其中的某些人,因为或许只有对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而言,我们才可以说,他们摆脱了“受约束”的状态,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其次,对于哈耶克用“受威胁”(menace)一词来界定不自由,阿隆也不敢苟同,实际上,“觉得受到威胁”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标准,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概念,用
其去定义自由,有其不妥之处。即便我们依照法律行事,而非服从某个具体的命令,并以此来保证命令的合法性,这也没法消除主观上感到“受威胁”的可能性;再次,法治社会中,人们虽受到法律的约束却仍然享有自由的论断,其实需要另外一个前提,即法律是体现全体公民意志的良法;而事实上,我们不难设想恶法存在的可能,比如当一国的法律规定所有国民都被禁止出国,很难说,其中的人们仍然是自由的。
由此,我们看到,哈耶克的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以保护私域的初衷是好的,而用“受威胁”或者“受约束”的状态来定义不自由,实际上使得自由这一概念本身的意义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因而,对阿隆而言,重要的不是寻找一种人们没有受约束感的普遍法,而是确定法条具体需要规定哪些禁止。他说,“最终,一个国家法律的形成,总是明确地禁止与对公民义务的规定一方,和个人合法的愿望另一方之间斡旋的结果”[3]206。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哈耶克关于自由的宪政社会的设想还引入了“共同的价值”的概念,他认为“一个自由社会的顺畅运作必须仰赖于由某些共同的价值引导的个体”,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行动又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就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而言,阿隆并不否认政治行为的道德基础,从根本上,他不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然而,他确实反对将道德标准一以贯之于政治领域。在他看来,鉴于政治所要维护的是一个集体的利益,当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之时,就无法避免动用到非道德的手段,因而,政治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应有其独特的一套衡量标准,简单的非黑即白的评价标准是不足以衡量的。在我们看来,他强调两者的分界是有其意义的,毕竟在现实政治中,各种建制必须基于对人性恶的规范和牵制,而并非始终基于对“良善”的人性的期望。由此引出哈耶克体系中理想化的一面,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宪政社会在作为最终的目标之前,就已经成为其论证的前提了,阿隆说,“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哲学实际在前提中就已经预设了行动所预期达到的结果……留给每个人决定和选择的自由其实需要一个前提,即所有人至少大部分人愿意共同生活在一起,认可同一套价值理念,并认同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换言之,在我们可以谈论这个自由的社会之前,首先它必须已经是自由的了(Avant que la société puisse être libre,il faut qu’elle soit)”[3]221。
就哈耶克和阿隆的自由主义的内容和实质而言,自由的意义对于前者主要存在于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私域,而后者则更强调政治参与自由(la lib⁃erté-participation)的重要性。具体言之,哈耶克将企业家的精神和消费者的自由作为其定义下自由的典范,“第一种人拥有首创和组织生产资料的自由,第二种人则拥有消费者购买力主权”。而对于阿隆而言,既包括了消极意义上的免于被干涉的自由,又包括了实际拥有实现能力的自由(这实质上是一种要求参与的自由),它们代表了自由的两个面向,缺一不可。我们看到,古典自由主义常常被批评为“少数人的自由”或者“保护富人的自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前者片面强调自由的消极意义,而忽略了其积极意义。阿隆认为,这是前者没有意识到人们对平等的诉求的结果(la force des revendications égalitaires)。事实上,某些场合下,人们是愿意主动牺牲一部分私域,参与公共生活的,因为他们希望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得到相对平等的对待。
阿隆和哈耶克在自由主义问题上的异见,实际反映了自由主义传统内部的两条理路。根据Cathe⁃rine Audard的研究,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传承了十九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薪火,与他同一阵营的,还有极端自由主义(ultralibéralisme)和诺齐克的源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l’anarcho-capitalisme);而阿隆的自由主义则代表了冷战以来反抗极权主义体制而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卡尔·波普尔、以赛亚·柏林都可被视为该阵营的思想家。
即便如此,在阿隆眼中,哈耶克仍然是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现代民主表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官僚气息和体现越来越少的民意,对民众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对行政者权力的上升和立法者权力的下降等问题,哈耶克对此表现出的担忧,是值得引起重视和探讨的。同哈耶克一样,阿隆同样认为现代民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变得越来越形式化,我们越来越少去探讨自由的深意,议会流程也变得程式化,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反映了民众关心自己经济上的获益胜于对公共事务的关心。阿隆对政治自由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自由”的强调,则提醒我们后者才是防止我们耽于对普罗米修斯的期盼和落入极权主义窠臼的利器。然而,如何激起民众对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真正实现消费者、劳动者和公民身份的结合,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
前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鼓励民众参与和自身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决策,加强公民的民主意识的教育,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需要肩负的责任。
在传统的政治论辩中,人们倾向于用左和右来界分知识分子,左和右呈现出各种版本的对立:左派更强调平等,而右派更重视自由;左派重分配,右派重效率;左派理想,右派现实;或者像法国人常说的,摸胸口时是左派,摸口袋时是右派。此二派所持的观点,其实代表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不可偏废的两个面向,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势必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阿隆所期待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众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然而,在自由的福利国家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阿隆无疑会选择前者。无论任何时候,他都将自由视为最高的价值,不自由毋宁死。
三、结论
总的说来,阿隆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学院式的,接续于某个学统,而是成形于他对所处社会的体察。他自称是法国“政治社会学”学派的传承者,该学派由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创立,与阿隆同时代的历史学家Élie Halévy亦可被视为其中的一员。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只是因为其中的成员对某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致:它是非教条的,对政治感兴趣同时又关注社会结构,认为政治是具有自主性的、持自由思想的学派。具体来说,阿隆的自由观一方面涵盖了哈耶克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要求尊重个体自由和宪法程序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同时认为自由不应只具有单一意义,它兼具政治和社会意义。不同于马克思,他并不认为政治自由只是形式的,它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他并不试图给出一个自由的定义,他尊重“多样性”,因而他认为自由是具体的,其定义不是唯一的。
此外,为阐明自由和平等这对二律背反的关系,阿隆曾对不平等的类别作出过划分,即社会—经济的、社会—政治的以及种族的不平等。他认为,即便现代社会有平等的趋向,而实际能够实现的平等也不是左派所追求的经济上的平等,即财富或者生产资料的平均分配,而更多地表现于权利层面上的平等,或者说政治地位的平等,即拥有相同地分享政治权力的平等权利。我们看到,阿隆所追求的平等,与其说是结果的平等,不如说是机会的均等。事实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背后,正如阿隆所说,即便人们有平等的愿望,人类社会却必须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等级制度架构起来的。[7]总要有一些人发号施令,一部人服从。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员总是相对应存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阿隆接受不平等的存在,并将其视为是公正的事情,他只是认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甚至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相反地,依赖于国家的二次分配,总量的增加是可能有益于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贫富差距的缩小的。同时,就实现平等的手段而言,他不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实现平等的唯一方法,因为只是将生产资料从一部分人的手中转移到作为集体名词存在的“人民”手中,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架构方式。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众诉求依靠政治手段的实现,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相对的平等是可以预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平等可以实现一种共生的关系。
并且,他也不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论点。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两大特征是资本积累和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他看来,前者无疑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共同目标,而后者反映了人类社会等级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在生产的组织方式上几乎是同质的。因而,他认为,能够将现代社会真正区分开来的,与其说是经济因素,不如说是政治因素。他说,“所有对工业社会的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的分析,不足以区分各个社会众多的政治上的可能性。而只有依靠对政体的分析,我们才能够确定各个社会的本质和基本走向”②。
阿隆应该属于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对所有的学说思想持开放的态度,不介意改变原有的看法,但却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用自己的判断去鉴别。他罕有臣服于某个权威或某个学派,这一点在和他同戴高乐的关系中可以看出。1940年,阿隆加入由后者发起的自由法国运动,一度被视为“戴高乐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后者当政之后,阿隆会无条件为其辩护:在法德关系,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对法国是否加入北约问题上,阿隆对戴高乐的施政一直持批评态度。忠于真理,而不是权威,因为对他而言,“持有某种政治观点,并不是持有某种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而是在变幻的时局中,努力做出正确的判断”[8]。
注释:
①“Each of disciplines - economics,sociology,politics,social psychology - uses a vocabulary and a system of concepts of its own. Each aspires to a partial social reality or if you like,ap⁃proaches the whole of a society from a particular angle”,参见Miriam Bernheim Conant(eds.),politics and history,select⁃ed essays by Raymond Aron,London: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p. 24.
②Raymond Aron,La Lutte de classes,Nouvelles leçons sur l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Paris:Gallimard,1964,p. 362.就“工业社会”议题,阿隆的其他两本书也值得关注,《工业社会十八讲》(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1962)以及《民主和极权》(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1965)。
参考文献:
[1]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M]. Paris:Gallimard,1986:414.
[2]Raymond Aron. 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M]. Paris:Galli⁃mard,1965.
[3]Raymond Aron.Études politiques[M]. Paris:Gallimard,1972:340-341.
[4]Raymond Aron. Essai sur les libertés[M]. Paris:Calmann-Lévy,1965.
[5]Friedrich A. Hayek,La Constitution de la Liberté[M]. translated by Raoul Audouin,Jacques Garello,Guy Mil⁃lière,Paris:Édition Litec,1994:223.
[6]Friedr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s of Libert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133-134.
[7]Raymond Aron. 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Essai sur la dia⁃lectique de la modernité[M]. Paris:Calmann-Lévy,1969:40.
[8]Raymond Aron. Le Spectateur engagé,entretiens avec Jean-Louis Missika et Dominique Wolton[M]. Paris:Julliard,1981:180.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zhengxiaoyan1023 @ hotmail. com)
Knowledge and Action——Raymond Aron’s Reasonable Politics Based on a Determinism of Probability
LI Lan
(Philosophy Research Department,Zhejia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Hangzhou 311121,China)
Abstract:Raymond Aron is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in France in last century. In this article,we will try to give an overall view of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frame of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Generally speaking,he advocates a reasonable politics built on a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social structure,which considers the politics both as a progressiv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as an art of irreversible choice and a long-term plan. The politics,as it seems to him,is actually the outcome of judgments and choices flowing together of all participants of history,even if sometimes it appears to be the result of a plan beforehand. From this emphasis on the autonomy of man,his liberalism adjusts that of Hayek,who overemphasizes the economic factor,and assimilates critically the division between formal freedom and real freedom in the sense of Marx,and arrives at a conclusion in-between,namely,a kind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For us,what he has done shows not only the respect for human nature,but also the anticipation for a good civil society.
Keywords:reasonable politics;formal freedom;real freedom;political liberalism
作者简介:李岚,女,浙江绍兴人,浙江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与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哲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4 - 08 - 15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