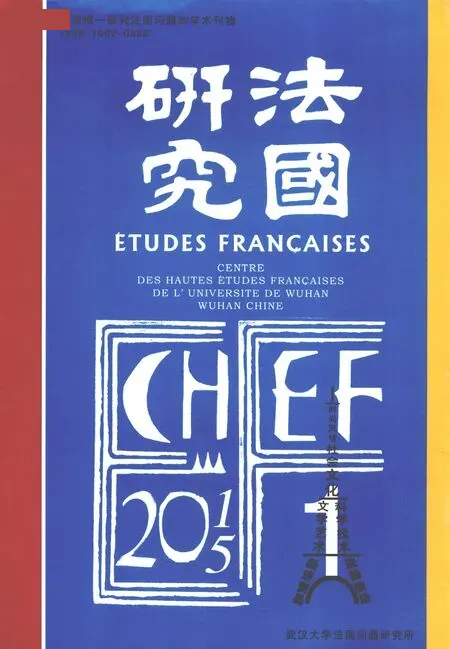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从萨特、阿隆之争看二十世纪法国知识界
李 岚
要了解二十世纪法国的知识界,萨特和阿隆当属不可绕过的两位人物。同于 1905年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同期(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同样拥有留德经历,受到现象学和诠释学学说的影响;在学生时代,都曾经信奉和平主义者法国哲学家阿兰①原名Emile Chartier(1868-1951),阿兰为其笔名,代表作有Propos等。(Alain)的主张。早期曾亲密无间,以“我的小同学”互称,并相约百年之后后逝者为先逝者致悼词。然而,三十年之后诺言不复存在,1956年,阿隆在一篇文章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什么友谊能够抵挡得了政见的分歧,如果不想和友人分道扬镳,那么就跟他始终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吧。道理虽是这样,但仍不免让人觉得伤心。”
萨特,早先在阿兰的影响下成为反战主义者,1940年前并未对政治表示出多大的兴趣,自二战后被从德国集中营释放之后,先后以存在主义者和亲共产主义者的身份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生前名声大噪。阿隆,对激情澎湃的政治运动始终秉持怀疑和静观的态度,主张抛弃左或者右的政治标签,忠诚于自己对时事分析基础上的判断,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阿隆曾经如此有理。然而,此二者处境的相异并不纯属偶然,个性和旨趣的相异使得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按照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的说法,法国学生运动期间的口号,“宁可跟着萨特错,也不跟着阿隆对”实际上反映了法国知识界论辩的典型特点,即“形象之争”(querelle d’images)。在这个背后,我们可以列出许多个标签对两者作出区隔:历史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左和右,或者按照西里奈利的提法,历史的梦想家和历史的思考者,抑或按照埃提安·巴尔里埃(Etienne Barilier)的说法,“颂扬的主体性”和“受管束的主体性”。除此之外,两者旨趣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前者热衷于宏大的事件和理论,后者对所有成套的等待被灌输的理念抱有天然的敌意。其实,两者的分道扬镳,早在 1928年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便可一窥端倪。那一年,阿隆在题为“理性和社会”的笔试中一举拔得头魁,而萨特惜败;次年,萨特问鼎首席,而那年的笔试题为“偶然性和自由”。理性和自由,两个并不必然冲突的概念,其矛盾性在阿隆和萨特的命运中尤为凸显,克制的理性还是绝对的自由,在学生时代,两者就似乎已经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具体言之,两者政见的差异主要表现于对前苏联政权的态度。早在 1939年,阿隆就在《形而上学和道德》杂志上著文将法西斯主义和前苏联宣扬的共产主义进行比照,他认为,尽管存在着差异,两种政权在本质上都奉行“独裁统治和国家式的激愤”。而在萨特眼中,反对共产主义是一项罪行,1954年访苏归来之后,萨特说,“在苏联,人们拥有绝对的批评的自由”。阿隆并不曾到过苏联,然而值得作为比照的是,罗曼·罗兰和纪德都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有过访苏之行,跟萨特不同,前者选择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时间中闭口不谈,而后者在《访苏归来》一书中表达了对前苏的极权统治的失望之后,即被视为左派的敌人。
左派和右派的区分,最初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与教士贵族阶层座席位置的左右之分,尽管阿隆本人并不接受这样单一的政治标签,无可厚非的是,它曾被用于在旧制度下区分革新派和守旧派,在上个世纪,又被简单地用于区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而且,这种区分仍将持续。在阿隆看来,法国知识界的论辩,大多呈现出意识形态层面贴标签式的争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论辩。他说,“法国人之间的争论总是难以平息的,因为它们总是表现为‘思想家族’之间的对立,因为它们互相不满,因为意识形态的狂热总是反抗性的而非妥协性的。”①Raymond Aron, Espoir et peur du siècle, Essai non partisans, Paris : Calmann-Lévy, 1957, p. 117.只是所谓的左派或是右派,在他眼中,也从来没有像想象地那样铁板一块,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左派或者右派。“左派”,起初代表的是反抗旧制度下世袭地位的不平等的自由思想,而当今,它几乎成了经济集中和集体自由的代名词。在不同的时代,它总是以当权者的反对者的面貌出现,它先是反抗教会、贵族而后是资产阶级。而就“左派”本身的核心概念而言,“平等”,“自由”和“组织”各理念间也并非如此自洽。平等的左派,反对的主要是世袭的权贵阶级;自由的左派,反对公权力的滥用,主张保护个人的安全,因而相异于宣扬扩张公权力的社会主义;而组织的左派,主张用理性的秩序来替代传统或者个人行动的盲目性,易于蜕变成专制的、国家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立场。
而右派阵营也并非如此界限分明。举例言之,1815年,法国保皇党内部在保护君主制方面就已经分出极端的和温和的两派,只有前者才要求严格回到君主专制。又如 1940年前后,法国实际存在三支不同的右派,其一延续了极端保守的右派对共和国、民主和议会制的敌意;其二是主张资产阶级议会制而非君主立宪制的右派;其三是寻求铁腕政治的布朗热主义和戴高乐主义右派。在理念层面上,“家庭”,“权威”和“宗教”被视为右派的核心价值,然而事实上,右派的基督徒和进步主义基督徒(左派)的共存从侧面说明了“左”和“右”其实又共享了某些理念。并且,实际上,极左和极右的政权,以苏联和纳粹德国为例,就同样是个体被剥夺自由的极权统治而言,本质上不存在太大的差别。阿隆认为,左派进步,右派怀旧之类的一刀切的提法只具有“心理层面上的意义”,他说,对于温和的左派或是右派而言,是不吝啬于承认对方的观点中是有部分的合理性的。①Ibid., p.98.无论是进步的理性主义,还是传统主义,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要维护前人费尽艰难才争取来的民主和自由。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教授的说法,阿隆的思想更近乎于一种居于维护传统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新保守主义,他一方面主张从现有传统出发行动,另一方面又和野心勃勃的新自由主义保持距离。
就阿隆本人持改良观点,对革命持批判态度而言,他确实可被视为右派知识分子,然而,他的保守的态度并不源于对进步的怀疑,而是可被视为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妥协精神的推崇。就保守主义的态度而言,他十分敬重英国思想家伯克,他评价后者为,“与其说对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对明智本身更感兴趣,具体说来,这指的是就事情本身所呈现的那个样子解决问题,而尽量不去牵扯比如永恒的原则等的这样一种精神。”②Raymond Aron,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 Calmann-Lévy, 1955, p. 261-274.而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所致力于批判的,也正是后一类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衷于价值和原则的探讨,以及道德的评判,而不屑专注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层面的讨论;他们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和鄙夷,因而对政治运动从不缺乏热情,并总是寄希望于一场一切从零开始的革命去打造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以及新人。而当这个逻辑被推向极致,我们不难想象这样话语的出现,萨特在为法农所著的《大地上的卑污》(Les Damnés de la terre)一书的序中写道,“……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这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到他脚下植物下面的国土。”
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萨特从神坛坠落,而阿隆所扮演的另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介入的旁观者开始重入人们的视野,对此,西里奈利这样说,如果说萨特代表了意识形态领域激奋的“荣耀的三十年”③指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法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的思想引路人,那么阿隆则是治疗这三十年以来的知识界的创伤的疗伤人,他使得人们在激情过后,开始反思那个时代,并重新审视和传统的关系。这就不得不提到阿隆那本著名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在其中,他深刻剖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在技术和意识形态各执一端的法国与英美知识分子的对比中,他跟同属法国“政治社会学”学派的前辈托克维尔一样,明显偏向了后者。
在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微妙的张力,马克·里拉把这种张力称之为“叙拉古的诱惑”。宛如当年柏拉图曾三赴叙拉古,希望通过小戴素奥尼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两千年以来,知识分子怀揣着同样的“哲学王”的理想,前赴后继。究竟知识分子应该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承担什么角色?在阿隆那里,他无疑首先将这个问题转换成了,如何远离政治漩涡,始终冷静达观地对事件作出理性的判断?
如果说,阿隆著于 1938年的《历史哲学引论》一书奠定了他思想的哲学基础,那么《知识分子的鸦片》可被视为他的历史哲学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具体展现。该书分为“政治的神话”,“历史的崇拜”和“知识分子的异化”三个章节,以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为结论,集中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以反对当时法国知识界盛行以萨特为代表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争论。
总的说来,在阿隆看来,“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这些概念依托于“进步”、“理性”和“人民”的概念而存在,它们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并且它们能够很容易唤起激情,却很少人会去深究它们真正的含义。而阿隆的批判就是从理清这些概念开始的。就“左派”该词而言,其一,如上文所述,阿隆并不认为它的界定是清晰的;其二,就它追求的经济层面的平等而言,阿隆认为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一来,单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国有化并不能消除经济层面的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全民所有”是一个虚假的概念;二来,即便是持有该理念的左派当政,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效益最大化和分配的平等之间的矛盾,一味追求绝对的平等和国有化,必然会损伤多样化的经济主体的利益,并使得民众除了国家以外无所依傍。并且民众对国家经济上的依附也会导致政治上失权的状况,当传统的地方社团和社会力量消失殆尽,能够约束公权力侵入私域的力量就消失了。在集体拥有权力的名号下,个人实际无以抗拒强大的国家机器。正因如此,阿隆才尤为强调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的价值。
就“革命”这一概念而言,阿隆也并不赞同左派的逻辑,即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社会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他曾说,“我并不厌恶在每一个当下对具体事件作出判断,我所反感的,是宣扬暴力、反对和解的态度,这是一种为暴力而暴力的哲学”①Raymond Aron, Histoire et dialectique de la violence, Paris : Gallimard, 1973, p. 218.他认为,左派对革命的偏好,其实源于一种历史的理性主义,当上帝已死,人类历史失去既定的意义,那么我们所要做的,便是赋予历史一个新意。在这一点上,阿隆实际跟萨特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初衷都反对历史的目的论,主张人类实践的重要性,所不同的是,在阿隆看来,后者实际上又偷偷地重新引入了历史决定论的结论。革命的理念实际反映了左派对无阶级的理想社会的期盼,后者对现实持鄙夷的态度,将希望寄托于推倒重来的过程。
至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阿隆认为,就它的所指而言,也是十分不明晰的。在大机器生产的时代,对于各工种,各职业的产业工人而言,因为缺乏共同的利益,很难说他们构成了一个阶级。同时,从官僚体系的哪一级开始可以被算作是工人阶级也难以被确定。阿隆同时追问道,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手工业工人还是无产阶级么?因而阿隆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被生造出来的词,它的意义在于,“从它能够代表一个集体的意志开始,无产阶级就成了一个自觉的统一体。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的数量多少,由谁构成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小部分斗士合法地成为了该阶级的代言人。” 这里,阿隆所致力于批判的,是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机器的服务者,还是革命的战士,无产阶级从来也不是作为一个政权的代表,受益者或是实际的领导者出现的。只是因由知识分子的神话,它变身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政权的掌权人。”①Raymond Aron,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Op. cit., p. 113.
综上,阿隆认为左派的这三个概念构成了其政治乐观主义的面貌,阿隆称之为“关于未知、未来和绝对的诗作”,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导向的是一种现实的悲观主义和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在阿隆眼中,现实并不因为理想社会的美好而变得可鄙,即便它也许充满了荒诞的纷乱。并且,对现实的不同态度,归根结底,是基于双方对人类本身认识的差异。前者将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完人和公共生活完全理性的组织,对人类理性的能力充满了信心。而如阿隆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传统、人类非理性的激情以及受束缚的群体行为划定了人们行动的界限,他说,“自由主义者将不完美的人视为考虑的出发点,认为一个好的政体必然是不计其数的合力之结果,而并非只源于一个良善的动机。至少,它怀抱这样一种悲观主义,政治就是创造条件使得众人之恶为国家之善服务的一种艺术。”②Ibid., p. 310.
他认为,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弊端在于,忽视实际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命题,比如像英美的知识分子那样致力于技术性的问题,却醉心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世俗的宗教,在其中,他们既是先知又是布道者,“对党的热爱”,“经院式的解读”以及对“战士的培养”构成了这个宗教的重要部分。
在阿隆看来,“左”和“右”的争论,在技术层面上,实际上反映了一个良善的民主社会所追求的双重目标,无论是集权的民主还是自由的民主,实际反映了对两种理念——自由和平等的不同侧重,对于前者而言,个体的自主是最为首要的,因而更为强调对个体自由的保护;而后者则更倚重强大的国家的调控作用以实现经济层面的平等。
同时,阿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也让我们清醒地看到,政治行动的起点无非是接受政治的平庸性乃至生活的平庸性,它必须基于长久的规划,同样也是一门选择的艺术:它总是对一个具体情境的个体的负责任的回应,我们弥补一个错误并不是单纯地跑向另一端;它预设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它必须从现实条件出发。对阿隆而言,康德所说的“运用你的理性”是必须的,然而这种运用又是时刻带有自省性质的,意识到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意识到理性的界限,意识到人自身的不完美,是避免政治乐观主义的良药。同样地,人类的各种政治建制也是不完美的,“它们或多或少会表现出不平等的现象,对于公共生活,我们无法实现完全的人道主义。”
即便不完美,阿隆对自由的民主的偏好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这样描绘一个良性运作的民主社会,“它应该包含对宪法的尊重,对个体首创精神的敬意,对科学和效率的崇拜,还包含一种既强烈又宽松的并区别于宗教间的敌对状态的人道主义。它并不强调什么事无巨细的正统或者官方说辞。学校教授这一套信念,社会助其变成现实。也许它会显得有点因循守旧,然而它却不是专制的,因为并不禁止人们在宗教,经济和政治等议题上的自由讨论。”③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démocratie et révolution, Paris : Édition de Fallois, 1997, p. 324.
在我们看来,阿隆并不属于原创型的知识分子,按照柏林知识界的分类法,阿隆显然属于狐狸型的学者,或者按照哈耶克的提法,属于一种解谜类型的学者(另一种类型被称为精通所研究领域的学者)。托多罗夫已经在阿隆回忆录的序中,最为精准地描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所选择的立场,“阿隆没有担任君主的顾问,而是成为一个公众的服务员和解说员,一个带来光明的使者。他放弃充当贩卖幻想的商人,他推动每个人去了解身边的世界并公正地批判世界,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做出了表率,但不愿意带领人们直达目的地,因为应该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承当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发现一个什么真理,因此,没有任何阿隆主义可言,尽管有不少人承认自己接受了阿隆的某些做法。与其说他要激励人心,不如说他要启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