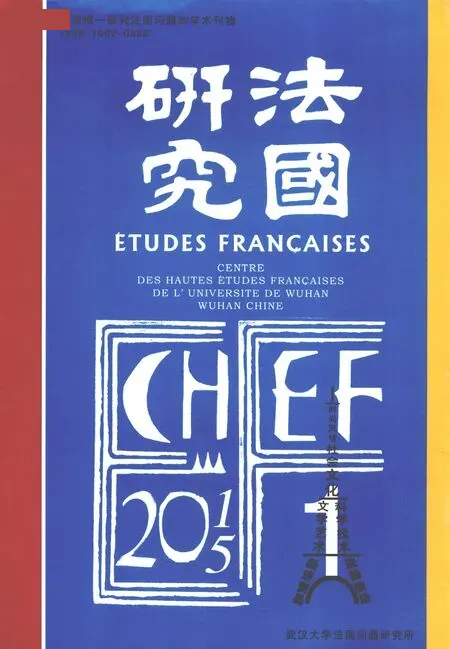雷蒙 ·阿隆的知识分子论
符 晓
即使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至少30年,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高名在中国恐怕也只有少数专业研究者才了然于胸,其实当年阿隆也是同萨特比肩的风云人物,二人 1924年同入巴黎高师成为同窗,毕业时哲学教师资格会考相继拔得头筹,后来又都去德国接受理性主义的熏陶,早年经历可谓惊人相似。但从 1930年代开始尤其是“二战”之后,二人因为思想的歧途而分道扬镳,“五月风暴”后竟然走向了彻底决裂的深渊,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让人深思其中的原因。
本文要讨论的知识分子论可以成为答案的一个方面:1950年代初期,冷战刚刚开始,以萨特为首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信仰苏联体制、迷信革命的激进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阿隆基于此于 1954年写就《知识分子的鸦片》,对左派知识分子这种法兰西病进行深入地剖析、反思和批判并阐明其自由主义的立场。阿隆在本书的序言中声称他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三各方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①[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 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1页。但实际上阿隆讨论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三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难从《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透析出更深层次的意义。
一、去政治神话:对左派政治的批判
雷蒙·阿隆的哲学总是带有一种德国古典主义的思辨色彩,因此虽然批评左派知识分子,但是却并不像左派知识分子那样情绪激昂、言辞犀利,而是针对某个问题进行抽丝剥茧般细致入微的分析。阿隆认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最主要问题在于相信政治的神话,所谓“神话”指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虚妄和对政治的幻想,这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即“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1)阿隆无法接受这种态度,因此对“政治的神话”进行批判,其中最主要的着眼点是“革命”。
革命,可以说是法国近现代历史的精魂所在,而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则是革命思想的生力军和急先锋。毋庸置疑,大革命是这种精魂的渊薮,它象征着法国“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斩钉截铁地将法国史一分为二,如托克维尔所言,大革命“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3]①[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60页。正是这种澎湃的激情催生了左派知识分子的雄心壮志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革命不知不觉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鸦片,使他们萌发出“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自大革命以来,无论是反对旧制度左派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左派都将自己视为大革命的继承者,他们从大革命中获得勇气、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然而,左派知识分子表面上形成了一个以大革命为表率的统一的合体,但是实际上左派内部却混乱不堪甚至让人很难定义什么是“左派”,这就是阿隆所谓“左派的神话”。
阿隆认为,人们对英国“左转”的好感来自某种社会改良的巧合,而在欧陆左派内部却存在严重的分裂,更不用说与英法截然不同的南美和东欧,甚至声称“在大西洋彼岸,很难捕捉到能与这一欧洲术语相吻合的现实事务”,可见在世界范围内而言,左派存在严重的不稳定性。另外,阿隆指出无论是鼓吹“自由”和“组织”的左派,还是鼓吹“平等”的左派,他们虽然在口号上保持一致,但是三者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这些都说明“左派”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甚至混乱的概念,追求左派统一的神话或多或少已经宣告终结,如阿隆自己所说,“永恒的左派精神实际上已经死亡”。同样,“革命的神话”也源于一种怀旧情绪,即对大革命尤其是对暴力的信仰,暴力似乎成为左派的一个标签。但是阿隆认为其实革命也很难定义,因为革命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而且世界各国的革命方式不尽相同。即使左派知识分子在思考法国大革命时也会存在偏见,如认为只有符合左翼的意识形态才能被纳入到革命范畴,或者革命的成功必须以颠倒现存财产为标志,其实这种革命的概念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所以阿隆认为“革命的神话为乌托邦思想充当了避难所,并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说情者”,可见左派的所谓“革命”也是个神话。
左派知识分子一般认为,无产阶级的核心目的是“解放”,但是阿隆认为就像他们对“无产阶级”的界定存在多义性和矛盾性一样,左派对“解放”的定义也存在问题,因此,阿隆将“解放”分为“理想的解放” 和“真实的解放”,“理想的解放”是指无产阶级内部所体现出来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高高在上的生活生产革命,而“真实的解放”是“通过具体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得到表现;允许一些抱怨继续存在;有时候也允许多少有点强大的少数人起来反抗政治体制的原则”,(雷蒙·阿隆:71)以苏联为代表的理想解放因为带有浓重的激进主义色彩对左派知识分子充满了诱惑,而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真实解放则在左派看来相当乏味。然而阿隆却认为是左派知识分子铸就了 “无产阶级的神话”使得所谓解放表面上光鲜亮丽实质上存在很多问题,就社会进步而言,真实的解放显然更理性、实用并且具有时效性。
阿隆将左派知识分子幻想出的神话称为“政治乐观主义”,即在看待“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思想深处存在谬误,这些谬误使得他们的观念不合乎情理并且具有神话的色彩。左派虽然不甘于顺从不公正,但是却忽视最普遍的社会现实,比如不同政党价值观念的转变、右派中倾向于左派的价值观念和在矛盾的目标中建立妥协的必要性等;一味地追求革命也并不值得称道,因为“它丝毫没有显示统治阶级已经吸取了教训,而且也未曾显示人们在不践踏法律和动用军队的情况下就能够去除不称职的统治者”;(雷蒙·阿隆:89)而无产阶级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上说是代表了强大的工人阶级,但是事实上却是一个由经理组织且极易受煽动的群体而已。由此可见,阿隆并不是以将左派知识分子批判得一无是处来抢攻左与右的思想高地,而是提供给左派以清醒地认识,应该现实地看待当时法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出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建构思想和政治的空中楼阁。
二、反历史偶像崇拜:反思“历史决定论”
“左派”、“革命”与“无产阶级”,在法国当时知识分子看来是比较神圣、比较崇高的词汇,但是阿隆认为这都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一种神话,而在神话背后,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偶像崇拜。究竟是否应该对历史偶像顶礼膜拜在阿隆看来是一个问题,因此阿隆从三各方面对历史的偶像崇拜进行了反思。
首先,阿隆阐述了圣职人员与信徒的关系。所谓“圣职人员”是指共产党人,而“信徒”指的是亲共人士。在左派知识分子看来,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正确,共产党的目的就是用自身的神圣思想拯救全人类以实现理想的解放,共产党的历史也是通向人类救赎的历史,因此共产党人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党的传统、宗旨和信念。而作为信徒的亲共人士则接受共产党的大部分纲领,但是不会对纲领的每一句和每一字都奉为圭臬,他们是理想的革命主义者。以此为基础,阿隆阐述了圣职人员和信徒的三个区别:一是圣徒人员无条件屈从于党的纪律而理想主义者则主张从事实出发;二是圣职人员不会对党的历史产生怀疑而信徒则认为历史的真实性并不存在;三是圣职人员相信党的历史中的偶然性而信徒则还同这种偶然性保持着距离。这三方面的区别在“历史的偶像崇拜”问题上仿佛和论题无关,但是却是阿隆的精义所在:圣职人员所谓的历史是一种偶然性,强调的是“事件的细节”和偶然因素,而信徒则追求一种同一的完整的历史,这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历史而言,阿隆认为左派知识分子对某位历史人物和某个历史事件的无限放大不但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反而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步伐,显而易见是对人物决定论和事件决定论的反思。
其次,阿隆重点阐述了历史的意义。阿隆一贯认为“历史”不可定义,因为“‘历史’一词时而表达这个意思,时而表达另一个意思,有时甚至没有明确分别,既指主观的历史认识现象,也指客观现象或者人们所以为的客观现象”,[6]①[法]雷蒙·阿隆:《历史讲演录》,西尔维·梅叙尔 编注,张琳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第90-91页。在阿隆看来,历史概念的意义也存在着多样性,无论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文化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定义都不尽相同,他们的历史概念虽然有交叉之处,但是却也各有所指,因此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不可能指出其纯粹的意义,也不能呈现出深层次的本质所在。阿隆认为“意义的多样性一方面源于整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源于历史解释的不断更新引起的特殊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的区别”,(雷蒙·阿隆:133)可见确实很难给历史下一个比较完整周延的定义。阿隆又提到了历史的目的问题,认为历史的目的并非一个固定的常量而同样具有多样性,并非指向一元而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在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背后是理性的力量,指出“历史的目的是一种理性的观念,它并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穿越时光的群体的努力上显示自己的特色。”(雷蒙·阿隆:145)其实,阿隆阐述历史意义的目的在于认识历史的态度,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态度往往激进而又感性,这势必导致对历史的误读,而阿隆则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历史,因为“对历史有真正的认识会使我们时时记得宽容,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雷蒙·阿隆:145)一方面要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查而不是单纯地分析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一方面要理性地认识历史及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历史的意义。
再次,阿隆对历史偶然性和未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一贯相信历史的偶然性,他们认为无论是政治史、战争史还是国家史都被偶然因素所操控,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成长经历都存在偶然性,他们甚至认为历史中极少存在必然性而都是偶然性。阿隆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历史的偶然性无论如何都是历史整体的一部分,他指出,“人们担心在个人的主动性或一系列的偶然性事件之类的局限性的时时干扰下,对整体的理解会受到影响。这种担忧并没有多少根据。那些在细节上可能会有些出入的事实并不会妨碍我们去理解‘整体’”,(雷蒙·阿隆:157)可见阿隆不相信历史的偶然性而相信众多偶然性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阿隆也对左派知识分子对未来盲目地进行幻想给予了批判,左派知识分子普遍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他们根据左派政党的理想对未来进行“理论性的预测”和“历史的预测”,而阿隆则认为这种预测并不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所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和不可能性。
初看起来,阿隆字里行间的论述仿佛和历史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深究之还是会发现,阿隆对左派知识分子历史观的反思和批判并不像他们自己那样慷慨激昂,而是有条不紊、抽丝剥茧般娓娓道来。其实,阿隆反对的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种偶然因素,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可以决定所有事件的发展方向和总体走向。
三、异化:知识分子的处境
无论是政治神话还是历史的偶像崇拜都是当时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现状,阿隆在对这种现状提出质疑的同时也对创造这种现状的主体——知识分子及其处境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阿隆认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正呈现出一种异化趋势,无论是法国知识分子,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
阿隆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但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指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构成结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把自己职业的思维习惯带入到了政治领域中,这其中,英美知识分子重视实践经验,德国知识分子重视民族意识,而法国知识分子则更看中左翼意识形态。基于此,阿隆将法国称为是知识分子的天堂,无论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社会风气,都适合左翼知识分子的生存,狂热、革命和政治幻想可以说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关键词,而当时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恰恰为之提供了有利的温床。相反,阿隆认为美国是知识分子的地狱,因为整个美国社会都有一种反知识分子倾向,他援引布罗姆菲尔德的言论指出知识分子的缺点,比如缺少男子汉气概、抓不住事务本质并且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等,可以说,当时美国的反知识分子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得左派知识分子在美国颜面扫地。最理性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在英国,英国“避免了美国实用主义产生的狂热的反知识分子思潮,以及法国不加区别地对作家的政治观点和他们倾向于各种极端的判断和拙劣的文章”,(雷蒙·阿隆:222)这使得阿隆认为英国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最可让人接受,这种态度既不狂热也不冷漠,是一种“有分寸的傲慢”。
阿隆讨论了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问题,围绕 1950年代初期的冷战,阿隆指出了 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三个事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对代议制的质疑;一位知识分子对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否定和亚非知识分子的狂热之间存在的一种先定和谐(harmonie préétablie),这一系列的事实引起了知识分子内部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就国家而言,意识形态争论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英国知识分子将意识形态冲突简化为技术层面的冲突,美国知识分子则将那些道德争论转变为更重方法而不是目的的争论,法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是全人类的意愿而往往忽略本国当下面临的问题。阿隆继而将这种争论转向全世界,认为日本的争论模式趋近于法国而印度的模式则同英国相仿。值得注意的是,阿隆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历程存在其特殊性,中国在亦步亦趋中逐渐习得了马克思主义,无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地位如何,它在中国显然是绝对权威并呈现出了鲜明的积极效果,如阿隆所言,“马克思列宁主义超越了历史意识赋予它的相对主义,治愈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因西方技术优越性而蒙受的痛苦”。(雷蒙·阿隆:248)从某种意义上说,阿隆的这种判断既可以使人洞悉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历程,也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所在。
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仰,阿隆不无担心地指出其已经具备某种宗教色彩,甚至指出左派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某种世俗宗教。共产主义是左派知识分子的最高教义所在,阿隆认为理论上实现共产主义的三个阶段是政党崇拜、解释性的经院哲学和积极分子的训练,但是事实上这三个阶段之间存在着矛盾性,比如很多积极分子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信仰者,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宗旨、纲领也随之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在阿隆看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内部派生出很多替代宗教的企图,但是基本已失败告终,斯大林主义获得成功也只是基于革命的胜利而并不是在思想深处征服了左派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的宗教色彩在阿隆看来也存在多种不可能性,也就是说,阿隆觉得左派知识分子不该在冷战时期盲目地接受源自苏联的左翼思想,更不应该狂热地将这些并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当作知识分子的宣言书。总而言之,走向宗教的知识分子在阿隆看来让人可怕而又可怜。
实际上,讨论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意在说明1950年代初期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和世界左派知识分子的异化问题。冷战初期,全世界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各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尽相同,他们有的向左靠,有的向右靠,有的则两不相关,作为右翼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阿隆将矛头指向左派知识分子的狂热、幻想与不切实际,认为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都赋予了纲领和口号,是典型被左翼意识形态异化的结果,而实际上最应该关心的是小到本国大到全世界的现实问题所在,只有将这些问题解决好,世界才会有进步的可能,既然无论左右都是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那么为什么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进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隆对于知识分子的担心不无道理,即使放到当下,这种言论也掷地有声、不可轻视。
“政治神话”、“历史偶像崇拜”和“知识分子异化”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三个关键词。回过头来,我们再重新思考阿隆在本书序言中抛出的那三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在法国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法国大获成功?世界知识分子的处境如何?其实,针对这三个问题阿隆给出的是同一个答案,也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也就是知识分子受到鸦片的驱动使得当时的思想界弥散着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即使这样知识分子也对鸦片情有独钟。但是知识分子的鸦片究竟何指呢?阿隆也在书中给出了答案: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阿隆借用这种观点指出意识形态是当时左派知识分子的鸦片,知识分子幻想政治的神话、对历史的偶像崇拜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其实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既可以让知识分子成瘾又反过来毒害知识分子的鸦片,意识形态并不能统治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不能称为世界的唯一尺度,如阿隆所言,“同一种工业文明在地球上的传播,以一种明显的悖论方式,赋予当今不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独特的特征。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由于对这些独特性毫不了解而谬误百出”。(雷蒙·阿隆:291) 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将生活和时代想象的过于美好,甚至把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和信仰无意识地强加给自己,去建构一个神话般的乌托邦世界,而往往忽略了脚下的现实,其实现实才是走向终极价值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永远都是一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