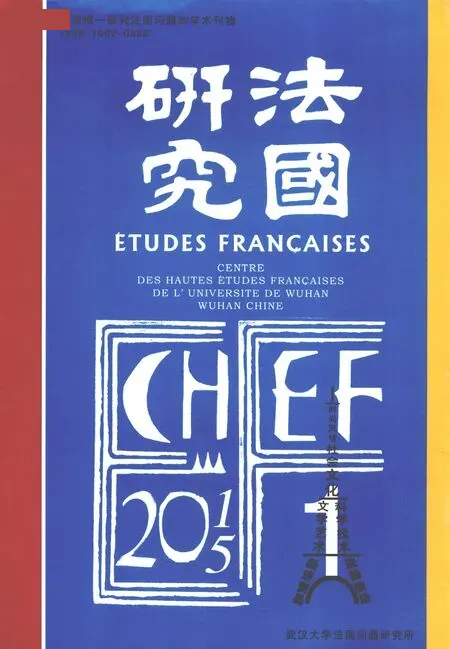亚洲职场上的文化碰撞(一)
讨论:Bernard Ganne 吴泓缈
引言:王战 翻译:黄珊珊
引言:社会人类学注重田野,用纪录片的形式直接拍摄事件研究之,这一方法在欧洲始于20世纪60年代。摄影行为在社会学中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介入,介入分本位和他位:记录是本位的,记录中的取舍是他位的。
本文的最初形式是一个用于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纪录片,原名《亚洲职场面对面——不同文化观的碰撞》。它共有三个篇章,每篇章由两部分构成:现场拍摄的文化碰撞,事后对碰撞的阐释和讨论。里昂二大的GANNE教授作为局内人用“本位”角度描述现实,武汉大学的吴泓缈教授作为局外人以“他位”视野解读现实。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看重的过渡。
跨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关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习惯于西方抽象模型的GANNE从事实出发,力求突破形而上的思维;受中国文化熏陶并接受西方教育的吴泓缈却往往借用西方理论来建模,以解读和阐述东西方文化的间距。他们的对话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或思想的碰撞。
另外,《亚洲职场面对面——不同文化观的碰撞》已被法国20多所大学的经管学院、社会学、人类学或心理学专业选作教材,中国某些大学的商学院也有将其作为参考教材的。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 王战
纪录片录音稿
序幕 : 介绍
Bernard Ganne:里昂二大里昂人类科学院马克斯·韦伯研究中心社会学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吴鸿缈: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语言学教授。
Bernard GANNE :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部纪录片,它名叫“亚洲职场面对面”。事实上这是在中国和亚洲的一些企业里拍摄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片段,然后进行评述和讨论。
吴泓缈 : 好的。
Bernard GANNE:……你任意说,就从你武汉大学语言学教授的角度出发。而我呢,作为一个法国社会学家,虽然做了这项工作,但对里边的一些东西还没完全弄懂。实际上,这张光盘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跨文化障碍的,谈人们在工作现场遇到的一些情况。第二部分更多地谈人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日常问题:如何安排时间,与上司的关系等等…… 至于第三部分嘛…… 自然会谈到不同文化的冲突,当然它们之间也有配合与协作。
吴泓缈 : 我明白。
Bernard GANNE : 这是影片的三大篇章。每篇章里有很多不同的场景。我们先来观看第一篇章的第一场景,这是在日本的一家法国企业里发生的场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位日本高级职员在谈自己对法国同事的观感。
吴泓缈 : 好。
章1 障碍和误解
1.1 在技术领域
电影剪辑
东京
竹中雅之
视频开始
日方经理 : 当时,我几乎天天和法国同事吵架。我试图解释日本的需要。我试过了,不知能不能成功。反正我尽了力,用一些他们可以理解的逻辑来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关注细节。在有些事上,我想我成功了;在另一些事上,我想法国人至今还是弄不明白。
(…机器的声音)
日方经理 : 在法国,人们根据功能用途来判断零部件的质量;而在日本,人们根据尺寸精度来判断质量好坏。换句话说……
BG (即Bernard GANNE,后同): 你可以稍稍展开这个话题吗?
日方经理 : 好的。换句话说,在法国,这个零件的作用是保证油路畅通,那么只要能保证油路畅通不漏油,同时也符合我们提到过的“拔出力”标准,那么这个零件它就是合格的,就能通过质量检测。在日本,质量检测实际上首先看尺寸:他们把该产品分解成各个部分,然后根据我们提供的图纸和公差为标准对这些零部件一一测量:如果尺寸不符合要求,不管功能如何,零件都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我把日本人的这种观点或者说立场上报给法国总部,可我从总部法国人那儿得到的回答却是:“不,这个零件是合格的,因为它在功能上符合要求”。你说说,这是不是鸡同鸭对话,完全说不到一块去……
讨论:不同文化视角的交锋
BG : 跨文化交流沟通之难,这是一个例子。在上述场景中,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可能会认为在这样一个专业领域里,不应该有文化交流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领域,一个技术领域,技术标准已被规定,所以我们会以为我们在使用同一种通用语言,用同一种方式来解释一切。可结果呢?通过日本同僚给出的这个例子,我们发现,光规定标准是不够的,因为双方在诠释标准时各执一词,各有一套;日本和法国,诠释标准的方式截然不同:日本人更多地是根据形状、尺寸以及精度来判定零件是否合格,而法国人看重的却是它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在这一点上,我们眼前突然冒出两个世界,如果不相互解释彼此的出发点,不澄清各自实际上是如何建构规范的,双方就无法理解沟通。从社会学角度看,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会让人觉得规范没什么用,因为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总在不停地建构规范。功能=效能。当提到功能时,个人(流水作业上的工人)如果只看形式、准确性,就有可能在支离破碎的环境里感到气闷,并且工作的意义也被剥夺。
吴泓缈 : 你说得真对!就我个人而言,作为中国人,十分了解法国文化的中国人,我也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东西。比如说,关于形式和意义的对立。我是学语言学的,所以,对我而言,尺寸与功能的对立,就是形式与意义或曰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体与用的对立。因为功能就是用处:制造一个零件,是为了让它起到某种作用,做某件事,达成一个目的。这个零件好,是因为它功能好,这是从法国人口中说出来的,可我怎么就觉得这句话应该从一个中国人或一个亚洲人口中说出来呢?我始终认为你们法国人崇尚形式的尽善尽美,在语言学或美学中甚至说没有形式就没有意义,这是欧洲思想区别于东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奇怪的是,在这里角色互换了,法国人更看重功能、用处、意义,日本人更看重尺寸。
这个例子说明,武断地说亚洲人是这样的,欧洲人是那样的,是有问题的。拿法国人和日本人比较与拿法国人和中国人比较,就大有不同。我想说,我们建立某种参考要素,比如说一边是形式,一边是意义,那么法国人可能站在意义或曰功用一边,日本人站在形式或曰尺寸一边,但我们中国人则一定会极为看重意义和用处,我们有时甚至根本不把形式当回事。不知道在此对形式和意义进行一些哲学思考是否合适。在语言学里,我们很早就发现很难对语义做研究,语义研究停滞不前,我们只能在对语音和形式的研究上取得进步。如果我们回溯到上古时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谈造型艺术时,就说形式和材料之间有一种依附关系,从来都是形式占上风,是形式赋予材料以灵魂。
BG : 形式向我们传递信息。
吴泓缈:对,是形式向我们传递信息,是形式让原本“无形且无意义”的材料成为艺术品。如果我们继续深入,我们会发现在这一领域,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重实效,我不是说完全一样,但至少,法国人比日本人更重实效。
BG : 我认为有趣的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完全跳出了跨文化交流,日本人会这样,中国人会这样,法国人、西方人会那样。由此,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某些因素跟其它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如精确性和功用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说书写形式跟语义之间的关系,你说的那些比较零散的东西和那些相反地更加标准化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用来了解不同文化的工具,即我们在形式和内容之间,以及功用和意义之间找到的平衡。正是这些因素可能能够让我们理解或者在某些时候用这样一种尺度来看待某些不同文化,而不是用另一种尺度。正因如此,我们能够一起工作,因为影片开头的那位日本人提出的双方像在打架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不理解彼此,双方同为工程师却无法相互理解,因为一方强调尺寸的重要性,而另一方强调的是功用,只要我们一直无法明白我们需要的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走进另一种逻辑思维的多样化的企业建设,不明白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两种逻辑思维,我们就不能共同进步,就只会发生冲突。
吴泓缈 : 你说得对。我不清楚能不能这样说,即一边是形式,另一边是意义,一边是功用,另一边是尺寸,两边相互对立。但在某些时候,某一个特定时刻,在某一个特定背景下,会存在一种恰当的分寸感(mesure),二者之间的分寸感。我之所以用分寸感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在古希腊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且一直沿用至今。实际上,中文里孔子说的“中庸之道”也有这个味道。分寸感很重要,不过分寸感和所谓的“正中间”还不全是一回事。是看重这一面还是看重那一面,这种选择由文化决定,甚至是无意识的,即人们忘了对此进行反思。正因如此,文化间才会有种种出人意料的冲突。
BG : 并且各自有各自的分寸。
吴泓缈 : 对头。当然,总有某种走极端的形式,比如说某个文化特别看重某个要素,甚至完全忽略其他要素;我们无意识地受到某种思维定势的支配,顽固的思维定势,如果这样说你觉得更合适的话。
BG :是的,这种顽固的定势深深刻在我们心中。我们接着往下看?
吴泓缈 : 好的。
BG : 现在摄影场景移到中国,这一部分涉及到办理行政手续时所发生的文化冲突。
1.2. 行政领域
电影剪辑
影片开头
圣热朗女士 :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怎么说呢,是让我的同事们明白在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多同事在美国或在欧洲工作了很长时间,于是会有某种固定的思维和行为,但他们对此却毫无意识。不知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打个比方吧:免疫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规章条例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在市场上推销产品,营销又应该是那个样子的,这不用说大家都明白,都同意。但在中国情况却不太一样,有人这样做并不是故意给你找麻烦,也不是看你不顺眼,但事情就是不太一样。
我有过登记注册的经验,当然是在欧洲,好吧,也可以说是在法国或德国登记注册的经验。如果有人告诉你,登记注册须分三步走,那我们就分三步走,我们不会觉得这程序有什么问题,既然这样规定,就一定有它的道理。于是我们注册成功。可在中国,如果人家跟你说同样的话,老实说,那就很可能有别的意思。好吧,法律有其条文,执行方式有其规范,但实际上情况却很可能大有出入。
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涉及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你去南昌看过,情况很糟糕,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我的欧洲同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是的,我们必须建立良好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这样才能让南昌厂获得继续生产的许可证,中国法律要求在2005年底把它做好,于是欧洲人认为,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拖到2005年底。唉,但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因为这是一项五年前就已颁布的法律,而且已经执行了五年。如果你六个月后就把管理规范做好了,那你就是一流的;如果你过了一年才做好,也行,只不过你的质量管理被认为是二流的;如果你等了三年才作好,那你的质量管理就只能是末流的了。现在距离截止日期还有一年半,质管部门就不理解了,“你们咋还不交材料”,他们对我们说。
(BG : “你们在做什么? ”)
“你们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一家外国公司,你们说你们公司的质量最好,有最棒的企业管理,有最好的这,有最好的那,可你们到今天还没有交材料,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觉得我们这是不配合,是傲慢;也就是说,你瞧,不把他们这些职能部门当回事。而我们欧洲人,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在欧洲,人们会说:“你别急,期限不是还没到吗?我们正在尽力做到最完美,赶造一个特别的实验室,可以大大提高工厂效率,你会看到一家最棒的工厂,等等,等等。”
讨论:不同文化视角的交锋
BG : 这是第二个例子,跟第一个有点类似,在办理行政手续方面,较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还是跟标准有关。我觉得她很好地表达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规范虽有条文,有字面意思,但实际操作又是另一回事,具体操作有可能很不一样。总有一些没明说的东西,甚至是被一种文化认为无需明说的东西,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意识,搞清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无法走出困境。她说的很清楚:“西方文化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意识中的影响,让我习惯了西方的行为方式,习惯了法、德等国家的行政运作,清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可行的。但现在,面对貌似同样的文字规定,我却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总之,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行为编码,是这套行为编码在背后决定我们如何对待法规文字,并对其进行阐释或应用…… 这一点,很有深究的必要。”
吴泓缈:上述说法很有内容,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深挖。首先,对我而言,是人与文本的关系,好像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很不一样。例如,在你们的语言里,一旦有了某种概念,就必须对它作精确定义,否则这个概念就不能算真正的概念,或曰清晰的概念。对一个法律的概念而言,定义就更是不可或缺了,你说对吧?
BG : 对,完全正确。
吴泓缈:面对一个概念,你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给定义。但在我们汉文化圈,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也可能给定义,但定义是否那么严格,那么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规定,即充分性与必要性,就两说了。在给定义时,我认为我们汉语所给出的定义不会像你们的语言那样准确。所以呢,为理解一个词,我们通常会先去找这个词的反义词,然后再看哪些词与之相关,然后再联系上下文对其进行解释。当然,对于法语概念,这样做也是可行的。对你们而言首先是定义,对我们而言首先是语境。我们先看该词的上下文,然后看它与哪些词发生关系,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以为自己理解了,可以进行操作了。联系上下文当然重要: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一个概念、一个词的字面意思,因为一个词总会因不同语境而生出种种含义。其次,比如说法律中的一项条款,或者高层领导人颁布的一项政策,中国这么大,这项政策或者这项条款能够适应每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吗?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异真的很大,有时这种差异甚至会超过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差异。这个时候,每个聪明的地方领导人会习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读。……
BG : 恕我冒昧,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法国人十分重视用语言文字来描写或规定现实,崇尚用尽量准确的文字来表述来定义法律。当法律对现实的表述或规定不够准确不够完善时,我们再增加新的条文,依靠更精确更繁多的文字来描写或规定现实。……
吴泓缈: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第一场的讨论。是否很好地执行了一项政策或一项法规,到底用什么来评判?我们认为是根据它的效用或功用来判断。我执行同一政策,然后我取得了好的结果,我做得很好,尽管我把政策改了一点(尺寸不对?),尽管我以另一种方式解读了该政策,但是我有好的结果。评价一项政策好坏的根本和最终标准是它的功效。然后再来说说与法律文本的关系。我不能说我们中国人不寻求用文字很好地描述真实情况,反映现实,我们也力图做到这一点,但问题是我们没有精确定义的传统,没有这个习惯。通常情况就是这样的,与一些没有欧洲文化背景的朋友和同事们讨论问题,常常用的是同样的概念,说的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没有定义的习惯,所以我们的讨论很难深入。
BG : 而且每个人对概念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说,我们法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把一个概念单独拿出来,想它究竟指什么,思考如何给它一个精确定义,这个概念在我们这儿首先是孤立的,于是我们有可能吃透它的含义,是这样的吗?
吴泓缈: 完全正确,正是这样的。
BG:是啊,如何建构我们与词语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说我们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方式。
吴泓缈:说得太对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甚至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对一项政策,一条法律条款,我们缺乏对文字的尊重,我们很可能肆意解读。作为一家外国企业,即使你们非常尊重了条款原文之义,那也没用,因为我会根据自己的方便来进行解读,而你却想不到我会这样解读;你必须站在我的立场上来想象,也就是说你必须移情!或者,即使你们不太尊重条款原文,我也可能放过你们。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法律文字条款的阐释上往往会出现问题…… 但这绝不是说你们严格遵守文本就一定是对的,永远是对的,就一定没问题。我无意谴责任何文化,我想说的是每种文化都有缺陷,大家应该思考别人的文化好在哪里,从中受到启发。
BG : 是的,这是两种有本质区别的方式,是这样的。
吴泓缈:没错。
BG : 想要准确抓住或圈定现实,这努力或者说这逻辑可能有点狂妄自大。相反的逻辑应该是,始终试着把事情纳入它自己的具体环境,有意留出一些“模糊余地”,模糊余地给后面的调整提供方便。
吴泓缈 :你说得很有道理。
BG:你上边讲的这一段正好适用于前边那家等待审批的法国公司。的确,该公司老老实实地按字面义来对待审批,为让管理机关满意,他们在审批期限到达前尽量完善自己的生产质量体系,你还记得她是怎么说的吧:我们一直要努力到最后一天,尽量利用所有属于我们的时间,对生产设施精益求精。中国行政管理部门的话语却是:我们好意让你们了解审批内容和期限,所以你们越早答复我们就越觉得你们有诚意有能力。结果呢,他们二者各按各的想法行事,想当然地表达善意却被对方当成蔑视,最后误会对工作进程产生极大阻碍。
吴泓缈:我也不敢说一定是这样,我不是企业家,没接触过这类事物,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只能作一些假设。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设我是一个地区的领导,然后有一家法国公司来我区落户,自称水平一流,技术领先,听到这些话我肯定非常高兴,但我有可能希望你们立刻就能证明你们技术领先,我需要证明。因为一方面,我对本地区又有了一家高新企业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我可能想马上把你们公司的情况报告给上级。于是呢,你们要申请许可,我当然支持,给你们一段时间准备,我可能会做出一个判断,认为这个期限对你们来说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会等,耐心地等。但你们若是拖拖拉拉的,这未免会令人生疑,甚至让上级对我生疑,法语是这样说的吧?
BG : 是的。
吴泓缈 :种下怀疑的种子。
BG : 拖拖拉拉肯定导致怀疑。
吴泓缈:对,导致怀疑。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认为你们没有必要拖延,可以早点为什么要拖到最后一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真是一家高质量企业吗?莫不是有其他想法?到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BG : 她的说法走得更远,因为她扯到“傲慢”上去了:“你们不想把材料交上来,你们自认为是最好的,所以有意拖延以显得与别人不一样。”这对主管机关来说就是傲慢!
吴泓缈 : 谢谢你重新提到“傲慢”。到这个时候,你们还不交材料,是因为,我甚至要说,是因为你们不拿中国法律当回事。
BG : 没错,产品质量这么好,是不是可以不太遵守法规?这当然是傲慢。
吴泓缈 : 是的,我肯定会觉得被轻视了。
章2 日常工作
BG:现在来看第二部分。这部分更加侧重于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问题。对活生生的事例——与上司的关系,面子问题等——进行反思。让我们一个个地来观察。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日本人,他谈他自己的经验体会。
误会与隔阂
2.1. 上下级关系
影片开头 :(日语)
东京
大桥裕一: 比如说,在梅里亚(Merial)这样的公司里,当我们和总经理或某个领导一起开会时,我们一般不会发言,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或看法。基本不会!日本全薬工業(NIPPON Zeniaku)来了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事实上,在日本,只要领导人在场,我们一般都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礼貌地应答,不会深谈自己的想法。在合资企业里,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但德·圣马克先生来了,他一来就开始直接这么问下属:“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对那个问题怎么看?”
毫无疑问,他如果不这么直接问我们,我们什么也不会说。
影片结束
讨论:不同文化视角的交锋
BG : 瞧,这位日本人向我们解释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文化群体的行为方式有多不同。他谈到了跟领导的关系,特别是在合资企业里,有日本人也有法国人,这种不同就显露出来;他解释日本人是怎么开会的,可能你们中国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开会的,过一会你再给我们讲讲。只要领导在场,日本人就有保持安静的习惯,他们习惯不说甚至不敢在领导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会对两种文化的交流造成一些困难,比如说那位法国管理者来到合资企业,他不一定了解日本人的习惯,于是便开始向每个人询问他的看法。这位日本人解释说,一开始他对此很不习惯,因为这完全不符合日本人开会的习惯,违反了他们在集体活动中的隐性规范。不过最后他又说他很欣赏法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但还是认为这样做对上级有点不敬。那么我们如何解读这个案例,即如何融入团队如何面对权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法国体制通过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更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但与权威与领导的关系和中国人、日本人却大有不同。
吴泓缈:这个我不敢断言。深究的话,再深入一点的话,我会说每种文化在某个领域都会有自己的编码,这个需要进一步观察。比如说关于开会这件事,我会问在工厂里会不会有一些常例性的会议,比如说有两种会议,一种会每个星期开一次,开会时日本人也征求工人们的意见:“大家同意吗?”“同意!”那就ok了。
BG : 这是一类会议的规定。吴泓缈:工人们必须发表意见,这是这类会的要求。但在一个车间里,会议的性质是车间主任布置任务,在这种会上工人们当然无须发言;主任发号施令,工人们执行之。之后来了一位法国厂长,非要征求意见不可,这当然……
BG:不合规矩!
吴泓缈: 这令人惊讶。不过我说的这个编码只是假设,我不太了解日本文化。按照这个假设,在后一种会上我们是不允许发言的。如果那个时候你发言,当然就是冒犯,就是不尊重领导,因为在此情况下惟有他拥有上传下达的权力,拥有布置任务下命令的权力。
BG: 的确是不尊重领导。
吴泓缈:就是如此。当然这行为编码很可能也与社会性质即父权社会有关。据说在你们民主体制里,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想发言就有权发言。但在父权体制里,随便发言会被认为是不尊重长者,不尊重长者后果会很严重,因为社会是由等级建构的,所谓上下有序,破坏等级就等于破坏秩序,毁坏社会,你说对不对?
BG : 秩序高于一切,带有强制性,人人都必须遵守。
吴泓缈:的确是如此。于是两种行为方式,两种行为编码发生冲突,相互碰撞。
BG:下面进入下一章:一位中国女士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