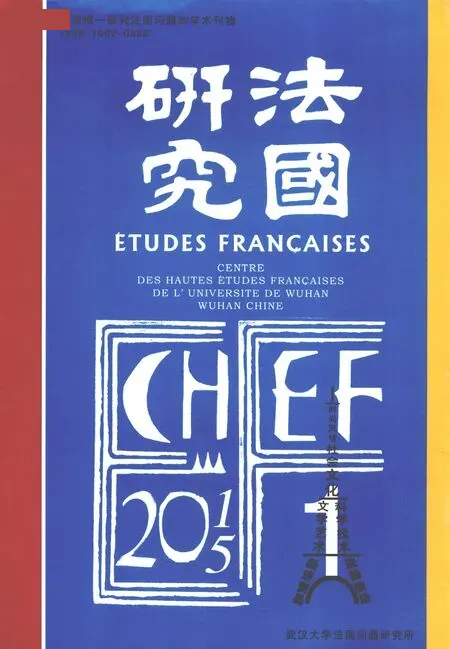管窥近代法国政治文化特点及成因
于艳玲
提起政治文化,每个国家的表现是不相同的,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说法:面对一头大象,上帝让这星球上每个民族的人写出一篇描述性论文。于是,德国人写出厚厚一本书,题目叫《大象在生物学分类中的位置及其哲学意味》;英国人也写了一本书——《论大象的绅士风度》;法国人写的是一本小册子《大象的爱情》;日本人写得最厚,总共写了三大册《大象研究资料汇编》;最后轮到中国人了,中国人很简约,很概括,大道至简,写的是《象、相、像考》。这虽说是个笑话,而它反映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和本质。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有着明显的“模糊性”特征的政治文化呢?
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阿尔蒙德曾对政治文化做过经典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①柯黎鹏:“法国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科教导刊》,2010,第1期,第160页。从政治文化入手,我们才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中与众不同的一面,了解法兰西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政治的“态度型式”,才可以从诡谲多变的历史事件中,发现其与众不同的民族心理特质和文化特征,看到它对政体框架和国家发展的影响。
一、法国的政治文化特点
从法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政治文化特点,他们“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常常容易耽迷于不切实际的空想,陷入非理性的狂热”。①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10页。法国的民族性格在大革命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攻陷巴士底狱,将国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热月政变后恢复帝制,每一次事件无一不是浩浩荡荡、热血澎湃进行的,他们“爱走极端”,不受控制,将血腥、恐怖、暴力发挥到极致,在革命口号和理性原则的刺激下,他们将心中对现实不满的怒火发泄到自己的行为中,群体的盲目和无意识地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不同阶级轮番上台执政,采用不同的政体,直到拿破仑恢复帝制。但毫无疑问的,正如高毅在《法国式革命暴力和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里所说的,“这种革命的结果带来了专横的意识形态统治,或者说带来了一种集权统治”。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三面环海,不仅有海上交通的便利,而且还充分享受着大西洋的暖流和地中海的阳光,不仅拥有高山和丘陵,更拥有大片平原和耕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交通环境使得法国很早就成为欧洲的思想、政治和文化中心。法国较早形成民族国家,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因此悠久的历史传统使法国的政治学说、运动和制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马克思曾说:“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重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②[德]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三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法国政治制度之所以充满了典型性,源于大革命中人民大众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革命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他们的参与构成了法国激进、热情、理想主义的政治文化特点。具体说来,法国政治文化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激进主义
法国自从1789年到1870年,短短的八十一年中,法国竟爆发了四次革命,经历过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帝国制、民主共和制的频繁更迭。起义,恐怖,革命与反动,内战与卫国战争,把近代法国搅得天翻地覆、满目疮痍,大革命的浪潮没有为法国带来稳定和繁荣,相反,革命却助长了一种激进倾向,打着“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旗号衍生出一种不断破旧立新的热情。大革命创造出一种对起义的幻想,使法国人两百年来不断想通过造反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法国人在骨子里不甘于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的现状,这种不满足就像一堆干柴,一遇到火星便会形成难以扑灭的火焰。与英国人不同,法国人缺少改革和妥协的文化。在法国,一方面是崇尚社会战争的社会要求;另一方面是热衷保持现状的政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很难找到进行深刻改革的空间。”①邝杨、马胜利:《欧洲政治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18页。
(二)对平等的热情
法国人的热情体现在他们对平等的热情,促使革命者与旧世界彻底决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法国人想在自由中获得平等,如果在自由中得不到,他们宁可在奴役中得到它。也就是说,在法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平等的价值远远高于自由的价值,为了平等,宁舍自由。但是,“这种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平等观念显然是虚幻的,这种超阶级的狂热,脱离现实的绝对平等,反而会抹杀自由的价值,使人们求助于某种权威的力量。”②王海涛:“浅谈政治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英、法、美三国为例”,《法制与社会》,2009,第2期,第197页。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政体从君主制被推翻,到建立君主立宪,再到共和制,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专制制度。
有一段在大革命时期耳熟能详的歌谣能够反映这种对平等追求的狂热:把高个儿截短,把矮个儿拉长,大家个头一般高,人间天堂乐无疆。旧法国封建特权的典型性和顽固性,导致了法国革命平等观异乎寻常的绝对化,但这种平等的绝对化又充满着危险性,因为这种绝对化的平等观不仅极其虚幻,而且很容易危及资产阶级本身的安全,资产阶级在实践后不禁惊呼与感叹“绝对的平等是一种空想”。
(三)理想主义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需要有良好的组织和动员,需要有充足的思想舆论准备和社会基础,而法国的文人们正好担当起这一职责,大旗一挥,民众云集响应。这些文人们大多都对封建专制制度有着一种深切的痛恨和排斥,他们义愤填膺地批判社会不平等,怒斥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压制和罪恶,同情人民的疾苦,沉湎于理想社会,虚构未来世界的美好,而且这种情绪越是慷慨激昂,越能引发人民的共鸣。“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致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③[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187页。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会怎样,他们终于在精神生活的世界里建造起来那个理想国家了。
二、法国政治文化形成的因素
为什么法国人的行为如此冲动激进,缺乏冷静呢?为什么法国不像美国那样,在革命的洗礼下,变得自由和富强,却加剧了政体的动荡和骚乱?这主要是还是因为法国对政治的设计多是纸上谈兵,存在着明显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脱离的现象。不像继承英国模式和英国经验的美国人,法国人光靠启蒙思想家的大声疾呼,在文学之士锐利的笔锋下一味批判社会现实,倡导“公意”、“自由平等”,脑海中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在模糊、抽象、先验的理性原则和理想主义的指导下,他们斗志昂扬,易怒且具攻击性,宣告与旧制度势不两立。“由于法国人沉浸于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政治观念从而缺乏政治实践,更由于它对公意和纯质性、透明性政治的追求使其反对一切政党和中间自治组织,致使法国中间自治组织的严重缺乏,没有这些中间自治组织的活动,正如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所阐释的,参与型的公民文化是很难形成的”①柯黎鹏:“法国政治文化观念中的政治”,《教科导刊》,2010,第1期,第160页。,也使法国社会产生出极端的分化现象,一旦民众参与革命,他们会任由脑海中的观念胡作非为,这也体现了法国政治文化中激进、热情和情绪化的特点。具体来看,法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启蒙运动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无疑是革命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对 18世纪欧洲秩序的影响非同小可,可从革命的结果来说,它是一次失败的革命。它的失败源于它政治经验的缺乏却又喜爱幻想追求完美的政治文化属性,启蒙运动为这种理想主义和追求完美的情愫奠定了基础。而作为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文人们反感君主政体,极力将统治者的经验从国家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知识和幸福没有完成联姻”,但这种做法却赢得了法国人民的青睐。那些从不卷入日常政治,没有丝毫权力,也不任任何公职的文人,如今放弃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开始关心与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由于决心要与旧制度决裂,文人们坚决抵制旧的国家机器和政体形式,不断尝试探索新的政治方案,于是出现了政体更迭频繁的现象。其中,以卢梭为代表的“公意”、“主权在民”理论深入人心,他的学说强调“先验的政治的道德性目标”,其批判社会异化的理论和为反异化而建立理想国的主张点燃了法国民众们建设新制度、摧毁旧制度的热情。在卢梭的思想中,他对政治实践并不推崇,还认为统治者和个人之间的“中间人”会影响公意的表达,因而,不承认政党、利益集团等中间团体的合法性,以至于法国的政党、利益集团等组织发展欠缺,如政党体制不完善,无法形成稳定多数派,利益集团数量也较少等等,这样他们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公民的政治参与。另外,他反对代议制,倡导直接民主制,认为总统是全体公民选举出来的,是公意的代表。这些观点都引导了法国政治观念的倾向,使民众更为相信政治理念,而不是重视政治实践。约翰·亚当斯曾评价这些启蒙思想家,说伏尔泰是个“撒谎者”;卢梭是个“纨绔子弟”和“好色之徒”;乌托邦理论家孔多塞是个“骗子”和“白痴”;达朗贝是个“寄生虫”和“虱子”;杜尔哥是个缺乏“判断力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他们不仅对持续大民主制度的创造没有任何贡献,还在把历史推向后退。②[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55页。这种评价是片面的,但是确实体现了法国人过于理想、追求完美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质。
(二)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体制的影响
对于中央集权制,托克维尔曾说它“不是大革命所带来的,而是一种旧制度的产物”,“只有它才能维系大革命所建立的新社会”。法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由来已久,“占法国人口四分之一的三级会议各省地处偏远地区。在这些省份里,仅仅有两个省真正具有自由权”,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除此之外,国王设立御前会议,将所有权力集中起来,是国王意志的代表,虽然御前会议有权力,但是“它从来不怎么张扬”,组成人员都是“身份卑微的小人物或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大领主”,同时作为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总监和作为外省代理人的总督,这些职位具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大多由平民担任,而不是掌握在贵族手中,这样国王便瓦解了贵族的统治权。国王通过官僚制将一切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权力触角延伸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控制着帝国所有人的一举一动。它使得所有阶级和所有的人都相互分离,为的是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统治。它高高在上,其他人只能仰望它服从它。正是因为法国人长期受专制主义的荼毒,缺乏政治权利和自由,它们便对旧体制产生出深深的仇恨和抵制,对于王权的高度集中无法容忍,因此并不像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相互妥协,也不像美国独立战争签订停战协定,注定法国人的革命是暴风骤雨式的。
另外,从革命中所追求的价值理念而言,法国人似乎更要求平等,对平等的渴望成为公民和社会的一致愿望,出于对平等的呼吁使公民在革命中有了相同的革命目标和任务。18世纪的法国,仍保留了中世纪界限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国全国居民被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其他人属于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的贵族、僧侣只占全国人口的2%,却占有全国35%的土地。托克维尔说:“18世纪的法国人民的处境比 13世纪的农民的处境更为恶劣”。恶劣的处境导致法国人对“平等”的要求特别强烈,其在启蒙运动中的口号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对自由的要求是伴随对平等的要求出现的,并不十分强烈,但是这种对平等的狂热而又畸形的追求,最终还是导致了一个集权政治的出现。
(三)无神论、不信教倾向的影响
无神论、不信教倾向也是法国民众热情推动大革命的动力来源。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除法国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均尚未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的、不宽容也不压制人的激情”。①[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190页。从历史上看,当人们对宗教进行强烈抨击的时候,这种抨击的热情大多来自对新宗教的忠诚,而“法国的民众带着满腔的愤怒去抨击基督教,但是并没有尝试用另外的宗教来代替基督教”。原因在于法国的文人们对基督教的极力反对。首先,教会用以管理自身的各项法则,是文人们想要在俗世的政府中推行的规则的障碍,教会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靠山和榜样,要想改变国家体制,就一定要把教会体制毁灭掉。其次,教会总是试图将政府的罪孽进行掩盖和漂白,让政治势力中的罪恶变得神圣,对教会进行攻讦,必定会引发民众的激情。再次,从文人们个人角度出发,教会的主要职责就是检查和管制他们的著作,并且每天和他们作对,因此,文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号召民众起来反对教会。最后,教会在法国是最明显最薄弱的一环,其将权力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制度基础上,根基不稳。正是文人们的提倡和大肆反对,法国社会掀起一股巨大的声讨教会的运动,无神论成为占据优势的热情。
无神论的影响,在托克维尔看来,不是“让人腐朽或者品格低下”,而是让人“精神错乱”。在宗教抛弃了灵魂的时候,并不会像通常那样出现让心灵空荡无所依的状况,而是让心灵在那一刻充斥着情绪和意志,补充了原来宗教所占有的空间,让心灵暂时不会沉沦下去。法国人不信教,但是他们保留着他们对自己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相信人类的美德。他们把这种骄傲自信心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诚然,骄傲自信心常常导致错误,但没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使人们经常胸襟开阔,不斤斤于一般人计较的秋毫得失。”①[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196页。有不少学者没有单独讨论这种无神论、不信教倾向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正好是法国大革命激进和热情的重大影响因素,这对理解法国人推翻一切的勇气和信念是有帮助的。
(四)法国社会结构的影响
法国的社会各阶级彼此分离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可是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希望改变他们处于相同附属地位这一情况,努力拉近各阶级间的距离,使其连为一个整体。托克维尔比较了英法两国贵族的不同,他指出英国贵族可以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做任何事,而法国贵族却依赖国王的免税特权生活,只保有名利,丧失了统治地位。而从法国的农民生活来看,他们遭受着最残酷的对待,相较于 13世纪法国农民的境况,他们过得更加悲惨,乡村里的农民一旦赚到钱之后马上跑到城市买官,有学识的人也尽量往城市跑,农民就这样和上层阶级分成了两部分,他们成为被抛弃的阶层,虽然不再向以前受到残酷的暴政,但是却也不会受到任何开解和帮助。他们享有自由权,但是他们的愚蠢程度跟他们的农奴先人不相上下,而在贫困程度上,他们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穷人和富人在共有的利益、怨言和事务差不多完全消失之后,二者从此就断绝了往来。法国贵族阶级执意要割断与别的阶级的关联,最终,别的阶级担负了绝大多数公众征税,贵族却一身轻,可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愈来愈低下,旁人对此一无所知,理都不理。资产阶级呢,他们虽然越来越富裕,成为一个有内涵的阶层,可是他们却一直跟农民和农民的贫穷保持距离,他们想创造不平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并未密切联系农民。资产阶级是从农民发展起来的,但他们却将农民完全当成了陌生人。当资产阶级把武器送到了农民手上时,他们才察觉自己已经在不经意间激起了平民阶层的热情,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掌控这种热情来做平民阶层的领导者,最后使得革命形势不受控制。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能力的欠缺和农民长久以来被隔离、被压迫的情况,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仇恨和无知加深,一旦他们被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其破坏力、其不计后果的做法,加深了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激进、热情和情绪化。
结语
思想、体制、宗教、社会结构这四方面因素,孕育了法国大革命激进、热情、理想主义的政治文化,造成了法国政治体制长期的动荡和不稳。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些政治文化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国人民的生活,对于塑造法兰西民族个性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但是,由于法国在面临全球化浪潮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其在本国国情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政体形式,使之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后形成较为稳定的政体形式,政治文化的特性还将延续下去,影响法国人的处事方式和政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