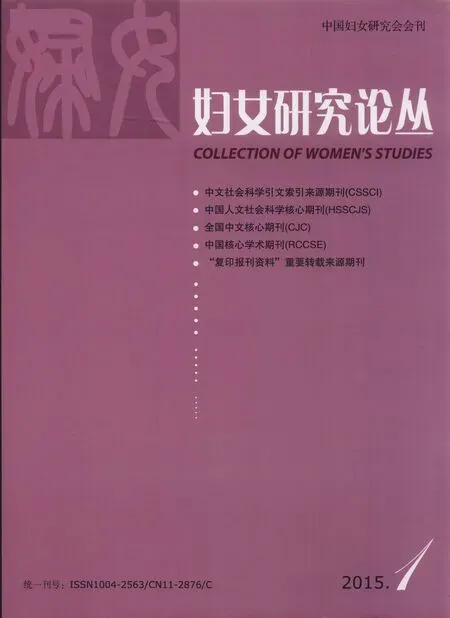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
——以女杰传记为中心的考察
[韩]李贞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
——以女杰传记为中心的考察
[韩]李贞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古典资源;晚清;女军人;“贬男”想象
近代报刊非常突出地运用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形式,在史实互构、古今相系、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古典资源与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联系。有关历史人物题材的改写蕴含着对共同命运的理解和启示,将感时忧国的现实情怀与民族意识融入其中,呈现了国民想象的形成与性别之间的多重书写模式。文章将女杰传记文本的改写段落还原到晚清的情境中,观照其与现实思考之间的关联,辨析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所蕴含的文化心理。
《女子世界》①《女子世界》于1904年1月创刊,月刊,1907年停刊,丁初我等人主编。该杂志的宗旨是“振兴女学,提倡女权”。是晚清一份重要的妇女刊物,在中国女报史上,将“传记”(史传)设置为固定栏目,乃自《女子世界》发端。许多传记打通了古典资源与现实革命间的壁垒,将古典资源中的传统女性形象提升到关乎时代政治、民族文化的高度上。如柳亚子(署名亚卢)的《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职公的《女军人传》系列。
一
晚清文人对女国民想象的重塑,摒弃了中国自古以来评价女性的传统尺度,颂扬了一种“女强男弱/妻强夫弱”的表象。他们在女杰身上发现并赞赏原属于男性的“雄强美”,有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在作品中以男性的庸懦作为反衬。这自是立论所需,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为女子张目的作用。下面以“斥夫”的女军人形象为切入口,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从韩世忠、梁红玉故事在民间的接受和流传过程而言,妻强男弱的倾向早在《说岳全传》中就出现过。《说岳全传》把韩世忠斥责秦桧谋害岳飞的史实移到梁红玉身上,小说中梁红玉全身披挂直入相府,对秦桧疾言厉色,大喝兀术为“番奴”,大怒中抡起手中刀就砍,为岳飞讨公道,吓得大奸臣秦桧也胆战心惊。[1](P345)
相比之下,韩世忠对皇帝的“忠心”被岳飞的光芒所遮蔽,梁红玉的义气和侠肝义胆则被大为宣扬,这多少体现了民间百姓的欣赏趣味和接受心理。梁红玉对奸臣的怒斥是普通民众对忠义、爱国等品质的变相认同,这种改写方式流露出文学的伦理化倾向。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梁红玉形象比韩世忠形象更为丰满、动人、突出,这种“女强男弱”基于对男性不能对时局力挽狂澜的失望。梅鼎柞曾以女史氏的口吻这样说道:“不贰心之臣岂复得辱以巾帼哉!则又何论于倡也!”[2](P75)梅鼎柞寄寓了对须眉不如巾帼的慨叹,这和晚清时期潮涌而来的众多言论基调相同,带有一种踔厉与雄强之风交融的悲壮感。
刊载于《女子世界》的《女军人传》对梁红玉、秦良玉等女军人形象的塑造,无不流露出刻苦己心的性别顾虑,并通过“斥夫”的情节来排除女军人从属于男将的性别等级关系。它无疑与新文学的现代性民族国家诉求密切相关。作者一再强调女军人/妻子对男将/夫君的威慑力,女军人的才识与胆略被刻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柳亚子增补了梁红玉呵斥男将的场景,怠慢、无能的男将形象衬托出梁红玉的勇猛、豪爽之气。文中写道:
声浪既及军士之耳,慷慨激昂,精神百倍,争致命前敌,杀人如草,虏骑死伤且尽。汉将从天,胡儿褫胆,兀术翘首乞怜,求得归死黄龙。世忠以还我中原相要约,红玉自后叱之曰:“贼种胡奴,罪大恶极。死则死耳,犹与效丧家之狗,摇尾求活耶?”鼓声益急,军威益振。而汉种公敌之虏酋,遂不得不瞑目以待藁街之诛矣。[3]
在金山战斗中,敌军将领向韩世忠乞怜的场景未曾出现在任何历史记载中,这一情节纯属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柳亚子增补了“兀术翘首乞怜,求得归死黄龙”,韩世忠便“还我中原相要约”,最终导致“失机纵敌”的情景。为此红玉斥之曰:“贼种胡奴,罪大恶极。死则死耳,犹与效丧家之狗,摇尾求活耶?”红玉对兀术的喝斥,语义双关地折射出对韩世忠的愤怒。这些被改写的情节微妙地反衬出男军人的龌龊、懈怠,在这负面形象的陪衬下女军人的正面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在人物形象安排和处理上,柳亚子将女军人与男军人相对而设,但更加强化和凸显的是女军人的“蕙质兰心”。女军人以天下为怀的爱国情感体现了“刻苦己心”的一片赤诚。传记文中,柳亚子对韩世忠晚年的描述沿袭了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骑驴隐士形象。他写道:“厥后秦桧兴谗,岳飞流血,长城自坏,三字沉冤。小朝廷之残山剩水,绝无复振之时。世忠拂衣而去,河上骑驴,不复加入政治之运动。”[4]
这里承袭了《双烈记》中韩世忠在忠奸斗争中失败,愤而隐退,“骑驴游湖”、“牵蹇驴携酒”等远离名利纷争、退隐山水的隐士形象,美化了这种闲居生活。柳亚子为梁红玉安排的结局则截然相反。相较于韩世忠“闲适”、“隐逸”的避世/出世生活,梁红玉则是“郁郁以终,蕙质兰心,化为黄土”的结局。
当兀术之被围于黄天荡也,红玉与世忠,以为猛虎在槛,孽龙入井,自无插翼飞去之理,时而激励将士,时而酌酒相庆,以直捣黄龙,为前途之希望。兀术亦自问必不能生出汉关矣。乃夜漏方半,忽有诣舟献策者。兀术大喜,遂掘河中间道而去。而红玉、世忠辛苦经营之奇计,瞥焉化为泡影。世忠裂眦冲冠,怒不可遏。红玉则唏嘘泣下曰:“甘心祖国之陆沉,而必欲为伪朝廷不世之功。皇帝子孙,乃有此不肖,失复何言!”盖光复旧物之雄心,至是而红玉亦自知其不过乌托邦之梦想矣。厥后秦桧兴谗,岳飞流血,长城自坏,三字沉冤。小朝廷之残山剩水,绝无复振之时。世忠拂衣而去,河上骑驴,不复加入政治之运动。而红玉亦郁郁以终,蕙质兰心,化为黄土。甘心异族欺陵惯,可有男儿愤不平?呜呼!女将军之心苦矣。[3]
关于梁红玉的结局众说纷纭,后世戏曲小说和各种话本都安排为梁红玉与韩世忠辞去军权后共同归隐山林,白头偕老,富贵余生。最后,梁红玉在韩世忠死后两年病逝,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这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根据邓广铭的研究,梁红玉在绍兴五年(1135年10月6日),随夫出镇楚州抵御金军入侵时,遇伏遭到金军围攻,腹部重伤,肠子流出以汗巾裹好继续作战。最后血透重甲,力尽落马而死。首级被敌人割去,金人感其忠勇,将其遗体示众后送回,朝廷闻讯大加吊唁。②据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二于绍兴五年八月丁卯条“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四两”。
可以看出,柳亚子对古典资源的取舍相当明显。他保留了韩世忠超然度外的隐士生涯,而对梁红玉则安排了因政治上的落魄与无奈而“郁郁以终”的结局,并且将这种忧愤情怀与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操联系起来。进而慨叹道:“甘心异族欺陵惯,可有男儿愤不平?呜呼!女将军之心苦矣。”[3]婉约地表现了梁红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片苦心”,刻画了淑美善良、品德高尚的女军人形象。这与通过“斥夫”场景体现的耿直、坦荡的豪气相辅相成,凸显了“苦死”的爱国者形象。
传记文中“斥夫”的女英雄形象,与“巾帼不让须眉”的时代呼唤有着必然的关联,与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需要吸纳女性力量的国家需求亦有一定关系。
二
晚清文人对中国古典资源的利用与借重,多取材于历史上民族存亡之秋,表现出各自所属历史阶段的文化特质。类似的描述在秦良玉传记中也可以看到。秦良玉是唯一被载入正史《明史》的女军人,晚清《女子世界》的《女军人传》中,敌军趁官军设宴夜袭的描述,别有韵味地凸显了秦良玉的战绩。这明显与《明史》的记载有很大出入。职公如此叙述:
明年正月二日,官军张夜宴。千乘酣饮张中,酒酣再飞白,亲割生彘肩。军士皆解甲,以为元夜夺昆仑,成功在指顾间,驰不为备,贼众奄至,官军自相残践。良玉率部下死士导前驱,奋与贼驱,奋与贼斗。时贼徒方谓蹴踏榆关,蹂躏全蜀,朱明偏旅,立为灰烬。见缝火光中,与红妆相辉映,相顾愕眙,不战而溃。良玉益肉搏而前,连破金筑第七寨。已偕酋阳诸军,乘破竹之势,直袭桑木关。时人谓潘州之后,南川路战功,以良玉为第一。[4]
与《明史》的陈述不同,秦良玉在丈夫“酒酣再飞白,亲割生彘肩”,其他军士也随之“解甲”、全军上下“驰不为备”时,“率部下死士导前驱,奋与贼驱,奋与贼斗”,成功败退了敌军的突袭。秦良玉立下赫赫战功,“连破金筑第七寨、直袭桑木关”。秦良玉使敌军“不战而溃”的威严与丈夫千乘“酒酣再飞白”而无济于事的无能形成对比。在关键时刻,男将军的失责/缺席给女将军创造了施展战斗力的机会。这一书写策略突破了女军人原本随夫从军的角色定位,拓展了女性在沙场上发挥作用的范围,其对丈夫的从属地位亦被淡化。如果与《明史》相对照,尤可看出用心良苦。《明史》中载:
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万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与副将周国柱扼贼邓坎。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5](P4644)
《明史》中,面对敌军的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秦良玉夫妻创下“连破金筑等七寨”、“直取桑木关”的赫赫战功。而作者职公将良玉夫妇的功劳改写成良玉一人的战功,这一细节流露出推崇女军人的心理。他以彰显女性能力作为主要旨归,并予以与之相应的调整和改塑。或许可以说虚构这样一种情节并极力提升其意义,实质上是民族/国家等集体话语在历史关键时刻对女性价值诉求的积极“赋义”。
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急切地需要义无返顾的女军人、女英雄。这与只有将女子纳入整个救亡事业,中国方能强大的政治觉醒紧密相关。“斥夫”的女性在救国与革命事业中成为有实力的参与者,奠定了社会舆论与自身素质要求的基础。“斥夫”的象征意义由此产生多重指向。主要是针对“吾国女子日趋文弱”的现状,强调女子要参与国族救亡事业,突出女子应尽的义务。对此,金一有过贴切的表述:“爱国与救世,乃女子之本分。”[6](PP11-12)这一点被用来强调“非以匹妇而仔肩国家之大事业者乎。我诸姑伯姊,其不可不崇拜之,我诸姑伯姊,其不可不师法之”。[7]
可以看出,晚清文人对“斥夫”的女杰所体现的爱国“真谛”十分崇拜。而这种抑男扬女的书写策略,同样表现在对西方善女子的描述上。女杰传记的作者采取叙论相间的方式,联系晚清时势发表议论,文中夹叙夹议,笔锋常带感情,凸显了雄浑豪壮的女杰形象。女杰“斥夫/贬男”的形象如点睛之笔,勾勒出其以国家为怀的英雄气概。
梁启超在《侠情记》③梁启超在《侠情记》中本拟写意大利三杰之一——加里波的,后来仅成第一出《纬忧》。它以爱国为主线,塑造了加里波的之妻——马尼他(1821-1849)的形象。此曲本为《新罗马传奇》中的片断。据卷末《著者自记》云:“因《新罗马》按次登载,旷日持久,故同人怂恿割出加将军侠情韵事,作为别篇。”剧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原署“饮冰室主人撰”,载于《新小说》第一号。④《世界十女杰》,未署作者姓名及出版信息,根据1903年5月31日《苏报》广告《〈世界十女杰〉出版》,推知其大约同年5月出版于上海。中假借马尼他之口向男性发难:“难道举国中一千多万人,竟无一个是男儿,还要靠我女孩们争这口气不成?”[8](P131)如此振聋发聩的责难,将矛头指向救国不力的男性,对其痛加指责。这些叱咤风云的女杰形象成为唤醒民众为了中国的独立与自由而呐喊的“启蒙”标识。“斥夫/贬男”的女杰形象令懦弱愚昧的男人们无地自容。她们为拯救祖国而表现出的高尚的思想抱负、坚定的斗争信念被视为“建光复之大业”的重要资质。“斥夫/贬男”的女杰形象所体现的雄强之美正是革命文学所期待的,因此柳亚子给“厉声骂敌将”的女军人冠之以“奇女子”的美名。
党中多女军人,群易健儿妆,战斗绝悍,迷离扑朔,莫辨雌雄,敌军勿能识也。今夏四月,清将谭某,攻一万山左右之村,村为党中女雄根据地,拒战不克,为敌军所擒,十馀人咸不屈死。党魁某氏女,年仅十四龄,艳如桃李,而冷如霜雪,拒斗尤勇,既被获,厉声骂敌将,慷慨就义,盖奇女子也。昔读《新罗马传奇》,尝叹烧炭党女侠不生于中国。今乃知皇汉人种,固非居人下者。特不知自今以后,更有马尼他起建光复之大业乎。[9](P182)
柳亚子对“厉声骂敌将”的女军人给予了无限的赞扬,同时也孕生了新的女性评价标准。这位无所畏惧、慷慨赴义的女军人是梁启超在戏曲《新罗马传奇》中虚构的人物。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取材于烧炭党人为从奥地利手中解放意大利而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业迹。他在剧中借扪虱谈虎客之口批注道:“俄罗斯之虚无党,闺秀最多,其荆聂之高者,大率皆妙龄绝色之女子也。烧炭党中有此等人否。我不敢知,……然以情理度之,未必无其人也。这位女首领在带领人们斗争时,不幸被捕入狱,可仍要‘今日里拼着个颈血儿,溅污桃花床。’”[10]
表面上看,这位首领没有奇巧谲智,也不身怀绝技,但她“将奸奴骂醒、把国民唤醒”的英雄气概与充当革命先锋无疑是崭新的女杰形象。她的发问更令人深省:“铁血关头,问须眉愧否,漫公愤落他人后。”梁启超批道:“吾续上,亦如冷水浇背。”[10]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为了更好地凸显女性与救国的时代命题,人们不约而同地将“斥夫/贬男”的女杰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精神塑像。这种自愧不如的言说方式,体现了人们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心理。“斥夫/贬男”的女杰与须眉救国难有着相近的情绪联想,勾勒出“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高尚品德。“斥夫/贬男”的强势姿态是反衬革命意志的外化表现,强化/巩固了女性为革命献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与号召革命的时代诉求一脉相承,通过文学形象的传递过程,这些“斥夫/贬男”的女杰成为推动革命进程的经典形象。
在《世界十女杰》④中也有马尼他“斥夫/贬男”的情节描述。马尼他始终以爱国为怀的一片赤诚经常让男将无地自容。她对士兵“叱之曰:‘妇人从戎,宜其鼓声不振’,妾今日誓与此舰存亡共之,无多言!”[11](P39)有时,译者将“斥夫/贬男”的言行作为表现其爱国情愫的试金石,“斥夫/贬男”的强度越大,越能证明其一片炽热的爱国情操。译者刻意增补了马尼他责备被誉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中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人物——玛志尼的细节。“少年意大利”党领袖玛志尼(Giuseppe Mazzini)因当时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的口号——娶妻当娶“苏菲亚”、嫁夫当嫁“玛志尼”而广为人知。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中把玛志尼说成为“天”所“诞育”的天才,是秉受“天命”来拯救人类免于受灾难的。如此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在《世界十女杰》中的形象描写竟远不如马尼他的爱国觉悟高。加里波的与玛志尼时隔十年于罗马相会时,二人“患难重逢,悲喜迸集”,这时在旁的马尼他带责备的口吻指责道:“今日相逢,是诸君救国之日,非宾朋话旧之时。”这让他们“不觉塞其咽,缄其口。”[11](P43)马尼他时时刻刻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迫切心理跃然纸上。在此,哑口无言的两位男将所表现出的羞耻感潜藏在视女性为“爱国正统”的意识之下。
三
在晚清言论中,女性常以负面形象出现,被描述为“国家贫弱的祸根”、“男子的累赘和奴隶”,“斥夫”的女杰形象将这种论点倒转过来,体现了对女性理想价值的重新确认与建构。由此,传统的女性史传叙述与时人的革命情怀紧密勾连起来,并为后者理论表述和实践的展开提供了鲜亮的历史资源。“斥夫”的女杰形象作为在清末民初对女国民这一社会身份的指认,包含了提高女性地位以改善国民素质的目的。晚清文人从历史沟壑中重塑/再创气度不凡的女杰形象,借女子“斥夫”的口吻厉斥“扶阳抑阴”的积习,与其说这之中表现了作者作为男性的劣势感,不如说这种正面论述反而建构了对新女性的想象及其新的性别规范。
这些令女性扬眉吐气的女杰形象,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文化表象,其背后有一种支撑这一形象的无形的时代精神力量。它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性别秩序的重整。
“斥夫/贬男”的女杰与被贬黜而悬置的男性,这种对比本身具有话语建构的力量。例如《沙鲁土·格尔侄传》[12]中,译者借女刺客之口指责晚清男性“负其七尺躯,以朝而食,夕而睡,问之以国之亡,种之奴,则曰,某一人其何能承此局”。译者作传时有感于男子无所作为,欲讨伐男子在国族危难之时,推卸责任,明哲保身的消极姿态,贬斥男子为“弱虫”。相反,沙鲁土以一女儿身,主动承担起刺杀马拉的救国大业。作者并借其未婚夫之口,激励男人们:“沙鲁土能以铁血为人作嫁,愧我须眉竟默尔而息哉!”一腔抱负、满腹韬略的女杰形象,贴合晚清时势,愤慨男子救国不力,痛斥面对国族灭亡“就是男子,也碌碌无为”的现状。
“斥夫/贬男”的女杰形象作为性别文化长期积蓄的能指,在不同女杰传记中得以延伸,作为爱国话语的文化传承与共享的资源被不断演绎。有关以仁慈博爱之心著称的南丁格尔的描写也不例外。《世界十女杰》中,南丁格尔到达克里米亚战场后,见到因受伤而痛苦流泪的士兵时斥责道:“诸君仅可以流血贺之,焉可以流泪践之?今日绞予脑血,拼予微躯,乃为爱国志士有所尽也,诸君焉可作此丑态以馁壮士之志哉。”[12](P50)如此掷地有声的训话,其意义并不止于新女性形象的建构与爱国精神的宣传,还包含着从一个侧面为巾帼英雄提供和追加合法性的意图。这有助于对救国至上的倡导,“斥夫”的女杰形象使原本男女两性之间强与弱的对立关系发生倒转,呈现了独立言说的女英雄形象。
梁启超在《罗兰夫人传》[13]中,夹叙夹议地衬托出罗兰夫人优胜于罗兰的出色表现。传记文中,罗兰因从“地方一小商务官”成为“内务大臣”而沾沾自喜之时,罗兰夫人“驱其夫,驱其他诸大臣,驱狄郎的士全党”,这种嗤之以鼻的态度主要是由于罗兰夫人看清了“将倾之路易朝”,所以在她的眼里“政府不过一酒店耳!大臣不过王之一傀儡耳”。《世界十二女杰》⑤梁启超版的《罗兰夫人传》(1902年)刊登之后不久,《世界十二女杰》(1903年)以单行传记集的形式出版,其中还包括“郎兰夫人”,即罗兰夫人。《世界十二女杰》,日本岩崎徂堂、三上寄凤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发行。该书叙述了法国沙鲁土·格儿垤、法国苏泰流夫人、美国扶兰志斯、普鲁士王后流易设等世界十二位杰出女性的英雄事迹。该书首开近代为女子作新传之风,该书出版不久,《世界十女杰》也紧随其后推出。更为形象地描述当罗兰临危逃脱时,夫人“大斥其卑怯”,然后自己“从容就缚,毫无惧容”。[14](PP1-2)
作为政客,罗兰不但胆识不如罗兰夫人,政见亦在罗兰夫人之下。罗兰夫人“以慧眼观察大局”,乃至于“法国内务大臣之金印,佩之者虽罗兰,然其大权实在此红颜宰相之掌握中矣!”罗兰夫人的高尚情操与深邃的洞察力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事实也证明,罗兰夫人不但善于应付乱局和党争,而且知人善用,若没有罗兰夫人的帮助罗兰是不会引人注意的。他所缺少的一切:毅力、机智、雄心、远见,都由罗兰夫人作了弥补。[15](P119)罗兰政治上飞黄腾达得益于罗兰夫人的精心运作。沉着机智、富于决断的气质风度以及处理政事的圆熟手段使她独具人格魅力。在天下混乱、群雄竞逐的局面下,政见与才识出众的罗兰夫人所展露出的“强势”特征,不妨理解为鼓舞女性积极参与救国伟业的政治动员与号召。因为梁启超关注与赏识罗兰夫人的超常能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以罗兰夫人之平凡无奇的出身背景为出发点,热情洋溢地抒发了“时势造英雄”的救国观点。他写道:“其家本属中人之产,父性良儒,母则精明,有丈夫气,父母借鉴储蓄,为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产罗兰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时势造英雄,而非种姓之所能为力也。”[16](P319)也就是说,这种能力不仅是罗兰夫人的个案,而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是只需有爱国热忱,就人人都可以具有的潜力。再如,亚卢(柳亚子)在《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一文中,强调英雄不分男女、不讲出身的道理。他说:“西哲有言,历史者,国民之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芝草无根,醴泉无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岂不信哉,岂不信哉。真德生于牧羊之舍,玛利侬产于雕匠之家,我木兰其比例矣。”[7]男性在指认女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方面极力铺衬女杰贬斥男性的强悍形象,一方面又渲染无名之英雄的时代召唤。男女对照的二元修辞框架时隐时现,这两组画面互相依存,表现了在男性言说与女性社会实践中求得平衡的叙事模式。“斥夫”的女杰形象因弥补由男性所造成的缺憾而变得富有意义和价值。
面对国势的危难,知识精英企图通过列举“出身平凡却芳誉赫然”的女杰事迹,来强调无名之英雄的历史地位,以弥补在世界权力格局中有名之英雄缺席的危机处境。也即是说,在性别类比的基础上,“无名之英雄”承担了成就/支配“有名之英雄”的角色,大力挖掘和发扬无名之英雄,寄托了女子像男子一样介入历史与社会事务的殷殷希冀。“斥夫”的强势姿态与无名之英雄的附庸地位通过相互支持和抵消,实现女性自我开解的寓意。随着国难日益加剧,为了营造普遍的救国氛围,男性作家们将女杰的内涵奋力推向了极致。“时势造英雄”的民族救亡思想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敢于担当与为国无私奉献的自我牺牲。“斥夫”的女杰在政治格局中反客为主,站在了革命话语的前沿,充当了这一自我牺牲的角色。
当然,这种“强势”并未改变两性格局中的男性主体性地位。因为那些品质优秀、爱国觉悟高的女性主动积极地投身于救亡事业的公共形象,不过是有利于号召女性成员为国献身。女杰传记中,男性人物尽管表现出被动、无能,但事实上他们才是革命的主导者。对此必须回到历史语境,才能接近文本意义的原貌。因为,“斥夫”的女杰形象涵盖了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男性与女性相激相荡的“作用力场”,是新与旧、传统势力和新生思想最先交锋的话语实践。
这种性别定位的身份建构是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囊括了多维度、多层面的女性意识。一般女杰的强势姿态仅仅是文本的表层,而文本的意义深层所指向的往往是对“须眉不如巾帼”的警示与告诫,作者用迂回婉转的方式暗示须眉才是主导历史的“有名之英雄”。刻意重塑强劲的女杰形象作为激励和鞭策男性奋发图强的补偿性机制,倾向于一种女性历史神话的建构,体现了独特而不无悖论性特征的性别意识。比如,在《精卫石》中,秋瑾借女主人公黄鞠瑞之口(后改名黄汉雄)骂尽天下男子:“见那般缩头无耻诸男子,反不及昂昂女子焉。如古来奇才勇女无其数,红玉、荀瀴[灌]与木兰,明末云英、秦良玉,百战军前法律严。虏盗闻名皆丧胆,毅力忠肝独占先。投降献地都是男儿做,羞煞须眉作汉好。如斯比譬男和女,无耻无羞最是男。”[17](P499)
这一优越感建立在巾帼英雄形象与须眉之间孰优孰劣的预设基础上,直接以对比的形式抒写大敌当前、男不如女的历史题材和事迹。当“奇才勇女”的功绩远胜于“男儿”的历史先例普照在晚清女性身上的时候,意味着对男性的鄙薄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女性以往低眉俯首的社会地位。
上文出现的木兰、沈云英、秦良玉等,都是秋瑾在诗文中反复歌颂和向往的英雄人物。她们在王朝遭受外族入侵的危机时刻,经由金戈铁马、杀敌立功步入英雄的行列。她们的“军人”身份较之于披挂上阵前显得更为强悍。同样,文本中表现的“斥夫/贬男”的女杰想象出于猎奇心理和文学的述异性质,指涉着民族主义话语对女性本体构成的特定、多重的形象改造和重塑。强势的女杰形象成为一个极具活力又不断发展变化的主体。这一形象的精微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抑男扬女书写的“名贬实褒”特质。强势的女杰形象作为一种隐喻手段,在这种想象体系中,男与女的强弱类比没有对立和冲突,而是处于永恒的互补、互变、互动之中。对“男弱女强”书写的强化与升华,一方面是“男降女不降”话语承递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在传播启蒙的“女豪杰”的精神指向中鼓动女性争取和追求个体的“独立”和“自由”。
晚清知识分子面对“沦为异族奴隶”的惨淡现实,革命的政治伦理以救亡名义言说着女性救国的合理性,这往往导向情感结构上的二律背反,即辛亥革命时期通行的“欲……,必……”的思维公式。[18]“岂男子独遭之境遇乎”/“岂男子独具之能力乎”/“岂男子独逢之怏事乎”等反问句,实际上在暗示女子应承担与男子同等的社会责任。即使是“斥夫/贬男”的强势姿态,也是反衬革命意志的外化表现。也就是说,“斥夫/贬男”的女杰形象也在凸显女英雄风范的思想脉络上,作为伸张女性地位的修饰语出现的修辞策略,这样做的目的一来为“国势积弱不振的病灶”清洗历史污点,进一步使“男降女不降”的话语变得切实可行;二来为女界表率,通过树立“强势”的女性形象为新女性形象的接受和输入提供了理想规划,在强与弱、褒与贬的较量和抗衡中,见证了晚清以来中国性别观念革新的曲折道路。
[1][清]钱彩等.说岳全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5.
[2][明]梅鼎祚辑纂.青泥莲花记[M].合肥:黄山书社,1996.
[3]松陵女子潘小璜(柳亚子).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J].女子世界,1904,(7).
[4]职公.女军人传[J].女子世界,1904,(2).
[5][清]张廷玉等著.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金天翮著,陈雁编校.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柳亚子[亚卢].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J].女子世界,1904,(3).
[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侠情记传奇[M].上海:中华书局,1936.
[9]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新罗马传奇[M].上海:中华书局,1936.
[11]世界十女杰(未署作者姓名)[O].上海图书馆藏书,1903.
[12]大侠.女刺客沙鲁土·格儿垤传[J].女子世界1905,(2).
[13]粱启超.罗兰夫人传[J].新民丛报,1902年10月第17号.
[14][日]岩崎徂堂,三上寄凤著.赵必振译.世界十二女杰[M].上海:广智书局,1903.
[15][法]米涅著,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从1789到1814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6]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
[17]秋瑾著,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G].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18]刘纳.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J].北京社会科学,1986,(3).
责任编辑:绘山
The Image of"Degraded Men"in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Late Qing:A Study Based on Biographies of Women Martyrs
LI Zhen-yu(Korean)
(School of History at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classical resources;late Qing;women soldiers;image of"degraded men"
Popularized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figures have been commonly used in contemporar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They are particularly known to combine factual history with story telling,link past with present,and combine western with Chinese languages,presenting strong and important connections that have been overlooked between Chinese classic material and contemporary revolutionary movements.These revision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re built on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and insights from,the shared course of history,combining nationalist awareness with emotions for the country at that point in time,an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gender-based writing styles to capture the nation's imagination.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imagining big from small"to place the revised biographies of women martyr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late Qing,not only paying attention to contemporary considerations but also dissect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embedded in the image of"degraded men"in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of late Qing.
I209
A
1004-2563(2015)01-0092-07
李贞玉(1982-),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性别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