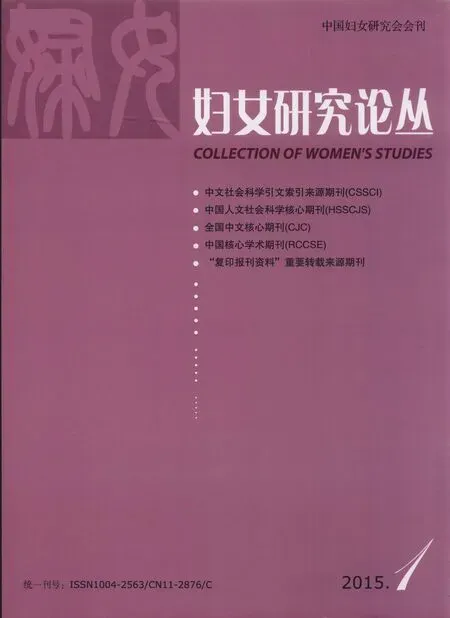“公共性”逻辑与性别正义的政治空间*
宋建丽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公共性”逻辑与性别正义的政治空间*
宋建丽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公共理性;性别正义;政治空间
文章以围绕女性“差异性身份”而产生的两种女性主义权利诉求路径为例,利用罗尔斯公共理性的推理方式和公民性责任的概念,辨明不同路径的女性主义可以依据公共理性证成其主张的合理性及限度,简要给出一种“公共性”逻辑指引之下的女性主义公民政治的未来方向。
女性的性别身份与其出身、血统、种族、所处社会阶级深刻纠缠在一起,因而呈现出多元和异质的特征。当这样差异多元的女性群体带着各自独特的性别身份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她们将如何在政治中呈现自身?换句话说,对女性而言,“我们是谁”的自我身份认同上的本体论立场是否会直接影响到应该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呈现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性别本质论一直与女性纠缠不休:理论上和策略上,似乎需要有一种统一的“性别身份”来反映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群体权利诉求,然而,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性别身份”的固化和强化又往往正在瓦解女性作为整体的团结。为走出这种困境,女性主义必须在理论层面厘清一个规范性的问题: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在进入公共领域、面对公共议题时,应该如何去思考和推理以形成共同意志?如何保证她们所诉诸的理由,能够同时为其他异质群体所接受?如何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在一种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积极的女性公民身份,证成(justification)自己作为“女性公民”而不仅仅是“女性”的正义主张?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他称之为公民性责任的政治义务,展示了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在进入公共领域,就公共议题辩谈时所必须尊重的一项价值规范。这种公民性责任的提升和遵守,不仅有助于确定更合乎正义的政治体制以及形成有利于女性生存的政治文化背景,而且也将有助于女性积极公民身份的塑造,以及最终作为大写的“人”而不仅仅是作为“女性”而获得平等尊重。
一、“性别差异”与公共性逻辑
在西方漫长历史时期内,女性身份常与非理性、私人性、情感等同,并由此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当女性主义向这一切提出挑战,性别差异自然成为女性主义权利诉求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以“性别差异”为立足点的女性主义权利诉求路径,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女性”独特的身份经验和身体体验,是对女性声音在历史上长期保持沉默的一种回应,其根本特点都在于持一种实质性女性差异的学说,在此意义上,可视为一种苏姗·穆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所说的性别意味的“整全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①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对美好生活的看法,往往诉诸于形而上的论说方法加以表达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这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整全性的或完备性的学说,英文原文是“comprehensive doctrine”。对于这个词的翻译有不同版本,比如万俊人先生译为“完备性学说”(详见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474页);石元康先生译为“整全性学说”(参见石元康著:《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2页);时和兴译为“全整论说”(参阅时和兴译:《公共理性观念再探》第1、8页,载《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译法。所谓整全性学说,实际上就是指一种适合于全部社会生活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真理。后文提到的“全面性学说”、“整全性价值”等概念,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在奥金看来,如果政治自由主义允许宽泛范围的整全性学说进入,那么,一些支持性别等级制以及实质性女性差异的学说即性别意味的整全性学说进入公共领域将影响女性实质平等的获得。[1][2](PP23-43)奥金的担忧②在罗尔斯后期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明确指出,现代社会面临着一种互不相容却又合乎理性的诸整全性学说并存、冲突的多元化境况。政治自由主义关注的问题就应该是:在当代民主社会拥有合理却不兼容之宗教和哲学主张的前提下,如何可能会产生一个使这些合理对立学说都能共存且都能共同肯定宪政体制的稳定、正义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正义观念其实就是在没有任何一个全面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作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基础的前提下,从当代民主社会的特殊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寻找一种持有各种相互冲突之整全性学说的公民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一种正义共识。罗尔斯区分了公共(政治)领域、背景文化领域、市民社会领域,大学、教会以及其他自愿形成的协会都属于背景文化的一部分,而主导背景文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整全性理论。罗尔斯对整全性学说是否可以出现在公共讨论中曾做过多次修正(参见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2005,P.247,453),这里奥金的担忧就是对此问题的回应。固然有道理,然而,如果杜绝具有实质性女性差异的学说进入公共领域,同样容易重蹈歧视女性、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覆辙。
因此,这里的问题似乎应该不是“允许”或“不允许”的问题,而是在不人为设置公私领域之间界限的情况下,政治自由主义将为性别正义提供怎样的空间?这就需要深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公共性逻辑”。我们将会发现,如果严格遵循这种“公共性逻辑”,任何具有性别意味的整全性学说要发挥其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都必须首先能够在自由民主的公共领域内以一种“公共理性”证成其性别正义的主张。
公共理性的观念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明确加以论述的一个议题,然而,正如查尔斯·拉摩尔(Charles Larmore)所认为的,公共理性的观念其实早已隐含在罗尔斯的前期著作中。[3](PP368-374)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之后就正义原则立约的公民设计中其实就已经隐含着公共理性的观念,不过,在早期阶段,这种公共理性是以“公共性”(publicity)的观念来加以表达。[3](PP368-374)所谓“公共”的,在逻辑上体现为公共的推理以及大家都能理解并接受的证据;在内容上则体现为公共接受的理由。在《正义论》中被罗尔斯给予极高重视的公共性维度中,其实已经隐含了这种公共理性的概念:由于正义原则的推导是经过公平的程序正义来保证的,因而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由于无知之幕的设计排除了个体私意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因此由无知之幕之后推导出来的正义原则是公共的,是一种公众都可以认可和接受的公共理由。
然而,正如罗尔斯本人指出的,尽管《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都包含某种公共理性观念,但是公共理性的分量在两本书中是不对称的,在《正义论》中,公共理性是由整全性的自由主义理论赋予的,因而属于一种契约内的论证,没有充分考虑合理多元的事实,可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在充分面对合理多元事实的条件下,公共理性成为关于自由与平等的公民所共享的政治价值的一种推理方式。只要这些学说和自由民主政体相兼容,公共理性就不对公民的整全性学说进行压制。[4](P490)
简言之,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政体中的公民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资格的人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主题是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是政治正义观念的要求。换句话说,为确保政治的正义,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任何公民,在处理宪政要素和基本正义问题时,都要受到公共理性的规范。[4](P214)根据罗尔斯的论述,公共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共理性是公民本身的理性,是公共大众的理性;第二,公共理性的主题是公共大众的利益和基本的正义;第三,公共理性的本质和内容是公共的,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观念所表达的理想和原则所赋予的,并在政治正义观念的基础上公开施行。[4](P442)
然而,人们会质疑:为什么公民在就最为根本的政治问题讨论和投票时要遵守公共理性的限制?它如何能够是合理的或者是理性的,当基本事务危在旦夕时,公民为什么能够仅仅诉诸公共的正义概念而不是诉诸他们所理解的整全性真理?当然,最为根本的问题应该通过诉诸最为重要的真理来解决,然而这就超越了公共理性的范围如果这种质疑持续存在而未能得到解决,那么,当就公共事务投票和审议时,公民将没有理由不去诉诸他们的整全性学说,其结果就是:在公共辩论以及公共审议中,一个理性的公民将可能面临两种价值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她自己对某种整全性学说的信奉以及她对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概念的同样坚持。或者,公共领域中的公民干脆放弃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而仍然从各自整全性学说出发来发言,而这无疑导致一种交叠共识和稳定性的危机。
因此,公民性责任就成为罗尔斯解决公共理性之悖论的一个途径,这种责任将是一种高于一切的价值,在普遍接受的理由基础之上,它将能够决定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即公民所信奉的整全性学说和政治概念之间的冲突,而且将会提供一种服务于持久稳定的公开性承认的道德标准。按照罗尔斯的清晰定义,公民性责任是一种非法律的道德责任,它“能够在根本性问题上对彼此解释他们倡导和投票支持的原则和政策是如何能够被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所支持的。这种责任也包括在决定中聆听他人的意愿以及一种公平心”。[4](P217)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公共证明不只是有价值的推理,而是要向其他公民证成的推理:它从我们接受同时他人也能接受的前提出发,这就满足了公民性责任。[4](P465)由此可见,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以承认差异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一种本质意义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越过这些自然的差异)至少存在于公共领域。
二、政治正义的性别空间
如上所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以承认合理多元的事实为出发点的,所谓承认合理多元事实,也就是承认他人的合理全面性学说和自己一样地合理,这不代表个人不能视自己的全面性学说为真,而是他必须同时承认他人也有好理由认定其学说为真。罗尔斯对全面性学说是否可以出现在公共讨论中,曾经作过一些修正,在1993年的说法是:在某些情境下,公民可以基于其全面性学说认定什么是政治价值的基础,只要这样做可以强化公共理性,他称此为“包容观点”(inclusive view)。[4](P247)到了1997年,罗尔斯扩大全面性学说可以被引进的情境,他主张,不论宗教或非宗教的合理全面性学说,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引进公共的政治讨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呈现出正当的政治理由,也支持该全面性学说所支持者,他称此为“但书”(the proviso)。[4](P453)根据“但书”,我们可以在公共政治论辩中援用背景文化的内容,只要我们从公共理由出发给出考虑。
但是不可置疑的是,不论“包容观点”或“但书”,证成任何一个公共政策或主张的最终基础仍然是公共理性,因为一个基于全面性学说的主张可以具有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是,这个主张也可以被公共理性所支持。换句话说,罗尔斯只允许和公共理性精神相合的全面性学说进入公共讨论之中。下面我们以母性思想和差异政治为例,来思考一下政治自由主义能够为性别正义提供怎样的空间?或者说,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性别正义的诉求将呈现出何种合理性的限度?
首先来思考母性思想③所谓“母性思想”就是强调母亲或妇女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够改造公共生活的道德观。其核心观点认为女性拥有她们作为母亲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思考模式或一套情感上的偏好,这种独特的思考模式或情感上的偏好是特别有价值的,并且应该给我们的政治生活注入活力。代表人物有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和简·爱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是否可以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框架内证成。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点质疑:第一,母性思想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社会的性别安排,即赋予社会中的女性以作为母亲的责任,然而其他公民可以合理质疑为什么只有女性能够成为或者需要成为母性思想者,因为我们还可以探究是否还存在照顾孩子的其他方式,例如“父性的”思想?或者“母性的思想”是否是那种任何承担照顾小孩责任的人都能够学习到的一种思维模式?第二,母性的价值或母性的视角如何转换为政治的价值和政治的视角?母亲的行为如何可能教导或帮助母亲们成为好公民?在玛丽·迪兹(MaryDietz)看来,在民主的公民资格中,母性是一种特别不适合于政治主体的模式。她指出,母性的美德涉及特殊性、独占性、不平等以及爱和私密行为,而民主的公民资格要求总体性、包含性、一般性以及距离。[5](P31)因此,女性主义政治意识必须利用的是作为公民的女性的潜力以及她们作为一种集体性、民主性力量的历史现实,而不是喧闹的所谓母性要求。在迪兹看来,这种母性思想是一种“女性化主义”(womanism),即认为女性拥有一种优越的民主本性或者拥有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声音。她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对女性的关注,但却应该同时避免女性化主义。[6](PP17-19)
因此,以女性道德推理的独特性似乎难以成为其他公民都可以接受的公共理由,按照罗尔斯对政治自主和道德自主的区分,道德自主不是政治价值,因而,既定的合理多元的情况下,受互惠性条件的限制,这种单纯的道德价值将无法获得其他公民的承认。[4](P456)由此看来,即便是根据罗尔斯宽泛的观点,对“女性的”推理模式进行单独界定并止步于援引女性的道德推理是不够的,要想证成这种主张并促进公民友谊,必须继续给出政治公开性证明。[4](P465)在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分析框架之内,女性既非唯一地由母性思想来识别,母性思想也并不必然促进简·爱尔希坦声称要促进的那种民主政治。关怀、养育以及对关系的保持应该是人类伦理上成熟的一种表现,而不必总是与一种特殊的母性或女性思想及实践相连。女性主义只有通过鼓励民主的实践以及通过将女性自身培育为公民,才能够在其政治使命中获得成功。[5](P20)一种更为恰当的方式应该是在一种政治的框架中展开对母性等关怀价值的重新评价,将关怀实践置于制度性问题的背景之中加以考虑。以自主性的优位排除有价值的关怀的可能性,无法成为一个公民都可以接受的正义框架,同样,仅仅诉诸强化女性特殊道德视角和道德身份,也无助于女性权利诉求成为一个公众均可接受的公共理由。因此,遵循罗尔斯政治正义的公共性逻辑,应是在承认母性价值的背景中对公共供应和政治规则进行改变。
如果说母性思想的民主潜能是广受争议的话题,那么以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却由于其质疑传统的正义分配理论,挑战公私领域的划分,为女性群体争取政治领域的代表权而备受关注。那么,杨的这种差异身份的政治是否可以遵循罗尔斯公共理性的要求证成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杨在断言传统分配理论必须予以超越时给出的是何种理由。简单来说,杨给出的理由主要有:第一,传统正义分配模式由于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益品(goods)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上,有可能转移了对形成分配模式的制度背景和结构背景的关注。第二,当正义分配扩展到非物质的善,诸如对权力或自尊的分配时,这种分配模式就无法准确反映它们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动态特征。传统的正义分配理论将人们看作益品的所有者和消费者,而杨提出一种致力于改变支配和压迫关系的模式,并由此将人们视为积极的行动者,表达了一种参与平等的权利诉求。在这种阐释中,正义指的是“个体能力之发展和行使以及集体性交流和合作所必须的制度性条件”。[7](P39)
依据参与平等的原则,我们一方面可能评估社会安排合理与否,当且仅当它们允许所有的相关社会活动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这些社会安排才是恰当的。此外,依据参与平等的原则,我们可能评估规范的民主合法性:当且仅当它们能够尊重包括在协商的公正与公平过程中(所有人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的所有人的意见时,这种民主安排才是合法的。有鉴于这种公共理由的推理,作为参与平等的正义观点拥有了一种内在的反思性,它既能揭示推定性歪曲民主决策的背景条件,也能揭示产生实质性不平等结果的非民主程序。[8](PP28-29)
由此,在批判基础上对正义理论的重构如果立足于政治价值的推理,那么,不论抱持何种整全性学说的公民,应该都能同意这样一种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原则,也就是说,指向差异正义基础之上的社会团结的身份政治,当不应和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精神相悖。而且罗尔斯也明确表示容许政治制度保持开放,并指出,由于政治价值不会被唯一一种来自于整全性学说的价值所操纵,因此,我们可以自信,我们可以做到容许政治制度保持开放,同时又不会被某种整全性价值操纵。[4](P454)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差异身份政治建立在“我们-他们”这种道德身份的区分基础之上,因而潜藏着诸多实践中的困难和理论上的困境。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寻求包含压迫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s)的差异化运动常常面临差异的两难。一方面,差异需要被承认,弱势群体的权利需要被提升,从而消除弱势群体常常不得不面对的不公正的处境;另一方面,特殊群体的成员又必须不断地否认任何本质性的差异,例如男女之间的差异、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异、残疾者和健康人之间的差异,等等,因为对差异的强调将带来其他危险。例如,一种不恰当的信念可能会鼓励人们否认妇女、黑人以及残疾者和他人拥有同样的机会,从而阻碍他们获得平等的工作职位。另外,我们必须承认妇女之间的差异是客观的事实,但妇女在不同的社会被对待的方式则是主观任意的。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曾以反本质主义的名义指出,一些学者尽管承诺提升妇女权利,实际上却强化了对女性构成的具有压迫和性别歧视意味的处境。[9](P212)普遍和差异之间存在明显的两难。杨的差异性身份逻辑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把纯粹的差异转化为绝对的他者,将差异置于一种普遍性概念之下的做法必然产生内部-外部、我们-他们的区分。
综上所述,适当建构的群体性身份固然可以鼓励女性积极的政治参与,但这种身份政治的解放潜能只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根据罗尔斯公民性责任所要求的主体间性精神和形成交叠共识以维持社会稳定性的初衷,身份政治的我们-他们之间道德身份的截然区分不仅面临普遍和差异的理论困境,而且也会给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运动的团结带来诸多困难。[10](P95)
三、解构与建构:性别空间的辩证法
继差异性身份政治的诉求之后,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进一步以身体代替身份,解构基于共同身份基础之上的政治主体性,解构性和性别的差异。对于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来说,政治代表是一种权力游戏的偶然结果。在她们看来,唯有不求女性固定的主体性,才能包容无限的可能。肯认女性独特的身体经验无疑被后现代女性主义视为实现性别公正的基础,然而,仅仅肯认这种独特的身体经验是否能够在公共领域中证成性别正义的主张?
换言之,作为公共领域中的公民,我们有责任发展并运用我们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即在自己的思考中整合他人的立场,而不是简单地以此来替代自己的立场。遵循这种公民性责任的要求,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了养活孩子而出租子宫、出售肾脏的印度妇女能否与中产阶级、上层社会女性精英感受同样的身体体验?“全球化平台”的出口加工区、血汗工厂中收入微薄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工人能否与主张身体政治的女性主义者有同样的需求?当进入公共议题之时,我们对彼此合理证成的将是:差异性的女性生活经验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共决策的正义性?差异性的女性身体体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女性平等权利的获得?简言之,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对社会差异作出解释并且使之合法化,而是去进一步寻求背后的根源并找出治理之道。
以解构立场和多元认识论为理论基础,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对于引导女性摆脱二元对立、二元等级论造成的不利地位,并避免陷入新的霸权结构有着积极意义。果真如此,女性主义就不再是作为男性中心主义之对立面的一种声音,而是反映了不同种族、阶级、民族的妇女及边缘人群和社团的多种声音,为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可以共存的空间,从而较客观地反映出世界多元、多视角的真实面貌。[11](P198)然而,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盲点一样,在正确地指出更为充分的正义理论不能依赖于一种超验的或抽象的理性的同时,也面临失去斗争目标的危险。尽管依赖抽象的理性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却不能由此而认为所有有关正义和主体性的谈论都能够或者都应该被抛弃。
相反,各具分歧的生活方式越多,正义问题也就越突出。然而,在其目前表述中,后现代主义却抑制了可替代的正义观念和正义实践的发展。这部分地是由于许多理论家并没有对当代支配形式(特别是性别和种族的支配)的具体运作给予充分的关注。同样重要的是,由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将所有的主体性观念都瓦解为一种有极大瑕疵的观念形式,他们也就无法阐明对于正义实践来说既充分又必要的政治主体性概念。正义首先是一个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滋生出来的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问题。正义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人们深刻持有或感受到的需要、欲望、观念以及目的各不相同并常常发生冲突。同时,由于人类主体性的相互依赖性和人类主体性的社会性方面,正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此,对正义的需要来源于人类主体性的复杂性。因此,只要没有完全抛弃主体性,就不能抛弃正义,反之则亦然。[11](PP198-199)从身份政治到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是进化亦是退却,进化在于:进一步解构了性别本质论,将差异化关怀渗透到各个层次、各个领域;退却则在于:身份政治之差异正义的理论诉求及政治解放内涵也被同时消解。
没有建构的解构就等于学术和现实斗争的分离,正因如此,社会变革不只是“解放”潜伏于压迫阶层之下的本质意义上的主体,还意味着对多元新兴主体的政治建构。有效的政治行动所要求的将不是追求一种基于阶级或性别的同质的行动者,而是处于具体关怀和目标背景中的多元群体之间为达成“政治团结”而进行的努力。同样,更具建构意义的女性主义也并不只是有关解构的批判,而是要积极地创造政治空间以允许边缘群体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提供一种令她们的声音都能够被倾听的适当的平台。[12](P496)
简言之,以性别差异为立足点的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打破了以男性、理性、权威、原则作为唯一声音的道德哲学,[13](P3)但这之后的实践重点,不应该是去建立另一个以女性观点为权威、唯我独尊、自说自话的“女性主义化”的哲学,也不应该是一种女性的政治主体性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见的哲学,而应该是在“公共性”逻辑推动下进一步扩展女性政治参与的性别空间,如此,我们才可能期望摆脱在寻求与主流政治哲学对话过程中差异化和普遍化的对立,在一种更为宽广的公共视野中审视性别正义的要求和意义。
在公共性逻辑指引下,正义可以是一个预期的概念。讨论正义为如下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如支配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考虑任何其他形式的关系是可能的?可能存在何种可替代的选择?简言之,正义不是一次建立且永远有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有限状态或者一套规则。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力图实现什么的想法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12](PP199-200)
从公共理性的视野出发来审视性别正义的政治空间,可以说,社会正义要求尊重不同群体的差异,但却不是固化或强化差异。女性主义的政治需要和指导原则可以通过要求主张差异以及与之相伴的承认而实现社会正义的扩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单一维度的对差异的承认必然是不充分的,可能会被指责为另一种性别本质论。其次,差异的内涵也并非仅指对立,而是意味着多样,差异性即意味着多样性。如果局限于一种对抗性思维而将“差异”理解为对立,则可能陷入多种立场之间的对立和纷争。
因而,如果改变思路,以一种公共理性的精神,遵循公民性责任的要求,去追寻社会正义原则进一步扩展的可能和张力,就可能使得女性主义摆脱性别本质论的纠缠,摆脱女性身份的束缚,摆脱对抗性模式的桎梏,在一个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表达自身。差异总是易于和对立相连,而多样则预示着丰富和无限可能。因此,多样性的生存,多样化的表达,而不是不同的生存、不同的表达,才是我们所渴望的未来。强调差异和不同,就大大减弱了对话和沟通的意愿和可能,而强调多样,则可能使得具有差异性的各方都处于一种彼此合作、丰富彼此的思维框架下,而这无疑有利于实现差异性各方之间的沟通和对话,进而减少冲突。也正是在这里,女性主义与罗尔斯再次相遇。
[1]Christie Hartleyand Lori Watson.Is a Feminist Political LiberalismPossible?[J].Journal of Ethics&Social Philosophy,2010,5(1).
[2]Susan Moller Okin.Political Liberalism,Justice and Gender[J].Ethics,1994,(105).
[3]Charles Larmore.Public Reason[A].Samuel Freeman.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C].Cambridge Mas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03.
[4]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M].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2005.
[5]MaryDietz.Citizenship with a Feminist Face:The Problemwith Maternal Thinking[J].Political Theory,1985,13(1).
[6]MaryDietz.Context is All:Feminismand Theories ofCitizenship[J].Daedulus,1987,116(4).
[7]Iris Marion Young.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90.
[8][美]南茜·弗雷泽著,欧阳英译.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9]Martha Nussbaum.Human Functioningand Social Justice:In Defense of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J].Political Theory,1992,(20).
[10]Rian Voet.Feminism and Citizenship[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8.
[11]Jane Flax.Beyond Equality:Gender,Justice and Difference[A].Gisela Bock and Susan James(eds).Beyond Equality&Difference: Citizenship,Feminist Politic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C].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2.
[12]Christine Sypnowich.Justice,Community,and the Antinomies ofFeminist Theory[J].Political Theory,1993,21(3).
[13]Susan,J.Hekman.Moral Voices,Moral Selves:Carol Gilligan and Feminist Moral Theory[M].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Press,1995.
责任编辑:玉静
The"Publicity"Logic and Political Space for Gender Justice
SONG Jian-li
(School of Marxism at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Province,China)
public reason;gender justice;political space
The paper applies Rawls'duty of civility in an examination of two kinds of feminist approaches which focus on women's"differentiated identity"and identifies the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e different paths of feminism.It argues for an approach to feminist citizenship politics directed by a"publicity"logic.
B089
A
1004-2563(2015)01-0005-07
宋建丽(1972-),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伦理学。
本文为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南茜·弗雷泽反规范的正义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3YJA710038)、2013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当代资本主义正义批判理论前沿”(项目编号:2013221019)以及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社科A类“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文化正义”(项目编号:JA13007S)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