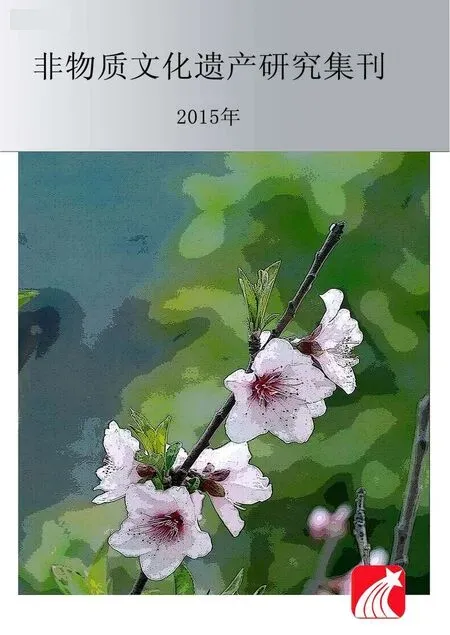浅谈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①
——以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为例
简圣宇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南宁 5300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个案调查与研究
浅谈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①
——以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为例
简圣宇②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南宁 530022)
文化的发展,除了需要宽容的开放之外,也需要适度的封闭以实现层层的积淀和保持其相对稳定。正如河流里生物的丰富性既需要活水的滋润,也需要流速的相对缓慢,否则全开放的信息洪流可能将把之前好不容易累积起的文化冲击殆尽。信息时代的现代性洪流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毁各种原本以为相对封闭而得以保存下来的原生态文化据点。而网络新媒体上的资讯由于商业等原因,片面地、有选择性地进行报道,把纷繁复杂的原生态文化简化为旅游解说词。所以我们如何一方面顺应新媒体日渐繁荣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避免原生态文化被占有绝对优势的网络传媒简化乃至改写、屏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议题。
互联网 生存状态 广西 黑衣壮 白彝
从局域网,到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我们进入这个全新时代之后,“交互”在社会学领域前所未有地得以普及,主体间性才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狩猎、农耕、工业化等数个时代,而如今我们所处的当下,正是一个全新的“交互”时代的开始。新媒体替代传统媒体已经是时代的必然,然而,在这场历史性的时代转化中,我们必须留意和警惕文化生态问题,即在网络交互平台上,依托新技术优势的新媒体艺术,如互动游戏、手机电影等,正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脆弱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构成重大威胁。本文将以2013年12月对那坡县吞屯和达蜡彝族村的黑衣壮、白彝等社区的具体调查为例,就此展开阐述。
一、黑衣壮之乡的当代文化状况
“黑衣壮”作为壮族的一个支系,在广西以及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中有着重要意义。黑衣壮也由此被当作广西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在现在可以搜索到的网站介绍中,他们的文化特征被定义如下:“黑衣壮服饰是至今仍然保留着最为传统、最具有特点和内涵的壮族服饰。它不但以黑为美,以黑作为穿着和民族的标记,而且在穿戴上讲究实用,款式大方,朴素美观,别有风度”,“其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质受到世人的关注,居住的环境还保存着壮族古老的干栏式结构房屋,他们的语言用‘敏’为母语”等等。
这类介绍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黑衣壮仍然处于相对隔绝的文化状态,现在媒体拍摄到的和文章记录下的黑衣壮形象,就是黑衣壮本身的现时态。而实际上,在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再偏远的村落也不会孤立存在了。
大石山区那坡县吞屯,是黑衣壮之乡。我们未进屯,先在村级公路上盘山而行,途中看到了山中的农作物。在这儿的石山上没有一块平整的田地,农民只能在石山间巴掌大的嶙峋石缝中,见缝插针地种上农作物,其中之艰难,非亲眼所见,不能体会。这里颇为偏僻,手机信号不是特别好。按照笔者原先的想法,本地应当保持着非常纯正的原生态文化。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就算是昔日如此偏僻的山寨,仍然不会脱离现代社会的整体发展步伐。
一进村,就看到村口挂个牛头,跟黑衣壮的民俗风马牛不相及,估计是从云南旅游村学来的挂饰。接下来发现,这个村落整体上已经开发为旅游接待村。屯中女子介绍黑衣壮风俗时提到,此地老人49岁就要祝寿,每隔12年再祝一次。49岁即祝寿,可猜测原先此地人均寿命偏短。《尔雅》云:“黄发、齯齿、鲐背、耇老,寿也。”古时候的“寿”在今人看来,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骨质疏松的典型症状都出来了。不知道黑衣壮49岁而非整数的50岁做寿,其用意何在,问当地人,可惜一问三不知。须知,在其他少数民族,这种做寿中的细节往往包含着主要的文化信息。①比如,壮族的兄弟民族毛南族就有一种风俗:“添粮补寿”。毛南人认为每个人一生的口粮有定数,老人所余口粮不多了,亲友们为他添粮便可补寿,所以在为老人举行“添粮补寿”仪式时,要请师公和歌师为老人唱添粮补寿歌,以期老人能够健康长寿。见蒙国荣、谭亚洲译注:《毛南族民歌》,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20页。
当地老妇人为我们进行“传统舞蹈”表演。如“黑枪舞”——舞动黑色的长柄矛。据当地人介绍,这是庆祝战士归来的舞蹈。但奇怪的是,此舞应为青壮年男性表演才对,但表演者从始至终都是这些老妇人。这些50—70多岁之间的老妇人,身高在1.3—1.5米之间,矍铄开朗。经询问,得知此地年轻人都已经离乡谋生,只剩下留守老人。这个“黑枪舞”与其说是“传统舞蹈”,倒更像广场舞,疑为应付游客而新近编排的,询问当地人,对方笑而不答。再问陪同干部,答曰:有部分舞蹈是年轻人上网搜舞蹈视频之后编演的。
之后又表演了“8”字舞,说是祈求兴旺发达,能保佑发财、发展,对“8”的崇拜不是20世纪从香港传来,然后流行于粤方言地区的吗?“8”在壮语中与“发”并无谐音。笔者越发对这些传统表演感到怀疑。
最后一个舞蹈是游客与当地的舞者,围成一圈跳集体舞,这更让笔者生疑。恕笔者孤陋寡闻,就笔者所阅读到的有关壮族的史籍文献,从未提及此舞蹈,倒是在云南旅游时,在景区比如丽江,见到过这类“传统舞蹈”,而且似乎现在中国所有少数民族景区,无论是北至内蒙古,还是西至青海,全有此类“传统”围圈集体舞。
方才笔者进屯时,村口大树上挂着牛头骨,当时还诧异,这不是羌人、藏人的习俗吗?现在看完“传统舞蹈”表演,再看到表演的晒谷场边上挂的“广西那坡黑衣壮原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牌,估计也是旅游公司策划组的“杰作”。
导游是本地妹子,高中毕业后从事此工作,她身上的黑衣壮服饰也已不是传统手工制作,而是购自县里的商店。我问她日后的打算,她坦言:“我以后肯定是要嫁出去的,谁想待在这种(艰苦的)地方啊。”
此地“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能打工的劳动力都出走了,仅春节才回乡。在村里的年轻人当中几乎没有男青年。如此状态,本民族分支的文化继承,看来颇为艰难,孩童已不再穿传统黑衣壮服饰,亦不熟悉传统民俗。现在的所谓民俗,也都只存在于文献记载和遗存的器具上。现在所谓的“原生态”,等这一批老人亡故之后,很可能沦为为旅游业而衍生的表演。
屯中还有不到十座干栏建筑,其余都是新建的水泥房,仅存的干栏建筑也基本不用作民居,而仅仅用作储物房,偶尔见一建筑有人居住,门口也已经加砌了扎眼的水泥楼梯。导游姑娘不经意一句话说明了问题:“老房子住得难受,谁不想住(条件更好的)好(水泥)房子。”
我看到一些房子颇有创意,建造者为了兼顾在外观上的传统和住得舒服,发明了一种敷衍法:先用水泥建房,接着用泥巴和木竹片覆盖在外墙上,再用石头砌在墙角。乍看跟传统民居还颇为相似。
在另一处的空地上,有传统工艺品销售。我买了一条40元的五彩围脖。老妇人说是自己织的,但我砍价时,她又说公司已经统一定价。我细捏围脖,明显是机织的。尽管如此,本地民风仍然非常朴实,老妇人虽然不停劝我们团中的女性穿上当地黑衣壮服饰拍照,但都止于耐心热情劝说,而绝不强求,收费也仅仅10元。不像湖南、云南的一些地方,先热情哄游客穿上,再漫天要价讹钱。老妇人都是先提醒游客穿服装要收费,然后才递上服装,神情慈祥殷勤。此地人也正在被商业化时代所侵蚀,有的老妇人要给钱才拍照,否则捂住脸。当然,索要资费也很少,也就一两元。
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递存在着“级差”,新涌现的文明成果和思潮一般萌始于文化中心(如国家首都),然后传递到其周边的重要都市,再从都市传到其周边的乡村,继而从一处文化区域流传到另一处文化区域。这种文化的传递速度相对较慢,所以当这个“新的”文明成果和思潮在其始发地早已经不再是“新的”,甚至被视为“落伍”的文化象征时,在相对于中心而言较为偏远的文化区域却才刚刚接收到这一切,当地人们认为这是中心地区正在流行的风尚。这种传递过程就像一块石子投入水池,当波纹产生的中心已经平静下来时,池塘边上才刚刚感受到涟漪的传来和泛起。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中,记录着一段公案,朱熹的学生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那为何两者从未相遇,书中也不曾提及对方?”朱熹认为大约是因为两人住的地方相距太远,所以虽然同是那时的诸子大家,却无法同声相应或彼此争鸣:“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而“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且不论朱熹是否确切回答了这个问题,单就这个“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的问题,就可看出前现代社会交流的不便。后来17—19世纪大量欧洲学者的交流,也是依靠延时几个月甚至数年的书信往来实现的,著名的如伏尔泰《哲学通信》、卢梭《书信集》、普希金《书信集》等。而如今互联网早已消弭了信息的时空阻隔,隔着大洋都能即时争辩。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只要可以联网查询的,那么最迟都不会超过次日就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在以往的非互联网时代,知识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上,一个人可获得的知识资源往往与其权势、地位、年龄成正比。但在我们这个交互社会中,知识资源逐渐呈现出开放多元、获取便捷的态势。社会成员无论权势年龄,在面对可获得的知识资源时,其知识权力日益平等,知识的社会等级和地域级差的传统格局开始瓦解。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即时通信功能已经消解了文化传递的“级差”,整个世界忽然变成了一个平面。这已不再是传统时代那种涟漪一般的慢慢传递,如今文化中心新发生的事情,即便在相对边缘、偏远的地方也同样可以即时了解。比如,在吞屯的空地旁边就有酒吧,无论是游客还是店主都习惯性地开着手机,通过手机信号或者店内WiFi来进行通讯交流。黑色的传统服饰也不再是新一代本地年轻人的日常衣服,仅有老人家还穿。年轻人因为景区的需要在白天才穿着传统服饰,只要没有招徕游客的任务,他们就直接穿上普通短袖长裤,跟游客穿着基本无异。而且就算是在工作中穿着传统服饰,闲下来也掏出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玩游戏、看影视剧。一位本地女孩子聊起最新的韩剧如数家珍,对相关资讯的了解远超于我。跟酒吧里的女孩子聊了一下,她高中文化程度,对三星手机的使用,以及对里面的游戏软件诸如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等,颇为熟悉,可对本民族的诸多民间信仰则较为漠然,竟然不太了解花婆神信仰,而这一信仰乃是广西壮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信仰的重要核心。
年轻一代人热衷于花时间和精力在新媒体上,追逐所谓的新潮文化,玩游戏、看影视剧,但就是不愿意去传承那些他们认为“老土”的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化。许多原本是黑衣壮最简单不过的日常传统,对年轻人而言,却已经变为必须主动去了解才能知道的冷知识;而且他们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知识的动力,还是来源于旅游公司的考核,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黑衣壮有一个较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那就是缺少整理和传承本民族分支的特色文化的自觉意识。这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过去他们大多没有关于自身历史的文献记录,有关他们的历史需要借助中原王朝的文献才能得以管窥,于是他们实际上处于一种被叙述而非主动自我叙述的状态。“黑衣壮”这个称谓,也并非这个民族分支自称,而是1997年广西右江民族师专的何毛堂、李玉田、李全伟等研究者在对其进行人类学考查时,根据他们服饰的颜色等族群特征加以命名的。由于此命名简洁明了、朗朗上口,所以获得此民族分支内外的广泛认同,成为正式称谓。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如何自觉主动地展现自身的文化艺术特色,是黑衣壮需要思考的课题。
二、对达蜡彝族村实地考察的文化启示
去黑衣壮吞屯的次日,我们到达蜡彝族村,见到“白彝”民众,即穿白上衣、黑裤子的彝族人。白彝以白色为显要标志,但他们并非以白色为贵,彝族在旧时,“黑彝”的社会等级是要高于“白彝”的,彝人原本以黑色为贵,这正好与昨天的黑衣壮形成对比。
为了发展旅游经济,网上的宣传资料说黑衣壮“以黑为美”,百度百科也直接引用此说。但我在吞屯向当地人细致询问时,才得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黑衣壮是因为本地人在壮族族群中地位不高才用黑色系的服装。黑衣壮服饰的主要染料,来自大山里随处可见的植物蓝靛草。除了黑衣壮之外,许多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也曾使用过此染料制作的服装,只是没有黑衣壮这样从头饰到衣裤都纯黑装扮而已。当其他族群已经不再以黑衣为风尚服饰时,黑衣壮仍然以此为衣,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这里在旧时代属于文化传递较为边缘的地区。如壮族作为中国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有相当多的支系,由于语系众多,所以对自己的称谓也非常之多,如“布壮”“布依”“布侬”“布越”等。这类自称达到近20多种。①曾经有文寨的壮族受访者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太讲“布央”“布敏”了。讲也讲,但是讲得少,都是老百姓讲的多,开会都是讲“壮族”,讲我们都是“壮族人”。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也晓得自己是“壮人”,都是讲话来分的,“布央”“布农”“布敏”是怎么划分的?很久以前的我也不晓得,我想是因为讲的话不一样吧。讲的话不一样,就划分成“布央”“布农”“布敏”,还有汉人了。汉人讲我们是“讲壮的”“讲土的”。我们讲汉人是“讲官的”,高山汉是本地的,我们叫“桂州佬”。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分咯,分成汉族、壮族、瑶族、苗族、彝族、回族,样样都有。“布央”“布农”“布敏”统统都叫壮族了。见海力波:《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吞屯的黑衣壮在本地自称“布敏”,据称并非本地原住民。此地已有原住民和先行迁移来的居住者,他们早已占据了居住和生产较为便利的水边区域,这些后迁徙来的黑衣壮不得不转到条件恶劣的大石山坡上定居。“黑衣”实际上在当地曾经含有贬义。
由于手头资料的匮乏,我仍然无法确定历史上布敏人究竟是“以黑为美”还是“以黑为卑”,但可以确定的是,黑色在过去等级森严的旧社会是有特定意味的,而目前网络上的资料只提供了片面的信息,让浏览者误以为只有“以黑为美”一种说法,而不知还有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种说法。可见,对于网上的宣传资料是否符合真实情况,一定要做实地调查和参阅文献,切不可被宣传资料所误导。实事求是去调查,乃是学术研究严谨性之所在。
无论是黑衣壮还是白彝,其所穿衣服的颜色都显示其当年在族群中的等级秩序中地位并不高,他们被排斥到相对边缘、环境恶劣的边远之地居住,这本是他们当年不幸历史的见证,但又因为地处偏远,而使得其特殊的传统服饰得以保留,记录下中国文明史上的幸运一笔。
白彝传统女式服装中有一条宽20厘米左右的大腰带,她们对外称是“这个地方太艰苦,怕女人跑了,所以要有一条精美的腰带拴住她们(的心?身?)”。但当介绍完之后,这位韦姓妇人却在转身与另外一个人聊天时,说了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还说刚才给我们说的版本是“应付外人”的。由于这位妇人在交谈时没用彝语,而是彝调官话,结果被同操桂柳官话语系的我全听懂了。
韦姓妇人用官话提到,在她们的口头传说中,彝人穿上现在的白色服装之后是能飞的,后来汉人为了防止他们造反,就加上这副夸张的宽腰带,于是彝人就再也不能飞了,只能困守此处。妇人的这个略带魔幻和荒诞色彩的传说,或许未必完全荒诞不经,而是隐含着几百年来的当地历史信息,是历史记忆的曲折反映。白彝原本居住在水边,在彝人文化中,白色就是水的象征颜色,而达腊的白彝却住在山里。联想到这个妇人提到的口头传说,或许暗示一段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各个族群之间经常有冲突,这个宽腰带传说,乃是当时的彝汉争地的历史在口头传说中留下的痕迹。①族群之间的征战,从秦代即开始。公元前214年秦始皇进军岭南,战胜西瓯、骆越,桂东的壮族先民原始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桂西原始社会尚未解体。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李宏节进军桂西“始拓生蛮”,设置环洲(今宜州、环江),唐武后垂拱(685—688)中,在环洲之东北境设抚水州(今环江北部与贵州三都、荔波),西部设羁縻智州(今河池),这些政治措施使广西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地区受到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原始社会开始解体。见《毛南族民歌》,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1—2页。可能是当时还处于刀耕火种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白彝人,在争地盘时被赶出肥沃的水边土地,移居山上。
就我接触到的地区而言,都有类似的俗语,如“壮人住山头,彝人住水边,汉人住街头”。这句话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版本,比如“汉人占街头,彝人占田头,苗人占山头”等,可资旁证。
接着达腊白彝同胞为我们表演民族歌舞,虽然也掺入了“折扇舞”之类明显是当代舞蹈(尤其像大妈最爱的广场舞)的杂质,但整体上保持了原生态歌舞的大部分样貌。
演出涉及两种乐器:五笙五和铜鼓。五笙五,又名葫芦笙,用一束共计五根细竹子制成,两头置葫芦,葫芦底部有五个孔,演奏者以手指按压孔,控制音调。铜鼓有大、小各一只,大的那面鼓目测直径1米,似乎有些年头了,鼓面已经被敲打到变薄。
我问他们这面铜鼓的年代,说法不一:一人说200多年,另一人说有2000年了。或许他们误以为我准备收购,所以故意把年代说得更久远一些来提高价钱。等当地文化部门工作人员过来之后,才从他们口中得知,大的那一面鼓是民国时期的,小的则是10多年前制作的。可见,田野调查不可轻信被访人的介绍。也有些时候,被访者有可能因为怕答不上来丢面子及其他原因而胡诌,如果不加辨析地就此做记录,恐将出错。特别是当被访人的文化程度不高,当地又无档案记录的话,尤其要小心。
我原以为大、小二鼓的设置只是为了调节音律。直到他们告知:二鼓是一公一母的。此时,我又以为公的大,母的小,再次猜错,其实恰好说反了。他们是按照自然界母大公小的常态来设置的。目前网络资讯中,极少提到铜鼓分公母的关键文化特征,若非刻意在搜索引擎中键入“铜鼓+公母”的关键词,很难搜索出如此重要的民俗细节,甚至在公立博物馆的网站中都缺少甚至干脆没有这一关键介绍。这提醒我们,即便是学者,也总是或多或少带着主观的想法进入观察现场的。而在现代性思维浸染下的我们,极容易在不经意间,用自己惯常的思维,想当然地误套给被观察的对象。
二鼓用草绳悬挂在木架上,两者鼓面相对。演奏者对它们进行交替击打。顺序大致是双击大鼓一次之后,迅速多次单击小鼓,再反复若干次。我过去曾以为铜鼓都是鼓面朝天,双手抡棍子击打的。特别是这种小型铜鼓,本以为是像当代的架子鼓一样击打演奏,原来是自己主观误读了。白彝同胞的这种击鼓方式,或许暗示:(1)此鼓以母为尊,母大公小,有着母系社会的遗风。(2)鼓分公母,相向对击,或有原始巫术的遗风,阴阳和谐,对鸣求雨。
铜鼓文化是广西八桂大地延绵数千年来最重要的、几乎未间断过的代表性地域文化,但现在却处于衰微状态。目前复制出的铜鼓,在外观上基本达到古代氏族社会礼器的标准,但作为乐器,却难说够格。金海鸥先生对乐器之音提出过著名的四条标准:音准、音量、音色和分辨率。而无论是在广西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还是在这次的田野调查现场,笔者所见的现代仿制铜鼓在品质上都有待提高。这次白彝同胞敲击这两面铜鼓时,大的那面民国时期的铜鼓鼓面中心发出的声响颇为浑浊,而小的那面新近仿制品发出的声音又太杂乱。真正的作为乐器的铜鼓,鼓膛的回波共振非常重要,浑厚的鼓壁产生的波振量相当大,其穿透力可达千米之外。而我们如今在现场看到的铜鼓,也就是相当于道具性质的东西,其发出的与其说是“音”,倒不如说是“声”。
此外,真正的白彝服装是镶嵌银饰的,笔者却在几位年轻妇人身上看到塑料质地的仿银饰。这一廉价制品表明外界商品化批量生产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白彝,正在对白彝的传统社会文化进行强有力的渗透和深刻的改写。
许多真实的民俗,由于缺少噱头而往往是寂寞无声的。比如,2013年国庆节,笔者晚上夜游龙胜,沿着河岸走,看到有当地老人唱山歌,老妪和老翁相互对歌,歌词用的是当地瑶语。对歌调子凄切哀婉,若泣若诉,与白天歌圩的青年男女热闹非常、欢声笑语的情歌对唱大异其趣,而且与白天歌圩的歌者看见人来就唱得更起劲完全不一样,这些当地老人看见有陌生人经过时就降低嗓音,歌声含混不清。
我感到非常诧异,忙立刻开展田野调查。经询问旁人,才得知他们所唱的内容,乃是老年生活的不愉快,如婆媳矛盾、父子代沟、残年病痛,乃至回忆当年美好胜景不再的,内容伤感凄切。可惜我无法确切记录他们对歌的具体歌词。当时我忽然意识到,其实现在各地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多是有选择性的,公开对外的基本上是能够吸引游客的,而能够吸引游客的则是热烈奔放的。在网络文宣和电视台宣传的“传承民俗文化”的“龙胜十大节庆”,无一例外全部是这种类型的:瑶族禁风节、三月三壮族传统对歌节、三月三侗族花炮节、三月三瑶族干巴节、龙胜红衣节、龙脊金坑春耕摄影节、红瑶晒衣节、桂林龙脊金秋稻浪节、瑶族盘王节、苗族祭鼓节。结果这样一来,中外游客就被误导认为对歌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内容都是热烈开心的,却不知道那些对歌都是为了吸引他们而选择过的。他们只知道白天里的那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已经从他们视野中被屏蔽了。
如今除了节日和迎客之外,无论是黑衣壮还是白彝,日常生活都已经日渐难见传统服饰的身影。真正的“原生态”生活,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而被现代生活冲击得支离破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纯正原生态”,不过是商家的噱头罢了。
与黑衣壮一样,白彝的传统房屋也逐渐被废弃。因为传统建筑在夏天不够透风,闷热阴暗;而到了冬天又难敌严寒,冻得人难受。当地政府人员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木瓦结构房屋将慢慢消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感到惋惜,问当地村民为何不愿意再建传统房屋,村民答曰:除了不舒服之外,现在木料价格也已经太贵,无力再建传统木瓦干栏房屋,只能选择建便宜许多的水泥房。
村里全是老人和孩子,作为中坚力量的青壮年多已外出打工,年轻人接受、认同和追求的,乃是大山外面的“时髦”生活方式。被上一辈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到了下一辈人那里,就成了来自父辈口中的记忆,最后只能在博物馆、图书馆里面看到的文物、记载等了。
这就是“现代性”横扫一切的可怕力量,其借助当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载体,无形而无处不在。不少国外学者动不动就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归罪为所谓“被汉化”。其实,这不过是现代性扩张的结果,只是现代性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扩张,是以汉文化作为中介进行的罢了。换个文化语境,如在印度,这种现代性扩张又会被归咎为“不列颠化”“美国化”。
三、小 结
互联网的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和持久地颠覆我们以往的认知模式,族群文化之间的稳固边界正在模糊。互联网时代给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挑战,迫使我们在新的时代氛围中重新思考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问题。在现代性文化的整体冲击下,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如今的政府投入,不应当过度倾向于那些能立刻显现出明显经济效果的节庆活动,而是应运用激励机制来吸引年轻人投入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实施活态保护。不过,尽管如此,由于时代风尚、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日新月异,这样的保护措施可能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这些传统民间文化的衰亡,它们即便在保护政策中延续生存下来,也依旧无法避免变异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汉族文化亦是如此。
所以及时进行资料整理,如文字材料的编撰整理、影像资料的拍摄和归档,就成了政府和学界的当务之急。这些资料在整理之后,不能仅仅留存在资料库中,而要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及时通过网络向大众展示出来。这些整理工作其实非常紧迫,如果我们不尽快开展,那么随着互联网通讯的稳步铺开,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化很可能在20年之内无记录地消亡。日后再想深入细致地做相应的研究,也只能是此情只待成追忆了。
① 本文为“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简圣宇(1981- ),男,南宁人,广西艺术学院艺术学二级学科“艺术理论与批评”学科带头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