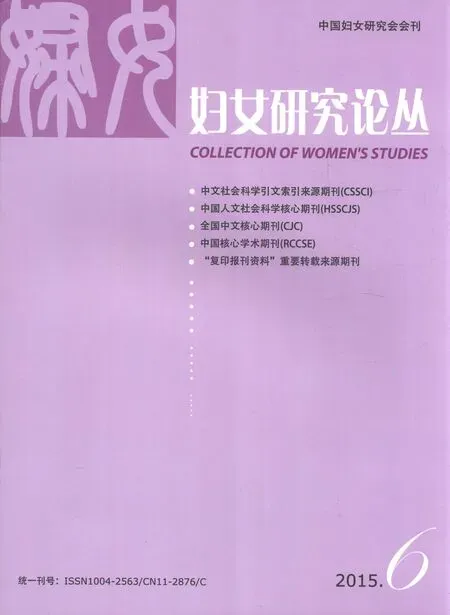积极保障妇女权益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 宪政研究所,北京 100088)
积极保障妇女权益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刘小楠
(中国政法大学 宪政研究所,北京 100088)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提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第二点主张是“积极保障妇女权益”,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并提出保障妇女权益的途径和重点领域,即“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能力,保障妇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学,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指明了方向。
北京世妇会以来,在涉及妇女权益的几个重点领域,中国取得了诸多成就,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第一,近年来,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有所提高,但是总体说来,女性在参与决策和管理方面的进展仍然缓慢,比例总体较低,女性正职少、副职多。这与中国法律政策中关于妇女参政比例的规定存在刚性不足、执行力不强、目标值设定过低、缺乏违规
惩罚措施等问题密切相关。第二,’95世妇会后,中国在妇女与经济这一重大关切领域中的法律发展比较快,2006年签署了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先后制定了《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修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特别保护规定》等涉及妇女经济权利的法律法规。但是在促进妇女就业,维护女职工劳动权利方面依然存在障碍,妇女就业率降低,性别歧视现象比较普遍。第三,中国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妇幼健康法律政策体系,妇幼健康逐步实现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规范服务。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131个。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由 1995年的 61.9/10万下降到 2014年的21.7/10万,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1]。但是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妇幼卫生服务可及性较低,而且中国至今尚未将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全面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第四,中国女性在教育领域中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层次上都不断提高,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村贫困地区女性受教育权利受限,受流动影响女童生存发展环境有待改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不平等及高等教育的性别隔离也比较严重;性别平等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从全球范围内看,越来越多的女童获得前所未有的教育机会,孕产妇死亡率大幅度降低,更多妇女成为商业机构、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但是,总体来说,性别平等的进展仍然缓慢而不均衡。2015后发展议程强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等目标。这些目标与习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所提出的“积极保障妇女权益”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将性别观点纳入发展决策的主流”是’95世妇会提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主张。北京世妇会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观点逐渐渗透到中国的立法工作中。这一方面体现在立法中开始增加性别视角,另一方面体现在制定和修改了多部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以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规章为补充的保障妇女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从而在更广泛的领域为妇女权益提供法律支持。
目前,中国虽然多部法律法规中都包含了保护妇女权利的条款,但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分散,重复性规定较多;在立法模式上,重保障、轻赋权,把女性作为保护的客体,而非权利的主体;在立法技术和内容上,原则性的规定比较多,缺乏必要的概念界定和认定标准,法律救济和法律责任部分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这些缺陷都削弱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导致了法律适用性的不足。我们应分析相关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政策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克服法律中的性别本质主义和生理决定论,减少法律对女性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
1.将单性别“保护”模式改为“赋权”给每个性别群体是世界性立法趋势。目前中国立法中仍然存在着一方面对女性权利保障不足,另一方面对女性过度保护和强制保护的问题。如中国《劳动法》中规定了女职工劳动禁忌范围,立法者的本意或许是保护和照顾女性,但是,这类规定的依据大多来自对两性生理差异的认识,即女性比男性弱小,而且女性的生育功能及特殊的生理现象对工作环境的要求更加严格,如果不对女性进行特殊保护,就会危害到女性和下一代的健康。其实,基于科技的不断进步,有些工作已不再对女性造成危害;医学的发展证明过去某些禁止女性从事的工作对男性的危害与女性并无不同。因此要根据科学和技术进步情况定时进行审查,考察这些限制性措施是否确实是为了保护妇女健康和工作安全而设置的,是否确实有禁止的必要,是否有单独禁止女性从事的必要。这样,不仅从生理层面保护了女性,也赋予了女性一定的选择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慢慢扭转人们对所有女性都无法从事某种劳动的性别偏见。否则,忽视了女性内部差异的所谓特殊保护其实是以实质平等为名限制女性自由,剥夺了女性自主选择工作的权利,也给了用人单位拒绝雇用女工的借口。再如,中国的相关法律政策
中多次使用“安置”女干部这样的用语,女性成为被动安置对象和客体,忽视了妇女在参与权力和决策中的主体性、积极性以及能力、意识的提高和培养。
2.适当使用暂行特别措施。采取暂行特别措施是“由于历史和社会文化原因,女性在受教育程度、经历、能力和心理上处于劣势地位,她们与男性竞争的历史起点不同,造成‘结果的不公平’,并且日益形成‘劣势积累’、‘劣势叠加’,造成与男性的差距日益拉大”[2]。为了实现实质平等,有必要在某些情况下实施暂行特别措施。比如,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研究,任何一个群体的代表在决策层达到30%以上的比例,才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实际影响力,而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妇女参政比例方面,使用“适当数量”“适当名额”“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部”等倡导性、模糊性词语取代具体的配额制,导致其仅具宣示性,不具备操作性。目前只有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要求“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1/3以上”。也就是说,对于女性参与权力和决策,中国法律基本上只是规定了消极的不歧视义务,即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对于促进女性参与权力和决策的积极措施基本上是宣传倡导性的,除了对村民代表会议中妇女村民代表规定了明确配额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具体的政策措施确保循序渐进地提高妇女代表比例。这种原则性的表述造成了执行的困难。消歧委员会也多次建议,为了加快实现妇女在各个领域实质上的平等,中国应该充分利用暂行特别措施[3]。
此外,“积极保障妇女权益”也要加强对立法、执法和司法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中国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中侵犯妇女合法权益以及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审理涉及女性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今后应加大对公职人员,尤其是立法、执法和司法人员进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的力度,提升其社会性别分析的能力,促使其将性别平等理念贯彻到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中。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2015年9月)[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刘莉,李慧英.公共政策决策与社会性别意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七、八次合并报告[EB/OL].http://guoqing.china.com.cn/zwxx/2012-03/ 08/content_24841972.htm,2014年5月4日访问.
刘小楠(1973-),女,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理论法学、宪法学、反歧视及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