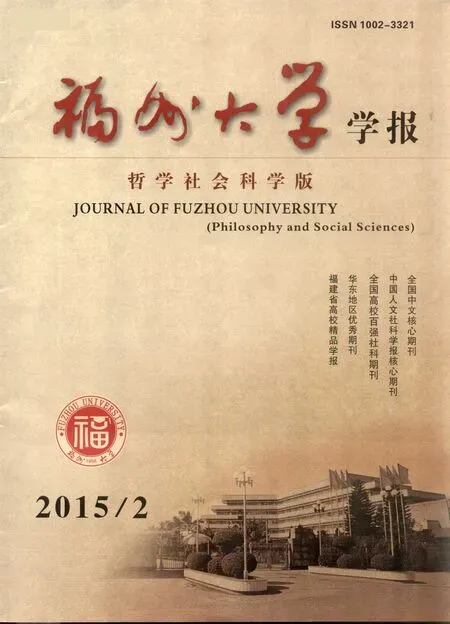我母亲/我自己:论《乡村女孩三部曲》中“她故事”的重写与再现
王 斐 林元富
(1.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2.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一、引言
翻开厚重的爱尔兰民族历史,不难发现这片于1543年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土地,战祸绵延,天灾不断,社会动荡。尤其自20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面临的文化存续、民族尊严维系及国家重建等重大议题构成了当代爱尔兰文学宏大叙事,而爱尔兰民族主义则是不可或缺的重大母题。正如伊格尔顿(Eagleton)曾经这样评价:“民族主义将爱尔兰(作为独立的国家)绘上了世界地图。”[1]然而,爱尔兰民族主义却体现为菲勒斯一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在如此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爱尔兰文学传统中的民族主义投射出“国族即女性”(nation as woman)的文化想象,正如琼斯所言“在爱尔兰,爱尔兰性被深刻地性别化了”[2],女性的身份已经被盗用和改写。换言之,在父权主义宰制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修辞话语中,现实生活中的爱尔兰女性从未被视为独立的、有生命、有思想的个体——她们要么成为男性诗人哀悼亡国之殇的客体[3],要么被物化为无生命的国家象征物。[4]这种将女性国家化,理想化以及去人性化的修辞策略实则将爱尔兰女性的真实选择、权利和欲望集体抹煞。在爱尔兰漫长的民族历史,“她们一直为英雄的存在创造着可能,但她们却一直是沉默的”[5]。换言之,真正的女性早已在女性/民族主义/国家形象等一连串的置换位移中,被吞噬不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符码化的空洞能指,是男性虚构想象中的爱国主义与国家形象。
对于这种变相尊崇下对女性主体性的实质扼杀,爱尔兰女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感触颇深。在她那本带有半自传性质的杂文集《母亲爱尔兰》中指出,这种父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爱尔兰女性压制的共谋关系,“爱尔兰至始自终是一个女性、子宫、洞穴、母牛[6],一个叫罗萨琳的女子[7],一个新娘或者是一个女巫。[8]。在奥布莱恩看来,自爱尔兰文艺复兴以来创作的文本所刻画的女性都是在父权凝视下的客体。例如叶芝《胡里痕的凯瑟琳》中的凯瑟琳,《疯女简与主教对谈》中的疯女,剧作家辛格《骑马下海的人》中的老妇茅里娅,甚至在这场运动中著名的女性作家格里高利夫人在《旅人》中塑造的母亲形象,女性都是作为虚构的概念,被降格到叙事和历史的边缘。如苏雷曼所言,男性的书写把女性的书写置于边缘化的地位,使之成为权力关系中位于中心外的现象。[9]
因此,类似以女性记忆、经历为主体的故事与论述却一向被压抑或忽略,而无法进入公共论述之场域。在父权社会中被隐匿的“她故事”的状况表明女性无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历史的被动者,她无法走进历史,她的奋斗与嘶喊只能是在历史边缘,最后被历史中心的声音所吞没。概而言之,爱尔兰民族主义中的性别再现和性别陈述完全隶属于男性,并与父权主义一起实行对女性的宰制,扼制进而戕害女性之主体性。
然而,正如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中的那句名言所述:“书写可以为变革、为社会和文化结构变革的先驱运动提供可能性,书写所创造的空间可以成为颠覆性思想的跳板。”[10]随着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自我意识觉醒,以艾德娜·奥布莱恩为代表的新时期的爱尔兰女性作家试图僭越从男性实际暴力到话语的象征暴力,还原再现重写爱尔兰女性的真实故事。她们往往着眼于以女性为主体的欲望论述,以女性意象、生理经验与情欲解放,娓娓道出属于女人的私语,从而在父权文本的空隙中开掘多维度的话语空间,用以女性为主的历史置换男性话语为主的历史,检视女性认同的转机与危机。
奥布莱恩1932年出生于民风保守的爱尔兰西部的克莱尔郡,以文风抒情,手法大胆而在英美两地拥有大量的读者群。她凭借1960年出版的《乡村女孩》声名鹊起,并将该小说扩展成《乡村女孩三部曲及尾声》(Country Girls Trilogy and Epilogue)[11]。此后笔耕不辍,出版了20 余部长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以及乔伊斯和拜伦的传记。2011年已经80 高龄的奥布莱恩凭借小说集《圣人们和罪人们》(Saints and Sinners),获得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该届奥康纳奖评委、爱尔兰诗人和小说家托马斯·麦卡锡评价说,“她是爱尔兰生活中的索尔仁尼琴——当所有人都闭口不谈爱尔兰妇女的命运时,她还一直在讲。”[12]
在初试啼声之作《乡村女孩三部曲》中,奥布莱恩首开爱尔兰文学历史先河,以女性独到的视角透视爱尔兰女性苦楚境遇的现实,为女性的不公命运发出第一声呐喊。《乡村女孩三部曲》可以说是一部现代爱尔兰女性的成长小说。小说以腼腆的凯特(Kate)为主线和叛逆的芭芭(Baba)为副线,以诗化的语言、坦率的热情与愤怒讲述了两位成长于爱尔兰西部贫困乡村的女性在父权主义和天主教会压制下的痛苦成长过程以及试图摆脱传统社会强加于身的枷锁的挣扎。因书中对女性情欲的坦率描写,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口诛笔伐;甚至爱尔兰政府当局将她的小说列为禁书。她的克莱尔郡的父老乡亲指责她对爱尔兰女性的恶意抹黑,并在教堂空地举行了焚书仪式;她的母亲甚至用墨水圈出书中每一处不当用字,刻意使她难堪。而吊诡的是,她在作品里所想要反抗的这是这种固步自封的思想态度,以及令人窒息的“道德标准”。
本文拟以《乡村女孩三部曲》为案例,通过小说中凯特的母亲以及凯特两代女性的人生悲歌,探讨奥布莱恩如何以通过言说爱尔兰女性在父权主义和天主教会重负下所遭遇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以及女性权利信仰和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在小说话语中反馈自我的主体性,藉以诠释女性自我的存在。
二、无名氏的母亲——爱尔兰传统女性的悲歌
母亲可以说是奥布莱恩在《乡村女孩三部曲》创作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因为母亲身份在女性性别身份中处于重要位置。一方面母亲是女儿身份的延伸,另一方面,从传统伦理观念看母亲身份又暗示了妻子身份的在场。与其说奥布莱恩关注“个体”的母亲,不如说关注的是“母亲”这一群体的人生传奇。这样对母亲身份的关注事实上表达了奥布莱恩对爱尔兰女性命运的全面关注。
在《阉割与斩首》中,西苏指出,在父权主义话语中,步入婚姻殿堂前女人是“沉睡”的,没有意识没有身份。[13]只有通过婚姻,女人才能真正醒来。但是,女人被唤醒之后,也只是从其“婚床——童床——灵床”生命的历程的一个阶段走向另外一个阶段而已。[14]可以说西苏的这一番言论一针见血地概括了20世纪中前期爱尔兰女性的生存现实——女性被男性定义为他者并局限在家庭领域。传统的女性特质观围绕着关怀、家庭和生育为中心。[15]事实上,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位无异于将女性又推入了另一种梦魇的深渊,等于开始了另一种沉睡,因为她们依然没有自我,一切都以家庭为中心,“女人只是从一种死亡(沉睡)走向了另外一种死亡(被驯服并被限制在家庭中):失去身份和主体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死亡”[16]。易言之,在父权话语中,女性是沉默的,从未存在的,是死亡的。
小说中,凯特的母亲在整部小说中的符号命名只是“妈妈”,小镇中所有人对她的称谓也是以“妈妈(MAMA)”而代之,至始至终,读者对母亲的名字一无所知。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人名是人类社会中指代每一个具体成员的符号。当一个人只有取得名字,才能取得其社会存在的标志。名字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一种符号。可见,奥布莱恩通过凯特母亲的无名状态隐喻了爱尔兰父权社会中女性并不是以一个完整而独立的人存在,而是充当了“失声”的“哑女”。
凯特的母亲“妈妈”是爱尔兰父权社会和天主教会定义的“理想妻子”的典型代表。诚如亚德安里奇所言:“制度化的母性要求女性具有母亲的本能而不具有智慧,要求他们无私而不是自我实现,要求她们建立同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创建自我。”[17]在父权话语中,母亲是天使般关爱和宽容的源泉,母亲成为道德价值和温柔情感的象征与残留。母亲身份的制度化压抑了女性的发展潜能,把她们束缚在家庭并赋予她们一些具有模式化的品质特征,使女性不得不按照男性理想来塑造自己。
于是,“妈妈”克己忍让,逆来顺受,终日辛勤劳作于贫瘠的土地上,起早贪黑料理家务,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而凯特的父亲(Dada)则是终日无所事事,沉溺于酒精中,常常将家中微薄的收入在酒杯中挥霍一空,并常常在酩酊大醉的时候对“妈妈”虐打谩骂。对此,“妈妈”没有加以反抗,恰恰相反,她总是处于一种矛盾式的压抑苦楚。确切说来,“妈妈”全然忽略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和地位——是她用柔弱的肩膀而非酒鬼丈夫支撑起家庭的生计;在她眼中,酒鬼丈夫仍是家中的支柱,担心丈夫倘若酒醉不归,家庭就由此崩塌。但另一方面,一旦丈夫归家,她又陷入了更深的惶恐,害怕丈夫对自己和女儿凯特的殴打。爱尔兰社会历史学家布莱德利曾经如是描述过早期爱尔兰农村妇女的悲惨境遇:“生活对于她们而言是辛劳而又毫无回报的,婚姻对她们而言不过带来的是永无止境的农活家务以及所得甚少的婚姻幸福感。”[18]少女凯特也洞悉了母亲痛苦不幸的婚姻,“(妈妈)就像是冬天荒原中寂寞无助的小麻雀。真难以想象她是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头戴宽大礼帽,披上缀满蕾丝的嫁衣出阁的。那时的母亲定是因为要嫁为人妇的欢悦而留下幸福的眼泪,而今母亲则是婚姻的不幸而泪眼朦胧。”[19]可以说,当母亲步入婚姻后,她的灵魂已死,她不再去奢谈爱情,不再幻想一个女人世俗的荣耀、满足与幸福,她只能恪守父权强暴话语权威压制下负重忍耐的使命。
吊诡的是,作为这套规则的受害者母亲也参与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机制中,传统女性不仅默认父权制,而且内化并传承给下一代,尤其是女儿。如南希·弗莱迪而言:“母亲依照自己的形象培养女儿,由于母亲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否定了自己的性征,她也因此必须阻止女儿有自己的性征。”[20]母亲也渴望凯特能拥有更好的生活,不要重蹈她的覆辙,然而并非鼓励凯特勇敢追求自我的独立,母亲却将女儿的幸福寄托于对天主教的皈依,“(母亲)她更愿意我成为一个修女而非为人妇。”[21]由此可见,爱尔兰父权制度与天主教会达成某种共谋,对妇女建构了一整套的严格规范。
饱受精神和物质折磨的母亲,最终在一场沉船事故中溺亡于幽暗漆黑的香农河。小镇中的居民们对母亲之死不无惋惜,他们安慰凯特道:“你母亲是一个真正的淑女,一个人人都为之敬仰的贞妇。”[22]所有这些赞扬之词不过是将母亲禁锢在父权社会的狂热崇拜之中,她被用来维护某种霸权机制,她的生命尊严沦为对社会的一种功能性诠释。如圣母般的神圣光环事实上掩盖了母亲所遭受的残虐与不公。母亲的溺亡,充满了某种隐喻——沉入晦暗冰冷的香农河底意味着陷落于母性文明前的黑暗大陆,意味着死亡的冲动,和被社会抛弃冷落的边缘命运;而浮出水面则暴露于父权制的象征世界,意味着束手就擒。
三、“母道的内化”——女儿徒劳的抗争
小说中,母亲的溺亡,是母亲形象不在场的隐喻。“缺失母亲”意味着女性对母亲所负载的父权社会加之于的社会功能的拒绝。然而拒绝“母亲”之后,女性又将以怎样的情感模式替代母爱呢?
对于凯特而言,与母亲的前俄狄浦斯联系是一个神话和幻觉,它遮蔽了碎片、缝隙和断裂。而母亲的早逝揭示出一种文本深层象征意义:在一个父权制和象征语言的社会体制中,女儿要成长为父权社会所期望的的“好女人”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压制和扼杀“前俄狄浦斯母亲”的暴力。凶暴而愚蠢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站在父权社会以及天主教会典章规范的高度,阻止凯特追求独立与个人幸福。他训诫凯特不要让她早逝的母亲失望。事实上,他不仅用父权社会中“理想妻子”的标准耗尽了母亲的生命,甚至在其死后肆意篡改扭曲妻子对女儿的真实心愿,仿佛成为一个好女人、好母亲是女人们之间母女相承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男性强加于女性的自私要求。
母亲的早逝给凯特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面对粗暴蛮横、自我为中心又道貌岸然的父亲,凯特充满了恐惧、仇恨与厌恶。和母亲一样,幼年的凯特害怕酒醉的父亲对自己的拳打脚踢。看着卧病在床陷入昏迷的父亲,凯特对父亲仅有的一丝同情随即被一种无法名状的兴奋与愤恨所替代。[23]易言之,凯特不可能对自己的生身父亲产生任何亲情。她内心一方面拒绝重蹈“母亲”的覆辙,然而父爱的缺失又使她渴望拥有“父亲般的庇护”的情感归宿。小说中,这种“对母亲的排斥”和“对父亲的追随”的痛苦挣扎在凯特身上得到了预演。
克里斯蒂娃认为父权制的作用不仅仅包括阉割和法律,父亲不只是法律中严厉的父亲。相反,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也就是所说的“想象之父”,即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史前史的父亲”。换言之,他是被俄狄浦斯压抑的所掩埋于前意识底层的“双亲两者”(mother-father)。儿童对他的认同是立即而直接的,不同于俄狄浦斯以后的认同。传统的心理学认为,儿童进入社会和语言秩序是由于害怕阉割。小孩与母亲躯体的分离是一种失落与悲剧,而克里斯蒂娃相信这种分离既是痛苦的又是快乐的,儿童进入社会和语言不仅仅由于父亲的威胁,而且由于父亲的慈爱。[24]
慈母的早逝给少女时代的凯特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这种分离意味着失去了与母亲共同拥有的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幸福美满。现实中的父亲冷酷暴戾更加重了她的孤独和伤感。然而也正是由于母亲的猝然离世,使她能够远离闭塞的家乡,前往都柏林追寻自己的人生,也开启了凯特的爱情之门。进入凯特心扉的正是“慈爱”的父亲“绅士先生”(Mr.Gentleman)。他就是第一个引领凯特脱离母亲躯体走向父权宰制下的语言和象征秩序的父亲。而这种背离母亲转向父亲认同的方式,必然使得凯特遭遇了客体化与色欲化的命运,成为男性凝视下的客体。
绅士先生是一位由都柏林搬到克莱尔郡的法裔律师,“他是个法国人,德·莫里哀先生,但是乡里没有人能正确地发出他的法国姓氏的读音,但他一头柔亮的灰发与笔挺的西装马甲让他如此与众不同,故而乡人便尊称他为绅士先生”。[25]与周遭粗野鄙陋的乡民相比,他出身高贵、温文尔雅、睿智谦和。绅士先生身上所具有的“慈父”与“情人”的双重特质,深深吸引了凯特。然而,在这段年龄身份相差悬殊的婚外恋中,凯特始终显得无足轻重——她只是一个卑微的乡下姑娘,一个供他赏玩,将之色欲化客体化的美丽玩物,他赞赏凯特那如巧克力般丝滑的秀发,如珍珠般圆润的双眸,如阳光下蜜桃般的柔美肌肤;[26]他曾亲昵地称有丰腴之美的凯特像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小母鸡。[27]绅士先生许诺与凯特私奔到维也纳,最终因凯特父亲的威逼而以一纸电报结束了两人的恋情。因为凯特不过是绅士先生死水微澜般的婚姻中偶尔泛起的涟漪,故而绅士先生所能给予的幸福最终幻化成海市蜃楼。
在小说第二部《寂寞女郎》中,心灰意冷的凯特在都柏林的一次酒会上邂逅了另外一位年纪与父亲相仿的已婚男子——尤金·盖乐德(Eugene Gaillard),一位曾经辉煌但而今却抑郁不得志的好莱坞纪录电影导演。和尤金的相恋,使凯特陷入了来自于父亲、乡邻以及天主教会道德谴责的漩涡。愤怒的父亲将凯特从都柏林强行带回家乡,怒骂女儿是离经叛道的浪荡女子,令其母亲蒙羞。当凯特坦言尤金与身在美国的妻子劳拉(Laura)长期分居即将离异,她的出现并非构成他们婚姻的威胁时,她的姨妈随即犀利地指出,“离婚比谋杀所犯的罪行更令人不齿”[28][29]。家乡教区哈格提神父(Father Hagerty)谴责凯特“踏上了道德腐化的歧路”[30],劝诫凯特要重拾对上帝的信仰,抵制尤金的诱惑。面对来自于父权与天主教会的压力与种种苛责,凯特勇敢地予以回击,回到了她所深爱的尤金身边并与之同居。可以说,奥布莱恩以凯特和尤金的恋情撼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民风保守的爱尔兰社会的根基。
然而当尤金带着强烈的欲望进入凯特的世界时,他带来了毁灭。诚如西苏所言“(在父权社会中)如果你是女人,你将被塑造成理想的女人;你将服从一切规训你的指令。你将控制你的愿望,并让你的愿望只出现在合适的场合,以合适的方式奉献给合适的人,你将崇尚并履行法律。”[31]在形同牢笼的“家”中,尤金按照爱尔兰父权社会对传统女性的要求重新塑造凯特,不顾及凯特的情绪和感受,企图使她成为一个对男人的情感索要有求必应的女人。尤金自认为自己担当了凯特人生道路的引路人和拯救者,陶醉于对凯特的教导。他认为妻子愚昧无知,是需要男性启蒙的——他像对待孩子一般教导凯特,为此他指定凯特要读的书,甚至在夜晚也只能是他带给凯特身体的愉悦。[32]为了将凯特塑造成他臆想中的爱尔兰女性,尤金对凯特的衣着打扮以及言行举止进行了严格的限定。除了要求凯特安分守己,足不出户,他甚至要求凯特的衣着打扮要符合一位贤妻良母的形象,为此他为凯特购置了无张扬色调的脂粉,黑色窄边的天鹅绒束发带以及一双蕾丝平底鞋。[33]尤金“导师”的角色,傲慢与独断,久而久之令凯特心力交瘁。当她试图反抗的时候,却遭到尤金如雷般的斥责,“是我提供了所有的一切,让你衣食无忧,我竭尽全力地教化你,教会你如何谈吐得体,教会你如何待人接物,建立你的自信。如今,你竟敢想占有我!”[34]
在与尤金的婚姻中,凯特逐渐丧失了起初与父权社会抗争的勇气,自我的主体性渐渐被尤金的男权意识无情淹没。在小说的前两部中,凯特做为叙事者,以她的视角,娓娓道来个人的经历与所思所感;然而在小说第三部《婚姻幸福的女孩们》中,奥布莱恩一改前面两部小说中以凯特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将故事叙事者另立为芭芭。换言之,凯特叙事者身份的缺失,暗示了已为人妻人母的凯特自我主体性丧失。
面对自私冷漠、独断专行的尤金,倍感压抑痛苦的凯特做出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次对父权社会礼教的抗争与背叛——她与已婚男子唐肯(Duncan)一见钟情并与之幽会。然而面对令人窒息的礼教和久违甜蜜的爱情时,凯特忍受着巨大的煎熬,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楚。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语指出婚姻束缚了女人的自由,她们无法离开婚姻,无法脱离男人而生存——因为婚姻也是她们生存的保障,依附性使女人无法改变父权社会的既定秩序。最终带着负罪感的凯特向尤金坦诚了自己的不忠并祈求丈夫的宽恕。然而,早已发现这段私情的尤金断然拒绝了凯特的乞求,强行带走了儿子卡诗(Cash)前往美国,抛弃了凯特。
当伪善冷漠的丈夫利用道德礼教和儿子折磨凯特;当怯弱的情人唐肯不能脱离所生活的环境和社会来全心地爱她时,凯特对生活和理想彻底失望了。她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悲哀与不幸,她需要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干扰。她要用她的方式寻求到心灵完全宁静。凯特最终也和她的母亲一样,在幽暗漆黑的河水中溺亡。家乡的亲朋都认为凯特死于意外,并对她的生平过往闭口不谈。与母亲那场“祭奠伟大母性”的盛大葬礼相比,凯特的葬礼则是冷清而静默的——对于他们而言,离经叛道的凯特违反了父权社会、宗教及伦理道德的游戏规则,是一个自私享欲的荡妇,是家族的耻辱。然而,作为凯特悲惨命运见证者的芭芭相信这是凯特最后一次以壮烈而决绝的方式表达对自我命运的掌控以及对父权社会不公的控诉。
四、结语
奥布莱恩在《乡村女孩三部曲》中塑造的“妈妈”和凯特这一对母女,互为镜像。她们的人生悲歌真实再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爱尔兰女性的真实境遇——她们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身上压着宗教和礼教的枷锁,顺从者无声地沦亡,反抗者悲惨地死去。不管是母亲还是凯特,她们鲜活的生命在爱尔兰保守的父权社会和压抑人性的天主教会双重压制下中归于寂静。诚如西苏所言,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面临的两难境地:消极被动意味着死亡,积极主动同样意味着死亡。[35]凯特抗争的一生最终代表的是如母亲般的所无法摆脱的命运——有生命,无声息。虽然她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找到一块比母亲更为广阔而自由的生存空间,拥有一种不会置她于死地的思想和声音,但所有的一切事与愿违,灵魂之死,沉默回归母亲的位置。最初寻求女性声音的渴望幻化成最后女性声音悲哀的寂灭和扭曲。
综上所述,一方面,奥布莱恩在文本中以情爱欲望的流淌、叙述声音的释放等张扬女性主体意识的表现方式,对爱尔兰社会、历史和文化加以重新审视,对爱尔兰父权主义、天主教权威提出挑战与质疑,揭示了当代爱尔兰女性所面临的种种不公与屈辱,为争取爱尔兰女性的平等与公正发出了有力的呐喊;另一方面,奥布莱恩以言说“她故事”之方式,书写在时间的针脚中真实而隐形地活着的爱尔兰女性的故事,从女性叙事中形成爱尔兰女性自己的文化图景,彰显了爱尔兰女性从被迫失语到主动建构,从被书写凝视的客体到积极言说张看的主体,由“边缘”向“中心”挺进的努力。
注释:
[1]Terry Eagleton,The English Novel:An Introduction,New Jersey:Wiley Black- well,2004,p.291.
[2]Jones and John Paul(eds.),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Difference,Methodology,Representation,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7,p.21.
[3]在爱尔兰传说故事中,爱尔兰经常以可怜的老妇人为其象征。如1916年复活节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在其诗作《我是爱尔兰》(Miss Eire GI Am Ireland)中的诉说者为一位年迈老妇,她将自己比拟为爱尔兰,无尽歌颂了盖尔传统的无尽辉煌,鞭挞了英国殖民者的残暴血腥,但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却抹灭了女性人性化的一而,忽略了爱尔兰女性的现实处境。参见王斐:《父权文学传统描绘下的爱尔兰地图——浅论后殖民主义关照下的爱尔兰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 期。
[4]在民族诗歌创作中,被理想化为诗人灵感的缪斯女神海博妮娅逐步成为民族男性诗人集体意识反射而形成的镜像。另外,女神海博妮娅所弹奏的竖琴,也成为民族诗中常引用的一个国家象征符号;在此,女神和竖琴意象的结合使女性被物化的修辞得以进一步加强。参见王斐:《父权文学传统描绘下的爱尔兰地图——浅论后殖民主义关照下的爱尔兰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 期。
[5][14][31]Cixous,Helene,Catherine Clement,Newly Born Woman(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86,pp.110,66,110.
[6]这里指的是爱尔兰莫伊德牛(Irish Moiled),为爱尔兰本土特有的牛,常用于制作肉制品以及牛乳制品,同时被认为是爱尔兰的象征。
[7]罗萨琳为爱尔兰常见的女姓名,在盖尔语中为Róisín。同时罗萨琳一名又源自爱尔兰诗歌《黑暗罗萨琳》由爱尔兰诗人摩根(James Clarence Manganl (1803-1849))创作,此诗歌在英国打压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时,以爱情之名抒发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罗萨琳逐渐演化为爱尔兰的象征。
[8]O’Brian,Edna,Mother Ireland:A Memoir,New York:Plume Book,1999,p.12.
[9]Suleiman,Susan Rubin,“Wring and Motherhood”in Shirley Garner Shirley Nelson Garner,Claire Kahane,Madelon Sprengnether eds,The Mother Tongue:Essays in Feminist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354.
[10]Cixous,Hélène,“The Laugh of the Medusa”,in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edited),New French Feminisms:An Anthology,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1,pp.245-264.
[11]《乡村女孩》(The Country Girls,1960),《寂寞女孩》(The Lonely Girls,1962),《婚姻幸福的女孩》(Girls in Their Married Bliss,1964)。
[12]《埃德娜·奥布赖恩获世界奖金最高短篇小说奖》,《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4 版。
[13]Cixous,Hélène,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in:Annette Kuhn (Translator).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l.7,No.1,Autumn 1981,pp.41-55.
[15]一九二二年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通过过一连串的立法限制女性在家务场域外的表现机会,比方限缩女性公职升迁、法庭陪审权、婚后工作权,甚至规范职场女性劳动人数。1937年的新宪法更明定爱尔兰女性对国家的最大贡献是相夫教子,并善尽女人“自然”的天职。
[16][35]Cixous,Hélène,Three Steps on the Ladder of Writ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17.
[17]Rich,Adrienne,Of Woman Born: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5,p.42.
[18]Bradley,Anthony,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Ireland,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7,p.260.
[19][21][22][23][25][26][27][29][30][32][33][34]O’Brian,Edna,Country Girls Trilogy,Orion Books Ltd,1988,pp.9,67,80,253,12,61,90,269,269,323,322,358.
[20]Friday,Nancy,My Mother/My Self:The Daughter's Search for Identity,New York:Delta,1997,p.87.
[2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爱情传奇》,姚劲超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2年,第55页。
[28]爱尔兰从1996年起已经废除了禁止离婚的法律规定。禁止离婚,在爱尔兰历史上是存在的。深受天主教的影响,在1937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了“任何法律都不得允许婚姻关系的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