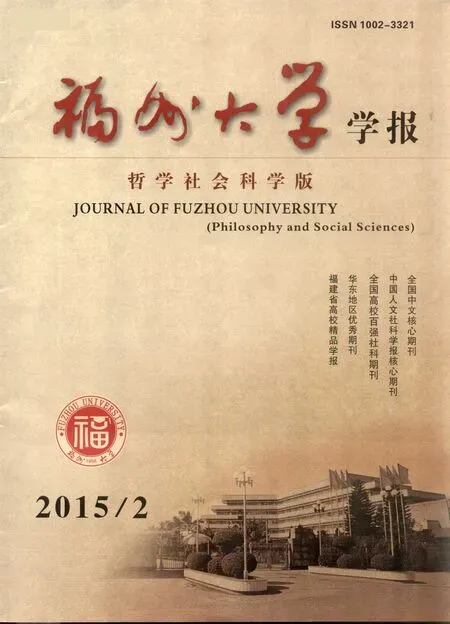论两宋时期文学作品的域外传播
谭新红 柯贞金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两宋时期,文学作品除了在宋朝境内得到广泛地传播外[1],还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西夏、辽、金等周边少数民族国家,有时甚至远播至隔海相望的高丽、日本。宋代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后,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而且影响了该国的文化修养和文学创作。
一、传播途径
宋朝是鼓励国际贸易的朝代。宋太祖首先定下商税规例,太宗完成统一大业后,于雍熙年间着内侍八人持以敕书、金帛赠南海诸蕃商。这一政策为宋代诸帝所继承,南宋时期,淮水以北土地沦入金人之手,为赠加国家收入,更要发展海外贸易。[2]由于宋朝统治者重文抑武,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书籍自然成为贸易的重要商品,文学作品也趁此机会传播境外。当然,由于有些时事地理类著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全,书籍的对外贸易也受到种种限制,民间走私因此成为必然。此外,外国使臣求赐也是宋代文学作品流往异域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购买
在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坊主将文学作品编印成集出售,或者干脆单篇印制出售。文学靠自己的音乐属性或文学属性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当时的国子监不但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国家最高级别的出版社和图书交易市场,读者可以在这里购买到质高价廉的图书。国子监的书既出售给本国人,也对外国人开放销售,如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新罗人来朝贡,因往国子监市书”[3];李朴《丰清敏公遗事》记载丰稷在做国子监祭酒时,“高丽遣使者朝贡,请买国子监书籍数十种。馆伴陈轩牒公请贸与之”[4]。
外国人不仅在国子监买书,也会到杭州、川蜀、福建等刻书和书籍交易中心购买。元丰年间,高丽使者到杭州后,就曾求购苏轼的集子。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十存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有同苏轼“同系乌狱”诗四首,第二首云:“拟策进归中御府,文章传过带方州。”自注:“前年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这是苏轼诗文作品传入高丽的开始。
日本素来仰慕中国文化,唐朝时的遣唐使更是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九世纪末日本虽然废止了遣唐使,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没有断绝,私商和僧侣承担起了传播文化的责任。他们从中国传回日本的书籍主要是佛教类及经部、史部类著作,也有文学作品,如据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白记》记载,景德四年(1007),宋商曾令文抵日,并以醇酒、苏木碗碟之类赠送左大臣藤原道长,此外又以《白氏文集》及五臣注《文选》相赠,道长献于朝廷。宽弘七年(1010)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商人献上“折本注文选、同文集”。“折本”即印刷本,指宋刻《昭明文选》和《白氏文集》。[5]绍兴二十一年(1151),宇治左府藤原赖长开列书目数十种,托宋商刘文仲代购。[6]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日本著名僧人圣一国师入宋从径山寺(余杭)无准师范学禅,后于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携数千卷图书回国。从1353年东福寺二十八世祖大道一以据此所编之《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可知,圣一国师带回国的图书中,就有《镡津文集》10 册、《注坡词》2 册、《东坡长短句》1 册、《诚斋先生四六》4 册等宋人创作的文学类书籍。
外国人不但购买整部的书,也会购买影响大的单篇作品:
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诗,人未知之。荆公爱焉,手写其一联“有时俗事不称意,无限好山都上心”于所持扇,众始异焉。弟清老,亦修洁可喜,俱从山谷游。山谷所书“钓鱼舡上谢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鸡林每入贡,辄市模本数百以归,亦秀老词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载《潘子真诗话》)
俞紫芝这首《诉衷情令》词全文如下:“钓鱼船上谢三郎。双鬓已苍苍。蓑衣未必清贵,不肯换金章。汀草畔,浦花旁。静鸣榔。自来好个,渔父家风,一片潇湘。”全词只有四十四个字,却因表现了隐逸情怀,更因为石刻文字是黄庭坚的书法,所以拓本深得高丽人的喜爱,每次朝贡时都会购买数百本以归。销量不可谓不大,传播范围不可谓不广。
为了满足更为广大的消费群体,文学作品被带到境外后,有时还会在当地的出版机构再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苕溪渔隐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此《栾城集》中诗也。《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于壁间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此二句与子由之诗全相类,疑好事者改之也。”
苏轼的集子被带到辽国后,范阳书肆的出版商从中选择了几十首诗并命名为《大苏小集》[7]进行再版,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记载了宋徽宗被掳北行后的遭遇: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虏必有赐赉。一赐必要一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
金国统治者将徽宗写的谢表汇编成集,在边境贸易市场出版刊行。这部集子和传记文学作品《李师师小传》并行于世,在市场上热卖了四五十年,士大夫几乎人手一册。
(二)走私
由于宋朝与辽、西夏、金国长期处于一种对峙状态,而时事地理类著作又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两宋时期并不是什么书都可以卖给外国人。欧阳修曾上《论雕印文字札子》说: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禁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他认为书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随意出版发行书籍的行为会给国家造成危害,要求今后出版图书时要进行严格地审查,如若违反,不仅个人财产要充公,而且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朝廷此后下达一系列诏书,对书籍贸易进行规范整治,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记载景德三年(1006)九月,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如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处罪,其书没官。《宋史》卷十五记载元丰元年(1076),诏除九经外余书不得出界。国家在图书对外发行时也确实提高了门坎,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二记载,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高丽国进奉,使人乞买《大藏经》一藏,《华严经》一部,从之。又乞买刑法文书,不许”。元祐八年(1093),高丽使臣又要求购买《策府元龟》、《太学敕式》、历代史书等国子监所刊书籍,并要求抄写北宋近年新制的词曲曲谱,馆伴使中书舍人陈轩等已经同意,作为主管文化外交的礼部尚书苏轼,连上《论高丽买书利害》三个札子,表示坚决的反对意见。他在札子中严厉地批评说:“今高丽使,契丹之党,而我之陪臣也,乃敢于朝廷求买违禁物。”认为词曲曲谱是郑卫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德”。曾经出使高丽的丰稷也认为高丽想购买的图书中,“如《册府元龟》、历代史敕式之属,不可以与外夷”[8],认为这些书事关国家机密,不能随便出卖。
然而,同样的图书,如果拿到境外出售,价格会昂贵得多。据苏辙《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记载,苏辙出使辽国时,发现他们父子三人的书在那里非常流行,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有利可图,自然会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即使朝廷明令禁止,他们也会偷偷运到境外贩卖。因此,客旅商贩越境走私,成为书禁背景下图书流传到异域的重要途径。
辽、金虽然与宋朝长期对峙,双方之间的图书贸易禁令也非常严格,但利益所驱,仍然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传播至此。元祐四年(1089),苏辙出使辽国时,发现“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归朝后,特奏上《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札子》,谈到辽国所传民间版行文字中,上自臣僚章疏,士子策论,下至“戏亵之语”,“无所不至”。北宋词曲,很多在契丹传播。宋室南渡后,“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南宋人诗文,则罕有传至中原者,疆域所限,固不能即时流通”[9]。然而“雅声远祧,宜非疆域所能限”[10],还是会有众多的文学作品被私贩出来。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云:
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金国三天就买到了胡铨有名的《上书乞斩秦桧书》,在当时的情势下,只可能是通过私贩。
高丽对宋代文化的消费量也非常大,而宋王朝又非常担心传播到高丽的图书流落到辽、金等国家,对书籍外销高丽也是有种种限制,因此走私成为主要渠道。据《高丽史》记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江南人李文通等献书册凡597 卷,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宋商献《太平御览》,高丽明宗赐白金六十斤。其余不见诸记载者必不在少数。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亦云:“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访闻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官私无一人知觉者。”徐戬雕造经板二千九百余斤,载往高丽,接受酬银三千两,而宋朝无人知晓,可见当时走私之猖獗。
(三)求赐
除了花钱购买以外,外国使臣还直接向宋朝当政者求取他们看中的文学作品。比如宋初著名隐逸诗人魏野,诗风清淡朴实,浅显易懂,深得辽人喜爱。但诺大个辽国却只有半部魏野诗集,于是契丹皇帝派使者到都城汴京,向真宗皇帝求取魏野诗的全集: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魏野字仲先,其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尔。如《赠寇莱公》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及《谢寇莱公见访》云:“惊回一觉游仙梦,村巷传呼宰相来。”中的易晓,故虏俗爱之。(文莹《玉壶诗话》)
其实,据《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传上·魏野传》记载,真宗早就听说过魏野,并曾请他出山做官,只不过魏野以“麋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为由,拒绝了真宗的好意。
辽人喜欢在野人士的作品,高丽人则青睐当权派的诗:
熙宁中,高丽使人至京师求王平甫诗,有旨令京尹元厚之抄录以赐。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之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蔡宽夫《诗史》)
王平甫即王安国,他的诗虽然“博而深”(曾巩《王平甫文集序》),但实在难说是北宋一流的大诗人。高丽人偏偏来求取他的诗,与他是当朝宰相王安石的胞弟当不无关系。熙宁年间(1068-1077),正是王安石当政的红火时期,高丽派人来求取他弟弟的诗,不失为在政治上示好的一种策略,虽然王安国并不满意胞兄王安石的变法。
除了求取已有的文学作品,外国使臣有时也会要求现场创作:
祥符中,日本国忽梯航称贡,非常贡也,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现,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明,则此光现。真宗喜,敕本国建一佛寺以镇之,赐额曰“神光”。朝辞日,上亲临遣。夷使面乞令词臣撰一寺记。时当直者虽偶中魁选,词学不甚优赡,居常止以张士学君房代之,盖假其稽古才雅也。既传宣,今急撰寺记。时张尚为小官,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而夷人在阁门翘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后钱、杨二公玉堂暇日改《闲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号闲,司谏拂衣归华山。”盖种放得告还山养药之时也。钱希白曰:“世上何人号最忙,紫微失却张君房。”时传此事为雅笑。(文莹《湘山野录》卷上)
日本使臣求取《神光寺记》,未知最终撰成否?
在外国使臣求取书籍时,宋朝统治者并不会无条件地满足对方的要求,他们往往会有选择地给予,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记载,元祐元年(1086)二月,“馆伴高丽使言高丽乞《开宝正礼》、《文苑英华》、《太平御览》。诏许赐《文苑英华》”。《开宝正礼》应当是一部礼制类的书,《太平御览》这部综合性的类书门类繁多,征引赅博,内容包括天文、地理、人文、官僚体制、军事等大小部类,关涉国家大事甚至是国家安全,因此哲宗皇帝没有批准,而只是答应赐给《文苑英华》这部文学类书。另据《金史》卷九记载,明昌二年(1191)四月己亥,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一次就从宋朝引进了二十六部唐宋人的诗文集,可见就国家层面而言,文学类著作在对外传播方面要比其他类著作更为便利。
(四)其他
除了以上几种方式,使节出使、因战争而流落异域也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异域传播。
《汉书·艺文志》曾云:“古诸侯卿大夫交邻国之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也。”到了宋代,使节在外交场合不再是用《诗经》中的句子来见志了,而是通过吟诵当代名人的诗词名篇达到外交目的。如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李季章(璧)奉使北庭,虏馆伴发语云:‘东坡作文,爱用佛书中语。’李答曰:‘曾记赤壁词:“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字,乃《圆觉经》语,云:“火出木烬,灰飞烟灭。”’北使默无语。”李璧巧妙地借用苏轼名篇《念奴娇》中的句子,表达了自己对金国的蔑视之情。赵与虤《娱书堂诗话》还记载他在出使金国时,“伴使李著能诵荆公‘草头蛱蝶黄花晚,菱角蜻蜓翠蔓青’,以为妙。此乃荆公《斜径》绝句,后联形状景物,语意精工,金使亦可谓知诗者矣。”无论是真心喜欢这些作品,还是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外交场合引用的诗词名篇,一定会流传开去,从而扩大其影响。
战争年代,文人士大夫、宫娥嫔妃等有一定文学素养的人或被俘北上,或滞留异域,在悲情难堪之时,往往会借诗词类文学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靖康之难,中原地区陷为虏地,上自徽钦二帝,下至文武百官、宫娥嫔妃,“当时高人胜士陷没者不少”[11]。他们长期身陷虏地,成为传播文学作品的主力军。他们有时直接将诗词作品书写在交通要道上,比如庄绰《鸡肋编》卷中记载,有人从金国逃归,途经燕山的一座寺庙,就在寺庙的墙壁上发现了徽宗的一首绝句:“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诗歌表现了自己深沉的悔恨和悲哀绝望的心情,“天下闻而伤之”。又比如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记载,在绍兴年间,陈相之出使金国,途经燕山驿时,在驿壁上发现了一首词:“书剑忆游梁,当时事,底处不堪伤。念兰楫嫩漪,向吴南浦,杏花微雨,窥宋东墙。禁城外,燕随青步障,丝惹紫游韁。曲水古今,禁烟前后,绿杨楼阁,芳草池塘。
回首断人肠,流年去如电,双鬓如霜。欲遣当年遗恨,频近清觞。听出塞琵琶,风沙淅沥,寄书鸿雁,烟月微茫。不似海门潮信,犹到浔阳。”这首词没有署名,“必中原士大夫沦异域者所作也”。
在战争中,女性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据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下记载,河南阳武县令蒋兴祖在靖康之难中为国捐躯,他的女儿被掳北行。到了河北雄州驿,其女题《减字木兰花》于驿壁。在词中,她描绘了北国的荒寒以及失去家国的悲愁绝望的心情。旧题辛弃疾《窃愤续录》也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是晚,宿于寿州之官舍左庑下。夜及半,闻室中有歌声,帝谓阿计替曰:“此间亦有人会唱柳耆卿词,虽腔词不成,亦何由至此?”洎明日,同阿计替询问为谁,其人姓斛律,名思,乃询问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主皇帝所赐婢妾。”问之,乃东京百王宫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罢,亦语吾曰:“前面宿的官人,好似我叔家。”我答云:“便是南国官家。”其女悲泣。帝闻之亦为泣,左右促行,乃出城。
二、传播效果
文学作品的异域传播,能够使被传作品走出国门,使作品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有利于作品的异地保存,多了一份传存后世的机会,少了一些亡佚的危险;还能够提升被传国家的诗词创作水平。
(一)扩大作品影响
文学作品被传播到异域后,并不只是静态地存在,而是会在当地得到二度传播,进而在空间上扩大了原作的传播范围和影响。苏轼的文学作品被传到辽国后,不仅被题壁传播,而且书店还再版售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弟弟苏辙出使该国时,“每被行人问大苏”[12]。罗大经《新刊鹤林玉露》丙编卷一记载柳永的词被传到辽国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赠之,云:“东南形胜(略)。”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
柳永这首著名的《望海潮》被传播到金国后,被金主完颜亮听闻,“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将一场战争的爆发归因于一首词,未免夸张,但这则故事说明了柳永这首词在二度传播中所产生的极大影响力。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记载,北宋著名诗人聂冠卿,奉旨出使辽国,契丹主对他说:“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为十分欣赏这部集子,所以对他礼遇极厚。聂冠卿回国后不久,就因此而被召为翰林学士。
作品在异域传播的过程中,遇见知音,还会得到深度传播,翻译和注释是其中两种重要的方式。辽圣宗耶律隆绪喜吟诵汉诗,经常出题目让文武百官赋诗,自己当裁判,辨别优劣,优胜者赏赐金带。他还亲自担任翻译,将白居易的《讽谏集》翻译成契丹文,命令臣僚阅读学习。[13]辽人萧韩家奴也精通契丹文和汉文,曾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等译为契丹文。在推崇汉文化的风气下,一定会有不少宋人的文学作品在当时被翻译成契丹文传播。除了翻译,也有人为了更好地让读者理解作品,会选择注释作品,如金人孙镇就曾注释苏轼的《东坡乐府》。翻译和注释,使作品变得更容易理解,自然扩大了消费群,提升了作品的影响力。
(二)提升被传地的文学创作水平
无论是北迁辽国、金国、高丽,还是东传日本,宋代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给输入国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正能量,推动了域外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建立辽国的契丹族与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均是剽悍尚武的民族,然而他们又均真心地崇拜南方文化,喜爱宋朝的文学。“北虏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14],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上自皇帝,下至百姓,很多人不仅阅读接受宋朝的文学作品,而且主动学习创作,为域外汉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太宗、真宗时的辽圣宗耶律隆绪、仁宗时的辽兴宗耶律宗真、神宗时的辽道宗耶律洪基等辽国皇帝,都兴学习儒,喜爱汉文化,喜爱南朝的诗词作品,并且学习创作。如辽圣宗很喜欢白居易的诗,曾云“乐天诗集是吾师”,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其中不乏意境深远、气势磅礴的佳作。再如南侵宋室的金主完颜亮,汉文化功底甚为深厚,诗、词、文、赋,样样皆能,既有“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立马吴山第一峰》)、“怒磔戟髯争春,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喜迁莺》)这样不逊辛弃疾的笔力雄浑、气象恢弘之作,也有“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孙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昭君怨·雪》)这样的多情婉约之作。
不仅仅是皇帝,文臣武将甚至是普通百姓也不乏创作汉文学的好手。《诗话总龟》卷四十五“伤悼门上”引《谈苑》曾记载一名武将的兄弟侄儿均战死沙场,后来途经战场时,悲愤难抑,不禁作诗道:“父子尽从蛇阵没,弟兄空望雁门非。”诗歌写得质朴多情,真切感人。
因为受制于辽国,高丽从宋太宗时起就几乎断绝了与宋朝的高层接触,但他们仰慕中华文化的心却一直没有变过。神宗元丰初年,高丽国主王徽更是神往中华文化,每天念诵《华严经》,希望来生能出生在中国。有一天忽然做梦到北宋都城汴京,“备见城邑宫阙之盛,觉而慕之,乃为诗以记曰:‘恶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移身忽到京华地,可惜中宵漏滴残。’”[15]所作诗朴拙可喜,表达了对中国的无限向往之情。高丽每次向宋朝派遣的使者也大多深谙汉文化,并且能够创作汉文学,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记载道: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环评参与主体“公众”内容不统一、混同,也没有对参与的“公众”的范围、代表性作出要求。以“任何单位和个人”或“公众参与”确定公众的外延,形式上为正面定义,但结合具体语境则实为排除法定义。[注]朱谦:《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的思考与建议》,《环境保护》2015年第10期,第27—31页。对于“单位”“专家”有的将其列为公众,有的将其与“公众”并列相提,排除在公众之外。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5条所说的公众是有关机关、专家和公众(这里的公众是不包括专家的公民)。
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以来,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自天圣后,数十年不通中国。熙宁四年,始复遣使修贡。因泉州黄慎者为向道,将由四明登岸。比至,为海风飘至通州海门县新港。先以状致通州谢太守云:“望斗极以乘槎,初离下国;指桃源而迷路,误到仙乡。”词甚切当。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悌),与同行朴寅亮诗尤精。如《泗州龟山寺》诗云:“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棋白日闲”等句,中土人士亦称之。
《高丽史·朴寅亮传》亦云:“文宗三十四年,与户部尚书柳洪奉使如宋,有金觐者亦在是行。宋人见寅亮及觐所著尺牍、表状、题咏,称叹不置,至刊二人诗文,号《小华集》。”所作诗文居然得到了宋人的称赏,可见其造诣之高。
更为重要的是,异邦人士还能够在吸收宋代文学养料的基础上,创作出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来。如曾敏行《醒醒杂志》卷五就记载,徽宗宣和年间,都城汴京流行蕃曲《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并云“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这些蕃曲应该是在宋词的影响下创作而成的俚俗之曲。
三、有利于作品的异地保存
文学作品传播异域后,或者是口耳相传流传后世,或者是载之书册传播久远,客观上都有利于作品的保存。很多文学作品在其诞生地中国已经难觅踪迹,可在异国他乡却还被很好地保存着。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即云:“宣和间有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盖不经兵火。今中秘所藏,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以高丽对宋代文学的痴迷程度可以推想,这“几千家几千集”中当有不少北宋文人的集子。
郑麟趾等撰《高丽史·乐志》著录自北宋传入的歌舞曲七套,曲词三十首,另外还有小令慢曲四十四首,共七十四首,列于“唐乐”。这些作品“其调多词律所未收,语则颂美居半,间有似屯田体者”[16]。这七十四首宋词中,有五十九首在中国失传已久,幸赖《高丽史·乐志》著录而得以保存。
注释:
[1]谭新红:《宋代的驿递制度与宋词传播》,《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6 期。
[2]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宋史研究集》第十一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9年,第223页。
[3]范镇:《东斋记事》佚文引《类苑》卷七八,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5]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6]李孟晋:《宋代书禁与椠本之外流》,《宋史研究集》第十三辑,第324页。
[7]按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辽东,宿幽州馆,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首,谓之《大苏小集》。”知范阳出版之苏轼诗集名应为《大苏小集》。
[4][8]李 朴:《丰清敏公遗事》,《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八册,第146页。
[9]赵 翼:《瓯北诗话》卷十二,《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46页。
[10]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455页。
[11]赵 溍:《养疴漫笔》,《古今说海》本。
[12]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3804页。
[13]《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吴文治主编:《辽金元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14]阮 阅:《诗话总龟》卷四十五伤悼门上引《谈苑》,《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14页。
[15]《石林诗话》卷中,《宋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703页。
[16]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七,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