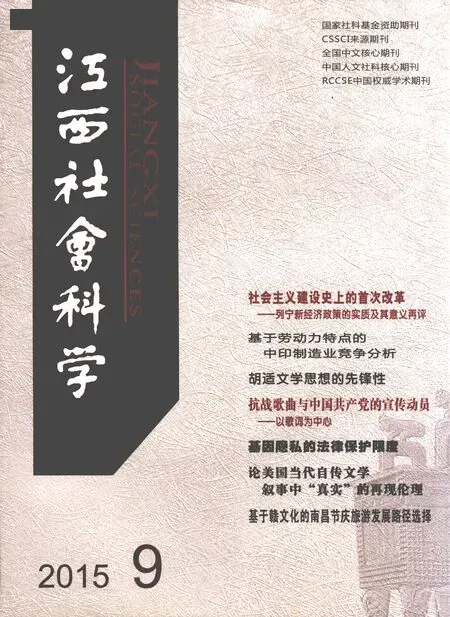“临川四梦”人物塑造的空间表征法
■王 琦
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诗赋、文论、尺牍,尤为可贵的是留下了代表中国戏曲创作高峰的 “临川四梦”。 作为 “明传奇之冠”(王季烈语),“临川四梦”以其强烈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折服观众,成为历久不衰的戏曲艺术经典。众所周知,人物、情节和环境一直被视为构成小说、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作品的三要素,且人物在其中往往居于首要位置。“临川四梦”的闪光之处就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典型人物,如:为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女子杜丽娘,为爱才不惜散尽家财、典当玉钗的痴情女子霍小玉,路见不平仗义挺身的豪侠黄衫客,等等。正如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所言:“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1]这些生动鲜活的典型人物,无疑使中国戏曲文学人物画廊五彩缤纷。从叙事学的视角,细探这些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为我们深入解读“临川四梦”戏曲文本开辟了一扇“窗”。
一般来说,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展示行动,让读者在人物的言谈举止中把握其典型的性格特征;二是描写人物外貌,从而使读者对人物形象先产生一个静态的‘图像’;三是专名的暗示与粘结。‘专名在人物生成中的作用不光是暗示,更重要的作用是粘结各人格特征,把它们统一为一个有机体。’”[2](P227)除了上述三种人物塑造法外,龙迪勇在其著作 《空间叙事研究》中首次命名了一种新方法——空间表征法。所谓“空间表征法”指的是“让读者把某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与一种特定的‘空间意象’结合起来,从而对之产生一种具象的、实体般的、风雨不蚀的记忆”[3](P261-262)。龙迪勇详细论述了“空间表征法”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它不仅可以出色地表征出一个群体的 ‘共性’或 ‘集体性格’,而且可以很好地表征单个人物的‘个性’或‘独特性’,就像它既可以出色地表征 ‘扁平人物’,也可以很好地表征‘圆形人物’一样”。[3](P314)
通过细读“四梦”文本,我们发现,空间的确是人物性格生成的具体场所及人物形象的绝佳表征。汤翁在“临川四梦”中非常善于通过书写一个个特定空间来塑造人物典型。故此,本文欲着重探究“临川四梦”戏曲文本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空间表征法。
一、家宅:居住空间——人物原初性格的塑造空间
“家宅”对于人的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生于斯长于斯,它既是人类遮风避雨的庇护所,又是最让人放松和怀想的精神家园。“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确实是个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4](P2)不同的家宅环境可以表征着人物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现实处境,是人物原初性格的塑造空间。
《邯郸记》第二出《行田》中,主人公卢生正式登场。他的几句宾白,便将其困顿窘迫的家宅环境描述殆尽:“白屋三间,红尘一榻,放顿愁肠不下。展秋窗腐草无萤火,盼古道垂杨有暮鸦,西风吹鬓华。”①显而易见,主人公卢生居住在“空田噪晚鸦,牛背上夕阳西下”的乡村小店“三家店儿”;全部家当只有 “白屋三间”、“数亩荒田”;衣着方面,“到九秋天气,穿扮得衣无衣,褐无褐,不凑膝短裘蔽貂”;出门无高车驷马,而是“乘坐着马非马,驴非驴,略搭脚青驹似狗”的跛足“蹇驴”。看到这些描写家宅的“空间意象”,一个时运不济、落魄无依的乡间穷儒形象瞬时跃然纸面。如此贫愁潦倒的出身无疑为其跳入吕洞宾的磁州玉枕中历经自以为 “得意”的人生——做足了叙事铺垫。
相较于卢生孤寒窘迫的居住环境,女主人公崔氏的“家宅”显然是富贵奢华的侯门深院。卢生跳入枕中惊讶地发现:“(生转行介)怎生有这一条齐整的官道?”(行介)“好座红粉高墙。”随后,叙述者借助卢生的视角,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细细打量这座粉墙高院,接着,“镜头”继续拉近,开始对宅院之中的闺阁进行“特写”:从嗅觉到视觉,从远景到近景,把“世代荣华,不是寻常百姓家”的清河崔氏的富贵府邸描写得生动传神。显然,崔氏出身豪门贵族,日后形成强势霸道、财大气粗的性格顺理成章。毫无悬念地,随后的情节由 “思想起我家七辈无白衣女婿,要打发他应举”到“奴家四门亲戚,多在要津,你去长安,都须拜在门下”,再到“奴家再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取状元如反掌耳。”门庭显赫的崔氏可谓一手设计并促成了卢生出将入相的仕途荣辱之路。其间,叙述者对崔氏“家宅”浓墨重笔的描写,鲜明地烘托出崔氏性格中的强势大气,极大地推动、铺陈了后续情节的发展。
《紫钗记》中女主人公霍小玉的居住地“霍王府”,亦是足以表征人物性格的居住空间。在第四出《谒鲍述娇》中,媒人鲍四娘将霍小玉的居住地霍王府的地理位置告知李益——“住在胜业坊三曲莆东闲宅是也。”因霍小玉的母亲郑六娘原是王府歌姬,嫁于霍王为妾。霍王死后,诸兄弟嫌六娘出身低微,遂分了一份财产,将其母女二人驱逐出王府、迁居于胜业坊。这里的“胜业坊”为唐代街坊的名称,实乃倡优聚居之地,由此暗示了霍小玉母女的社会地位:虽名为霍王之女,实则社会地位低微。居住于胜业坊的霍小玉,自小目睹了母亲因身份低微被逐出王府的情景,于是对爱情婚姻的态度始终带着母亲留下的先天伤痕,既充满向往又心存隐忧。这种心有余悸、复杂敏感的人物心理,在其日后对进京赶考、多年不归的李益的分外担忧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这里,家宅不仅仅是人物遮风避雨的居住地,更具备了提示人物身世、预示人物命运、塑造人物性格的叙事功能。
可见,家宅可以为人物的原初性格赋予一个合情合理的缘由。人物与其所生活的空间环境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统一性,已然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了。作为物质生活环境的“家宅”,对塑造人物性格具有原生态的空间表征意义。联想到人物的居住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绣像便呼之欲出,令人印象深刻。
二、花园:休闲空间——人物自然天性的释放空间
在中国古代,“花园”是一种艺术,也是休闲娱乐的场所。它是游离于规范秩序之外的“私人空间”或“休闲空间”。相对于高度仪式化的宗庙、陵寝、祠堂及已被充分秩序化的家宅而言,“花园”是一种“法自然”的“原生态空间”。[3](P304-307)那些已被宗法社会规范化的家宅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千篇一律,将人的自然天性压抑、束缚得动弹不得。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日复一日重复着合乎“规范”的日常活动,近乎丧失了灵魂深处的自然旨趣。而作为不可多得的休闲空间的花园,则可称得上是释放人们纯真天性的天堂。
《牡丹亭》中的“花园”无疑是全戏中最为核心的空间意象。出生于宦族名门、“才貌端妍”,素来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循规蹈矩的太守千金杜丽娘,平日里足不出户,只在闺阁里做些刺绣、读书、临帖之事,到日后她如何会性情大转,因梦成痴,因痴成病,最终“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5]?这期间的巨大转变,起因皆在于这个典型化的空间意象——“花园”。
“花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牡丹亭》的第七出《闺塾》。丫头春香借口“溺尿”逃学出去,忽然发现“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素来沉稳的杜丽娘闻后故作不发,待先生下课后少女情态立现。可叹已是“二八年华”的少女丽娘,日日闲守空闺,足不出户,竟浑然不知自家后院有如此景致的花园。既已知晓,仍能故作矜持,隐忍不发,尽显名门闺秀的家教涵养。随后第八出《劝农》、第九出《肃苑》皆为第十出《惊梦》中的丽娘游园创造条件,做足铺垫。
在第十出《惊梦》中,随着丽娘的盛装游园,这个充满神秘感的后花园的空间布局开始逐渐呈现出来。春香眼中的花园原是反映了“花园”本来面貌的:“(行介)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青。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疼煞小金铃。”而丽娘眼中的花园却是“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并存的空间:“(旦)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看到园子里百花开遍,丽娘不禁心生一丝埋怨:“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尽管花园中的景致委实不错——“(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然而,对长期禁锢深闺的丽娘来说,却仍是:“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可见,面对同一空间,不同的人物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心理感受。这里的空间叙事,鲜明地反映出了丽娘和春香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
尽管此前也有对这座后花园的空间描写,但大多停留在对花园景致的笼统概述上。直至丽娘伏案入睡,叙述者才将其梦中云雨事的发生场景详加描述。随着叙述的层层递进,后花园的空间画面也渐次明晰了起来。众所周知,杜丽娘和柳梦梅梦中的交合地点是全剧空间叙事之肯綮。叙述者运用多重叙述的手法对这一核心空间进行了反复渲染和刻画,令观众难以忘怀。第一次是在叙述者对丽娘梦境的叙述中。第二次则是在丽娘对梦中情事的回叙中。第三次是在第十二出《寻梦》中。丽娘欲在真实花园中重寻梦中情事的发生场域,却只看到:“牡丹亭,芍药阑,怎生这般凄凉冷落,杳无人迹?好不伤心也!(泪介)”然而,现实的花园中却多了一个空间标识物——梅树:“(望介)呀,无人之处,忽然大梅树一株,梅子磊磊可爱。”丽娘顿生死后葬于此地之念。第四次是在第十四出《写真》中。丽娘自绘,只见画中的自己“谢半点江山,三分门户,一种人才,小小行乐,捻青梅闲厮调。倚湖山梦晓,对垂杨风袅。忒苗条,斜添他几叶翠芭蕉”。这幅女子行乐图再现了 “青梅”、“湖山”、“垂杨”等空间意象,大多暗合了其梦中之景,前后呼应。第五次是在第二十七出《魂游》中。丽娘的鬼魂继“冥判”后魂游旧地所见的空间场景:“呀,转过牡丹亭、芍药阑,都荒废尽。”离魂三年,尚能记得梦境和后花园中几个富有典型象征意义的空间意象,可见这些标志性的空间意象何其令丽娘魂牵梦萦。
总之,通过上述五次对花园中的“牡丹亭、芍药阑”这一典型空间的反复书写,充分体现出花园这个休闲空间对激发妙龄少女丽娘心底最真实纯粹的人性本能所发挥的重大功能。杜丽娘这位被封建礼教禁锢身心的贤良淑女,在“花园”这个休闲空间的偶然“电击”下,潜藏于其理性外壳中的本真情感被彻底激活了,从而转变为一位为爱情可生可死、生死不放的至情女子。显然,在这个彻头彻尾的巨大逆转中,“花园”这一休闲空间的叙事发挥了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花园”这个封建礼教鞭长莫及的休闲空间和私人空间,是释放人物自然天性的绝佳场域。它既可以是各种浪漫故事的发源地,亦可以是各种幸福回忆的安放地。概而言之,《牡丹亭》中后花园的空间叙事至少发挥了如下三重功能:一是让杜丽娘被封建礼教禁锢、压抑的原初本真的人性有了释放的空间;二是使原本朦胧混沌的梦境叙事有了清晰的空间标识,让原本不可靠的梦境叙事变得真实可信;三是多重空间叙事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富饱满,立体生动。
三、树国:虚幻空间——人物性格的拓展空间
想象是赋予艺术作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往往可以为艺术作品的传播插上流芳千古的翅膀。相对于“家宅”“花园”等源自真实世界中的虚构空间,想象世界中的“虚幻空间”的叙事则显得更为奇幻神秘。在《南柯记》中,汤翁用他的灵性笔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神奇的乌托邦——大槐安国。
“槐树小穴中,何因得由国都乎?”——《南柯记》中的主人公淳于棼与我们同样有此一问。对此,槐安国的紫衣使者给出的答案是:“淳于公,不记汉朝有个窦广国,他国土广大;又有个孔安国,他国土安顿,也只在孔儿里。怎槐穴中没有国土?”寥寥数语便令受述者信服:大槐安国乃“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虚幻空间。
随后,叙述者让大槐安国主蚁王详细介绍了本国的历史由来。由此可见,大槐安国聚众成国、稳如磐石的原因源于天时、地利、人和。
接着,蚁王又将槐安国内的空间布局向受述者娓娓道来:“……火不能焚,寇不能伐。三槐如在,可成丰沛之邦;一木能支,将作酒泉之殿。列兰锜,造城郭,大壮重门;穿户牖,起楼台,同人栋宇。清阴锁院,分雨露于各科;翠盖黄扉,洒风云于数道。长安夹其鸾路,果然集集朱轮;吴都树以葱青,委是耽耽玄荫。”国都具体格局如下:“北阙表三公之位,义取怀来;南柯分九月之官,理宜修备。右边宪狱司,比棘林而听讼;左侧司马府,依大树以谈兵。丞相阁列在寝门,上卿早朝而坐;大学馆布成街市,诸生朔望而游。真乃天上灵星,国家乔木……”。由此可知,大槐安国都城虽小,却有着一套完善的行政司法体制,官员各司其职,欣欣向荣,国泰民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对这一神秘空间的叙述,受述者仿佛可以亲见这位霸气威严、有胆有谋、文可治国、武可安邦的国主蚁王正威风凛凛、饱含深情地俯瞰城池众生的画面。
此外,对大槐安国都城的空间描写,不仅体现了国主蚁王的形象,更将男主人公淳于棼的复杂心理充分表现了出来。淳于棼被选为蚁国驸马后,两位紫衣使者驾牛车前来接他入国。初见蚁国风貌,淳于棼用陌生化的叙述语言描述了他眼中的大槐安国的风土人情,充分表现了初来乍到的淳于棼见到蚁国臣民对自己莫名的恭顺敬畏时,他的新奇、忐忑、疑虑等复杂心理。
随后,当牛车抵达城门时,淳于棼眼里的大槐安国一派繁华富贵的景象:
(生)好一座大城,城上重楼朱户,中间金牌四个字:(念介)大槐安国。(内扮一旗卒上)传令旨,传令旨,王以贵客远临,令且就东华馆暂停车驾。(卒叩头走起,同向前道行介)(生)城楼门东有这座下马牌,怎左边厢朱门洞开?(紫)到东华馆了,请下车。(生下车入门,背笑介)这东华馆内,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帏肴膳,陈设于庭上。俺心里好不欢悦也……②
显然,“重楼朱户”、“金匾题字”、“左侧朱门洞开”、“彩槛雕楹”、“华木珍果”,这些奢华和礼遇,既凸显了蚁国国主对淳于棼的重视与厚爱,也为人物日后的失落埋下了伏笔。
淳于棼在梦中出守南柯大郡,富贵二十余年,公主薨逝,拜相还朝,专权乱政,被国王见疑,着紫衣使者遣送回家。还是原来的那条来路,还是原先接驾的二位使者,然而,此情此景,人物的心境和眼前的风物却与来时迥然不同。
[绣带儿]才提醒趁着这绿暗红稀出凤城,出了朝门,心中猛然自惊。我左右之人都在那里?前面一辆秃牛单车,岂是我坐的?咳,怎亲随一个都无?又怎生有这陋劣车乘?难明。想起来,我去后可能再到这朝门之下,向宫廷回首无限情,公主妻呵,忍不住宫袍泪迸。看来我今日乘坐的车儿,便只是这等了,待我再迟回几步。呀,便是这座金字城楼了。怎军民人等见我都不站起?咳,还乡定出了这一座大城,宛是我,昔年东来之径……
紫衣使者随意行走,做不畏生,打歌唱道:“一个呆子呆又呆,大窟弄里去不去,小窟弄里来不来。你道呆不子也呆?”随后鞭牛道:“畜生不走。”语带双关,极尽轻蔑。
作者前后两次对同一条道路和都城风土人情作了截然不同的空间叙事,以充分表现淳于棼从权臣贬为庶民、从云端跌入谷底的极端失落沮丧的心情,以及与人间无异的蚁国臣民的世态炎凉,为淳于棼最终之“悟”作足铺垫。所有的一切皆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完全符合虚构叙事的“艺术的真实”。
由此可见,“虚幻空间”为人物性格发展拓宽了空间,为人物个性的张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通过对一个个富有梦幻色彩的“虚幻空间”的空间书写, 叙述者可以巧妙塑造出一个个“圆形人物”[6](P67)。这些立体饱满的圆形人物,连同一个个神奇玄幻的叙事空间一起,成为令受述者难忘的人物形象。
总之,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之一,空间表征法自有其独特出色之处。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正是充分运用了空间表征法塑造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为中国戏曲文学典型人物长廊增添了数面传神的“脸谱”。
注释:
①文中所引《邯郸记》中所有戏曲文本均出自汤显祖《临川四梦·邯郸记》,邹自振评注,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②文中所引《南柯记》中所有戏曲文本均出自汤显祖《临川四梦·南柯记》,黄建荣评注,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
[1](明)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A].《牡丹亭》王思任批评本[M].李萍,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3]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4.
[4](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明)汤显祖.《牡丹亭》作者题词[A].汤显祖.牡丹亭[M].吴凤雏,评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
[6](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